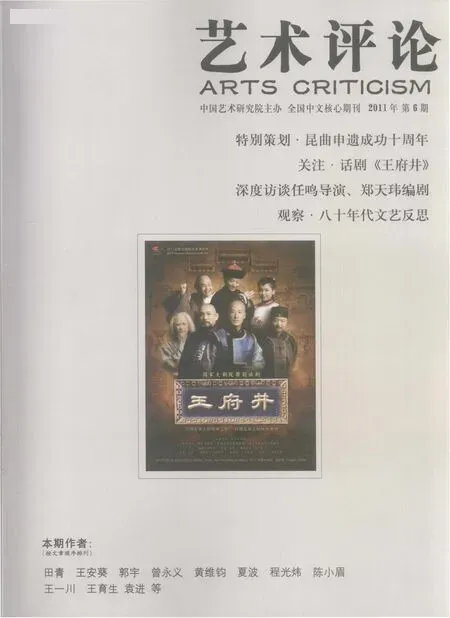寻找传统:新时期前期戏剧中的形式与内容
陈小眉 刘佳 译 冯雪峰 校
本文聚焦于新时期前期的一组话剧,这些话剧都因为其形式主义的特征而为人所知。评论家们声称这些戏剧正是因为其具有革新意义的形式特征而获得了人们的认可。但是,我们在许多例子中都可以清晰看到,这些所谓的美学面相之所以能存活下来,或者变得富有文化意味,恰恰是因为它们同时又总是事关个体与政治的。这表明,当代中国戏剧中的美学思考只有与那些在当时非常个人化的政治思索相结合时才能被更多的观众所接受。戏剧化的风格和技术作为历史和政治语境中不可剥离的一部分,从来就没有被仅仅当成是形式主义的范畴。它们总是深嵌入语境之中,并被内容所预先决定。这一系列的戏剧特征在本文中将被看成是一个交汇点,在此形式与内容以及诸如私人和公共、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等二元对立的辩证法纷纷上演。
一、从写实剧到实验剧

在现代中国,写实剧占据了主导地位,建国后,因为这一形式与社会主义文艺“再现现实”的理论相一致,其地位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同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也进一步推动了写实剧在中国舞台上的确立和巩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强调一种完全现实主义的表演,这种表演需要演员对身体和声音进行特定的训练,按照自己的印象和记忆对具体情景进行再造,同时还要完全沉浸入情景中并与剧中人物形成认同。中国戏剧界采纳了这一表演理论,并将其转化入本土的戏剧实践之中,用来再现社会主义中国。著名戏剧理论家和批评家刘厚生指出,新中国在1949-1966年的17年间,大约99%的戏剧作品明显地受到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影响。剩下的1%是布莱希特式的戏剧,总共只有三部,分别是:《八面红旗迎风飘》(1957)、《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1959)和《激流勇进》(1963)。
对于中国戏剧界而言,现代主义戏剧显然是一个新事物。那些具有现代主义实验色彩的戏剧能够受到观众的欢迎,正是因为其在剧情结构方面的大胆探索。而中国的戏剧家和评论家对现代主义戏剧的大力支持,反映出的则是他们意欲跻身世界戏剧舞台的愿望。有鉴于之前几十年过于政治化的文艺状况,戏剧家和评论家们往往认为在艺术的美学和形式探索方面,西方戏剧已经远远地领先于中国了,这使得他们对艺术价值的渴求异常强烈。因此,对于中国戏剧家们而言,创作出能吸引观众的现代主义戏剧,进而重新走向世界则自然成为了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早期实验戏剧因为受制于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状况,只能从引进西方已有的戏剧运动开始自身的戏剧实践,而在这个过程中暴露出的则是跨文化转换中的可能性和局限性。
比如一般被认为属于荒诞主义话剧的《车站》和《WM》,在它们借鉴西方荒诞戏剧因素的外表之后,更为根本的则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对文革作出的某种反应。通过将《车站》中那辆永远不会到来的公共汽车与《等待戈多》中相关情节的比较,白杰明(Geremie Barme)正确地指出:虽然这些人们只能在那里继续等待,但是他们却显然有一个值得期待的方向,等待者的处境远远不是存在或荒谬的两难困境。等待在此更像是一个策略,这些人只是在思考什么时候以及以怎样的方式向前迈进。在这里不存在真正的疑惑,人们坚信他们可以而且应该向城市前进,戏剧并没有把观众引向那些存在于人类思想中、并且已经部分实现了的担忧和焦虑。
与《车站》等十分相似的是话剧《屋外有热流》,这部备受称赞的话剧被认为是当代中国的第一部“荒诞戏剧”,然而却与它的西方同类鲜有共同之处[1]。这部戏剧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新时期,当时毛泽东时代理想主义的价值观正逐渐地受到物质主义的挑战,而整部戏剧就与一对孤儿兄妹的阴谋相关。这对兄妹极力阻止与从远方归来的大哥分享他们自己的屋子。在戏剧的结尾,广播播报了大哥牺牲的新闻,他为了保护村子的一袋麦种,一夜守在屋外,最后被冻死。这时,兄妹两人突然为自己的自私感到了无比羞愧,开始寻找大哥——两人相信他们的大哥无处不在,甚至就在舞台下的观众中间呼喊着他们。整部戏剧表现出的道德口吻使它更像是此前的现实主义戏剧。事实上,在整部戏剧中我们看不到丝毫那些原本属于荒诞派戏剧的本质特征:人类存在的荒谬境遇中的形而上痛苦,对文明无效性的愤怒以及对空洞而无意义的人类活动的描述。而戏剧批评家们却将这部话剧定位为现代主义的,认为这部戏剧是与西方式荒诞戏剧不同的中国版本。西方式荒诞剧的特征在于犬儒主义以及“消极等待中的绝望感”。与之相对,《屋外有热流》在手法上带有荒诞剧的形式特征,但整体上传递出的是“期待中的担忧”这一“积极”的意义[2]。这一阐释正好体现了戏剧家和批评家认为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辩证关系,虽然他们急迫地希望中国本土话剧能应用西方的戏剧技术,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有必要树立一个“被动的”、消极的西方他者,从而为建构“积极”、乐观的中国自我创造可能。
二、实验川剧:女性主义与传统形式
而像魏明伦这样的中国当代剧作家们则致力于改革中国的戏曲,他们的灵感往往来自于自己所理解的荒诞主义传统。1986年,魏明伦大胆的实验剧——荒诞川剧《潘金莲》震惊了中国戏剧界。魏明伦坚持认为这部戏的荒谬性主要体现在它所采用的荒诞剧形式。剧作家将不同国家和时代的角色放置在同一个舞台,让他们共同来评价潘金莲这位中国文学中最为声名狼藉的女性人物的悲剧故事。而魏明伦的最终目的却必须放回到本土现实主义戏剧传统中来看待,即通过发掘人类与社会,历史话语与当代社会之间的紧密关联,从而将女性从传统文化的重负中解放出来。他承认自己使用的诸如荒诞性这样的概念可能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然而在他看来西方剧作家并不享有对“荒诞”的唯一发明权[3]。也许别人认为,荒诞主义戏剧中的“荒诞”必然是意味着人类经验的荒谬性。但是,魏明伦却通过确认与西方式荒诞不同的中国定义,绕开了这个难题。
川剧《潘金莲》从《水浒传》、《金瓶梅》这些传统故事中提取了线索,并通过将其女主人公放置在与五个男人(张大户、武大郎、西门庆、武松、施耐庵)做斗争的位置上,从而批判了作品中的厌女(misogyny)情结。施耐庵在剧中明显的封建父权制和儒生作风备受争议,受到了东西方经典作品中或虚构或历史的角色的挑战。比如托尔斯泰笔下的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就出现在了舞台上,当潘金莲因为丈夫缺乏勇气无法保护自己而感到沮丧时,她为潘金莲绝望的婚姻而悲伤。甚至在一个关键时刻,安娜·卡列尼娜介入其中,劝告潘金莲采取自杀的举措,而不是谋害她的丈夫。当安娜与潘金莲讨论不幸的婚姻——不论是在中国还是俄国,在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契约对女性而言是否都将是永恒的问题时,吕莎莎——中国当代小说《花园街五号》中的一位人物也参与了她们的讨论。与生活于传统社会而无权选择婚姻的潘金莲不同,吕莎莎庆幸生活在当代中国,这样她才得以与自己的疯丈夫离了婚。而武则天则对这个父权制的不公社会表现出极大的愤慨。那些皇帝们一面享受着佳丽三千,一面炮制出一套话语,使得像武松这样的杀人凶手反而变成了英雄。武则天责令七品芝麻官唐成还潘金莲一个清白。然而他搜遍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法律文献,都无法找到一条律令可以豁免潘金莲别恋小叔武松的罪过。这段情节被认为是整部戏中最为发人深思的时刻之一,即使是“最为诚实和正直的官方历史”的大胆介入也无法改变封建社会女性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4]。戏剧揭发出整个父权制系统的恶行,这个系统一方面承认了自身的腐败(通过创造了唐成这一官员的神话),另一方面却依然没有停止对女性的歧视。
这出戏最初是由自贡川剧团在1985年10月8日搬上舞台的,并在成都、北京、上海和香港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同时受到它的启发,无数类似的戏剧纷纷上演,比如现代话剧以及陕西、上海等地的地方戏剧[5]。一度有二十个城市的五十个剧院在上演这出戏,超过一百家的杂志、报刊报道了这部戏剧,其中有十家开辟了专栏继续讨论这部话剧及其极富争议性的接受状况。
那么,是什么使得观众们张开臂膀热烈地欢迎这部戏剧呢?为什么原先对川剧完全不感兴趣的人们会突然间被《潘金莲》吸引呢?一个可能的答案是,《潘金莲》的成功指出了当代戏剧走出危机的一条道路:相对于用川剧之类的传统戏剧形式表现当代故事,更能吸引当代观众的是对传统剧目的现代重写[6]。在这个个案中,真正吸引观众的是作者对文学史上公案的大胆改写和颠倒。胡邦炜认为虽然《水浒传》是第一部有力地表现了农民英雄对抗腐朽朝廷政府的伟大小说,但是它对女性的负面描写也体现出了传统中国文学经典中随处可见的厌女观念。[7]与传统小说中对女性歧视并存的是阶级的歧视,一个农民起义的参与者,会像他的压迫者一样,维持第二性在整个系统中的低等位置。武松及其同伴也许会反抗腐败的官府,但是他们永远不会质疑确保了他们这些男性特权的父权制系统。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川剧《潘金莲》上演而形成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它的主题和“社会作用”展开的,而非形式创新。这部戏剧的形式主义创新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作者大胆地将戏剧与女性压迫、解放的现实议题联系了起来。文学批评家刘宾雁指出当时许多评论受困于它们“纯文学”的高尚追求,反而忽视了社会现实。而中国的观众、读者们则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们更喜欢这些被忽视了的戏剧形式以及与之缠绕的传统故事,而不是那些极少关注社会及意识形态议题的电视、电影、小说和其他现代主义戏剧。
三、史诗剧与写意剧
当代中国的史诗剧领域,在寻找自身舞台的时候同样发生了类似的争论。一些戏剧家被布莱希特有关社会介入剧的主张所吸引,他们发现,布莱希特通过史诗剧影响社会变化的信念,可以与此前的现实主义传统非常完美地契合起来。例如在刘树纲的剧作《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中就混合了布莱希特戏剧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戏剧两种传统(1985年6月6日,这部戏剧在中央实验话剧院首演,导演是田成仁与吴晓江)。这部戏是以安珂、曹振贤烈士的事迹为基础创作的。故事试图重构出当主人公叶肖肖在公车上被歹徒袭击,其他乘客袖手旁观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整部戏剧的重点是叶肖肖死后灵魂回来拜访那些依然活着的目击者,以及重新找回两位自己童年时最好的朋友:他的恋人唐恬恬和工作与感情上的对手柳风。戏剧遵循了毛泽东时代的戏剧传统,主要通过局外乘客的动作来展示现实生活的切面,同时突出社会问题。这些剧中的袖手旁观者受制于日常生活的琐事而没能在危机时刻挺身帮助叶肖肖。作为死后的重访者,叶肖肖完全能够理解这些人们,并且已经谅解了他们的行为。肖肖的选择使他获得了理想中社会主义英雄所具有的品质:只是给予而不求回报。
评论家们已经指出这部戏剧非常巧妙地融合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西方荒诞派以及象征主义的技巧,但是真正使得它成为一个有趣实验剧案例的,却是全剧体现出的“间离效果”。这一效果来源于戏剧对古希腊悲剧表演的模仿,即对面具和歌队的使用。为了引起社会关注,《一个死者》利用了布莱希特将零散情节与史诗剧式暗示结合的方法。通过将过去与现在,生者与死者,以及演员与原本被认为需要对戏剧表演作出理性选择的观察者/观众连接起来,从而持续地把观众与直接的戏剧事件分离开来。这些戏剧效果主要是通过对歌队创新性使用而获得的,歌队的成员在戏剧开始向观众致意,从而提醒观众他们一起在观看话剧。歌队除了对情节发表评论,以及穿着极富象征意味的戏服、道具而成为布景的一部分之外,还经常戴着面具,充当剧中的角色:公车上的乘客和罪犯、侦探、贪官、肖肖的雇主、墓地的看门人。这些戏剧技术的目的是促使观众对戏剧情节展开反思,同时推动肖肖对其人生的反思。
戏剧的结尾,当肖肖要被火化之时,柳风却向大家道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就是肖肖一直寻找的那位乘客——原本有着充足的正义感并坚持要将公车驶向公安局,将罪犯绳之以法,但最后却因为害怕报复而没有揭发他们的罪行。柳风进而还承认他写作了这部作品,以此来减轻自己的负罪感。而这自白促使观众更进一步地去思考剧场和剧作的意义。柳风通过将自己展示为对肖肖之死附有责任的冷漠看客中的一员,实际上是将自己置于这一无所分别的群体之上。他的戏剧技能使得他能够炫耀他的知识和权力,同时在这个享有特权的戏剧空间中以一种其他人物不具备的方式来表明、论述他的情况和理由。在这个意义上,这部戏剧可以看成是“元评论”性质的,它探讨了有关戏剧与生活、中国知识分子与他们声称去代表的庶民、以及一个人希望成为的与一个人能够成为的等等一系列问题的关系。这一出人意料的结尾挑战了理想的剧作家形象。
《一个死者》的形式主义特征中还包含着另两个寻找中国舞台的戏剧传统痕迹:写意剧(suggestive theatre)(在此剧中体现为无布景的舞台和时间空间的流动性)和希腊戏剧(体现为歌队和面具的使用)。写意剧的观念是由中国导演黄佐临提出的,他将未来理想中的中国戏剧设想成是由三大戏剧观相融合的产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以及梅兰芳的戏剧观。在黄佐临看来,这三种戏剧路径存在着本质的不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相信“第四堵墙”,布莱希特则想废除它,而在梅兰芳那里这堵墙从来就不曾存在。因为中国戏剧是高度程式化的,以至于从未尝试着去创造出戏剧再现现实生活的幻觉。黄佐临因此总结:西方艺术的主旨是现实主义,而中国艺术的主旨则是写意的。[8]
另外,杨健和朱晓平合著的《桑树坪纪事》也被认为是成功借鉴了希腊戏剧形式的实验话剧。整部戏以朱晓平关于桑树坪的系列小说为蓝本,讲述了这个中国西北闭塞村庄发生的故事,表现了村民的不幸、悲剧以及平淡的日常生活。这些村民生活的地方——桑树坪,几千年来一直处于一成不变的无知、愚昧、落后、性压抑和野蛮的父权制结构的笼罩之下。荒凉和回环的舞台设计,交替着展示出黄土高原的不同地理面貌:上坡、下坡以及其间的窑洞,传递出的正是因为任何变化都不可能发生而产生的无力感。
评论家曲六乙评论道:回环设置的舞台以及从不同角度看到的风景地貌的不同面向,所有这些都不仅仅只是单纯为了拓展戏剧的舞台背景。它为歌队提供了持续动作表演的空间,在其间歌队成员通过舞蹈和歌唱的方式来表现村民丰收或举行日常仪式等行为。[9]而舞台上回环的布景就构成了当地风俗和日常生活的“浮世绘”。它透露出的是在这漫长的时间流中个体意义的无足轻重:不论个体经历有着怎样的意义,他们都只是过客,在这空荡荡的舞台上短暂地占据了某一时刻,而他们的人生对于整个历史进程而言却是毫无影响的。只有在一个人试图在诸如希望、苦恼等情感帮助下葆有关于过去的记忆时,时间和空间才具有了意义。下面的一幕可以看成是恰当的佐证:青女被她的疯丈夫剥光了衣服,赤裸地站在村民面前,众人围着她,侮辱她,就好像在观看笼子中的动物。当围观的人群在嘲笑声中逐渐散去时,其中一人突然看见在女人原先站的地方,出现了一座汉白玉的古代女神像。同时,女人隐入到了歌队之中,与歌队一起反思这位无辜少女的命运——她被淹没在了历史的洪流之中,在这片由无能男性统治的贫瘠大地上留下了一个凝固的身影。
在导演们看来,这部戏借着文艺界“历史文化反思”的潮流,展现了“历史的活化石”,以此象征化地表达了对过去五千年的文化和历史态度,从而期望在当代中国寻求一种真正的变化。通过对村庄停滞的自然及其中所包含的一切事物的表现,戏剧传递出了对改变的渴望。这部戏还为观众保留了相当大的阐释余地,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进行解读。渗透于整部戏剧始终的是歌队的伴唱声以及其中对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欢呼与质疑的含混结合。
那么对于那些对女性问题有所意识的女性观众,这部戏剧又意味着什么呢?《桑树坪纪事》中的女性地位低下。李金斗成为了村里唯一的家长——他囊括了所有可能的权力:部落首领,古代皇帝以及毛时代生产队干部,从那之后桑树坪的女性就再也没能想象从父权制的传统中获得解放。她们对时间与变化的无动于衷可以说是症候性地表现了她们希望被历史忘却和埋葬的意愿。只有当新民族感到有必要反思自身的传统和遗产时,他们才会注意到这些性别政治为女性带去了怎样的痛苦。
在皮兰德娄(Pirandello)的话剧《六位寻找作者的剧中人》(Six Characters in Search of an Author)中,舞台上的导演被六位不同的人物说服,将他们复杂的生活故事改编进戏剧之中。然而导演在努力实现这些计划之时,却发现自己竟不知该如何为戏剧结尾。最后,他拒绝了这些人物的要求,停止了创作。皮兰德娄笔下导演的这一拒绝与中国戏剧家们感到的沮丧有着某种相似性——这些中国同行们不得不有选择地接受和拒绝各种西方戏剧传统。而这些不同的传统就好像剧中的六位人物,总是坚持要求一模一样地被搬上中国舞台。像在西方戏剧传统中剧作家寻找上帝或父亲角色一样,中国当代导演也在尝试着寻找权威去支持其自身的形式主义创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总是在最后时刻感到犹豫,并被他们的亲身经历引导回了文化复兴和政治解放的议题之上。中国戏剧家从东西方经典的形式主义戏剧传统中择取合适的资源,创造出了一个大熔炉。通过多样性的形式主义选择,以及致力于对文化死亡、现代性的开端、集体的消融以及父权制等议题的探索,中国戏剧已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有效力了。可以说它已经不需要再去寻找一个权威了。因为有许多权威存在于观众之中,并期待着他们引人入胜的经历被搬上舞台,同时这个舞台也因为融合了各种不同的传统而变得异常丰富了。
注释:
[1]田旭修编著:《多声部的剧场》,花山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30页。
[2]田旭修编著:《多声部的剧场》,第6页。
[3]魏明伦编著:《潘金莲:剧本和剧评》,三联书店1988年,第78-79页。
[4]魏明伦编著:《潘金莲:剧本和剧评》,第134页。
[5]话剧版本名称是《一女四夫》,1988年在香港首演,演员分别来自香港、广州、上海、四川和美国。由西安市秦腔一团和乌鲁木齐市秦腔剧团排演的秦腔荒诞剧《潘金莲》同时在1986年上演。上海昆剧团改编的昆曲版本则在1987年上演。
[6]刘宾雁:《川剧<潘金莲>与它引起的一点联想》,收录于魏明伦编著:《潘金莲:剧本和剧评》,第86页。
[7]胡邦炜:《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深层反思》,收录于魏明伦编著:《潘金莲:剧本和剧评》,第127-130页。
[8]参见Xiaomei Chen, Occident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33-135。
[9]曲六乙:《西部黄土高原的呼唤》,《中国戏剧》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