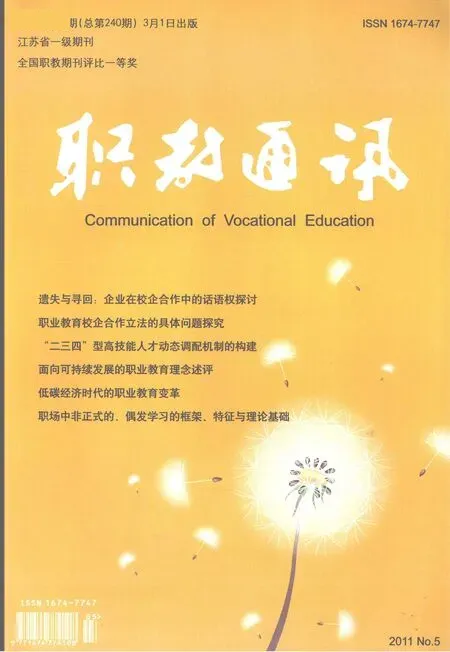重温韦伯
臧志军
重温韦伯
臧志军
1751年,一个德国牧师在一座教堂的门上钉了95篇论文,从而引发了改变世界的宗教变革,在这位名叫马丁·路德的牧师的推动下,新教思想开始广泛传播。254年后,另一位德国人,马科斯·韦伯,试图用一本叫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书来解释为什么新教地区会比天主教地区更加富有。在这本被后人视为经典的书里,韦伯强调新教徒的富有来源于他们对致富和劳动的态度。
韦伯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新教对人们的影响:“同样是波兰的少女,在家乡时,无论怎样有利的赚钱机会都提振不了她们传统主义的惰性,然而当她们到了像萨克森这种陌生的地方工作赚钱时,却好像完全变了个人,经得起无止境的剥削利用”。他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与传统生活关系的“撕裂”和新教教义所提振起来的“劳动的精神”、“进步的精神”和追求财富的精神改变了人们对生活、工作和金钱的态度,而这些态度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最终结果当然是资本主义的大发展。
这种分析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但同时,这种实质上对新教教义的褒奖也引来了无数的批评。许多宗教派别、非基督教宗教和非基督教文化圈无法接受他的结论,一些中国人如余英时等就不满于他关于中国商人不诚实、彼此间毫不信任、没有“资本主义精神”的说法。也有许多学者从方法论、历史学等方面对他的观点予以反驳,更有人提出这是一个“帕森斯化”的韦伯,需要被解构。一些教育学家也加入到了批评者的行列中。苏格兰斯特林大学的贝克尔教授通过对韦伯时代的普鲁士452个县的历史数据的分析发现,新教徒接受教育要比天主教徒早,因为“教育使人更好地理解世界是如何运转的,使人更易于摆脱从属地位”,所以是教育,而不是对劳动的宗教热情使得新教徒有更高的生产力。他更举例说,通过两个教育水平相当的新教地区和天主教地区的比较,发现这两个地区的经济成就相差不大,据此他认为韦伯不恰当地突出了宗教教义的作用,而对教育所发生的作用有所低估。
贝克尔很有可能误解了韦伯。在这本书里,韦伯确实没有进行大范围的关于教育的讨论,但并不表示他不重视教育的作用。因为文化的传承无法脱离教育而存在。我们可以分析韦伯所举的一个关于教育的例子。在韦伯的时代,工业化大生产仍处于上长期,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工厂大幅度地从手工业子弟那儿补充其熟练的劳动力,也就是让手工业为其劳动力做准备,并在准备完成之后将之交付给企业”,他注意到天主教徒比新教徒更倾向于留守在手工业。他认为职业的选择与职业生涯的发展取决于“经由故乡与双亲家庭的宗教气氛所制约的教育方向”以及由此“得自教育的精神特性”。
很明显,在韦伯的意识里,教育不仅仅发生在学校里,更主要发生在生活中,他所采用的是一种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相结合的观点。也就是,在一个青年的成长过程中,两种教育在平行进行,一种是源自家庭的相对正式(尽管不正规)的手工业技能教育,另一种是由当地社会和家庭共同进行的关于社会文化和工作文化的教育(可能是正规形式,也可能是非正规形式),他的生涯发展主要由后者决定。因为韦伯跳出了学校教育来看教育,所以仅从学校教育角度对他进行批判显然力度不够。
尽管韦伯的时代与今天已有100多年的时间间隔,但他所描述的职业教育的基本结构仍然未变:学生被安置在一个专门的学习机构中,这个机构因为专注于特定工作技能的传授而无暇过多地关注文化传承,而学生同时又浸濡于一个由学校、家庭、社会构成的社会文化圈中,其对成人世界、工作世界的认识由这个文化圈与学生的互动来完成。按照韦伯的逻辑,这个社会文化圈对个体的工作伦理的形成并最终对社会的富裕状况发挥极大的作用,相比而言,专门的职业技能传授机构的作用要小得多。如果能接受这个推论,是不是说我们今天的职业教育已经走向了它的出发点的反面?
人们对职业教育寄予厚望,是因为它能解决就业问题,提高生产力,并最终改变社会富裕状况。但按照韦伯的思路,真正起作用的可能并不是职业教育教给了人们怎样的技能,反而是人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工作态度、工作伦理。但当下的职业教育发展似乎有一个倾向,即越来越关注具体职业技能的传授,要求证书的获取,要求技能的娴熟,尽管德育两个字被叫得山响,但真正把“职业精神”四个字落到实处的能有几所学校?很有可能的一个结果是,我们培养出越来越多的有工作技能但没有工作意愿的青年。
今天重温韦伯的意义就在于让我们记住:技能教育只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部分,也许远不是最重要的那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