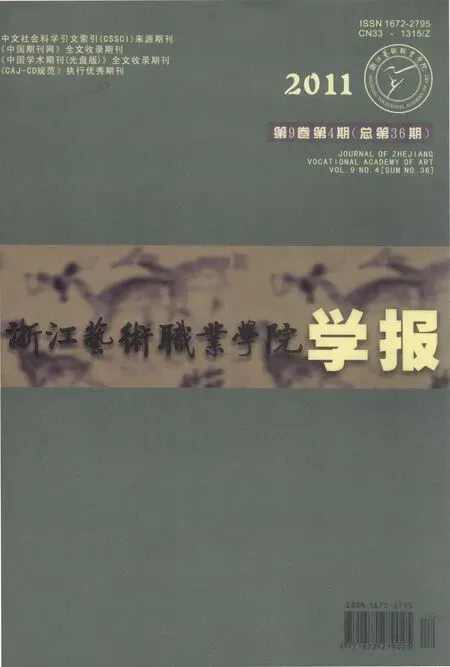夏乐《大夏》与《九夏》论考
金荣权
从史料记载来看,夏代流传下来的有两大乐歌,一是以颂扬大禹功绩为主要内容的歌舞《大夏》,后代文献又称之为《夏》或《夏籥》;另一个是大型组歌《九夏》,它包括《王夏》、 《肆夏》、 《昭夏》、《纳夏》、《章夏》、《齐夏》、《族夏》、《祴夏》、《骜夏》等九大乐歌。
《庄子·天下篇》云:“禹有 《大夏》。”[1]《汉书·礼乐志》云: “禹作 《夏》。”[2]《吕氏春秋》说,禹“命皋陶作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3]105。
《大夏》和《九夏》为周人所继承,并作为重要的礼乐而广泛用于重大典礼、燕享之中,《左传》、《国语》、《周礼》、《仪礼》、《仪礼》中屡次提到。虽然我们已经看不到它们的具体内容,然而,从现存的文献资料和周人对《大夏》和《九夏》的使用场合、方式等,仍然可了解它们的相关信息。
一、《大夏》、《九夏》为两种不同的乐歌
学者或以为《大夏》即《九夏》,二者异名而同实。今人韩高年先生在其《〈大夏〉钩沉》一文中,在总结前人诸说的基础上提出四条证据,以伸张《大夏》即为《九夏》之说[4]:《吕氏春秋》说大禹命皋陶作“《夏籥》九成”,这里的《夏籥》就是《大夏》,可见《大夏》也是九个曲子,它与《九夏》在乐曲结构方面是相同的,都与“九”有关,所以《大夏》即是《九夏》;《周礼·大司乐》郑玄注说:“《大夏》,禹乐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国也。”《九夏》与《大夏》内容应相同,均为颂扬大禹治水傅土之功的颂诗;“九”和“大”在先秦时期音近义通,因此,《九夏》与《大夏》在先秦可以互称。舜之乐为《大韶》,又称《九韶》,所以按此来推论,《大夏》也可以称为《九夏》。据此,韩先生认为《九夏》即《大夏》,应不成问题。但是仔细推敲,这四个证据都有值得商榷之处。
韩先生的第一条证据主要是从形式上认定二者完全相同。文献记载“《夏籥》九成”,所以说明《大夏》也有九篇。实际上,所谓“九成”,这只能说明《大夏》是一个复杂的大型乐曲,由多个部分组成,但最终却以一个整体存在,其在用于表演时也应是一个整体。而从周代文献记载来看,《九夏》却是相对独立的乐曲,它们分别用于不同场合、不同仪式。正如《楚辞》中屈原的《九歌》和宋玉的《九辩》虽然都以“九”命名,但却有实质的区别:《九歌》是一组诗歌,而《九辩》则只是一首诗歌。所以尽管《大夏》和《九夏》都与“九”有关,却并非同一种乐曲。
韩先生的第二个证据说《大夏》是颂大禹之德者,所以“《九夏》与《大夏》内容应相同”,这纯属推测,并且失之武断。因为《九夏》可以用于祭祀、朝聘、燕享乃至乡射等很多礼仪场合,由此可见《九夏》在内容上绝非和颂扬大禹之德的《大夏》相同。
韩先生的第三、第四两条证据可以归为一条,即“九”与“大”在先秦时代音近而义通,所以“九”即可为“大”,那么《九夏》当然即为《大夏》。这种汉字的通假现象确实存在,然而它却不具有普遍性,尤其很多与专有名词相关的“九”与“大”是不可以通用的。如“大雅”不能说成“九雅”,汤乐《大镬》而不称《九镬》;“九州”不能说成“大州”,“九歌”、“九辩”也不能说成是“大歌”、“大辩”。正因如此,“《九夏》是《大夏》的别名”之说没有直接的文献证据,是不可信的。
从夏灭亡到周王朝建立的500多年历史中,夏代乐歌奇迹般地得以保存、流传。周王朝建立之后,继承了夏、商礼乐制度,所以《逸周书·世俘解》就记载了周武王克商之后,举行为期六天的开国大典,其中论及周武王在典礼中用夏乐的情况:“乙卯,籥人奏《崇禹》、《生开》三终,王定。……告于天、于稷。用牲于百神、水土、社。”[5]刘师培《周书补正》认为“崇禹”即“夏禹”,“开”即“启”,夏启也。[6]说明周武王所奏的《崇禹》、《生开》两曲是和大禹、夏启有关的夏代乐歌。可见夏乐在周代初年的重要地位,这种情况一直到康王定乐歌、重修礼乐制度之后才有所改变。尽管康王之后周代有了自己的礼乐制度以及相对应的乐歌,但并没有完全抛弃夏乐,而且还在祭奠、燕享等重大礼仪场合继续使用夏乐。
从周代的《大夏》、《九夏》乐来看,这两者明显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乐曲。其证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大夏》主要内容是颂禹之功德而《九夏》则属于综合性的乐歌
《吕氏春秋·古乐》说:“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漻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于是命皋陶作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这里的《夏籥》即是周代所称的《大夏》。由此可见, 《大夏》的主要内容是歌颂大禹之功德的,它具有史诗性质。《吕氏春秋》所载在《左传》中得到印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当吴公子季札聘于鲁时,鲁人为之展示中原的乐舞,“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7]1122从鲁国乐人舞《大夏》和季札的评语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两个方面的信息:其一,周人的《大夏》乐舞的主题基本上保持了夏代的原貌,仍是歌颂大禹之德的;其二,《大夏》舞在周代和《大武》、《韶濩》、《韶》等一样广为流传,否则,远在吴地的季札不可能如此熟悉,也不可能评价得如此到位。从此来看,《大夏》首创于夏禹时期,以颂扬大禹治水、平治天下之功德为核心,其乐舞内容相对单一。
而《九夏》则不同,不仅由多个各自独立的乐歌组成,同时也用于不同的场合。《周礼·地官司徒》载:“钟师,掌金奏。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纳夏》、《章夏》、《齐夏》、《族夏》、《祴夏》、《骜夏》。”郑玄注引杜子春语云:“内当为纳,祴读为陔,鼓之陔。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宾客来,奏《纳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齐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骜夏》。”[8]800
《王夏》、《肆夏》、《昭夏》、《祴夏》、《骜夏》等五首乐歌的演奏场合已见之于《周礼》和《仪礼》,所以《周礼·地官司徒》说:“王出入,则令奏《王夏》;尸出入,则令奏《肆夏》;牲出入,则令奏《昭夏》。”[8]790《祴夏》,也称为《陔夏》,或直称《陔》,在《仪礼》一书中多次出现,在乡饮酒、乡射、燕及大射等礼事活动中,当宾客下堂出门时,都要奏《陔》乐。《骜夏》乐歌也见于《仪礼》,《仪礼·大射礼》说:“公入,《骜》。”[9]1044
《纳夏》、《章夏》、《齐夏》、《族夏》等四曲所用的礼事活动却不见于先秦典籍,杜子春当有所本。从《周礼》、《仪礼》和汉人的记载来看,《九夏》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其一,《九夏》中的九首乐歌不是一套乐歌的九个部分,而是各自独立的,它们在不同礼事活动、不同场合中分别演奏。其二,《九夏》的乐歌不仅可以用于节制人们的礼仪行为,同时也可以用于祭礼、庆功、朝聘、燕享等,说明它是夏代礼乐的集大成。从它的用途、名称来看,它们大多数都与歌功颂德无关。
(二)《大夏》主体为乐舞而《九夏》主体则为乐歌
先秦典籍中大凡提到《大夏》者,一般都和舞联系起来:
《礼记·明堂位》:“皮弁素积,褐而舞《大夏》。”[10]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见舞《大夏》者……”[7]813
《穀梁传·隐公五年》中有:“舞《夏》,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11]
《周礼·地官司徒》:“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8]787
然而,在提到《九夏》的相关乐歌时,大都只言“奏”:
《周礼·地官司徒》:“王出入,则令奏《王夏》;尸出入,则令奏《肆夏》;牲出入,则令奏《昭夏》。”[8]790
《周礼·地官司徒》:“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8]790
《仪礼·大射礼》:“奏 《肆夏》,宾升自西阶。”[9]1030
《仪礼·大射礼》:“奏 《陔》……公入,《骜》。”[9]1044
《左传·襄公四年》:“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7]813
王子初在其《先秦〈大夏〉〈九夏〉乐辩》一文中说:“《大夏》用‘舞’,可知《大夏》是一部乐舞。”“《九夏》之乐当是怎样的一种形式呢?先秦记载均用‘奏’字,其决非乐舞。”[12]王氏的观点是正确的。也可能在各种礼仪场合,《大夏》舞需要有音乐,甚至有歌,而《九夏》的演奏也可能会用舞蹈,但它们的主体形式和主要用途却有质的区别。这也正可以说明《大夏》与《九夏》的不同。
(三)周代文献中《大夏》与《九夏》并出
《周礼·地官司徒》说大司乐以乐舞教国子,其中包括《大夏》,而接下来又提到在不同礼事场合演奏《王夏》、《肆夏》、《昭夏》等乐歌。可见在《周礼》中,将《大夏》与《九夏》中的各篇分得十分清楚,《大夏》就是《大夏》,《九夏》自是《九夏》,二者泾渭分明,不可混淆。
二、《大夏》、《九夏》的演变
《大夏》和《九夏》在夏代的固有形式是什么样子?到了周代又有了什么变化?根据它们的用途、乐歌发展的规律以及周代文献的相关记载,我们认为,《大夏》和《九夏》原本都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它们产生的基础是诗歌,然后加以配乐、编舞,只不过因为用途不同,《大夏》之乐主体是舞蹈,而《九夏》诸歌则以乐歌为主体。至周代,这些诗歌的歌词因为不被周人所采用而逐渐不为人们所熟悉,然其乐曲及其舞蹈还用于周人的各种礼事活动当中。
史传大禹曾经征伐三苗、平定水土,《大夏》正是在这之后产生的。作为一部歌颂大禹功德的作品,应当是有歌词的,只不过在没有系统文字的时代,其歌词不会太繁复。但是在表演过程中,为了延长演奏和舞蹈的时间,通过变化曲调和舞蹈来反复地演唱这些简短的诗歌,这就是所说的“九成”或“九变”,也正是“《夏籥》九成”的含义。从现存典籍可见,至周代以后,没有任何歌《大夏》的直接或间接的证据,它只作为用来表演的乐舞而存在。其歌词亡佚的时代我们已经无法详知了。
相比《大夏》来说,《九夏》的情况要好得多,从周代诸多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九夏》组歌中的某些篇章的歌词还仍然在流传。
(一)《九夏》中的部分乐章歌词与乐谱同时存在
郑玄《周礼注》说:“《九夏》皆诗篇名颂之类也,此歌之大者,载在乐章,乐崩亦从而亡,是以颂不能具。”[8]800郑玄的说法并非是推测,这在周代的文献中可以找到相关的证据。
《左传·襄公四年》载:“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7]813《国语·鲁语下》也记载了这件事情:“叔孙穆子聘于晋,晋悼公飨之,乐及《鹿鸣》之三,而后拜乐三。晋侯使行人问焉,曰:‘子以君命镇抚弊邑,不腆先君之礼,以辱从者,不腆之乐以节之。吾子舍其大而加礼于其细,敢问何礼也?’对曰:‘寡君使豹来继先君之好,君以诸侯之故,贶使臣以大礼。夫先乐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飨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绵》,则两君相见之乐也。皆昭令德以何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闻也。臣以为肄业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箫咏歌及《鹿鸣》之三,君之所以贶使臣,臣敢不拜贶。夫《鹿鸣》,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每怀靡及’,诹、谋、度、询,必咨于周。敢不拜教。’”[13]63
从《左传》和《国语》记载来看, 《文王》之三指的是《大雅》前三篇: 《文王》、 《大明》、《绵》,《鹿鸣》之三指的是《小雅》的前三首:《鹿鸣》、《四牡》、《皇皇者华》。而《肆夏》之三,《国语》韦昭注:“《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纳夏》一名《渠》,此三夏曲也。”[13]63杜预《左传》注说:“《肆夏》,乐曲名。《周礼》,以钟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纳夏》,一名《渠》。盖击钟而奏此三‘夏’曲。”[7]813因为《周礼》记《九夏》的顺序是《王夏》、《肆夏》、《昭夏》、《纳夏》、《章夏》、《齐夏》、《族夏》、《祴夏》、《骜夏》。韦、杜二人依据“《文王》之三”和“《鹿鸣》之三”的说法而认为“《肆夏》之三”即《肆夏》以及它后面的另两篇《昭夏》、《纳夏》是有道理的。又依据《国语》,认为《樊》、《遏》、《渠》分别是《肆夏》、《韶夏》和《纳夏》的别名。晋人将《九夏》中的《肆夏》等乐歌与《文王》、《鹿鸣》等一起用来娱乐鲁国的使者,以示两国交好,而《文王》、《鹿鸣》等诗见于今本《诗经》,可见《肆夏》等在周代还是有歌词存在的。
(二)周人对《九夏》乐歌进行了再改造
据《史记·周本纪》载,成王平定东夷之乱以后, “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14]。《竹书纪年》说:“(康王)三年定乐歌。”[15]可见,在武王刚刚灭商时,尚没有自己成熟的礼乐,所以这才会出现在开国大典中用夏乐之事。至成、康之际,国家安定,为了配合礼制而作乐,于是周人才有了自己的颂诗,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用于祭祀、朝聘、燕享等各种礼事活动的乐歌。当周乐成熟之后,周人并没有完全抛弃前代的乐歌,而是有所选择并加以改造,这也包括对夏人乐歌的改造。周人对夏代乐歌的改造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筛选夏人的乐歌而重新定名,《九夏》之称源于周代。
《山海经》载夏启有《九辩》、《九歌》[16],《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载孔甲作《破斧歌》[3]116,《文心雕龙·通变》说“夏歌《雕墙》”[17],可见,夏代流传的歌诗数量还是十分多的,只是经商周时期文献失载而佚失。当夏人在系列的祭祀、燕享、朝聘礼仪中除《大夏》之外,一定有自己的系列乐歌,其数量当不限于九,其名称也不是周人所说的《九夏》。《九夏》之名是周人在筛选过夏歌之后而留下的九篇歌诗的总称。
其二,《九夏》由诗乐转变为礼乐。
《周礼·地官司徒》说: “王出入,则令奏《王夏》;尸出入,则令奏《肆夏》;牲出入,则令奏《昭夏》。”[8]790这里的“王出入”、“尸出入”、“牲出入”指的均是祭祀之礼,此时演奏《王夏》、《肆夏》、《昭夏》诸乐章正是为了节制君王、尸和牵牲者的步伐的。这正说明了《肆夏》等乐歌在周代礼事活动中的实际作用。
《九夏》中的《祴夏》即《陔》在《仪礼》的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及大射礼中都有广泛地运用,一般都是在宾客出门时演奏,如《仪礼·乡射礼》说:“宾兴,乐正命奏《陔》。宾降及阶,《陔》作。宾出,众宾皆出,主人送于门外,再拜。”[9]1009从主人站起身到走出门,这其中的时间并不会很长,所以奏《陔》的时间也会很短,这样,作为《九夏》之一的独立乐歌在这里就变成了礼事活动的结束曲。
关于乐歌的演变,朱谦之在其《中国音乐文学史》中说,三代音乐文学的发展,起初是原始的歌、乐、舞一体的,战国以后,各国间盟会聘问见于《国策》者,始有只奏乐器,不必歌诗的情况,也才有了歌、乐、舞的分离,即所谓“器乐曲”[18]。三代之乐固然是歌 (诗)、乐、舞一体,然而歌与乐、舞的分离早在西周至春秋时期便已开始。所以《诗经》除305首诗歌之外,还有6首是有目无辞的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这6首诗原本不应该叫做诗,它就是后代的曲,主要由笙这种乐器来演奏。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大夏》、《九夏》是夏代最重要的乐歌,它们不仅名称不同,内容更有质的区别。《大夏》是为了歌颂大禹功德而编制的大型乐舞,《九夏》则是周人挑选夏人遗留下来的乐歌而重新编定、命名的一组综合性乐歌。《大夏》、《九夏》产生的基础是诗歌,然后加以配乐、编舞。至周代,《大夏》仍然是周人最重要的乐舞之一,其歌诗内容不详;《九夏》诸乐歌至周代以后,其歌诗已渐渐退至幕后,而其乐曲则成了周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不同的乐章来节制步伐使之合乎礼仪。
[1]王先谦.庄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班固.汉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62:1038.
[3]吕不韦.吕氏春秋[M].北京:线装书局,2007.
[4]韩高年.《大夏》钩沉 [J].文献,2010(3):173—175.
[5]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455.
[6]刘师培.刘申叔遗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7]杜预.春秋经传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8]贾公彦.周礼注疏 (十三经注疏本)[M].北京:中华书局,1979.
[9]贾公彦.仪礼注疏 (十三经注疏本)[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孔颖达.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M].北京:中华书局,1979:1488.
[11]杨士勋.春秋穀梁传注疏 (十三经注疏本)[M].北京:中华书局,1979:2369.
[12]王子初.先秦《大夏》《九夏》乐辩 [J].音乐研究.1986(1):71.
[13]国语 [M].上海:上海书店,1987.
[14]司马迁.史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90.
[15]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 (二十二子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077.
[16]山海经 (二十二子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347.
[17]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30.
[18]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3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