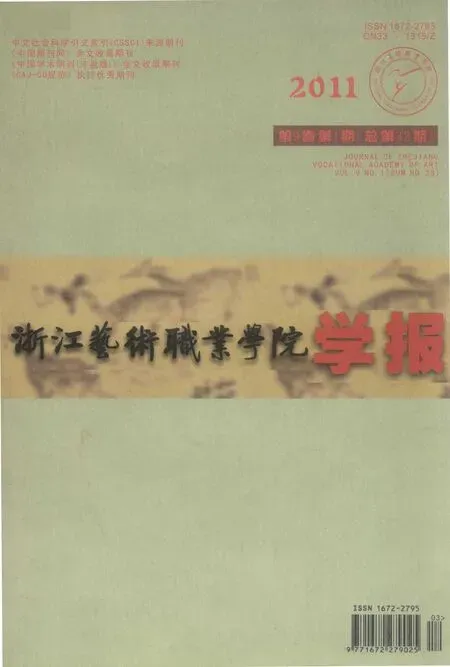从文化入手 释乐律悬疑—— 《中国古代文化与〈梦溪笔谈〉律论》读后
从文化入手 释乐律悬疑
—— 《中国古代文化与〈梦溪笔谈〉律论》读后
黄大同先生的专著《中国古代文化与〈梦溪笔谈〉律论》最近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此书运用民族音乐学从文化背景入手的研究方法,结合阴阳五行学说对沈括《梦溪笔谈》中的律论进行探讨,解决了律学方面的一些悬疑,是一本能给读者很多启示的好书。
沈括律论;民族音乐学方法;阴阳五行学说
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音乐学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是民族音乐学的确立和发展。1950年,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 (JaapKunst,1891—1960)提出这一学科名称后,“民族音乐学”便取代了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先后进入一些西方国家高等学校和音乐学院的课堂,成为与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并重的专业。不少国家相继成立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机构,出版了大量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著作。20世纪结束之时,民族音乐学在全世界已成为音乐学诸学科中最活跃、最具生命力、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引进这门学科之后,它在中国的发展也非常迅速。
民族音乐学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中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它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其特征、探索其规律。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是文化中的人,每一种音乐都是文化中的音乐,每一个与音乐有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也都是文化中的成果。因为民族音乐学把音乐作为一种文化和文化中的一个类别进行研究,音乐作品就不再被看做某个作曲家或某一社会群体对其人生感悟的“独白”,而是被解释成作曲家或这一群体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所作的一次文化发言;音乐现象不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是被看做整个社会形态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与音乐有关的科学研究成果也不再被简单地看做某一位或某几位专家学者苦思冥想的产物,而是整个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成果。
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在西方国家里发展起来的。正如我曾经指出的那样,将音乐当成一种文化,把它放在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进行研究的方法,实际上是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界在学习、研究非西方民族音乐,特别是东方民族音乐的过程中,借鉴东方民族综合性思维模式的成果,是对西方分析性思维模式的否定和对东方民族综合性思维模式的肯定。[1]西方民族音乐家的这种做法对西方音乐学中其他两个学科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少从事历史音乐学和体系音乐学研究的专家都借鉴了民族音乐学的方法,把他们的研究对象放在其所处的文化环境中进行探讨。他们不再简单地依据某一种科学体系,对过去的音乐现象和音乐学研究成果作出若干解释和评价,而是从当时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文化状况入手,对音乐现象本身和音乐学研究成果作出文化学方面的阐释。他们首先把音乐作品、音乐现象和音乐学研究成果看成文化现象,并将它们放到所发生、发展的背景中来,探索其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西方历史音乐学和体系音乐学专家们的做法对其他地区和其他国家的历史音乐学和体系音乐学界影响很大。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广泛采用了使研究对象回归于文化的做法,极大地推动了历史音乐学和体系音乐学中的各个分支学科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按照西方通用的音乐学分类方法,由于“律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数学有密切关系,被看作体系音乐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我国古代的律学研究十分发达,王光祈先生曾在《东西乐制之研究》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中国人“数千年以来,学者辈出,讲求乐理,不遗余力,故今日中国虽万事落他人之后,而乐理一项,犹可列诸世界作者之林,而无愧色”[2]。王光祈在这里说的“乐理”就包括了律学研究成果在内。我国古代的律学研究除和数学研究密切相连外,还有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三个特点:一是由于受“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影响,和天文学、历法相联系,故班固撰《汉书》,将律、历合一,设《律历志》,后来的史家效法班固,即使不将“律”、“历”二志合一,也将它们排列在一起;二是受主张“礼乐治国”的儒家思想影响,把律和度、量、衡相联系,并认为音乐中的律是生活中度、量、衡的先导;三是受我国古代综合性思维和科学观点的影响,把律学研究和阴阳五行学说相联系。第三个特点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王光祈说,自秦代以降,“后世言律之人除极少数例外,多以阴阳五行为大本营”[3]5。此特点所以能最突出,有深刻的历史渊源。汉文文献中“音乐”第一次出现是在《吕氏春秋》中,这本书的《大乐》篇说:“音乐之所以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4]由此可知,我们的祖先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把“音”、“乐”与阴阳五行相联系。后来的律学研究,更是和阴阳五行、气、象数、义理等哲学、科学的概念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具有综合性思维和博大精深的特征。
综上所述,无论从当代音乐学研究的时代潮流,还是从我国律学的历史发展特点,我们在对中国乐律学史进行研究时,都不能脱离其文化背景,特别是不能脱离阴阳五行学说。然而,由于我国音乐学界受欧洲科学主义的影响,在整个20世纪研究古代乐律时,几乎所有的专家都把阴阳五行学说抛在一边,甚至把这个学说看成“迷信”和“伪科学”。20世纪20年代,童斐说:“凡论阴阳五行,聚讼甚多,徒蹈于虚玄,无当于物理,足为言乐之障。”[5]20世纪30年代,许之衡说:“夫宫商律吕等字,自宋以来,既知为即工尺等字矣。与阴阳五行,有何关系? 《汉志》多本之刘歆,刘歆伪儒,以阴阳五行,比附作乐。不外以作乐为王者之事,务极玄奥,令人神秘莫测,以逢迎人主耳。”[6]王光祈先生也认为律学研究中阴阳五行是“穿凿附会,令人讨厌”[3]5,宋代大科学家沈括所著《梦溪笔谈》中的律论部分是我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乐律学典籍,只是因为它和阴阳五行有关,20世纪60年代被杨荫浏先生批评为“神秘主义”[7]。这样一来,这一重要典籍便被中国音乐史学界所忽略。音乐学界不但忽略了沈括的律论,甚至不愿意看到任何人把音乐理论和阴阳五行学说放在一起加以讨论,20世纪90年代末,拙作《中国民族乐理》一书中将宫、商、角、徵、羽五声和东、西、南、北、中五方等放在一起加以介绍,还被人批评成“奇谈怪论”、“江湖庸医的叫卖”[8]。
进入21世纪后,人类对成为过去的20世纪进行全面、整体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对过去被认为是确信无疑的真理和思想表示怀疑,并在实践的基础上,重新对它们加以考虑和审视。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开始用更清醒的目光来认识20世纪普遍流行的科学主义,也对学术界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一些看法和认识进行反思,并通过反思扩展思想认识,使之达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通过反思人们认识到,科学不是唯一的,而是具有民族性的。比如我们不能认为只有西医才是科学,而中医就不是科学。如果我们能够同意中医也是科学,那么作为中医基础理论的阴阳五行学说当然也是科学,它是一种具有强烈民族特征的、不同于西医基础理论的科学。既然如此,先民们把音乐和阴阳五行学说联系在一起也不一定都是穿凿附会,而其中也可能有一些道理。如宫与中、商与西、角与东、徵与南、羽与北相对应,很可能和当时不同地区的民间音乐不同风格、主要采用不同的调式有关。直到现代,长城以北的民歌以羽调式为主,长江以南的民歌徵调式为主,陕西、甘肃、青海民歌中商调式占有较高的比例,河南民歌中宫调式较多,而浙江等东部沿海省份角调式民歌显然比其他地区多,难道不是五个方位和五声联系的具体事实吗?另外,五声和五行在音乐治疗学方面的联系,亦需要从中医学的角度进行深入探讨,不能一概轻易加以否定。
如果我们能够承认阴阳五行学说也是科学,而且它和音乐的联系也不一定完全是穿凿附会,在研究我国古代乐律学成果的时候,就一定要按照民族音乐学的方法,把这些成果放在产生它们的文化背景中去研究,同时绝对不能避开阴阳五行学说。既然古代研究律学的学者“多以阴阳五行为大本营”,不入此大本营,焉能知道他们的学说是否正确?不入此大本营,岂能揭开律学史上的众多悬疑?不入此大本营,又怎么样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的乐律学遗产?不入此大本营,如何能让“数千年以来”,无数先辈“不遗余力”研究出来的中国乐律学和“犹可列诸世界作者之林,而无愧色”的古代乐理知识在今天的音乐学研究和音乐教育中发挥作用?
近来,读到黄大同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化与〈梦溪笔谈〉律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年出版,“21世纪中国音乐学文库”之一),感到兴奋、激动。兴奋的是在中国乐律学研究的领域中终于有人能够采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把古代乐律学的成果放在产生它的文化背景中加以研究;激动的是在这一研究领域,也终于有人把阴阳五行学说当成一种科学,作为古代大科学家沈括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地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并解决了中国乐律史上的一些悬疑问题。
黄先生的这本书是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在陈应时先生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时所写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和补充而成的,全书的主体分为导论、上篇、下篇和结论四部分。他在导论中分析了研究沈括《梦溪笔谈》一书中律论部分的前提以及文化背景,指出我国音乐学界20世纪在研究古代乐律文化时,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阴阳五行学说”是“陈旧的东西”,从而犯有“整体失语症”,而“构筑起由文化、哲学、律学三个逻辑层次组成的研究结构,以三者合一的综合视野进行审视”,不仅符合从西方兴起的“表现出整体性特征的学术思潮,实际上就是对古代东方研究方法的一种肯定和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归”。我想,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大的学术成就,和黄大同先生采用了既符合民族音乐学,又遵循我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正确研究方法分不开。
上篇主要研究《梦溪笔谈》律论中的律数,通过对宋代象数学的分析,批判了历代学者对“实积之数”的误读,指出“沈括所论述的管律律数不是真正的、与实际计算与有应用有关的律管参数,而只是一种先验性的理论概念数”,而且进一步指出,有关《史记·律书》中律数的问题沈括实际上已经解决,而沈括之后许多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均未超过沈括”。
下篇主要研究《梦溪笔谈》律论中的律吕问题,通过对宋代阴阳五行学说的分析及沈括对这一学说的论述,说明了“八八为伍”和“三分损益法”的区别,介绍了三双阴和三双阳交错对应十二律,并在此基础上解释了先秦文献《国语》中有关“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之于十二”记载的意义,介绍了“六十甲子纳音”的来源、概念、形态及其结构,对乐律学研究中的几个悬案做出了言之成理的解释。
结论部分强调了《梦溪笔谈》律论的历史贡献、研究价值,并着重指出中国乐律学说和中国古代哲学以及文化理论是互为前提的,两者具有同构性,也是融为一体的。因此,应采用“全科视野研究范式”进行研究。黄大同先生强调“全科视野研究范式”,对目前音乐学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尽管专家都一致肯定《梦溪笔谈》在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性,然而在黄先生写作这本书之前,尚没有任何人对沈括在中国律学史上地位进行全面地研究并加以充分肯定。黄大同先生作为生活在我们这个反思时代的中国音乐学家,站在了前人从未达到过的思想高度上,对沈括《梦溪笔谈》中的律论部分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不仅总结了过去,也说明了现在,并启示了未来。
黄大同先生通过这项研究,肯定了沈括《梦溪笔谈》中的律论部分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与两汉的律学思想和理论,填补了中国律学史上北宋时期的空缺,指出沈括律论是我国古代律学发展链条上不可或缺的历史环节,这是本书很大的一个贡献。黄大同先生还通过他的这项研究,指出当前我国音乐史学界“应从文化、哲学和律学等由不同逻辑层次组成的综合视野,去考察、分析和叩问融阴阳二气、五行、象数和义理等中国传统哲学文化范畴为一体的中国古代音乐理论”。我以为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一定会给有志在中国音乐史和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领域进行耕耘,希望有所发现、有所收获的读者很多启示。
这本书有两个附录,一是沈括《梦溪笔谈》中的律论条文的校勘,二是中国音乐史论著、教程、词典对沈括《梦溪笔谈》音乐条目之涉论。这两个附录也非常有学术价值。书后所附的索引,可以方便读者查阅书中有关某一问题的论述,值得在学术著作中大力提倡。
沈括是一个世界级的大科学家,而《梦溪笔谈》中的律论条文又是他在音乐学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向全球学术界宣传沈括在音乐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是我们的责任。外国音乐学家中懂中文的很少,即使懂中文的人,也未必看得懂古文,如果本书能有一个英文的摘 要,一定能帮助他们了解我们的研究成果。
[1]杜亚雄.从分析到综合——西方民族音乐学思维模式的历史发展轨迹[J].音乐研究,2002(3).
[2]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M].上海:中华书局,1936:9.
[3]王光祈.中国古代音乐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音乐研究所.中国古代乐论选辑[C].北京:音乐出版社,1981:35.
[5]童斐.中乐寻源 [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17.
[6]许之衡.中国音乐小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141.
[7]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132.
[8]周勤如.研究中国音乐基本理论需要科学的态度——从杜亚雄《中国民族基本乐理》的谬误谈起 [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9(3).
Explanation of Temperament from Culture—Comments on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and Temperament of Dream Brook Sketchbook
DUYa-xiong
The book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and Temperament of Dream Brook Sketchbook by Mr. HuangDatong is recently published by the People’s Music Publishing House. The book applies the researchmethod of ethnomusicology starting from the cultural background,discusses the theory of temperament inShen Kuo’s Dream Brook Sketchbook combining the theory of yin-yang and the five elements,solves somesuspense in temperament,and is a good book inspiring readers.
Shen Kuo’s temperament; methodology of ethnomusicology; yin-yang and the five elements
杜亚雄
J602
A
1672-2795(2011)01-0043-04
2010-11-09
杜亚雄 (1945— ),河北人,哲学博士,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音乐教育和民族音乐学研究。(杭州 31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