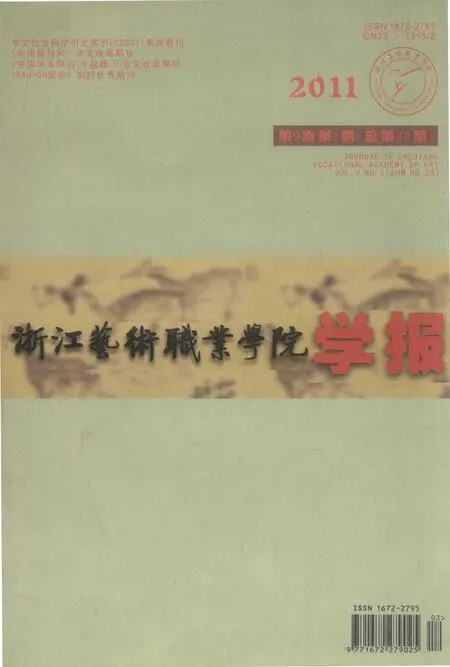新疆和田地区十二木卡姆之传承特点解析*
王建朝
新疆和田地区十二木卡姆之传承特点解析*
王建朝
本文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采用田野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互证的方法对和田地区十二木卡姆的即兴性、直接性、群众性、儒化、变异性等传承特点所做出的阐释与解析。
和田地区;十二木卡姆;传承特点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以十二木卡姆为代表和主体。除喀什、伊犁等地区之外,十二木卡姆在和田地区也曾经广为流传。据研究,和田十二木卡姆与喀什地区流传的版本同为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古典套曲。由于诸种原因,如今仅在墨玉县的芒来乡、奎牙乡、托乎拉乡、墨玉镇,和田市的伊里奇乡,皮山县的克里阳乡等地尚有十二木卡姆流传,除此之外的其余各县,随着老艺人的先后谢世,十二木卡姆后继乏人,已濒临灭绝。
本文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采用田野资料和文献资料互证的方法对和田十二木卡姆的即兴性、直接性、群众性、儒化、变异性等传承特点予以阐释与解析。
一、即兴性特点
“口传心授,言传身教”是和田十二木卡姆最主要的传承方式。虽然这种传承方式因没有完整的书面表达而显得缺少规范,因多于个人的口头表述而少有确定,因个人的主观支配而多有即兴创造,但是“口传得到了正宗的音乐精髓的真传,心授得到了音乐再创造的活性空间,使得教学双方具有自我创造的余地”[1]。维吾尔木卡姆也以“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因此,木卡姆其们在传授十二木卡姆的过程中,在不违背基本结构的情况下,受临时心境好坏的影响,对传授的木卡姆的节拍节奏、旋律等造成影响也实属正常。犹如周吉所言:“《十二木卡姆》和《刀郎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在遵循传统所确定的‘结构模式’和‘调式、旋律型模式’的同时,在填唱歌词、段落反复、伴奏手法、旋律装饰等方面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即兴性,从而达到继承传统和个人创造之间的最佳结合。”[2]和田十二木卡姆作为维吾尔木卡姆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其传承的即兴性也较强,主要体现在传承场、乐队组合、伴奏乐器、乐曲选择、段落反复等诸多方面。
(一)传承场的即兴性
传承场,即传承场合或传承基地。据调查,和田木卡姆其表演木卡姆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场合,而是有着很强的即兴性。他们既在孩子出生礼、成年礼、婚礼等人生礼仪上演唱,也在麦西热甫、巴扎、传统节日、麻扎朝拜、孤独的路途中等时间和场合演唱。周吉曾言:“诙谐幽默、爱唱爱跳、爱说爱笑、能歌善舞成了绿洲人的优良传统。哭也是歌、笑也是歌、生也是歌、死也是歌,绿洲人的一生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3]哪里有维吾尔人聚集的地方,哪里就是维吾尔木卡姆即兴表演的传承场。此表演场合多有该族人和外族 (家族)人踊跃参加,因此,这些表演场合不但成了承载维吾尔十二木卡姆的重要载体,也成了十二木卡姆的重要传承场。
(二)乐队组合的即兴性
据录音实况得知,流传于和田各地的木卡姆的乐队组合很是自由,特别是在日常表演场合,各地木卡姆艺人会根据演奏场合的不同和艺人数量的多寡而随机组合表演木卡姆。有的三五一组,一把弹布尔、两只萨帕依、一个达普、一支巴拉满,艺人就可以组合表演。皮山县克里阳乡托万恰喀村的巴拉提·艾木都拉和奥斯曼·阿洪的两人组合也可以很自如地演唱木卡姆。他们时而独唱,时而合唱,有时亦会一问一答,甚是诙谐幽默。一把弹布尔或都它尔的自弹自唱木卡姆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据录音实况发现,不同家族为木卡姆伴奏的乐器并不完全相同,即使同一家族,不同表演地点的伴奏乐器也不完全相同,他们会根据在场艺人的数量多寡而随机组合表演。笔者曾3次到墨玉县托胡拉乡波尔其村库球克家族录音,其伴奏组合很是随机:第一次,伴奏组合为3人,依该木·拜尔迪·艾山奏巴拉满兼主唱,艾合买特奏斯克里普卡,艾合买特·导合迪奏萨它尔。第二次,伴奏组合为5人,依该木·拜尔迪·艾山奏巴拉满,吐迪·艾合买特奏苏乃依,艾合买特·导合迪奏弹布尔,买买提·尼雅孜·买特努尔奏萨它尔,吐尔逊·托合体奏达普。第三次,伴奏组合为4人,依该木·拜尔迪·艾山奏巴拉满,艾合买特·导合迪奏弹布尔,买买提·尼雅孜·买特努尔奏萨它尔,吐尔逊·托合体奏达普。此外,笔者在其他乡镇录音时也发现同样的情况。他们的乐队组合皆带有颇强的随机性,会根据家族成员在场情况而即兴的组合乐队来表演木卡姆。
(三)乐曲选择和段落反复的即兴性
和田十二木卡姆在不同表演场合所选取的套数及每套木卡姆的乐曲选择上也有着很强的即兴性。据墨玉县文体局文物保护所所长艾热提介绍,维吾尔婚礼上主要表演十二木卡姆的埃尔乃额曼,且选取木卡姆的套数及每套木卡姆的乐曲选择很是自由,木卡姆乐曲后可直接跟唱当地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歌。2007年11月7日,笔者亲随墨玉县托胡拉乡几位艺人参加墨玉县城南一家婚礼。其表演实况如下。
第一首:潘吉尕木卡姆木凯迪满 (片段) +赛乃姆 (多次反复) +朱拉 (多次反复) +《木拉几汗》(喀什民歌) +《卡提巴拉汗》(库车民歌) +三首和田民歌+简短的尾曲 (潘吉尕木卡姆木凯迪满片段)。
第二首:纳瓦木卡姆木凯迪满 (片段) +朱拉 (多次反复) +赛乃姆 (多次反复) +达斯坦+乌斯尕 (漂亮之意) +赛依凯斯+麦西热甫 (数目不定) +夏迪阿那+民歌联奏+简短的尾曲 (纳瓦木卡姆木凯迪满片段)。
由上述录音可知,几位艺人并没有按照维吾尔木卡姆的常规结构演奏,而是“摘遍”演出了各部分的一些乐曲,甚至加进了一些民歌作为贯穿而演奏,但整体效果良好,并未给人以不连贯、不和谐的感觉。据木卡姆其吐尔逊·导合代介绍,以上木卡姆表演只是一般的乐曲组合,在不同的场合,他们可以自由地组合乐曲,充分发挥他们的即兴性。据此可见,和田木卡姆在表演和传承木卡姆的乐曲选择上带有极强的即兴性。
(四)演奏的即兴性
音乐家万桐书曾指出:“即兴表演是按某一调式旋律模式,在乐段的起结音,旋律的上、下进行,轴音位置和调式转换的框架中作自由的发挥,节奏比较自由……每个歌唱家或演奏家虽然按这种段式框架表演,但是即兴表演的音乐各不相同。”[4]这在和田十二木卡姆的传承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笔者曾在墨玉县托胡拉乡录音时,亲眼目睹了木卡姆其吐尔逊·托合体击打手鼓时即兴表演的情景,他可以在木卡姆规定的节拍节奏的基础上进行加花变奏。墨玉县芒来乡的艾合买特·艾海提在用纳格拉鼓为木卡姆演唱伴奏时也经常加花变奏,使整个木卡姆表演一直处于热火朝天的氛围之中。可以说,上述实例均体现了木卡姆在传承过程中带有很强的即兴性。
二、直接性特点
和田十二木卡姆传承中的“口传心授”,本质上就是通过“人—人”(由人到人)的直接唱奏来实现传承的一种过程。这种演唱和演奏是传者和承者都在现场直接参与的唱、奏。诚如刘富琳所言:“这种演唱和演奏 (由“人—人”的唱、奏)是即时现场的,传者和承者都直接参与音乐活动的唱、奏,传者以唱、奏来教授音乐,承者也通过唱、奏来习得音乐。”[5]71-77笔者在为伊里奇乡哈克萨家族录音时,也亲眼目睹了7岁孩童买买吐迪学习木卡姆的情景,其学习木卡姆的方法是直接参与到木卡姆的表演中,和家族的其他成员一起唱奏木卡姆,他不但是木卡姆的唱奏的直接参与者,而且也是木卡姆的直接承继者。
“口传心授”和“书写文字”都是人类文化的主要传承方法。人类学家李亦园曾谈到,书写文学是一种单线交通 (one way communication),传者得不到承者的反应,即使有也不能把内容改变。而口语文学则可以说是双线的交通 (two ways communication),作者和传诵者不仅可以随时感受到听者的反应,也可以借助这些反应改变传诵方式与内容。[6]无独有偶,和田十二木卡姆传承的“口传心授”亦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为“口传”,二为“心授”。二者所涉内容和性质有异,前者授技,后者授法;二者所重也不同,前者重摹仿习练,后者重“悟”。这种“口传心授”方式与口语文学异曲同工,我们同样可以把和田木卡姆中的口传心授理解为一种双线的交通,通过口传心授可以“使传、承双方都能够准确洞察和了解双方的心理状态,并根据自身对音乐的理解,缩小相互间的心理距离,使音乐顺利地进行传授”[5]71-77,并且这种“直接”的“口传心授”的传承,也是一种把和田十二木卡姆作为口传文化表达在动作与表演之间的最好方式。克里阳乡巴拉提·艾木都拉等艺人的木卡姆传授过程则将这一直接性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的木卡姆传人多是家族成员,让孩子们自幼跟随他们学习木卡姆,学习方法是直接参与现场表演或由家族长辈直接传授。孩子们正是在这种直接的“双线交通”中体悟到木卡姆的精髓。可以说,和田十二木卡姆的这种双方在场的“人—人”授受关系是互动的,均能够使传承的双方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坚定他们传承的信念。
三、民众性特点
众所周知,任何民众音乐都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中流动地展现的,都有一定的人群参与,从而具备一定的社会性和集体性,维吾尔木卡姆亦莫能外。其不但是民众和文化人心智的结晶,更是该民族人民精神气质的象征。“人民群众是《十二木卡姆》的真正创作者和保存者,而将歌、舞、乐连在一起的民间麦西热甫,则是培育《十二木卡姆》的真正土壤……凡是与人民的艺术生活紧密有关的、被人民喜闻乐见的部分,均被保存了下来;凡是与此相反的,都被遗忘或淘汰了。”[7]由此可见,维吾尔木卡姆的根是深扎在人民大众之中的,它所反映的基本上都是人民大众的心声。和田十二木卡姆主要在人民群众中传承,无论是从学习木卡姆的艺人、参与木卡姆的听众还是传承木卡姆的场合来看,均体现了民众性的特点。
如今和田木卡姆的传承人均为普通农民,他们传承木卡姆的场合亦都是民众踊跃参加的场合。如民间麦西热甫,它是维吾尔木卡姆的主要表演场合和文化生存空间,在民众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艾娣雅·买买提博士说:“麦西热甫是活着的文化传统;深深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历史的麦西热甫是维吾尔人生存历史、生活方式、生命情感、文化模式、民族精神、性格等方面集体记忆的片段式鲜活展现,是维吾尔文化中动态的、现实的、群体共享的草根部分。”[8]维吾尔木卡姆在此种活动中得以传承,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民众性的烙印。2007年12月11日,笔者在皮山县克里阳乡采访,于晚间参加了该乡林业站站长买买提·买东家举办的麦西热甫活动,等各方群众到齐后,麦西热甫就开始了。先是木卡姆木凯迪满的长音拉开了活动的序幕,顿时热闹的场面安静下来,围众者的目光皆聚焦于几位艺人一方,所有人都沉浸在优美的木卡姆乐声中。等到木卡姆进入赛乃姆时,围众者都成双入队地滑入中间的舞场而翩翩起舞。周围不舞者一边品尝着茶几上的美食,一边随着木卡姆的乐声为舞者呐喊助兴。由此,和田十二木卡姆的民众性特点则可见一斑了。
四、濡化特点
濡化,即“表示在特定的文化中个体或群体继承和延续传统的过程”[9]286。此概念由赫斯科维茨(M.J.Hertzkovits)提出,他认为濡化是把人类和其他动物加以区别的学习经验,能使一个人在生命的开始和延续中,借此种经验以获得在该文化中生存的能力。[10]从个体角度讲,人类有别于动物而独有的,即文化的习得与传承——濡化。从群体角度说,濡化是不同族群、不同社会赖以存在和延续的方式和手段,同时也是族群认同过程的标志之一。人们通过代代承继的语言、饮食习惯、人格、信仰、共同祖先和社会经历,认同于某一族群,成为其中之成员,并以此区隔于其他族群。也就是说,族群成员拥有一种族群认同感。[11]和田十二木卡姆的传承场即该地区的民众生存的特殊文化空间,此种空间是乡村礼俗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该地的人们正是在这种艺术的传承中得到精神上的陶冶和身心上的养息。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教化与学习
“教化与学习”主要指个体或群体通过文化上代际传递,建立社会的价值系统,使该社会延续与发展。维吾尔木卡姆将这种“教化与学习”体现得淋漓尽致,此主要体现在家族的传承和传承场的教化上。和田十二木卡姆的学习者主要是家族的成员,他们自幼即聆听家族长辈们的木卡姆唱奏,在长年累月的耳濡目染中,便学会了木卡姆。这种说法与其说是有意的传承,毋宁说是自然的习得,即濡化的结果。传承场是木卡姆表演的主要场合,也是木卡姆传播的摇篮。如和田木卡姆既在孩子出生礼、割礼、成年礼、婚礼等重要人生礼仪上表演,也在麦西热甫、巴扎、大型节日、麻扎朝拜等场合表演。这些场合皆是维吾尔民众纷纷参加的场合,他们不但可以欣赏到木卡姆,还可以在木卡姆的表演中得到教化。因为维吾尔木卡姆博大精深,被誉为维吾尔人生活的百科全书,既有对真挚爱情的热切赞美,亦有对良好道德的极力褒扬;既有对真主安拉的由衷歌颂,也有对人生苦境和生活艰虞的哀叹;既有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无限憧憬,也有对劝人行善之美德的大力弘扬,等等。木卡姆艺人通过他们的木卡姆表演,影响着民众的伦理观念、处世方式和审美情趣。因此人们能够在木卡姆的乐声中得到很好的教化,但这种教化不是刻意学习的结果,而是在参加木卡姆的活动中有意无意地自然习得。
总而言之,有了和田木卡姆这一文化语境,生活于其间的人们在娱乐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本民族文化的塑造,进行着传统文化行为模式与价值观的社会化过程。
(二)文化延续
文化延续是人类社会不同于动物界而特有的延续方式,而濡化表现为个体对于整个群体的文化内化的过程。“人们总是通过与他人展开共同的活动,依照传统或经验形成共同的思维与行为方式,让整个社会的文化按照一定轨迹延续下去。文化延续在其社会过程中的表现既是潜移默化的,也是显而易见的。”[9]287家庭作为人类古老而持久的社会结构,实际上是不同文化群体创造和传承他们文化的最主要的“单位”,也是通过“濡化”进行文化传承的单位,没有家庭,文化传承是不可能进行的。维吾尔木卡姆不是某个人的艺术,而是整个维吾尔族群的艺术。传承木卡姆的家族只是一个“文化单位”,只有他们自己的表演并不能将木卡姆传承下去。只有在家族的传承中,在传承场众人的参与中,在与参与者的交流互动中才能得以延续,这种场合是维吾尔民众踊跃参加的场合,他们都能在参与的过程中得到很好的教化。众所周知,麦西热甫是和田木卡姆的主要传承场,每到木卡姆的乐声响起,参与者皆会手足舞蹈起来,旁边的孩童也会模仿家族成员的舞蹈动作,可以想见,他们也会在不久的将来而成为舞者中的一员。因此,和田木卡姆的表演家族正是在与民众的交流和互动中,不但使自己的表演技艺日臻完善,而且教化了民众,从而保证他们的木卡姆艺术及蕴涵其内的文化内容得到了很好的延续。
五、变异特点
“变异性”和“传承性”是音乐文化流向过程中的一对孪生兄弟。音乐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发展着的文化传统,变异性也是它的典型特征。音乐学家项阳说:“有别于它种艺术形式,音乐艺术以其时空艺术的特性而存在。正是这种特性,人们以为历史上的乐曲很难稳定地保存到现在。即便是保存,也是变异而非其原样。”[12]30“中国音乐文化一直处于一种变化的过程之中,变是必然。”[12]30据此可见,作为时空艺术的音乐艺术的“变”即是必然,但不同类型的音乐引起变异的原因也不尽一样,尤其是中国传统音乐,有着独特的传承方式。
“口传心授”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主要传承方式,因其传承家族或传承人相异而使音乐形态产生变异实属正常。刘富琳说:“‘口传心授’的传承之乐,在实际的演唱和演奏中,表现出对所传之乐的变异和活化。一首民歌、一段唱腔,因不同的人来唱、奏,其曲调也各有差异。就是同一首民歌,同一段唱腔,同一人唱、奏,因不同的时间、地点,不同的唱奏情景,每次的唱奏也有所不同。口传心授把音乐从甲传到乙,再从乙传到丙……每次的传承,传承者都或多或少地根据个人的审美情趣,发挥出各自的创造性,进行了加工变化,曲调在传承中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相反,如果要求每个传承者在‘口传心授’的传承过程中,把曲调原原本本的保持固定不变的状态而继承下来的话,那么,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传承中的变化是必然的。”[5]74刘先生意在指出任何音乐在传承过程中一成不变是不可能的,皆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变化——变异。维吾尔木卡姆包括和田十二木卡姆皆属于中国传统音乐的范畴,其在传承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变异现象。这在和田十二木卡姆音乐形态特别是结构方面表现得尤为显著。据研究,和田十二木卡姆不像喀什版十二木卡姆的结构那般三大部分 (琼乃额曼、达斯坦和麦西热甫)俱存,且各部分也没有那么的庞大和完整,有的仅是规范版的些许片段。据了解,和田十二木卡姆的麦西热甫部分主要在墨玉县的芒来乡、奎牙乡与和田市的伊里奇乡流传,琼乃额曼部分仅在墨玉县的托胡拉乡流传,达斯坦部分只有皮山县的克里阳乡存在一些片段。通过比较发现,和田十二木卡姆因各地演唱部分、师承状况、演唱习惯等因素相异,流传于各地的木卡姆在唱词、结构、乐队组合、伴奏乐器等方面表现出不尽一致的面貌。就唱词而言,笔者通过录音发现,芒来乡、奎牙乡和伊里奇乡的艺人演唱同套木卡姆的木凯迪曼和麦西热甫乐曲时的唱词不尽相同。譬如,芒来乡艾海依提·司马义等艺人演唱的且比亚特木卡姆的木凯迪满部分长达8分26秒,但奎牙乡托乎提·买买提·斯迪克家族艺人演唱同套木卡姆的木凯迪满则仅有3分5秒。同套木卡姆的唱词风格也有不尽一致的情况,芒来乡木卡姆唱词相对雍容和高雅,奎牙乡的木卡姆唱词却相对通俗易懂。就每套木卡姆的结构而言,流传于芒来乡、奎牙乡的十二木卡姆中麦西热甫部分所包含的乐曲数目 (即使是同套同部分)大多皆不相同,一般在4—8首乐曲不等;流传于托胡拉乡的各套木卡姆埃尔乃额满部分所包含的乐曲数目也在传承的过程中因传承人、表演场合等不同而发生的相当程度的变化,有的甚至出现乐曲次序颠倒的情况。就伴奏乐器而言,流传于和田不同乡镇的十二木卡姆的伴奏乐器也因表演艺人之相继去世和传承师傅的不同而呈现出乐器种类、乐器数量正处于锐减的状况,很多传统的伴奏乐器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就乐队编制而言,各乡镇的十二木卡姆的乐队组合因传统惯制随时代变迁和乐器数量、种类的减少也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变异现象,正向小型化、单一化的趋势迈进。
由此可见,和田十二木卡姆在传承的过程中,其唱词、结构、伴奏乐器、乐队组合等方面皆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
六、结 语
综上所观,和田十二木卡姆的传承具有即兴性、直接性、民众性、濡化、变异性等几大特点。其中之即兴性特点既是民间木卡姆们其们在传承、表演木卡姆的过程中尽情抒发情感和尽兴炫技的有效手段,也是造成和田十二木卡姆在传承的过程中产生变异的直接动因;直接性特点是和田十二木卡姆的传承人进行木卡姆技艺传承的最便捷的方式;民众性特点是其根本特点,在民众的这种氛围中,它已经成为家族人身份认同和全族人文化认同的习俗惯制;其濡化特点更是成为维吾尔人传承和学习本族伦理道德、人情事往等传统文化知识的重要渠道。这些特点构成了和田十二木卡姆之传承的独特面貌。本文仅仅是对田野调查中肉眼能够看得到、触觉能够感觉得到的和田十二木卡姆之传承特点的初步探讨,有关其音乐形态乃至其与文化背景之间关系等深层次的问题,还值得我们留待来日进行深入的探究。
[1]陈其射.论高师音乐教学与民族音乐传授[J].人民音乐,2000(4):29-32.
[2]周吉.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的传承现状及对策[J].新疆社会科学,2007(3):67.
[3]周吉.新世纪维吾尔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J].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7(2):1.
[4]万桐书.“木卡姆”概念 [J].中国音乐学,1993(4):14-20.
[5]刘富琳.中国传统音乐“口传心授”的传承特征 [J].音乐研究,1999(2).
[6]陈明.湖南祁剧传承的考察与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06.
[7]阿不都秀库尔·穆罕默德伊明.论维吾尔古典音乐《十二木卡姆》 [M].杨金祥,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49.
[8]“第六届国际木卡姆研讨会”中方筹备组.第六届国际木卡姆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160.
[9]庄孔韶.人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0] M.J.Hertzkovits.Man and his work[M] .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1948:127.
[11] Gary Ferraro.Cultural Anthropology:An Applied Perspective,4th edition,Belmont[M] .CA:Wadsword Thomson Learning,2001:291.
[12]项阳.中国音乐民间传承变与不变的思考:当传统遭遇现代[C].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Analysis on the Inheritance Characteristics of Twelve M aqum in Hotan Prefecture
WANG Jian-chao
Based on the fieldwork,the paper applies both fieldwork data and literature materials to explain and analyze the inheritance characteristics of twelve Maqum in Hotan prefecture,including improvisation,directness,amass character,Confucianism,variability and so on.
Hotan prefecture;twelve Maqum;inheritance characteristics
J632
A
1672-2795(2011)01-0022-06
2010-09-17
王建朝 (1979— ),男,河南濮阳人,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民族音乐学研究。(乌鲁木齐830054)
* 本文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校科研计划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新疆和田地区《十二木卡姆》的调查研究” (项目编号:XJEDU2008I22)和新疆师范大学优秀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族吹管乐器巴拉满调查研究” (项目编号:XJNU0915)。
——以新疆莎车县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