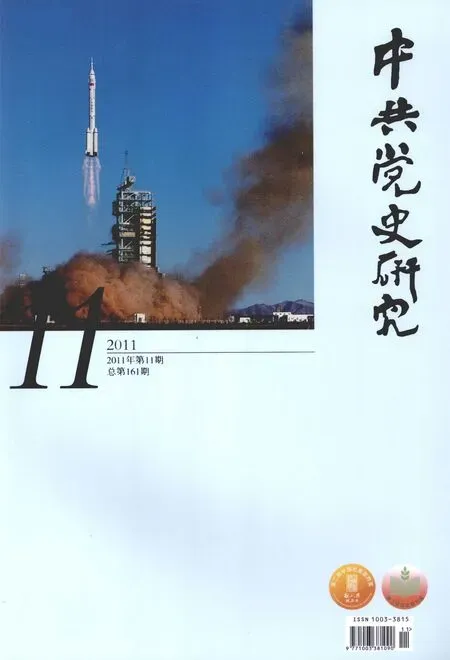财富与剥削在苏维埃革命划分阶级中的演变及启示——以中央苏区为例
杨丽琼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创造及阶级剥削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与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时至今日,中共领导的革命与改革实践,已经走过了90多年的历程,其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苏维埃革命,则是这近百年历程中,中共早期应用这一理论推进经济社会改革的重要阶段。以苏维埃革命时代的中央苏区革命而论,应用价值创造及阶级剥削理论的改革实践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以财富多寡来论阶级剥削,并推行共产平分财富的政策;继而以革命前是否“劳动”与形成“剥削关系”来区别阶级剥削,注意保护中下层劳动者的财富;最后将创造财富中的“劳动”及其“剥削关系”计量化,进一步保障此前土地革命中受到打击的中农、贫农劳动者的财产。它既体现了幼年时期中共理论探索的勇气与理论认识的水平及其经验教训,也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及其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脚步。然而,以对苏维埃革命及其改革的研究来看,学术界至今仍然没有涉及这方面的研究,它导致苏维埃时代的变革与当前改革发展的研究无法形成历史逻辑的对接,影响历史经验教训的准确总结与执政思维的及时转变。
一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研究一般商品价值入手,探究资本主义大工业化生产中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他首先将劳动区分为生产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生产商品交换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进一步又把生产商品的劳动的具体形式加以抽象和把生产商品的劳动的复杂性加以简化,以简化的抽象劳动 (它经由商品交换的劳动才具有价值)作为价值的计量单位,得出抽象劳动(“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即“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的耗费”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57页。)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使用“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论说工业化大生产的剩余价值源泉,揭示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秘密;提出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财富充分富足的情况下“消灭私有制”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87页。在这里,马克思还强调:“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消灭“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的私有制。,消灭阶级剥削,建立一个土地等生产资料全社会公有和没有商品货币及市场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
无疑,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人类经济学说史上一部不朽的著作,为人类探讨构建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然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央苏区,即赣南闽西地区开始推动的中国经济社会变革实践中,当年的改革者在具体应用价值创造和剩余价值学说时,形成了三个解读:第一,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的“抽象劳动”,简化成了只有体力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比如:1929年,中共六大的决议认为:“有钱的 (高利贷者)有地的 (地主)有货的 (商人)都是同一批人,他们用三种方法同时并进的剥削农民,有钱的是在变成有地的、是在变成有货的 (收集农民的劳动产品)、甚至变成‘占有农民的’”;富农一方面雇工剥削农民,同时又出租土地,经营商业和高利贷盘剥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史组编: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8—230页。。在这里,经商也成了“阶级剥削”④这一认识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解放社1949年7月单行本)中也有明确体现。,并认定“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成为反革命动力”和“最主要敌人”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6页。。这样,家庭农场管理、工商业经营、要素经营的管理等,统统都成了“剥削”,经营管理性的活劳动均被排除在价值与财富创造之外。第二,忽视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现有的土地及货币都具有物化了的活劳动属性,并在新的生产过程中继续转移价值或剩余价值。然而,当时几乎所有的文件决议均简单将地租与借贷利息的获得统统划归“不劳而获”的“封建剥削”;那些出租部分土地同时自己也耕种土地的人,则定为“半地主性的富农”剥削阶级;即使不出租土地的也不雇用他人,单以自己劳动耕种,但土地劳力兼备,每年有余粮出卖或出借的则称之为“初期性”剥削的富农,导致家庭财产较多也进入剥削阶级的视野⑥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史组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397—398页。相关资料在毛泽东的《寻乌调查》(1930年6月)和《兴国调查》(1930年10月)中也多有体现。。第三,没有充分考虑马克思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建构的前提条件与社会环境,急于动摇农民的私有财产观和通过全面重新平分土地、构建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①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史组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365—366、405页。,并把生产资料的范围向农民家庭的房屋、现金、粮食等生活资料扩大,以至于当年还准备搞苏联式的集体农庄生产②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史组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05—407页。。
循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早期认识和中共农村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价值创造及阶级剥削理论便在中央苏区这样的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完全意义上的初期实践。在苏区的阶级斗争中,体力劳动无形中成了价值或财富创造的唯一源泉,致使体力劳动之外得来的财富就成了“阶级剥削”。对于工商业者,则自革命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应被剥夺财富的“剥削者”,排除出革命政权之外,成为革命的对象。1927年4月,中共五大便提出中国革命已经走到了“需要建立一个工农阶级的民权独裁制”阶段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选编》,第143页。;随着当年9月中央确认建立苏维埃政权目标之后,苏维埃政权便确定为“工农民权独裁性质的政权”④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史组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199页。,到中共六大时又进一步提出:工商业“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成为反革命动力,正是我们争取群众的最主要敌人”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选编》,第346页。;并指出,“商品经济不消灭,被剥削的农民群众永远得不到完全解放”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史组编: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242页。。所以,工商业者不仅没有政治权利,在经济上更是应该被剥夺的“剥削阶级”。在1930年前后的中央苏区农村,“平田有多的”、“放债的 (不管多少,不管他有无借债)”、“较富裕的”定为富农,“无条件的没收……全家财产”⑦江西省档案馆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5页。;“有余粮剩米放债”的就是富农剥削阶级,“够食不欠债”的为中农、“不够食欠债”的是贫农⑧《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5页。;那些比较富裕的自耕农或中农“全部出产都是亲自劳动而不是剥削他人来的……他们有钱余剩,他们有多余的土地。他们在自己的农产物上面加工,如使谷子变成米子,自己挑出去卖。他们还做些小的囤买囤卖生意。他们供养猪子、猪条子或大肉猪。以上这些都与半地主性的富农一致”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31页。。这样,农民参与市场获取的商业收入、经营管理土地、运作资金以及善于经营家庭养殖的收入等等,都成了“剥削收入”的来源,获得更多收入的农民就成了阶级革命的对象。于是,在整个中央苏区内,到处便是平田、平谷、平 (毁)债10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史组编: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02、407页。、 “分房屋”、 “向富裕之家写款子” 、挖浮财的“共产”与均分财富的局面,全面动摇民众的私有财富及财产权,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也实行苏维埃政府公有;于是, “一个‘平’字,体现了没收与分配两种意义”12《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72页。。当年中央苏区盛传一首苏维埃政府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的歌谣,其中的歌词是:“万富欠我钱,千富不管闲,不富跟我走,每月八块钱。”“万富”指的是“地富阶级”,“千富”是指“富裕中农”和中农;“闲”是方言,相当于“他”, “不管闲”即“不要管他”; “不富”在当地方言中读“bǎi fù”,与“百富”同音;“跟我走”就是跟我去参加红军,“每月八块钱”是指红军每月有八块钱的伙食钱。这首在当地流传甚广的歌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阶级革命政策的实况:中央苏区时代的阶级分野,最深入人心的一个标准就是财富多寡。
综合1928年夏到1930年底这两年多的情况,中央苏区已经在划分剥削与剥削阶级的实践中,初步提出了区别阶级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与划分标准。然而,因为战争的频繁与苏区管辖地区随时变动,根据地极其不稳定,其财产政策实行的就是人人平均分配,农村土地则是在“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基础上的平均分配。应该说,这种均分的粗线政策标准确实是简便易行,而且也适应当年的特殊战争环境,所以,苏区内实际还未严格认真地以经济地位来真正区分阶级与阶级剥削,而“主要是从表面生活、从政治势力”来划分阶级①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1页。。于是,苏区这场颠覆性的初步实践,实际无形中已经异化为根据占有财富的多寡来区别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其存在的问题是十分明显的:如它不仅把土地出租者、债务借贷者、工商业生产与经营管理者甚至脑力劳动者定性为“剥削者”,而且还把自己劳动或主要自己劳动,同时又出借点小债的中农和富裕中农也划入“富农剥削者”,甚至把因劳动力强壮或劳力多而致富的家庭划为“剥削阶级”;进而将出租土地、雇工耕田的农民都称之为剥削别人劳动的“剥削阶级”。结果,一些老弱病残、鳏寡孤独因无劳力而不得不将土地出租与雇工耕种的人,结果都成了“剥削阶级”;同时,当时各地斗争反复,土地分配多次进行,划分富农又没有时间规定,所以在实际斗争中就出现把土地革命后改变了贫困面貌的一部分贫农、中农也作为富裕分子划入“富农”的剥削阶级圈子,当做“富农”加以打击,导致中农、贫农“同样发生恐慌”②《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29页;另参见《永定县苏区关于土地问题草案》(1930年),《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86—488页等。;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土地作为苏区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在全部收归政府重新加以均分之后,直接宣布归苏维埃政府公有,实际已经是平均主义的平分财富与共产公有的空想社会的初步实验。总之,不正确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经济关系认定,大大影响了中农以至贫农的生产积极性与对革命的正确认识,在当年的革命和土地改革实践中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二
中央苏区前期社会改革的全面平分财产财级革命视野相矛盾,被认为是一种非阶级的观点。这一时期,革命行进在平分财富与追求共产之间。以乡村为主的苏区社会,为了达到土地的真正平均分配,结果,“分田无论如何要分几次”③《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76页。,一次分不平而有意见,接着又分二三次,反复进行平分;一些地方一年二熟的农地,竟然一年分三四次④参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64—267页。。同时,依靠苏区传统民间借贷制度出借的债务,也不问具体情况,“一概废债”、“一概不还”⑤《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9—220页。,而依靠出租土地所获得的收入也被认定为“地主阶级封建剥削”,其财产列入全部没收之列。于是,一般农民的反应,就从认真分地发展到不要地,以致出现大量“荒地”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68页。;过去农村普遍的现金与实物借贷和土地租佃,现在则出现闭借、惜借和土地租佃耕种的停止⑦《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80页。,一些孤寡、病残、老人和无劳力的贫苦农民,一时陷入生活无着境地。
1931年1月,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通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针对中央苏区农村经济社会革命存在的上述问题,不是批评中央苏区前期的平均主义,而是从阶级革命立场出发,严厉批评原来中央苏区给一切人平均分配田地与财产属于“非阶级的路线”⑧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603。他们强化阶级革命意识与阶级分野,提出苏区的财产制度应该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要求这一有区别的阶级财富或财产政策,不仅要在新开辟的苏区执行,而且应该在已经过反复分配了土地的老苏区贯彻执行,重新进行土地及其他财富的分配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560页。。
这一政策与原先中央苏区实行的人人平均分配政策相比,其最大不同是,不仅地主不能分田,富农只能分坏田,而且那些被错划阶级成分的苏区民众,其现实生活与生存受到极大影响。所以,在要求准确划分苏区民众的阶级成分方面,王明“左”倾领导人显得更加重视与关注。自1931年春开始,他们多次指出了中央苏区党此前以财富多寡划分阶级成分,是没有认真、严格进行农村阶级划分,以致严重损害中农利益的错误②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602—603页。。因此,在1931年春夏以后的中央苏区,如何正确地划分各人的阶级成分,特别是认定有剥削的地主、富农阶级的成分和接近富农的中农阶级的成分,也就成为苏区土地分配中最为迫切的问题。
根据中共中央的上述精神,苏区中央局首先在1931年2月发出《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的第九号通告,批评过去中央苏区关于阶级剥削的认定存在的严重问题,错误地将“财产的多寡”作为构成富农及其阶级剥削的条件,进而把根本不剥削别人,“只用自己劳动谋得生活上稍优裕的富裕中农认作富农”,把“从封建剥削中解放出来的富裕农民”作为初期性富农阶级;打击地主、富农打击到了许多中农甚至贫农身上;要求苏区党立即改正以往这种错误做法,提出要从“剥削关系来决定”与“认识”阶级与阶级剥削问题③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98页。。同时,《通告》号召全党同志,认真而广泛地开展农村社会调查,特别注意地主与富农、富农与中农成分的分析,以制定一个准确的农村阶级成分划分标准。随后,毛泽东在4月2日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写的《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进一步强调指出:阶级剥削和分析阶级成分“特别要说清楚,剥削阶级的标准要以其剥削为他收入的相当部分,那些少量放帐或借帐的人还是列入中农”④《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2—13页。。到这时,剥削阶级的标准要由“剥削关系来决定”,剥削要占其收入的“相当部分”来决定;而且要将“少量剥削”的人划入非剥削阶级的中农。尽管这些认识还是一个笼统的初步概念,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价值创造及阶级剥削关系认识的进步。
为了准确地分析中央苏区的阶级与阶级剥削问题,认清决定剥削阶级的“剥削关系”与实质,以实行不同阶级的财产、财富政策,苏区改革主导者在实践中的探索进一步深化。其中,主要有苏区中央局1931年8月21日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中共苏区中央宣传部1932年初编写的《土地问题》和毛泽东1933年6月写的《怎样分析阶级》,等等。在这些材料中,认识进一步深化:在剥削阶级的标准认定上,具体提出了“出租部分比自己土地多”;在剥削与否的认定上,使用了“经常生活”、“经常收入”、“主要地位”⑤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560、650、704页。、“经常剥削”与“轻微剥削”加以区别;还提出“附带劳动”来说明地主与富农的劳动与不劳动,用“临时雇工也可以算作中农”,以与富农相区别⑥毛泽东:《怎样分析阶级》(1933年10月),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112、113页。。另外,明确构成阶级成分的时间要以“革命前”的状况为标准⑦参见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560页。,以增强阶级成分划分的准确性。
照此行事,中央苏区内按照“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实施,那便是立足于特别保护中下层民众的土地财产及其财富。它从前期的“分配土地给乡村中一切男女”这种“非阶级的路线”转变过来,首先就是收回地主豪绅及其家属的土地,“凡是革命前据有土地自己不劳动”而出租的人,“不问其据有土地的多少”都是“地主阶级”,“他们的土地、财产、森林及其家产、家具都应该完全没收”;“富农已分得的土地,应当交出来重新分配,好田应当转分给雇农、贫农、中农,而把他们的坏田调给富农,而且即使是这种坏田”,也“只有富农自己去耕种才分给他”;同时,“被没收者根本不能再分得任何土地,也不能据有其原有房屋的一部分,田中的稻禾以及已经收获的谷子也都没收,一部分要分给农民,一部分归政府以救济被难的群众”;被没收者如要生活,那只允许去“开垦或做苦工”①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562 页。。
由此可见,自1931年初到查田运动前期的两年多时间内,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财富创造与阶级剥削、阶级成分方面有了许多深化的新认识。但是,这段时间的划分标准,因缺乏具体的量的规定而难以准确操作。比如:什么叫“劳动”,什么又叫“不劳动”或“附带劳动”;什么是“经常剥削”,什么才是“轻微剥削”;剥削多少才算占其收入的“主要地位”;“革命前”又“前”到什么时候等等。由于没有这些数量和时间的界限,实际执行起来,就仍然难以把握分寸。同时,苏区长期形成的以农为本、农工商结合的传统经济生活中,民众的生产生活构成了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的多元生产体系:第一,一般农民尤其是贫困者也出租土地②贫困者也出租土地的现象,苏区各地也十分普遍;毛泽东所作的赣西南调查中有专门的记述。参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75、280—281页。;第二,农忙时的普通农民之间也普遍相互雇用短工③农民普遍雇用临时日工、短工的情况在苏区各地都有,毛泽东在兴国调查访问的八位贫农中,就有六位每年都要雇用不同数量的临时工或短工。;第三,农民相互间实物与现金借贷,更是苏区农民相互帮助的互助行为④温锐:《民间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20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 《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四,挑担打工做苦力以及做小本生意等兼业则是农民农户的重要谋生、特别是致富之路⑤《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8—51、208—210页。。因此,如笼统地仅以租佃土地、雇用劳力、借贷债务和做生意与否来区分阶级剥削与剥削阶级,进而用于处置社会财富,显然也是十分困难的事。
因为缺乏对实际劳动的具体判断标准,在当时的财富与剥削关系认识的影响下,中央苏区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以下现象:凡是剥削一个雇农以上的农民都是富农,有土地租佃的都是封建地主6《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8—51、208—210页。,甚至仍然把中农、富农的区别解释成“多些钱”或“少些钱”7《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8—51、208—210页。;在“剥削”这个名词的内涵中则把做买卖、加工农副产品等正常的商品经济活动也包括进去了8《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8—51、208—210页。。查田运动开始后,尽管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审慎决定那些介在中农与富农之间的疑似成分,不使弄错”9《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8—51、208—210页。,但在查田运动前期中央苏区内掀起的“查阶级”热潮中,阶级划分问题争议迭起,加上各地具体工作中搞争相竞赛,评比阶级斗争的先进与“模范”,很多地方仍然把中农和富裕中农划为富农、地主而加以打击,有些是把“仅仅放几百毫子债,请过个把长工,或收过几担租谷,而绝大部分是靠自己劳动过活的中农,当富农打了”;有些甚至“完全没有剥削别人,仅仅是多有几十担山田,生活比较富裕的中农,也当富农打了”,有的地方“把稍微放点债、收点租,而且大部分靠出卖劳动力为一家生活来源的工人当地主打了”10《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8—51、208—210页。。同时,又因中央苏区内基本是宗亲为主的乡邻社区,地方干部与群众为抵制“左”倾土地政策,许多地方给地富分子也分了一份土地,并隐瞒了部分地富分子的真实阶级成分,而当作中农、贫农处理。于是,这加剧了查田运动前期弄错阶级成分的问题,严重搞乱了革命的阶级阵线,使“左”倾土地政策更多地打击到了中农、贫农身上。以江西赣南的胜利县为例,查田运动前期及查田运动以前所划地主、富农成分为3124家,竟有1512户有争议或弄错成分①,导致了苏区内部的混乱与恐慌。于是,反对阶级剥削与重新分配财富的变革,实际仍然重复着1931年以前打击到中农与贫苦农民的许多错误,并成为需要亟待纠正的问题。
三
针对中央苏区查田运动前期在财富处置、阶级划分等方面出现的混乱与错误,中共中央1933年9月8日发布了《关于查田运动的第二个决议》,指出查田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弄错阶级成分,搞乱阶级阵线,“责成”中央政府党团和各级省委“切实检查”查田运动,“纠正所有错误”。这个《决议》还搜集许多实际例子来说明分析阶级与阶级剥削的正确方法,用以“指导其它各县”,并提出对个别地主出身而坚决参加革命斗争的红军,其家属的土地财产要以“特别条例规定”。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703—704页。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毛泽东为首的苏区政府,很快根据查田运动前期阶级与阶级剥削分析出现的严重问题,制定了《关于土地革命斗争一些问题的决定》,并于10月10日将它与6月制定的《怎样分析阶级》一起正式发表。
《关于土地革命斗争一些问题的决定》在肯定了苏区之前以“剥削关系”分析与决定阶级剥削的正确认识与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三个深化的认识成果:第一,以“劳动与不劳动”或“附带劳动”作为区别地富的主要标志,并对附带劳动作了详细说明,规定一个家庭中劳动的标准人数为1人,如全家有数人,其中1人劳动,这家即算有劳动;劳动的标准时间为全年的1/3,即4个月,以从事主要劳动满4个月作为劳动和附带劳动的分界线 (即地主与富农的分界线);主要劳动是指从事生产中主要工作部门的劳动,如犁田、莳田、割禾等,砍柴、挑担等重要劳动也包括在内;帮助耘禾、种菜、看牛等则是非主要劳动。第二,对区别富农与富裕中农的“经常剥削”与“轻微剥削”的标准界限,规定其剥削收入要占其全家年收入的15%,特殊情况 (指家庭人口多,劳力少,生活并不丰裕,或因天灾人祸反而转向困难者)不超过30%,不超过这个线为“轻微剥削”,否则就是“经常剥削”。第三,对构成阶级的时间起点界定,规定在利用上述标准分析阶级成分时,构成剥削分量的时间是以当地革命的时间为起点,连续上推3年,不能是其他什么时候,也不能是间断的或少于3年。③参见江西省档案馆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10—529页。
可见,这些规定对区别地主、富农的“劳动”与“不劳动”或“附带劳动”,区别富农与中农的“经常剥削”与“少量剥削”或“轻微剥削”,既给予了时间的规定,又给予了明确的数量限制。显然,这是针对查田运动前期出现的问题,又一次深化了对财富创造、阶级剥削和阶级成分划分的认识。至此,虽然生产管理、要素经营及其他经济领域的脑力劳动仍然没有被列入劳动的范畴,但苏区党对农村各阶级的分析已构建起了比较好把握的量化标准(尽管这时的苏区已经进入去留的最后关头)。按照这个量化标准,把大都兼有土地出租、高利贷和雇工剥削而又自己参加劳动的富农从地主圈子中划了出来;也把有少量剥削的富裕中农从富农圈子中划了出来;同时,还把因破产而已经是自己参加劳动、自食其力的破产地富从地主、富农圈子中划出来了;把曾经有过地主、富农剥削,但这种剥削是间断的或革命前非连续3年的农民,从地主、富农圈子中区别出来了。同时,《关于土地革命斗争一些问题的决定》还对参加红军的地主、富农及其家属作特别规定,并合情合理地考虑到天灾人祸、家庭中人口、生活状况等特殊条件。这样,阶级划分标准因有了量化的规定而具有明确的界限,更易掌握,更具有操作性。
《关于土地革命斗争一些问题的决定》还明确规定,此前各地处置的阶级成分,有不合本决定者,应即依据本决定“立即改正”,重新解决好错误处置的财富①江西省档案馆等编: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514页。。据此,中央苏区在新老苏区对以前处置的阶级成分进行复查,对弄错的阶级成分进行坚决纠正。胜利、于都、博生等县大量被弄错的阶级成分被改正过来,仅胜利一县就改变了1512家的成分②参见高自立:《继续查田运动的初步检查》,《红色中华》1934年5月7日。。至此,中央苏区内搞错的阶级成分,尤其是以体力劳动获得收入的中农、贫农及其他贫苦农民的阶级成分基本得以改正,他们在革命中被没收的土地财产及其他财富也在实践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
总之,在这一时期,以1933年10月《关于土地革命斗争一些问题的决定》为标志,中央苏区在土地革命中已经形成了一套具有操作性的、较为准确的阶级与阶级剥削分析与划分的标准,体现了中共努力探索社会改革的新成果。在这个问题上,即便当年推行“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他们的认识水平也是随全党的认识深化而提高的。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们的错误是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与此前贯彻按人口平分土地的政策相比,他们对地富分子不注意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犯有极左错误;与此同时,他们特别注重农村阶级的正确分析,进而主观上注意了保护中农利益,使其不受侵犯。应该承认,在土地革命初期,具体是1931年春以前,中央苏区普遍实行按人口平分一切土地办法,因而当时的苏区党没有对农村阶级的划分给以足够的重视,造成土地革命中平均财产政策侵犯了部分中农群众的利益。着重“阶级立场”的土地政策推行以后,要分配土地就必须先划分成分,客观上反而促进了苏区党对农村阶级划分的进一步重视,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对农村阶级与阶级剥削分析及阶级划分标准操作性、可靠性的不断提升,缩小了革命与改革中的打击面,大大减轻了土地革命对中农甚至贫农财富的冲击。
四
在中央苏区短短数年的苏维埃革命中,中共通过价值创造及阶级剥削理论在革命中的应用,走过了重要的早期实践与认识过程:先是以财富多寡来论阶级剥削,并推行共产平分财富的政策;继而以革命前是否“劳动”与形成“剥削关系”来区别阶级剥削,注意保护中下层劳动者的财富;最后将创造财富中的“劳动”及其“剥削关系”计量化,进一步保障此前土地革命中受到打击的中农、贫农劳动者的财产。这一发展演变过程,清晰展示了中共在早期阶级革命实践中的认识进程、勇于探索的勇气与历史脚步。然而,仅就苏维埃时代而言,这一时期对价值创造与剥削理论的认识与实践,仍然存在三大日后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在认识阶级剥削与处置社会财富时,农民的一些具体劳动没有得到尊重而没被划入劳动的范畴。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人类劳动可区分为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一般劳动,或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其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或“抽象劳动”是创造商品交换价值的源泉,而“社会一般劳动”和“具体劳动”,则是广义上的商品使用价值的源泉之一。然而,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相比较,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对于一般民众生产生活则更为具体与实际。但是,它在苏维埃革命者的这一时期认识中,却没得到应有关注。包括耘禾、种菜、锄草、下肥等农业生产中的田间管理等劳动,家务以及赶集等非农业劳动也都没有得到应有尊重而没被划入劳动的范畴。这将影响对社会财富保障的公正合理性。
第二,主要体现为脑力劳动的工商业经营、生产要素的经营管理等被排除于劳动属性之外。马克思在《资本论》分析抽象劳动创造价值时,包括了“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即“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的耗费”,其内容是多元的,手工作坊及其厂矿、商业的管理、土地出租与金融借贷及雇用农耕等要素管理,以及知识分子脑力劳动等等,均包括其中。但是,在苏维埃阶级革命的视野中,工商业者一开始就列入“剥削阶级”的行列,是阶级革命的财富剥夺与打击的对象。在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里规定:“剥削他人的劳动力者”、“靠土地、资本的盈利为生”,“商人资本家的代理人、中间及买办”等作为剥削阶级,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①江西省档案馆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131页。等政治权利。1933年,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议》中,虽有了不没收“商业及与商业相连的店铺、住房、财产等”的规定,但同时认为:“不剥削店员的小本经商者”和“自作自卖的小工业生产者”才“算独立生产者”; “自己负指挥生产之责”,即为“自己不劳动者……仍照地主待遇”②江西省档案馆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521、511页。,与封建地主同为“剥削者”,应拒之于“政权之外”,“剥夺其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③江西省档案馆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310—311页。,剥夺其财富及资产。在苏区广大农村,租佃是“剥削”、借贷利息是“剥削”、雇工并参与共同生产是“剥削”、经商投机倒把是“剥削”。这种对剥削与被剥削的理解,便一度简单地体现为家中财富的多寡,财富多、赚钱多者就是“剥削者”,就是革命的对象,而不论导致富裕与贫穷的具体原因。1933年10月后,通过阶级成分划分标准的量化,把适应农民多元经营的体力劳动者解放出来了,但此时及其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主要体现脑力劳动的城乡工商业经营、生产要素的经营管理等,构成传统乡村经济的工商业者、地主 (实际上有一部分是富农)、富农 (大多数是自耕农)等的劳动,仍然被排除于劳动属性与财富创造者之外,被视为“剥削阶级”;发展至极端,便是后来的生产资料单一公有制的全面建立,立足达到人人收入的平均化,以至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长途贩运与个人从事商业营运也成了“投机倒把”的阶级敌人行为,《刑法》还专设有“投机倒把”罪④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年)。关于“投机倒把罪”曾通行于集体化时代的人民公社管理条例,直到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才得以谢幕。,其财富与财产权也在剥夺之列。这显然是不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与劳动创造财富理论本意的。
第三,立足在生产经营领域解决民众收入上的财富平等问题。在现代经济学中,解决市场经济竞争机制中可能出现不公平、不公正(或阶层差别)问题的思路,不是立足消灭经济领域中具体劳动者的机会收入、风险收入,以及人的体力、脑力差别等等导致的差别,追求经济领域中具体劳动者收入的平均化,而是通过国家层面税收的二次分配、货币政策、最低工资标准、公共产品提供和其他政府调节手段,来解决经济领域市场竞争导致的差别与不公平问题。然而,出于对美好理想社会的急切追求,苏维埃时代对于价值创造及剥削理论的实践,是立足毕其功于一役,追求在社会经济生产领域一次性解决社会差别与平等公平问题。
目前,历经长期的学术研究与反复的实践检验,学界关于价值创造及剥削关系在学理研究中尽管仍存在诸多分歧,但它应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科学技术、信息等诸多要素则已经具有共识。然而,目前史学界关于近百年社会财产制度改革史的研究,至今则仍然停留于传统的价值创造和剥削理论之中,不仅无法对近百年中国社会变革进程给予具有说服力的准确解释,而且还继续影响着今天民众对价值与财富创造和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认识的清理,进而也仍然影响当前农地及其财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化与和谐社会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