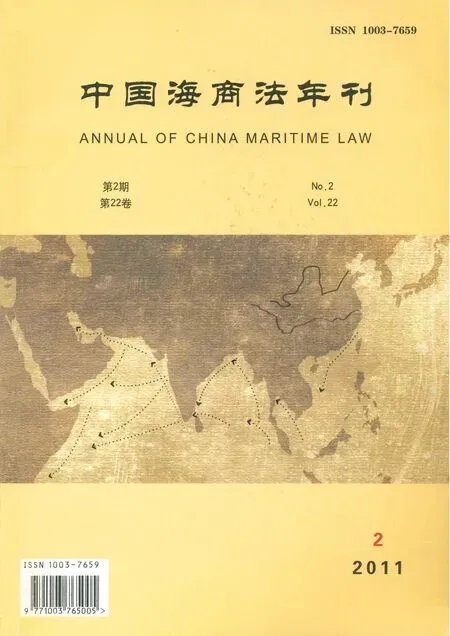2010年香港海商法判例综述*
赵 亮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香港 999077)
2010年,香港高等法院原诉法庭和上诉法庭审理了一定数量的海商海事案件,其中不乏新类型案件。在合同相对性法律问题方面,再保险人由于不符合该原则而不具有诉讼资格。在海上保险问题方面,虽然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但由于载货船舶不符合船级要求,被保险人没有履行及时告知义务而丧失索赔的权利。
由于“华天龙”轮的扣押,引发香港官方法律程序及豁免的争议,涉及中央政府及其财产在香港法院的豁免权利问题。在香港和内地法院之间管辖冲突问题上,香港法院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决定管辖法院的恰当性。对于仲裁的态度,香港法院秉承普通法的一贯作风,继续肯定和支持仲裁裁决的效力,避免了仲裁后诉讼导致的司法滥用。
一、合同相对性
(一)基本案情
船东Great Power是塞浦路斯注册公司,涉案船舶由保险人承保后再分保。1998年7月,涉案船舶承运一批大豆粉。船舶由于主机机械故障,货物迟延到达目的地,卸货时发现货物受损,船舶因此在香港被扣押,再保险人为货主出具保函后船舶被释放。在保函中,再保险人称其已经获得船东的不可撤销的授权,委派律师并出具该保函。再保险人于2002年4月22日委派律师开始法律程序。在诉讼过程中,再保险人接受保险人的指示。直到2008年,再保险人获知,Great Power公司于2002年1月18日被注销。2009年初,货主在塞浦路斯地方法院申请恢复Great Power公司的注册,该法院于2009年1月26日批准该申请。随后,货主向香港法院申请撤销再保险人递交的法律文件,因为Great Power公司在此之前已经注销,再保险人不可能获得授权。Reyes法官批准了货主的请求,并做出有利于货主的缺席判决。2009年8月3日,再保险人申请撤销该判决,并以Great Power公司代理人或第三人的身份进行抗辩。(the“Blue Bridge”案,HCAJ136/1999:[2010]2 HKLRD 285)
(二)法院审理
香港法院Reyes法官要解决的问题是,再保险人是否恰当地获得了授权代表Great Power公司参加法庭程序;如果没有获得授权,再保险人是否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如果可以参加诉讼(无论是以代理人还是第三人的身份),是否批准撤销之前有利于货主的缺席判决。
首先,Reyes法官认为,再保险人没有直接获得Great Power公司的授权。事实的关系是,保险人是Great Power公司的代理人,再保险人是保险人的代理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privity of contract),再保险人不能当然地成为Great Power公司的代理人,除非Great Power公司在给保险人的授权书中表明,保险人可以指定其他人作为Great Power公司的代理人,但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的授权。Reyes法官认为,仅仅因为保险人和再保险人的再保险关系,不能打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即使再保险人提供了保函,仍然不能认为Great Power公司和再保险人直接有合同关系,从而得出后者是前者的代理人的结论。(HCAJ 136/1999:第19段至第22段)
其次,因为再保险人提供了保函,除非撤销或变更缺席判决,否则会影响再保险人的利益。因此,再保险人似乎应当可以参加诉讼。但是,Reyes法官提出一个问题,再保险人于2008年得知Great Power公司已于2002年注销,为何要等到2009年才提出撤销缺席判决的申请。如果再保险人没有迟延诉讼的合理理由,现阶段则不能被允许介入诉讼。在Reyes法官看来,2008年对涉案船舶的对物诉讼中,由于涉及其利益,再保险人应当参加诉讼。但再保险人由于没有预计到Great Power公司可能会被恢复注册,故没有参加缺席审理。因此,Reyes法官指出,除非可以证明,如果允许对货主的抗辩,再保险人非常有可能获胜(a real prospect of success),否则不能批准再保险人撤销缺席判决的请求。(HCAJ 136/1999:第23段至第28段和第36段)
由于涉案运输已经过去10年之久,进一步收集证据不太可能。现有的证据已经不完整,证人证言很难再次获得,而且不可能再进行联合的调查和检验。对于装运前的货物状况,货主的证据材料是货物的质量证书等材料,而再保险人并无相反证据。此外,货主还证明,货物在装船过程中遭遇雨淋,导致日后货损。并且,由于船舶故障导致运输时间增加,恶化了货物的状况。Reyes法官认为,装货过程中遭遇大雨是否会导致货物淋湿受损很难确定,但船舶本身极有可能由于机械故障而不适航。对于卸货后的货损检验证明,再保险人认为应当进行联合检验。Reyes法官指出,现在不再可能进行联合检验。Reyes法官总结认为,即使法庭再次审理该案件,可能的结果是,货物在装船前状况良好,船舶的不适航至少恶化了货物的状况,卸货后货物由于货损而被折价出售。综上,再保险人在本案中不可能成功抗辩,其主张撤销缺席判决的申请被驳回,由于缺乏胜诉的可能,其介入诉讼的申请被驳回。(HCAJ 136/1999:第40段至第83段)
(三)案件评述
合同相对性原则,也被称为合同关系不涉及第三人原则(third party rule),是普通法特有的法律概念。尽管该原则在某些法律领域受到质疑,[1]但该原则在被保险人、保险人以及再保险人关系中仍然适用。除非合同另有约定,再保险人不因出具保函等原因自动获得授权而成为被保险人的代理人。本案中,再保险人就是这种情况。当然,尽管没有授权,由于和案件的判决结果有利害关系,再保险人仍然可以介入诉讼。再保险人不应将自己的诉讼资格建立在被保险人存在的基础上,从而放弃参加诉讼的机会。尽管如此,香港法庭仍然允许再保险人寻求法律救济,但前提是有可能获得诉讼的成功。这应当是基于普通法中公平的原则。如果承运人有可能抗辩成功,再保险人也有可能成功申请撤销缺席判决。由于货损案件证据难以长期保留,因此这种成功的可能性变得很小。这也印证了《海牙规则》建立起来的货损纠纷1年诉讼时效规则的要求,即货损纠纷要及时解决,否则将造成举证不利等后果。
二、保险利益
(一)基本案情
本案中,原告为货物买卖合同中的卖方。货物买卖通过信用证支付,买方在开证行申请开具信用证。原告向自己的议付行出具海运单证,议付行据此向原告付款,但议付行没有得到开证行的付款。在买方付款赎单之前载货船舶沉没。出于商业考虑,卖方通知议付行,允许买方从开证行获得海运单证,但解除信用证下付款义务。同时,应原告要求,议付行将已支付货款转换为长期贷款。另一方面,保险人先后签发预约保单和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单,保单承保一切险,并入协会条款“Institute Classification Clause 1/1/2001(ICC 2001)”。保险经纪人为原告获取预约保单。涉案货物灭失后,原告向保险人及保险经纪人提出索赔。保险人抗辩认为:第一,根据原告在贸易关系上的安排,原告没有遭受可以理赔的损失,其损失不在一切险承保的范围内,其行为妨碍了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第二,原告在货损发生时没有保险利益。第三,承运船舶不是预约保单和协会条款中规定的合格船舶,原告违反了对保险人的告知义务。{the“Kam H ing T rading(Hong Kong)L im ited v.The People’sInsurance Company of China(Hong Kong)L td and M ST Hong Kong L td”案,HCCL 27/2009:[2010]4 HKLRD 630}
(二)法院审理
首先,Stone法官认为,议付行向原告议付货款不等于原告没有损失。议付行可以随时向原告行使追偿权,并且,原告解除买方信用证下付款义务对损失的发生没有实质影响。尽管原告代替买方承担了损失,但毫无疑问的是损失发生了,由原告还是买方获得保险人的赔偿没有本质区别。此外,由于海上风险造成的货物损害和货款支付方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本案保险标的是受损的货物,而不是跟单信用证中的海运单证。原告既然没有获得保险标的补偿,也就没有丧失获得保险人赔偿的权利。至于原告的行为,即无条件向买方交付单据以及将货款变更为贷款,是原告的权利。而这些权利,不是货物发生灭失损害后保险人可以代位获得的,因此,不存在原告损害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问题。(HCCL 27/2009:第67段至第86段)
其次,根据法律规定[Section 6 of the Hong Kong Marine Insurance O rdinance(Cap 329),同the UKM arine Insurance Act 1906],被保险人在损失发生时必须对保险标的有保险利益,否则其不能要求获得相应利益。拥有保险利益的人可以转让保险单项下的利益,但只限于保险标的发生全损之前。[2]据此,保险人认为,保险单由原告背书给买方,但买方没有背书给原告,因此原告在损失发生时不具有保险利益。原告认为,保险单的背书转让,和提单的背书转让一样,必须伴随着转让货物所有权的意图。当议付行向原告议付单证并付款的时候,货物所有权并没有从原告向买方转移。议付行的付款没有减轻原告的损失,而是将原告放置在被追偿的地位。因此,原告事实上没有转让保险单利益的意图。Stone法官同意原告的观点,认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原告对货物具有保险利益。(HCCL 27/2009:第106段至第116段)
Stone法官认为,被保险人是否履行了及时告知义务,是决定本案的核心问题。根据协会条款,保险对船舶既有船级的要求也有船龄的要求。并且,当保险事项发生变化时,被保险人应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能否获得赔偿取决于该告知义务的履行(ICC/01第1条、第2条和第5条)。在普通法中,披露有关运输信息是被保险人的义务,被保险人有义务保证承载船舶符合协会条款的要求(参见the“BC EnterpriseSdn Bhdv BankofChinaGroup Insurance L td”案,[2004]1 HKLRD,26D-F)。协会条款中的船级要求是保险的重要条件(condition),原告没有达到船级要求,并且没有及时通知保险人,因此丧失向保险人索赔的权利。这一点足以决定胜负,无需再考虑禁止反言和最大诚信问题。(HCCL 27/2009:第118段至第186段)
与对保险人的索赔不同,原告对保险经纪人的索赔,更多地取决于对事实的认定。原告主张,保险经纪人有义务确保被保险人理解相关保险条款,这是保险经纪人的解释义务。原告认为,如果保险经纪人告知原告,使用不符合船级要求的船舶会影响保险的索赔,原告则不会使用涉案船舶。此外,即使原告没有提供某些信息,保险经纪人应当有独立的义务去尽可能地获得信息。Stone法官通过大量的证据和证人证言查明,涉案保险经纪人的介入,是因为原告之前的保险经纪人突然退出,导致原告无法安排货物运输保险。本案保险经纪人只是根据原告需要提供可能的保险人信息,保险经纪人和原告之间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保险经纪人没有所谓的指导和建议的义务。即使假设本案保险经纪人有这样的义务,事实上保险经纪人已经妥善地尽到告知保险条款内容的义务。因此,保险经纪人对原告不承担赔偿责任。(HCCL 27/2009:第190段至第252段)
(三)案件评述
本案是个典型的海上保险纠纷案件。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一是被保险人损失的认定,二是对保险经纪人的索赔。首先,被保险人暂时获得货款,不等于没有损失,尤其是在货款可能被追偿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在买卖及其支付环节做出的行为,不影响承保风险的认定和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获得。其次,由于被保险人没有严格履行保险合同中条件条款规定的义务,并且没有及时通知保险人,违反了及时告知义务,从而丧失了索赔权利。如果被保险人能够及时告知保险人,重新协商保费和其他保险条件,继续获得保险保障不是不可能的。最后,保险经纪人是否承担独立的解释和告知义务,取决于被保险人和保险经纪人之间的合同约定。仅仅提供保险人的保费信息供被保险人选择,不能产生保险经纪人的上述义务,被保险人也不能将损失转嫁给保险经纪人。
三、官方法律程序豁免
(一)基本案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交通运输部广州打捞局所有的“华天龙”轮(起重船,2007年建造,吊重能力达4000吨,全球排名第6,号称“亚洲第一吊”,因打捞“南海一号”而特制和成名),于2008年4月16日抵达香港海域,协助打捞乌克兰油田补给船残骸。原告马来西亚Intraline Resources Sdn Bhd公司诉称,其承租“华天龙”轮到马来西亚为离岸钻油工程提供服务,但“华天龙”轮没有履行合同,因此,原告于2008年4月21日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将其扣押。广州打捞局作为被告,向法院寻求诉讼豁免,即官方法律程序豁免(Crown immunity)。(the“Hua Tian Long”案,HCAJ 59/2008:[2010]3 HKLRD 611)
(二)法院审理
在普通法下,官方在其本地区的法院享有诉讼豁免。香港的成文法《1997年官方法律程序条例》(第300章)[Crown Proceedings O rdinance 1997(Chapter 300)]规定了对官方的诉讼权利以及官方及其财产的司法豁免。Stone法官认为,香港在回归前存在两套官方机构,即香港官方政府和英国官方政府,但这两个政府在司法豁免方面的地位是截然不同的。[3]香港1997年之前的法律,即香港《1957年官方法律程序条例》,赋予法院对香港政府的司法管辖,但不包括英国政府。Stone法官指出,这种官方豁免的法律状况在香港回归之后没有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简称《基本法》)改变了香港的主权,但没有改变主权政府的地位。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取代了英国政府享有在香港法院的司法豁免权,即官方法律豁免(HCAJ 59/2008:第83段)。并且,Stone法官认为,主权豁免和官方豁免在此问题上是不同的,该豁免不受主权豁免制度中限制豁免理论的影响。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没有权力制定法律来约束中央政府。最终,Stone法官认为,广州打捞局可以享有财产上的司法豁免。(HCAJ 59/2008:第124段至第125段)
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广州打捞局代理人在2008年4月30日向法院要求驳回原告诉讼和释放船舶的申请中指出:“为本申请之目的,广州打捞局不寻求援引任何主权豁免原则。但是,广州打捞局保留在以后阶段援引的权利。”(“GZS is a Bureau of the M 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For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application,GZS w ill not seek to invokeany principle of Sovereign Immunity.However,GZS reserve the right to do so at a future stage.”)在普通法中,开始进行法律程序或在法律程序中采取任何措施都视为接受法院管辖,除非进行的法律程序或采取的措施是为了主张豁免,或有合理的原因导致无法知道享有豁免的事实,并且在合理可能的情况下尽快主张享有豁免。[4]Stone法官认为,广州打捞局的申请明确表明保留援引主权豁免原则的权利,说明其已经知道其享有的权利。但是,广州打捞局直到2009年10月21日的法庭传唤中才主张该权利,并且,期间还积极参加诉讼程序,包括于2008年7月31日提起反诉。因此,Stone法官认为,广州打捞局从2008年4月30日起应该已经意识到自己享有的司法豁免权,其随后的行为在事实上表明放弃了豁免的权利,接受了香港法院的管辖。(HCAJ 59/2008:第151段至第152段)
(三)案件评述
该案的判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香港法院是否能够由此获得管辖值得商榷。首先,香港法院对国家行为是否有管辖权,不以拥有司法豁免权的国家主体是否援引或行使该权利为前提条件。如果香港法院依法对国家行为没有管辖权,则除非当事人同意香港法院对案件的管辖或主动请求香港法院管辖,否则,即使放弃(包括视为放弃)官方豁免权,香港法院也不当然拥有案件的管辖权。在香港法律环境中,中央政府的官方行为是否属于《基本法》中的国家行为,是个需要解释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通过香港未来的普通法案例得到进一步的诠释,也可以依据《基本法》第158条第1款,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其次,根据香港《1997年官方法律程序条例》第25条的规定,本条例不授权就任何针对官方提出的主张而进行对物法律程序,或授权扣留、扣押或出售属于政府的船舶或航空器或属于官方的货物或其他财产,或就该等船舶、航空器、货物或其他财产而给予任何人留置权。由此可见,即使在不能享有官方法律程序豁免的情况下,法律也没有赋予香港法院扣押官方船舶的权利。
尽管该案遗留若干未解决的问题,从香港普通法发展角度看,该案不失为香港官方法律程序及其豁免法律制度的重大发展。可以预见,尽管能否被香港法院认可或接受尚不能确定,“华天龙”轮案仍然会引起与中国官方机构进行商贸活动的外国实体的密切关注,甚至会在将来的商业合同或法律中试图取消官方法律程序的豁免,从而获得更大程度的司法救济。据悉,该案已经上诉到香港高等法院上诉法庭。该案件的最终判决,不仅会再次引起香港对《基本法》解释问题的关注,也将成为中央政府及其财产在香港司法管辖及其豁免问题上的里程碑式答案。
四、不方便法院原则
(一)基本案情
2007年3月17日,“HuiRong”轮和“Peng Yan”轮在舟山岛海域发生碰撞,“HuiRong”轮随后沉没,货物全部灭失。2007年5月,受损货主在香港法院开始法律程序。2008年3月,受损方在宁波海事法院起诉“Peng Yan”轮所有人(船舶所有人),请求赔偿碰撞导致的灭失损害。4月,船舶所有人在宁波海事法院申请设立责任限制基金。11月,船舶所有人根据不方便法院原则(forum non conveniens)申请中止香港法庭程序,以便进行宁波海事法院的法律程序。(the“Peng Yan”案,HCAJ 12/2008:[2008]5 HKLRD 418)
(二)法院审理
由于船舶所有人不否认香港法律程序的正确性,香港高等法院原诉法庭Reyes法官认为,船舶所有人必须证明该案件由宁波海事法院审理更为恰当,例如,案件的审理更符合所有关系方的利益和司法的目的(参见the“Spiliada Maritime Corp.v.Cansulex Ltd”案,[1987]1AC 460,476C)。对此,船舶所有人提出如下理由:第一,碰撞发生在中国内地水域,中国内地是本案当然的管辖地;第二,“Peng Yan”轮在中国内地注册,船舶所有人是中国内地公司;第三,碰撞事故中的两艘轮船的船员均是中国籍;第四,香港海事部门和浙江海事局对碰撞进行了调查,但没有证据表明浙江海事局的报告人能够出席在香港的庭审;第五,宁波方面已受理了包括限制责任在内的其他诉讼,而所有请求交由同一法院审理更加便利;第六,船东在宁波海事法院已经设立金额和香港相同的责任限制基金。(HCAJ 12/2008:第9段至第10段)
然而,Reyes法官认为上述理由没有满足不方便法院原则的要求。第一,碰撞地法院进行管辖是很自然的(参见the“A lbaforth”案,[1984]2 L loyds Rep 91)。但是,法庭必须从审判的角度来看碰撞地法院是否成为恰当的管辖法院(参见the“Rambas M arketing Co.LLC v.Chow Kam Fai David”案,[2001]3 HKC 250,255B)。第二,涉案船舶是中国船籍,船舶所有人是中国内地公司,这些对法院的管辖选择都无足轻重。香港作为国际港口,有许多外籍船舶和外籍所有人,但这些并不影响货损案件的审理。当然,船员是中国国籍对法院的选择是会有些影响,特别是有些船员可能会被要求出庭作证。但是,Reyes法官认为,中国内地很大,需要作证的“Peng Yan”轮三副住在山东,没有证据表明证人从山东到宁波比到香港更方便。更何况船员随着船舶到达世界各地,没有理由认为这些船员到达宁波作证比到达香港更为方便。第三,无论是香港法院还是宁波法院都不需要受浙江海事局事故报告人的观点束缚。在香港法院看来,个人的观点是无关紧要的。第四,不能确定宁波海事法院是否会将所有的索赔请求合并审理,有一些索赔请求似乎不太可能合并审理,比如浙江海事局提出的油污赔偿请求。有关责任限制的诉讼可以在宁波法院起诉,但这种诉讼在其他地方进行同样不足为奇(参见the“Caspian Basin Specialised Emergency Salvage Adm inistration and Another v.Bouygues Offshore SA and others”案,[1997]2 Lloyds Rep 507,525)。船舶所有人既然在香港法院受理案件之后选择向宁波海事法院申请设立责任限制基金,就应当承担任何相应的后果。第五,相同的基金数额只是一个中性因素,不影响对法院的选择。此外,船舶所有人还主张宁波海事法院是审理海事案件的专门法院,并且证人可以用普通话出庭作证。对此,Reyes法官认为,专门法院不能成为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至于证人语言,香港法院几乎每天都有普通话作证。综上,Reyes法官拒绝船舶所有人以不方便法院原则为由中止香港法庭的法律程序。(HCAJ 12/2008:第14段至第46段)
作为抗辩,货主提出不中止香港法律程序的理由:第一,中国内地诉讼程序更加复杂,需提交很多表格和文件;第二,原告在中国内地法院不能获得律师费的赔偿;第三,中国内地没有证据披露制度;第四,中国内地对责任限制基金的利息低于香港;第五,中国内地有外汇管制,人民币作为赔偿款汇出会有困难。Reyes法官不同意上述观点。首先,就第一点而言,不同管辖地法院会要求提交不同的文件,这不能成为一个法院管辖更为恰当的理由。其次,第二点和第三点是大陆法系的典型特点,根据礼让原则,一个法院不能因为这些制度上的差异而自认为是恰当的管辖法院。至于最后两点,Reyes法官指出,有证据表明原告可以要求更高的利率,并且可以申请将赔偿金汇出国外,因此,这两点不构成实质的不利因素。(HCAJ 12/2008:第48段至第54段)
尽管货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但由于首要举证责任在申请人,[5]而船舶所有人作为申请人未能证明宁波海事法院是恰当的管辖法院。因此,Reyes法官判决驳回船舶所有人中止香港法庭程序的申请。船舶所有人上诉至香港高等法院上诉法庭,遭到驳回(CACV 269/2008:[2009]1 HKLRD 144)。船舶所有人被判令赔偿原告损失。最后,原、被告达成赔偿协议,被告船舶所有人赔偿原告在宁波海事法院的法律费用。原告主张被告同样应承担在香港法院发生的法律费用。香港高等法院W ong法官不认同原告的主张,判令原告自行承担香港法院发生的法律费用(HCAJ 12/2008:2010年2月5日)。
(三)案件评述
不方便法院原则是普通法中处理管辖地冲突时经常用到的法律规则。本案中原告和被告列举的考虑因素,是中国内地和香港法院管辖冲突中比较典型的事项。虽然案件是个案,但作为普通法的判例,该案的判决对今后处理中国内地法院和香港法院管辖冲突的问题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尤其可以明确的是,在海事诉讼的法院管辖问题上,设立海事责任赔偿基金不能成为法院获得管辖的理由和依据。不可否认,具体的考虑因素在不同的时期可能起到不同的作用,但香港法院对管辖的积极态度是显而易见的。法院间的管辖协议也许可以成为解决内地和香港之间法院管辖冲突的更好方式,例如2008年8月1日起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法释[2008]9号)。
五、仲裁和诉讼
(一)基本案情
该案起因于Galsworthy公司和Parakou公司之间的租船纠纷,因后者未能履行租约,Galsworthy公司于2009年2月在伦敦提起仲裁,请求裁决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因错误终止租约而导致的损失。在仲裁期间,被申请人在香港法院提起诉讼程序,主张其和仲裁申请人从未达成过租约。仲裁庭于2010年8月31日作出裁决,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有效的租约。(the“Parakou Shipping Pte Limitedv Jinhui Shipping And Transportation Limited etc”案,HCAJ 184/2009,CACV 225/2010)
(二)法院审理
香港高等法院原诉法庭开庭当日,根据被告(仲裁申请人)的申请,Reyes法官以原告滥用诉讼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法官认为,对仲裁裁决的质疑,将导致明显的不公平,并有损于司法实践(HCAJ 184/2009:第1段和第3段)。Reyes法官在判决书中就相关法律问题做出进一步解释。根据普通法,如果一个问题在一个案件中得到处理后,允许改变法律程序再审理同一个案件,会成为司法程序的滥用(参见the“Hunter v.Chief Constable of the West Midlands Police”案,[1982]AC 529,541-542),在一个法庭或仲裁庭获得不利判决后,在另一个法庭再次提起法律程序是对司法的滥用;若再次提起法律程序的一方在之前的法律程序中已获得充分的参与机会,情况更是如此。(HCAJ 184/2009:第87段)
Reyes法官就法律程序的滥用分两种情况予以分析。首先,一个人不可以因同一事由被纠缠两次(参见the“Arthur J S Hall&Co v.Sim ins”案,[2002]1 AC 615,701A)。因此,当一个纠纷或请求已经根据有效的管辖获得解决,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res judicata),无论之前的管辖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判决,都不可以根据原诉因再次起诉(cause of action estoppels),或就已经解决的问题重新开始程序(issue estoppels)。如果一方打算否定之前的判决,则需要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提出,而不是提起新的法律程序。其次,一事不再理原则可能扩大适用,例如,后提起的法律程序中的当事人不是原法律程序中的当事人或关系人。这种扩大适用的法律基础是公共利益原则(public interest)。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一概而论,而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只有再次审判会导致明显的不公平,或有损于司法权威,才可以被认定为滥用司法程序。(参见the“China North Industries Investment L td.v.Shum and others”案,Civ App No.321/2006,第58段至第59段)因此,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对事实的认定要十分谨慎(HCAJ 184/2009:第90段至第96段)。由于本案法庭程序中的原告和被告不是仲裁中的申请人和被申请人,而是存在隶属和控股关系的一系列公司,甚至还包括诉讼第三人,因此,尽管Reyes法官在判决当日即做出驳回诉讼的决定,但在判决书中仍然花费大量篇幅对事实进行认定,从而得出一事不再理原则扩大适用的决定。原告不服判决上诉,香港高等法院上诉法庭维持了原审判决(CACV 225/2010)。
(三)案件评述
该案是继英国the“Fiona T rust&Holding Corp v.Privalov”案([2007]U KHL 40)后,[6]香港法院做出的司法尊重仲裁的又一普通法典范。香港法院继承了对仲裁的尊重,使得普通法系中仲裁优先的理念得到继续发展,法庭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对仲裁进行干预。同时,香港法院通过该案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应用于仲裁和法庭程序的关系中,使得仲裁和诉讼通过该原则的适用处于同等法律地位。这种做法不仅发展了香港的普通法,而且使香港的仲裁法律环境更加宽松,有利于香港的国际仲裁实践得到法律上的进一步保障。
六、结语
2010年,香港高等法院审理的海商海事案件,不仅涉及传统的海商法内容,还延伸到香港其他法律领域。这些案件一方面反映出香港的普通法与英国的普通法的传承和联系,另一方面也体现出香港普通法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下继续发展。随着香港和内地的持续密切联系,两地法院的管辖之争也日渐明显,两地法院间的管辖协议也许可以更好地解决这种冲突,为两地的合作发展提供更有利的法律环境和保障。
[1]FISHER M J,GREENWOOD D G.Contract law in Hong Kong[M].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7:393.
[2]CHAN F W H,NG J J M,WONG B K Y.Shipping and logistics law: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Hong Kong[M].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2:521.
[3]Halsbury’s law s of England:Vol.6[M].4th ed.London:Butte worths,1986:817.
[4]DICEY A V.The conflict of law s:Vol.11[M].London:Sweet&Maxwell,2006:10-28.
[5]SVANTESSON D J B.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internet[M].New York:Aspen Publishers,2007:110-111.
[6]陈伟汉,赵亮.英国海事仲裁管辖权问题的新发展——Fiona T rust案件解读[M]//广州海事法院.中国海事审判年刊(2008-2009).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50.
CHEN Wei-han,ZHAO Liang.On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maritime arbitration of Britain—unscrambling the case of Fiona T rust[M]//Guangzhou Maritime Court.Annual of Maritime Trails(2008-2009).Beijing:Law Press,2010:150.(in 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