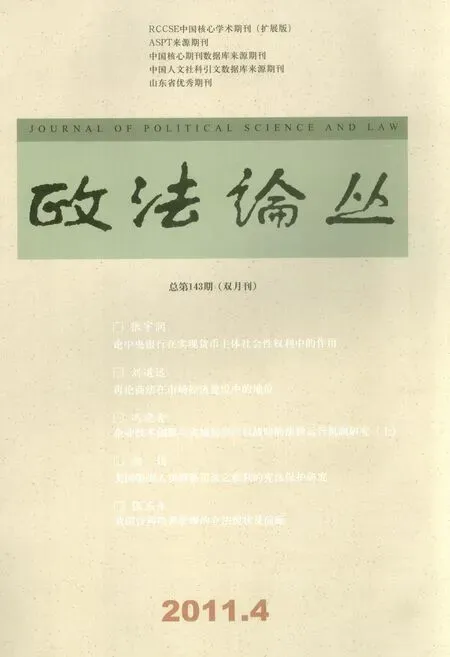基于投资偏好差异的股份公司股东类别化分析*
传统的代理理论在分析股份公司问题时,对其股东采取了一种以理性利己为特征的“经济人”模型,即认为股份公司股东虽然为数众多,但股东之间具有人性同质、利益同质的“同质化”特征,因而可以被简单视为抽象无差异资本的载体。公司法理中所谓“股份公司是最为典型的资合性公司”之命题正是源于上述理论认知。但是,股东“同质化”假定是与股东客观存在的差异性不相符合的。[1]现代股份公司股东已经因其实然的“异质性”而不断呈现出类别化趋势。其中,个体间的投资偏好差异无疑是股份公司股东“异质性”非常重要的现实表现之一,因此,以此为视角对股份公司股东进行类别化考察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但是,个体的偏好差异又是十分复杂的,以此为视角的股东类别化也必然是难以把握和难以周延的。本文在此仅分别从投资组合偏好、投资周期偏好、投资收益偏好、投资目的偏好角度对股份公司股东的类别化以及这种类别化对股份公司治理的影响加以初步分析。
一、投资组合偏好标准下的股东类别化:单纯型股东与多元化股东
根据投资组合偏好差异,我们首先可以将现代市场中的股东分为两个对应的类型:单纯型股东和多元化股东。单纯型股东是指那种将其全部投资金额用于购买某一公司的普通股股份,以获得稳定而持久的红利分配为目标,拥有完整的股权权能(红利分配权能、投票权能、剩余索取权能等)的投资者。单纯型股东最接近于传统理论中所描述的典型的股东形态,比如说他们是公司“单纯的资本所有者”或者“剩余索取者”。公司法制度设计中所使用的也是单纯型股东模型,比如公司法关于股东的规定一般都表述成:购买(认购)了公司股份;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所持每一股份拥有一个表决权;等等。不过,在现代金融证券市场中,单纯型股东尽管并不鲜见,比如某一公司的创始家族股东,但却早已不是主流,分散投资、规避风险的理念成为普遍信奉的金融教义。加之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也极大地拓宽了投资者的选择范围,于是,大多数投资者通过持有同一公司或者不同公司的不同证券品种或者证券衍生品而从一个单纯的红利接受者或者剩余索取者转变成为一种多元化投资者,拥有了多样的投资组合。另外,既向公司投入了股权资本又向公司投入了专用性人力资本的高管或者普通雇员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多元化股东。
单纯型股东和多元化股东分野的实质就是股东之间的利益追求从同质走向异质,进而不可避免地引发利益冲突。首先,单纯型股东和多元化股东对风险的偏好不同。单纯型股东必须非常关注其所投资公司可能发生的特殊风险,即那些与整个市场的表现无关的个别性打击,如重要高管的突然去世或者某项重大投资的血本无归等。因为这种特殊风险所可能造成的损失对于单纯型股东而言是难以消除的。而多元化股东通过投资于一系列公司就使得此类风险对他而言变得无关紧要,或者至少不必像单纯型股东那样时时忧心忡忡。因为一般来说,一个公司中发生的特殊利空将可能会被另一个公司中发生的特殊利好所弥补。其次,单纯型股东和多元化股东对于公司行为外部性的看法也不相同。某一公司行为所产生的外部性,既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或者说是对外部可能产生溢出效应或者减损效应。对于单纯型股东来说,公司通过其负外部性向外界转嫁成本会使其从中受益,同样,公司因正外部性而受到的相对损失也不可避免地要由单纯型股东来部分承担。但一般来说,单纯型股东主要关注的是其所投资公司内在的直接收益状况,对于公司行为外部性所形成的间接得失并不表现出明显的偏好。而对于多元化股东来说,这种情况就会变得比较复杂。因为,多元化股东通过其在众多的公司中的广泛持股,可能会将其投资的公司所产生的许多外部性在其自身的投资组合系统中予以了内部化。在这种情况下,多元化股东就可能转而会偏好其所投资的公司的那些能够最小化其负外部性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对其拥有利益的其他公司施加了成本。单纯型股东和多元化股东之间的风险偏好和外部性考量的差异所导致的利益冲突将会对公司治理带来的重大影响。传统理论所认为的通过股东大会表决机制可以很容易地集合出利益诉求一致的个体股东的集体合意,似乎只是一种天真烂漫的理想主义表达。多元化股东的投资组合有助于保护他们免遭某一公司特殊风险的致命打击,但也同时使他们更直接地受到公司行为外部性的影响。正基于此,多元化股东对于公司决策往往拥有着不同于单纯型股东的选择偏好。
二、投资周期偏好标准下的股东类别化:短线型股东与长线型股东
股份公司股票具有较好的流动性,尤其是公开交易的上市公司股票,在现代化交易方式(如集合竞价)和交易工具(如网络系统)的帮助下,转让效率大大提高,转让成本不断降低,股票的可流动性得到了空前强化。这种高流动性也反过来引发了股票市场价格的高波动性,涨涨跌跌成为现代股票市场的常态,甚至暴涨暴跌的发生周期也不断缩短。在这种情况下,某一股份公司的股东对其持股的取舍就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所投资公司的持续增长和分红能力;另一个就是手中股票市场价格短期波动的几率与幅度。这两个因素在不同的投资者心目中的权重是不尽相同的,于是股东之间便产生了对持股时间长短的偏好差异,我们可以将这种偏好称为股东的“时间视域”。以这一维度为标准,股份公司的股东可以被进一步类别化成短线型股东和长线型股东。短线型股东是指那种以高频率买卖股票,致力于从市场股价的短期变动中获得收益的投资者。而长线型股东则是指那种买入并较长期持有股票,注重所持有股票的长期增长能力,通常不考虑其短期市场价格走势的投资者。短线型股东和长线型股东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是否追求从市场股价的现时波动中获利,而对于这种波动是否是因具有实质性利好支承而能够持久不予考虑。
最为人们所熟悉的短线型股东的标志性形象是那些整天在股市中忙于追逐各种所谓的热点而频繁更换持股的所谓散户投资者。不过,这种短线型股东对市场和公司经营的影响都是微不足道的,真正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是现代金融市场大量涌现的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根据它们投资操作的时间视域分析,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基本上都属于一种典型的短线型股东,因为它们通常都不关心其所进行股票交易的公司的长期成功,而是倾向于关注某个公司股票的当前市场价格。共同基金是一种个体投资者据以集中财力共同投资于可销售证券的金融中介,在共同基金中的投资者可以容易地以市场价格清算他们在基金持股中的份额。这种流动性,伴之以对基金业绩信息的易获得性,不可避免地会对共同基金管理人产生一种强大的压力,即为了吸引和保持基金投资者,必须以牺牲对所投资股票长期价值的关注为代价来最大化短期回报。[2]P1093对冲基金也被称作避险基金或者套利基金,意思是“风险对冲过的基金”,它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美国。对冲基金也是像共同基金一样管理着一种集合财产,它也必须定期地回馈资本市场以便募集另外的资金。不过,与共同基金不同的是,对冲基金的投资人是有实力的和精明老道的,愿意也有能力根据基金业绩决定投资。对冲基金一般不接受较小的、不成熟的投资者的资金,以便增加其投资的灵活性。特别是对冲基金所面对的有关风险和复杂投资工具的法律限制以及可赎回性要求都是宽松的,因此,对冲基金可以采用更加广泛多样的市场投资战略,包括投资于困境证券、非流通证券、新兴市场公司的证券、衍生品和套利交易机会等。有学者将对冲基金刻画为“市场驱动机制的主要范式”。[3]P229
与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的短期视域不同的是,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股东则更有可能具备一种长期的时间视域,因而可以归类为长线型股东。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股东一般很少在意所投资公司股票短期价格的跌宕起伏,也不过分关注所投资公司季度的甚至年度的业绩。基于其自身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和较小的集中支付的可能性,它们有更大的动机和能力去追求其所投资公司的长期繁荣。
如果是在有效资本市场假说所表述的情境下,短线型股东与长线型股东在投资的时间视域上的差异性是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显著影响的。有效资本市场假说是对有效市场假说在资本市场的一种具体应用。在1978年,詹森宣称:“在经济学中有效市场假说比其他命题具有更坚实的经验性证据支持。”[4]P95法玛关于有效市场的一般定义是“价格在任何时候充分反映所有可获得信息。”据此,有效资本市场假说也就认为某一公司在特定时间的股票价格准确地反映了有关该公司的所有可获得信息。如果有效资本市场假说确实准确地描绘了股票价格,那么短期股票价格将反映出投资者对公司股票基本的或者长期的价值所进行的充分知情的评估。据此,短期价值的最大化将与长期价值最大化相一致,也就是说,“可获得信息”不会支持营利性的交易策略或者套利机会。[5]P383-385因此,在一个有效股票市场,股东对于时间视域偏好的差异将不影响公司管理的战略选择。然而,正像斯托特指出的那样,有效资本市场假说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似乎还享有坚实的经验性支持,但从那之后我们已经目睹了与它相悖的经验性证据的不停累积,包括定价异常、需求非弹性、过度的发散性、迟滞的信息反应以及层出不穷的高级交易者。[6]P667因此,有效市场假说已经不再是对真实世界的一种准确描述。尽管短期股价仍被认为与股票的根本价值之间存在某些关联,但从长期来看,短期股价极大地背离股票根本价值的情形经常发生。[7]P1616这种背离的存在表明短线型股东与长线型股东在投资的时间视域上的差异性将可能会对公司治理产生一定的影响。短线型股东一般偏好于所投资公司的管理层致力于最大化短期股价,因而会赞成以牺牲长期价值为代价而换取现时股价的膨胀;而长线型股东则更加偏好于所投资公司的管理层努力实现长期股东价值的最大化,所以会愿意为未来增值而牺牲即时利益。这种偏好差异就会使公司管理者面临着如何确定公司战略目标的一系列难题。鉴于短线型股东与长线型股东与下面将要探讨的投机型股东和投资型股东具有明显的对应性和相似性,我们将在稍后集中分析它们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三、投资收益偏好标准下的股东类别化:投机型股东与投资型股东
这一对应类别的划分主要是依据股东对于投资收益类型的不同偏好而进行的,即投机型股东预期的投资回报主要集中于资本收益,而投资型股东预期的投资回报则主要集中于红利收益。股东在投资收益类型方面的异质化偏好在公司制度发展的早期并没有充分体现,其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那时候缺乏行之有效的投机渠道,所以公司股东最大的期盼就是所投资公司能够经营良好,以便保证进行稳定的红利分配。而拥有高度流动性的现代资本市场创造出了无数的投机机会,从而大大刺激了人们潜在的投机欲望,于是,股东所追求的收益类型不断分化,投机型股东大量产生。由于所谓的“投机”只是一种主观心理活动的表达,所以要想给投机型股东下一个准确的规范性定义是困难的。德国学者莱塞尔等人对这两种股东类型有过简单的描述:投资股东仅仅将其股份当作一种资本投资,因此他每年可以获取股息;投机股东是通过参与股市投机而获利。[8]P67这种描述虽然也算抓住了两类股东“异质性”的要点,但终归显得过于简单。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一种对上述两类股东行为特征的概括来更加清晰地把握他们之间的“异质性”。就投机型股东而言,他们大多数都是一种短线型投资者,拥有一种短期视域,喜欢快进快出,频繁换手;他们以资本收益最大化为目标,主要看重的是资本收益而非红利收益;他们所重点关注的投资场所主要是二级市场,崇尚的战略是提前感知能够对所投资公司股价产生重大即时影响的信息、尤其是内幕信息,热衷于炒作概念和题材,闻风而动,实现所谓“先人一步”;他们对于公司实际的经营管理和内在价值并不感兴趣,那些长期业绩优良、股价随市场波动很小的蓝筹公司很少被他们纳入投资视野,相反,那些因经营不善、面临退市风险而寻求重组机会的垃圾股却往往成为他们进行风险收益博弈的乐园。简单地说,投机型股东主要是追求通过市场股价的短期波动获取差价而实现其投资收益。当然,在投机型股东大行其道的今天,仍然有许多的投资型股东在坚守着自己的投资理念。投资型股东并不过分关注市场股价的短期波动,而是寻找具有长期利润增长能力和良好发展前景的公司股票进行长期持有;他们一般是以红利最大化为目标,并不求在资本市场的快速变动中博取差价,而是希望所投资公司能够持续进行数额可观的稳定分红;他们对二级市场的潮涨潮落并不给与太多关注,所持有的某些股份甚至是处分权受到一定限制的股份;他们十分注重所投资公司的治理状况和内在价值,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对公司状况充分知情,并以此作为其选择投资目标的标准,因此,那些因基本面严重恶化而短线风险与暴利并存的公司被其视为投资的禁区。概言之,投资型股东主要是追求通过所投资公司的实际业绩增长所带来的稳定回报而实现其投资收益。
投机型股东和投资型股东的不同收益偏好会给公司管理者的经营战略选择带来很大的难题,尤其是对于上市公司来说,投机型股东主导的股票市场会对其短期盈利状况形成强大的评价压力。如果公司管理者完全以投机型股东偏好作为制定业务发展策略、红利政策和股票市场政策的依据,就会热衷于在公司外部随机寻找不相关的热点投资机会,轻率进行实业投机,以便创造所谓的新利润增长点。这种完全迎合投机型股东短期投机偏好的公司战略往往导致公司资本配置行为的随意性和短期化,它或许能够引起市场对公司股票的短期积极反应,但致命的负面影响是极易导致公司主营业务的市场竞争地位逐渐衰落。这种迎合短线投机型股东的心理也会诱使公司管理者通过将成本从本年度移至未来年度或者通过将收益从未来年度移到本年度而在形式上增加当前收益。[9]P387此类行为能够强化(或者避免恶化)公司的现时股价,但是却减损了长期的股东价值,甚至使公司管理者一步步滑入财务造假的深渊。[10]P181-182
另外,投机型股东和投资型股东的不同收益偏好也极大地影响到股东大会功能的正常发挥。投机型股东不仅在自身的价值最大化方面是与公司价值最大化常相背离的,其对于参与公司治理也多是表现为“理性冷漠”或者纯粹的利己主义。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持有一个公司的股票都极为短暂,甚至不去关心所买入股票的公司主要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即使他们参加公司投票,也是对那些能够为公司带来长期增长潜力但短期市场反应却会非常平淡的项目毫无兴趣。而一旦他们能够控制和左右公司经营决策,就可能会利用一切合法和非法的手段,与公司进行不公平的关联交易、置换公司优质资产、向公司转嫁市场风险,或者促使公司以长期稳定发展为代价进行短期投机冒险。一旦公司面临困境,或者市场稍有风吹草动,投机型股东就会在第一时间全身而退,他们信奉的箴言是“我身后那怕是洪水滔天,与我何干”。近年来,不少对冲基金以股东行动主义旗号积极介入其所投资公司的内部事务,利用“确保董事会关注于最大化股东价值”的口号向公众股东征集代理投票权,以此种敲山震虎的方式去迫使公司做出重大的结构变革。但对冲基金能否真正提升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是值得怀疑的。正像有学者对对冲基金本性概括的那样,它的唯一经营目的就是逐利,其控制人从来不关注那些被其所投资公司的经营所破坏的社会共同体或者生态系统,他们与公司的员工没有任何瓜葛,对于非金融的世界熟视无睹。[2]P229对冲型股东有可能为了最大化自己的衍生赌注的价值而进行有悖于公司利益的投票。[11]P836-842对冲基金的短期投资视域和投机偏好使得现实中的许多由其采取的积极行动最终都是与现任管理层达成“和平”解决方案而收场,比如由公司向对冲基金进行“绿邮”类的股票回购或者其他重大让步。因此,就长期而言,对冲基金的行动主义是否真正惠及了其他股东还有待考量。相反,如果公司管理者是以投资型股东的收益偏好为导向,就会致力于踏踏实实的实业运作,培育竞争能力,提高经营效率。这样的经营理念在把握商业机会方面是有着以一贯之的确定标准的,不会随着所谓的市场热点而频繁变更投资方向,并且能够把外生的投资机会转化为内在的经营实绩和企业价值,从而可以进一步集聚和增强公司主业可持续发展的竞争能力。投资型股东的收益偏好也是与不断得到认同的公司社会责任和利益相关者理念相契合的,和投机型股东相比,投资型股东的利益与公司利益以及其他相关者的利益表现出了更大的一致性。投资型股东对于参与公司事务也更加具有积极性,其在行使投票权时也更富知情性和远瞻性。
四、投资目的偏好标准下的股东类别化:营利型股东与公益型股东
尽管从商法总论的角度很难对股东是否属于商主体有一个笼统的定论,不过对于股东投资目的的营利性却是受到普遍认可的。按照传统的股份公司理论,那些通过股份公司形式聚合在一起的个体资本就是为了实现逐利增值的目的,因此,作为无差异资本之载体的股东当然在本质上也是具有“同质化”的营利性特征的。但是随着股东“异质化”的不断演进,股东在投资目的偏好上也开始出现差异,尽管营利性还是绝大多数股东共同具备的基本特质,但也有不少股东在获取投资收益的目的之外,还承载着与传统股东价值相分离的、非经济性的或者说体现一定公益性的目标。据此,我们也可以沿着投资目的偏好差异的维度将股份公司的股东进行另外一种的类别化,即可以将他们粗略地区分为营利型股东和公益型股东。所谓营利型股东是指传统理论所描述的那种以单纯的投资收益为目的而持有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所谓的公益型股东并不是说其不具有投资收益的目的,而是指其在投资收益目的之外还同时承载着其他的体现一定公益性的价值目标。这种非经济性目标的产生主要是基于该类股东自身独特的内在构造和社会价值。
在美国,有学者重点关注了公共养老基金和工会养老基金,认为它们虽然投资于公司成为股东,但有时候也非常关注于非经济性目标,因为这些群体在施加其作为股东的影响力时,有独特的动机去考虑与股东价值相分离的目标。[12]P588公共养老基金是美国各州及其地方政府公务雇员的养老基金。该基金财产的管理通常是按照一个州法上的所谓“谨慎人”(prudent person)信托标准来进行,该标准要求基金的管理要“审慎、自主以及明智”。对于公共养老基金而言,有一种广泛的政治压力要其去从事“社会投资”——刺激本州经济发展的投资。[13]P800-803将此种考量作为一种投资标准加以强调就在客观上将公共养老基金的利益置于一种与那些经济型投资者不一致的境地。像公共养老基金一样,美国数额庞大的工会养老基金也已经成为不断增长的重要股东。[14]P1019美国的工会养老基金是将工会成员的养老金集中在一起用于投资的私人养老金方案,它的管理首先要受制于美国联邦1947年颁布并经2000年修正的劳资关系基本法——《塔夫托—哈特莱法》(Taft-Hartley Act),该法第186(c)(5)条要求工会养老基金要由公司管理层和工会指定的托管人联合管理;该条款同样也对托管人施加了一种信托义务,要求信托持有的所有款项都是为着“雇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和受扶养人的唯一的和专属的利益”。不过,该法并不直接规制养老基金的投资行为。另外,美国的工会养老基金托管人也要受制于美国联邦1974年的《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中规定的信托义务,该义务要求基金托管人要具有一种“在一个具有相似特征和目标的企业的管理中将被运用的……审慎”,并且要求托管人进行多元化投资,除非不这样做明显是谨慎的。美国劳工部已经赋予工会养老基金在追求社会性或者经济性目标的投资上的回旋余地。
近年来,社会责任投资作为一种典型的公益型股东的独特价值理念而受到广泛关注。社会责任投资(SRI)是一种在投资决策中结合了社会和环境考虑的投资方法。在做出一个投资决策时,会同时考虑社会、环境和财务因素,所以社会责任投资又被称为“三重底线投资”。社会责任投资理念允许投资者在关注传统的金融问题的基础上,把目光投向诸如社会公平、经济发展、人类和平、环境保护等问题上来,在投资选择中加入个人或组织、团体的价值理念和信仰,表达他们对经济和社会、利益和伦理、当前状态和未来持续发展的选择。社会责任投资理念的现代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美国的宗教运动,即宗教信仰者的“伦理投资”。1920年,当时美国的卫理工会派教会打破从前对股票市场的偏见,决定投资到股票市场,但是他们决定在投资组合中排除那些从事酒精、赌博方面经营的公司。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责任投资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美国的社会责任投资基金资产从1995年的6390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2.29万亿美元。欧洲的社会责任投资基金数量到2006年6月底达到了388只,管理资产达到340亿欧元。[15]P23-26
上述的几组相互对应的股东类别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股份公司理论和制度设计获得正当性的逻辑基础——股东“同质化”假定,更是对股份公司的制度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课题。面对“异质化”投资者的不同偏好,公司法律是该固守传统的千篇一律的股权构造模式,还是可以允许市场自身重新组合股权的不同权能以便创造出多样化的投资安排。在这方面,我国的公司法律显然和公司制度本身的发展一样是后知后觉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司实践和制度设计已经认识到股东“异质化”的客观存在,因而在股权差异化构造的道路上先行了很远。或许,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正是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迈向市场推动型类别化的起点。
[1]汪青松,赵万一.股份公司内部权力配置的结构性变革——以股东“同质化”假定到“异质化”现实的演进为视角[J].现代法学,2011,3.
[2]William B.Chandler III,On the Instructiveness of Insiders,Independents,an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J].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law review,1999,67.
[3]K.A.D.Camara,Classifying Institutional Investors[J].The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2005,30.
[4]Michael Jensen,Some Anomalous Evidence Regarding Market Efficiency[J].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1978,6.
[5]Eugene Fama,Efficient Capital Markets:A Review of Theory and Empirical Work[J].The Journal of Finance,1970,25.
[6]Lynn A.Stout,The Mechanisms of Market Inefficiency: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Finance[J].The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2003,28.
[7]Stephen F.LeRoy,Efficient Capital Markets and Martingales[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89,27.
[8][德]托马斯·莱塞尔,吕迪格·法伊尔.德国资合公司法[M].高旭军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9]Michael C.Jensen,Paying People to Lie:The Truth About the Budgeting Process[J].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2003,9.
[10]Thomas Lee Hazen,The Short-Term/Long-Term Dichotomy and Investment Theory:Implications for Securities Market Regulation and for Corporate Law[J].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1991,70.
[11]Henry T.C.Hu&Bernard Black,The New Vote Buying:Empty Voting and Hidden(Morphable)Ownership[J].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2006,79.
[12]Iman Anabtawi,Some Skepticism About Increasing Shareholder Power[J].UCLA Law Review,2006,53.
[13]Roberta Romano,Public Pension Fund Activism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Reconsidered[J].Columbia Law Review,1993,93.
[14]Stewart J.Schwab&Randall S.Thomas,Realigning Corporate Governance:Shareholder Activism by Labor Unions[J].Michigan Law Review,1998,96.
[15]上海证券交易研究中心.中国公司治理报告(2007):利益相关者与公司社会责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