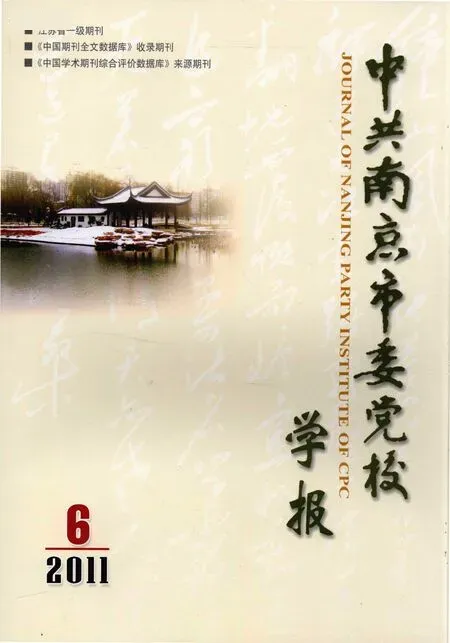湮没与重现: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
周爱民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上海 200433)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一直是马克思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因为这不仅牵涉到能否“回归马克思”这一重要的学术争论,还涉及到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观点。①在笔者看来,虽然近年来相关西方马克思学的著作被大量译介到国内,但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被“妖魔化”和“脸谱化”的现象仍然存在。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中文版序言中,卡弗甚至认为“他们的关系仍然没有成为一个标准的研究课题”。[1]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关系研究中,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是这一直也没有成为一个“标准的研究课题”。因此,本文试图阐明产生这一现象的缘由以及关于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研究的重要理论意义,借用并完善卡弗的研究方法,试欲重现被长期湮没的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
一、青年马恩关系:一个被湮没又被重新发现的问题
在西方“马克思学”(Marxologie)研究中,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一直是其重点研究问题之一。西方马克思学奠基人吕贝尔认为:“这个问题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这一点,表明有一种很能说明我们时代特征的现象,这个现象可以称为‘20世纪的神话’”。[2]但是我们发现,在众多经典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著作中,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问题则经常处于被避之不论或被大而化之的境地。
如马恩“对立论”的倡导者诺曼·莱文在其名著《悲剧性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中声称,传统马克思主义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而应称为恩格斯主义才更恰如其分,因为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机械唯物主义、社会实证主义、工具理性和清教徒式的职业道德伦理等都来源于恩格斯。[3]莱文虽然详尽地说明了“恩格斯主义”与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对立,但他对早年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关系没有做出合理的考察。在其另一本著作《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中,虽然作者专辟一章详细说明了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借用,认为青年恩格斯与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不同的借用方式直接构成了他们青年时期思想的主要分裂,[4]但可惜的是,作者只限于强调二者在理解黑格尔方面的对立,并没有对二者在其它方面的思想关系进一步展开论述。英国著名马克思学家麦克莱伦在《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中,虽然提及青年恩格斯与青年马克思的学术思想关系,但只是概略地说明了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发生了决定性影响。[5]另一位英国马克思学者李希特海姆在其产生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和批判的研究》一书中,利用马克思最终定稿的《共产党宣言》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之间的文本差异,详细地指出了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之间存在的学术差异,但作者只是根据这两个本文所作出的比较,就简单地把恩格斯划为“技术决定论”者,并将其与强调生产力毁灭性的马克思对立。[6]
在国内学术界,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持马恩差异论的俞吾金先生在其《问题域的转换》一书中,详细地论证了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与恩格斯的抽象的物质本体论的唯物主义之间的差异,并条分缕析地论证了“恩格斯式的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传统的形成,[7]但是,关于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问题却没有被提及。在《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中,张一兵先生对青年马克思的文本虽然做了系统的理论阐述,但在论及二者青年时期关系时,作者只是笼统地认为“赫斯与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影响了马克思,促使他转向经济学研究”。[8]
实际上,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早在马克思在世时就已被提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当中,马克思明确说明了“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讯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9]但是马克思没有使这两条道路明朗化,另外,作为被解释对象的“另一条道路”是否真正达到马克思的“结果”?这在马克思后来的反思中没有明确出场。由此可以看出,这两条道路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并没有被完整地展现出来。
找出这两条道路并使之明朗化的任务就落到了阐释者的肩上。恩格斯自然首先充当了这一角色。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首次为我们完整地提供了他对这种“结果”的理解。比较这两种理解可以直接帮助我们指认恩格斯的阐释是否已达到了马克思所达到的结果。对此进一步的追问就是恩格斯的这种阐释何以可能?如果说恩格斯在此已完整地对马克思所谓的“结果”作出了阐释,那么恩格斯在对待马克思文本时的“视界的融合”是何以可能的?马克思的文本是否存在着诱发这种“融合”的酵素?就此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问题首次被展露了出来,同时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问题的重要性也随之浮出水面。
作为被阐释语境下的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关系问题至少直接关涉到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尤其是青年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首次运用经济学范畴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这一做法,是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转向的重要触动器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这直接牵涉到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是否存在着一个“认识论断裂”时期的问题,而这是“两个马克思”与“一个马克思”之争的关切点所在。
第二,青年恩格斯的思想状况如何,他是否达致了马克思所认为的“一样的结果”?由于马克思没有对“两条道路”做过具体说明,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补充就显得尤其重要,这为我们理解青年恩格斯的思想提供了一把便捷的钥匙。
第三,为什么青年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突然中断而“让位”于马克思?这是否与马克思的合作有关?恩格斯的这一中断在马恩以后思想发展中是否产生了微妙的影响?[10]
第四,恩格斯晚年的思想是否是其青年时期的思想顺理成章发展的结果?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晚年恩格斯思想得到广泛地传播而青年恩格斯的思想为什么一直处于失语状态?
二、“对立论”:青年马恩关系研究的缺场
众所周知,“对立论”的发端与流行,是意识形态因素与马克思学研究本身相互促成的结果。虽然它在推进马克思思想研究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研究背景与研究方法的影响,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思想关系的研究。
的确,马克思与恩格斯观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在20世纪初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就有过相关论述。譬如: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批评恩格斯错误理解了马克思的辩证法概念。在卢卡奇看来,恩格斯的主要错误在于把辩证法看成是概念形成的辩证关系而忽视了“主体与客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辩证关系”,从而使辩证法失去了革命性的作用。[11]可惜的是,由于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斗争的需要,卢卡奇没有详细论述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关系问题。[12]如果说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马克思与恩格斯主要以共同合作的伙伴关系而出现,而他们之间的差异主要是一些个别主张的不同,那么在20世纪60年代后的西方马克思学研究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则主要以相互“对立”的姿态出现。“对立论”主要代表人物有:阿维内里、吕贝尔、科拉柯夫斯基、诺曼·莱文等。他们罗列出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对立的观点,概言之:
(1)哲学方法论的对立。虽然卢卡奇没有明确阐释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哲学方法论上的对立,但是他提及的恩格斯对辩证法的错误挪用却为后来的“对立论”者提供了一条屡试不爽的出场路径。如莱文认为,“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在哲学观上的对立,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同理解。由于没有理解黑格尔的对象化及辩证法中的主体因素,恩格斯否认主观意识的重要性,坚持一种理性泛神论的信念,认为普遍观念是历史的决定性的推动力。[13]晚年恩格斯继续坚持这一思想并把它运用到自然,认为整个自然界就是由物质和运动两大因素所构成,因此,恩格斯基本上是一个形而上学家。[14]与此相反,马克思则娴熟地利用并发展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主体方面。辩证法的本质不在于对自然或社会做出一种理性泛神论的解释,而在于坚持人的辩证的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恩格斯是从来不了解的。[15]所以,莱文进一步认为,“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的对立就在于这种哲学方法的根本不同。[16]
(2)社会发展观的对立。马克思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多线发展的社会更替模式,恩格斯所提供的则是五大社会模式依次更替的单线发展模式。马克思的立场是,《资本论》中所阐述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只限于西欧各国;对历史、地理环境不同的其他国家来说并不必然存在一种“历史必然性”,比如俄国社会就可能完全走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17]诺曼·莱文认为,这与恩格斯的历史观截然相反。因为恩格斯在分析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时,认为俄国只能走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论俄国社会问题》中,恩格斯驳斥了当时俄国的民粹派的下述观点:俄国没有必要经过封建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再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为俄国特有的农村公社是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基础,他认为生产落后的俄国不能直接跨过资本主义的这个“卡夫丁峡谷”。而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反杜林论》中,恩格斯的这种历史发展观进一步成了经济与技术决定论。[18]阿维内里甚至认为,正是恩格斯这种思想的影响使得马克思主义走向了机械论与决定论,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粗鲁与残暴,社会民主党思维上的荒原,直接来源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机械歪曲”。[19]
(3)解放道路的对立。马克思的“解放”观承接的是早年的“异化”思想,而恩格斯承接的则是早年在对私有财产的认识中所达到的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的“解放”不是靠单纯的“消灭”资产阶级,而是以扬弃整个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为前提。因为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所产生的物化现象,不但使工人而且使整个人的存在方式都发生“异化”,这种异化普遍存在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当中。因此,这种解放是一种“人本主义”的解放,它是早年“人本主义”的马克思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恩格斯由于坚持带有技术决定主义色彩的抽象唯物主义哲学观,他的“解放”的含义更侧重于工人阶级物质利益的解放,即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解放。本德认为恩格斯的这种观点“已经失去了他的无产阶级革命角色的意识,显然地相信共产主义在平等、安逸、产品的极大丰富和合理地有计划的生产方面极为富足——但没有强调自由与自我创造”,而这与马克思的“解放”思想是绝然对立的。[20]
纵观这些方面,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持“对立论”的西方“马克思学”者的分析方法有失偏颇。他们所利用的主要是“错位分析法”,即拿晚年恩格斯的文本与马克思某一时期的文本相比较来寻找二者的思想差异。很显然,在这种分析方法中青年恩格斯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关系是缺场的。另外,这种“点菜”式的比较,即脱离特定思想所凭依的文本情境来寻找文本之间的异同,容易产生立论的武断性。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存在的不足,也直接导致了同样持“对立论”的学者相互之间产生一些观点的冲突与对立,甚至自身同自身观点相互对立。[21]
三、“一致论”:青年马恩关系研究的冷场
意识形态的需要与影响,使得冷战结束前的苏联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都强调马克思与恩格斯是共同的伙伴关系和完美的合作者。而强调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的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在20世纪50、60年代的苏联被称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恶意歪曲,在80年代的中国,它同样也遭到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严厉批判。
熟悉马克思主义运动史的人都知道,工业无产阶级政党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才真正出现,因此,在工人阶级政党出现之际就已存在着“马克思的理论和无产阶级实践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不平衡的和间接地:两者之间很少直接相合”,[22]这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的接受情况和这些著作的涉及范围中可以看出来。从第二国际到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在苏联公开发表的这段时间里,众多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们对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理解主要集中于《资本论》和恩格斯晚年的几部著作,甚至连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权威们如拉布里奥拉、梅林、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理解也仅停留于此。这种理解使得他们理论努力的主要方向是如何使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有关人和自然的全面理论加以系统化,所以他们更加关注的是晚年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的著作。这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晚年恩格斯的过度阐释,造成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以恩格斯的思想为内容而出现和流传。从这一层面来看,莱文所主张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应该被称为“恩格斯主义”才更恰当具有一定道理。另外由于马克思没有留下完整的国家理论,有关工人阶级政党为推翻资产阶级国家而进行革命的具体战略、战术的政治理论,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治理论的成功补充,进一步使得这一解释传统获得了不容置疑的地位。[23]
处于这种解释传统下的马恩关系研究单调、独断,缺乏一定文本根据,其主要观点就是: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与恩格斯都是持唯心主义立场,由于受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冲击,马克思与恩格斯各自从不同的道路从唯心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由于把自然辨证法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马克思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则是自然辨证法的奠基人。由此,马克思与恩格斯便成了完美的合作者,而他们合作之前错综复杂的关系则被简单地归为唯心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说,处于这种解释传统压力下的“一致论”研究漏洞百出,对于真正认清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基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脱离意识形态影响的“一致论”研究却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其代表人物有古尔德纳、亨利、里格比。他们根据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本身,做到了有据可查、有章可循地具体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本身中的思想异同,而不是那种脱离文本式的对“对立论”者做一番义愤填膺的道德谩骂,再发些慷慨陈词就了事的驳斥。
如“一致论”倡导者亨利在《恩格斯的生活与思想:一个重新解释》中对“对立论”主要论点的驳斥完全以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具体文本为依据。例如,针对卡弗主张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发表《共产党宣言》后就再没有真正合作过的观点,亨利认为卡弗忽视了《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独自署名发表在《纽约论坛报》、《普特南氏月刊》和《美国新百科全书》等等的这些文本。通过对马克思与恩格斯众多被忽视的文本的比较,亨利得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工作过程的不同阶段中有着许多重要的合作”。[24]
另外,针对一些“对立论”者认为恩格斯篡改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3卷的内容并使之更加实证化的指责,亨利认为这些人忽视了恩格斯编撰工作的艰辛和马克思手稿的不完整性,而且恩格斯的编撰并不像他们所指责的那样“实证化”。譬如,莱文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14章和第15章的论述,反对人们仅根据《资本论》第3卷第13章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利润率必然下降规律的论述就认为马克思是实证主义者。莱文认为,马克思紧接着在第14章和第15章中就列出了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一些内部矛盾,这些矛盾足以揭穿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虚假性。但是亨利指出,莱文的论证完全忽略了杰罗德·西格尔的研究成果。西格尔发现恩格斯重构了马克思手稿中第13章和第14章的内容,使影响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诸因素获得了比原稿中更具独立性的地位。西格尔认为正是恩格斯的修改才使得马克思对利润率实证化的论述稍显辩证化,甚至第十五章的标题“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也是恩格斯所写。[25]因此,亨利认为,莱文为马克思的非实证化辩护的论据并不合理,以这些文本来论证恩格斯对《资本论》的修改具有实证化倾向是根本错误的。
这些学者虽然立足文本本身,采取相对客观公正的比较分析方法来剖析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但是由于他们并没有跳出“对立论”者所凭依的分析理路,仍是沉浸在这种外科手术式的解剖方法当中。因此,他们对马恩关系的分析偏重于局部的细节差异,忽视整体的关联,最终只会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看法。结果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变为众多孤立而又对立的幽灵同时出场,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关系则退为一段可有可无的历史,只是偶尔被迫登场。
四、“差异论”:青年马恩关系研究的开场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问题上,“差异论”采取一种温和的立场,既不像“对立论”那样极端,也不像“一致论”那样独断,可以说,它是一种弱化了的“对立论”。“差异论”基本上肯定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的一致性,但又认为他们在个别主张上存在着一些差别,主要代表人物是卡弗。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一书中,卡弗比较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前各自的思想状况,并具体论证了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马克思产生的巨大而持久的影响。[26]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青年马克思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这在学术界得到一致的认可。但是卡弗甚至认为,“马克思在1843年所主张的方法论——对当代政治问题进行分析、对政治家和哲学家所使用的现有分析范畴进行无情的批判、避免先验的看法和学说……在恩格斯1842年底的文章中都得以明确地体现”,“最值得注意的是,1844年初,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文章所作的摘要以若干压缩的短语预示了他终生工作的方向”。[27]
当然,这个分析并非完全正确。因为马克思曾明确地表述过自己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机:“1842 -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28]并且马克思认为他在德法年鉴时期的研究已经认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9]这在马克思1844年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两篇论文中得到了印证,特别是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及了“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解放出来——因而是从实际的、实在的犹太教中解放出来——就会是现代的自我解放了”。[30]另外,从马克思的文本考证方面的成果来看,我们也可以发现卡弗的论述有失偏颇。1844年左右,马克思作了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学的摘要笔记即《巴黎笔记》,从中我们发现,马克思阅读了近20位作者的经济学书籍,做了百多页的笔记摘要,其中包括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但对《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摘录所占的篇幅仅仅只有一张插页。[31]
不过,卡弗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较好的阐释路径。卡弗认为理解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的关键点是马克思的逝世,因为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独自担当了重述马克思思想以及“我们的观点”的任务。因此,卡弗的分析主要集中于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所重构的历史。在卡弗看来,正是这段时期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重构,铸成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形成以及这个传统中“马克思”形象的诞生;但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关系的原貌同时也就被遮蔽了,变得“含混不清”。[32]卡弗所主张的这种“差异理解”的分析方法,有助于重新发现在诠释过程中被遗忘的“第二小提琴手”,卡弗断言“多年后,恩格斯的作品会比马克思的作品更具有戏剧性的变化”,从近几年来学界对恩格斯作品理解的变化来看,卡弗的断言较为确凿。
可以看出,这种研究方法区别于外科手术式的解剖分析,它能完整地再现他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因为它没有事先设定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或一致,并且没有预先设定某个观点,再在马恩文本中寻找其相应的表达,然后再论述其异同,它主要是根据解释学视域中的“视界融合”问题来整体地提出马恩关系的。由于视域的融合,解释者在理解他者文本时必定要打上自己思想的烙印。因此,我们必须重新省视恩格斯的解释传统,此时二者都需要被读者阐释清楚,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能同时出场。尽管如此,卡弗并没有详细地廓清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思想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主要原因在于卡弗虽然注意到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的阐释可能存在理解的差异,但他忽略了合作者相互之间也可能在理解对方时存在一定的张力。因此,马克思逝世前与恩格斯合作的这段时期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有两个文本凸显了其重要性:《共产党宣言》和《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一个文本的重要性在于《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修改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的产物;第二个文本是恩格斯应邀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作的匿名评论。由于没有相关的材料表明马克思是否对恩格斯的阐释有微辞,这就更加使得二人的关系显得扑朔迷离,因此分析他们在做阐释前各自的思想状况就显得格外重要。
笔者认为,尽管“对立论”与“一致论”在某些主张上大相径庭,但是由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基本一致,他们最终无法使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成为一个“标准的研究课题”。以卡弗为代表的“差异论”由于引入另一种文本阐释方法使得马恩关系研究的视角发生了改变,这种方法不但能够完整地再现出晚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而且通过补充和完善,它也能够重新发现被湮没的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
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同样,在思想史的长河中也没有两位完全相同的思想家。马克思与恩格斯虽然共同合作近40年,但是这无法掩盖他们思想上的不同。利用上文所述的研究方法,这就必然追溯到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关系问题。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问题是个值得探索的研究领域。在此再次申明,卡弗的所主张的阐释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逝世至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研究史中依次出现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论,“共同冒险的伙伴关系”的“一致论”,对立论弱化形式的“差异论”。
[1][10][26][27][32]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前言、51、39-51、38-39、138.
[2][31]吕贝尔.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5、265.
[3][14][15][16][18]Norman Levine.The Tragic Deception:Marx Contra Engels,Clio Books,1975.xiv. 115-116、119、231、157-160.
[4][13]诺曼·莱文.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56、149-150.
[5]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6-47.
[6][21][24][25]J.D.Hunley,The Life and Thought of Friedrich Engels:A Reinterpreta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49-52、55-64、142、57-58.
[7][23]俞吾金.问题域的转换——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当代解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61-100、61-128.
[8]张一兵.回到马克——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122.
[9][28][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31、32.
[1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50.
[12]张亮.西方“马克思学”对恩格斯研究中的误解[J].教学与研究,2005,(8).
[17][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4-775、192.
[19]Shlomo,Avineri,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1968. 143-144.
[20]Frederick L.Bender,The Betrayal of Marx, New Y ork:Harper and Row,1976.28-29.
[22]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0.
——高考议论文写作中精准立论的思维策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