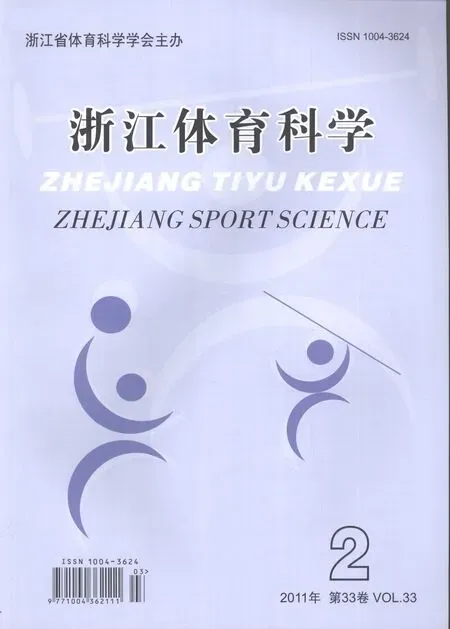唐代体育文化的传播与接受
王俊奇
(南昌航空大学体育学院,江西南昌330063)
·体育史学·
唐代体育文化的传播与接受
王俊奇
(南昌航空大学体育学院,江西南昌330063)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地主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使唐朝出现了巨大社会结构变动,主要是哪些庶族寒士登上了中国文化舞台,并成为上升的世俗地主阶级的精英分子,这些文化精英对自己的前途与未来充满自信和一泻千里的热情。唐代文化因而具有一种明朗、高亢、奔放、热烈的时代气质。
唐代;体育文化;传播;文化交流
Abstract:Tang Dynasty is at the peak of China’s feudal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Som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landlord class in Tang dynasty lead to a dramatic change in social structure.Scholars from impoverished background,confident in and enthusiastic about their own future,board the Chinese cultural stage and become elites of the secular landlord class.Tang Dynasty’s culture thus has a clear,sonorous,flowing,warm temperament of the times.
Key words:Tang Dynasty;Physical Culture;Communication;cultural exchanges
唐朝以强盛的国力为依据,使其文化首先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虑的兼并包容的宏大气派。唐文化的宏大气魄还体现在以博大的胸襟广为吸收外域文化。南亚的佛学、历法、医学、语言学、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西方世界的袄教、景教、摩圣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艺术及至马球运动等等,如同八面来风,从唐帝国开启的国门一拥而入;首都长安则是那一时代中外文化汇聚的中心[1]。另外,唐朝西域开边拓土,势力最远时曾与伊朗古国相接。这都可以看出,唐朝对外对内的文化交流是空前活跃,一方面大量接受外来文化,另一方面将外来文化吸收,并广为传播。
1 文化的传播概念
文化传播,是指从一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的散布过程。在很长的时间内文化传播的出现是通过具有这种文化的人们的迁徙,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之间人们的互动而出现的。通过文化特征的直接借用或通过借用这种特征中的原理,即所谓刺激传播,对于接受一种文化特征具有影响的诸因素包括:传出文化对于借入文化的实用价值;传出文化被整合入借入文化的难易程度;传出文化的声望;借入文化的保守程度;还有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性等等[2]。
里弗斯认为:“研究各族相互关系对于了解他们的文化发展是重要的。各族的联系及其文化的融合,是发动各种导致人类进步力量的主要推动力[3]。”什么原因促成了文化的流传?流传的过程是什么时间和通过什么方式发生的?研究民间叙事的本菲认为,战争、民族迁徙、文化经济的交流,促成了民间叙事在不同民族中间因袭流传。拉策尔认为,文化要素是伴随民族迁徙而分散的,所以他相信这些被分割了的要素,互相之间必定保持着历史上的联系[4]。拉策尔提出:“文化要素只有通过人,同人一道,随着人,在人身上,特别是在人之中,即在人的心上,作为一种模式的思想萌芽,才能传播。因此,民族学所研究的文化对象是同它的代表者一道移动的[3]。”
文化传播是文化发生、发展的特征之一,无论何地、何种文化,都有这样一种传播过程。文化传播主要是通过人或群体的迁徙,从一地到另一地,从一群人到另一群人,而且不同的人对文化的传播也会不同。借入文化对传入文化有选择,借入文化会让传入文化适合自身的要求,有价值的传入文化最容易被接受。
针对传播论对文化要素的机械理解,博厄斯认为文化现象不是处于真空之中,不能把它理解为机械的组合,文化的借用是发生在各种文化背景下面的具体事实,因此他强调必须细致地调查特定文化的所有侧面;特别是作为文化载体的人的心理情况。一个外来文化要想进入新的文化环境,并生存下来,必须经过新的接受群体的选择、学习和改造。由于人们原来文化传统的制约,文化的传播总是要有一个适应新的文化环境过程,文化历史的复杂性提醒我们要看到文化是一个衍生体系[5]。
唐朝是封建社会一个文化大交流的时代,它既传承汉以来的传统文化又与西域以及东南亚、西亚进行文化交流,并吸取异文化中的精华为自身发展提供养份。从而出现了盛唐具有宏大文化的气象,为宋元文化大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2 唐代体育文化的传播与接受
唐代也是封建社会体育文化的发展高峰,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体育活动都触处可见。从体育项目看,唐代不仅传承了蹴鞠、缘竿、马术、摔跤(相扑)、棋类、武艺 ……,而且还出现了马球、象棋等新的体育项目,在民俗体育方面,如秋千、斗鸡、踏春、赛龙舟也在城乡蓬勃开展,其中有些项目来自西域,也有些项目远播朝鲜、日本、东亚、西亚,甚至欧洲,出现了以唐朝为文化中心的传播流。
众所周知,唐代长安最流行的竞技体育是马球.但马球并不是起源于长安。据学者们考证,马球起源至少有三种说法,如史学家向达、罗香林先生曾对击鞠(马球)的起源作过考证:“波罗球,为一种马上打球游戏,发源于波斯。向达在1933年出版的《燕京学报》(专号之二)刊载的《长安打球小考[3]》一文就说:“波罗球(即马球)传入中国当始于唐太宗时。唐以前书只有蹴鞠,不及打球,至唐太宗,始令人习此。”马球之球藏语谓之“波罗”,唐代所谓之“金颇罗”当时指此而言。马球在汉地直传到明代,同时也传至国外。欧美及阿拉伯语称“球”为“颇罗”,均源自藏语。马球后来被唐朝做为训练骑兵的“军中常戏”,因而“虽不能废”。1972年在乾干陵发掘唐章怀太子李贤的墓,其墓道西壁上即绘有完好的彩色马球比赛图,可知吐蕃马球戏在汉地影响之深了。其后,由土耳其斯坦传入中国。日本、高丽亦有此戏,则又得自中国者也。”(向达《长安打球小考》)对此,阴法鲁教授已于20世纪50年代着文做过详考,阴法鲁先生在《唐代西藏马球传入长安》一文中认为马球始兴于吐蕃(现在的西藏)。唐代,吐蕃人兴起,其基本民众主要是羌人,其王室则可能是从喜马拉雅山另一侧过来的雅利安人。吐蕃和唐王朝的关系是复杂的,对中原文化既有斗争也有合作,既有威胁也有补益。唐初为了安定边防,与吐蕃人和好,于是吐蕃商贾云集长安。同样也带来本民族的体育活动,如马球便是其中之一。文献记载说:“太宗尝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此亦令习。”(《封氏闻见记》)。吐蕃另有“骑马之戏”,在长安也受到皇室官员的赞赏,此“骑马之戏”似即马术。桑耶寺落成时举行过盛典,其间即有精彩马术表演。据《全唐诗》载:“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正月五日,移仗蓬莱宫大明殿,会吐蕃骑马之戏,因重为柏梁体联句。”?可见唐初,吐蕃人已经在长安中心广场文化区打马球,并讲马喜引入长安。从太宗说的话来分析,这时长安人还不会打马球,中原打马球应是唐太宗之后,主要是西藏人带进并首先开展起来的。
约从唐中宗开始,马球至少在宫中盛行开来。《资治通鉴·中宗纪》说:“上(中宗)好击球,由是通俗相尚。”皇帝喜欢打马球,其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大的。罗香林先生在《唐代波罗球戏考》中说:唐代马球风行一时:“国君嗜好于上,武臣效尤于外,而佳人宠佞竞相讲习,以投时好,百业寝废,唯务击球。”从文化传播学角度说,马球文化在唐长安的出现和流行,首先是具有会打球的吐蕃人作为文化的传播者,而在接受的一方认为该文化有价值。唐朝统治者最初接受马球并非为了娱乐,而是认为马球对训练骑兵有实效作用。“伊击鞠之戏者,用兵之技也。”(《温汤御球赋》)。当然,一种文化的进入并被借入文化接受,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之互动是很重要的。仅从文献记载上看,马球文化在吐蕃与宫廷球队之间至少有两次正规的交流。如景龙三年(709年)吐蕃派遣使者来迎接金城公主入藏,带来了一支草原上的马球队,宫廷先派内园马球供奉与吐蕃球队比赛,结果“决数都,吐蕃皆胜。”吐蕃球队连胜几场,把唐中宗急坏了,于是下了一道圣旨,令嗣虢王李邕、驸马杨慎交、武延秀和临淄王李隆基四人上场,敌吐蕃十人。赛场上“玄宗(李隆基)东西弛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终于胜利,为大唐挽回了面子。
唐代来自西域的体育典型的还有百戏中的许多技巧。据《旧唐书·音乐志》中记载:“苻坚尝得西域倒舞伎。睿宗时,婆罗门献乐舞人倒行,而以足舞于极銛,刀锋倒植于地,低眉就刃,以历险中。又植于背上,吹筚篥者立其腹上,终曲而亦不伤。又优(人)伸其手,两人蹑之,旋身绕手,百转无已。”苻坚是前秦国主,说明唐以前西域技巧已传入中原。一个外来文化要想进入新的文化环境并生存下来,必须经过新的接受群体的选择、学习和改造。唐朝是一个十分开放的国家,而且也是敢于冒险和有创新精神的朝代,对来自西域的乐舞百戏更是喜欢,如唐代设有专门练习与排演舞乐的教坊:“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工舞,盖相因成习。”(《教坊记》)并且对汉以来的各种伎艺动作进行了适合唐朝文化的改造,首先在动作难度上有所改造,如戏马、高竿伎比之汉晋更为惊险可观。
其次,唐代伎巧运动趋向女子化发展。如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千秋节时,杂技表演的走索、“伎女从绳端蹑足而上,往来倏息之间望之如仙。”其中女伎还表演“有中路相逢侧身而过者;有著屐而行之,从容俯仰者;或以画竿接胫,高五六尺;或踏肩蹈顶至三四重,既而翻身掷倒至绳,还往曾无蹉失。皆应金鼓之节,真奇观者。”这里提到的双人走索,穿屐走绳,徒步走索,难度不小。说明唐代在伎巧运动方面对西域文化进行了不少改造。那么为什么汉晋西域技巧在唐代得到如此大的改造与创新呢?一方面是唐代文化开放有关系,另一方面是文化传播的又一特征。文化传播学上,把通过文化特征的直接借用或通过借用这种特征中的原理,即所谓刺激传播。刺激传播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欧洲知道了中国瓷器几乎200年以后才发明瓷器。唐代对数百年前传入的西域技巧进行改造、创新,也应是这种刺激传播的道理。
刺激传播,实际上与文化接受的时间,和借入文化对传入文化的整合有关系。博厄斯认为,文化现象中蕴涵着历史,每个文化特质的历史都是复杂的,每个民族文化的整合过程都是独特的。博厄斯把文化的整合看作是主要发生在主观领域里的事件,文化整合于是表现为文化特质依照一个群体的某些支配性的概念或态度被日益修正。文化传播是无休止的,文化整合就成为运动不止的一种趋势,在这样的趋势中文化整合永远不可能达到周全和完善。博厄斯注意到,每个民族的文化纹理的确存在无数迥异的线索,“翔实的材料证明,无论是各种产品还是生活习惯,其形成总是不断变化着,有时经过一段时间的稳定之后,又会发生迅速的变化。在这种变化过程中,有些文化因素乍看起来属于某些文化单位,但不久又会各自分离”,有的继续存在,有的至此消亡。从客观来看,文化形式本身就是一幅丰富多彩并且变化无穷的画面。随着各个民族变化着的精神背景,许多分散的现象变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不断改变着自己的面貌,各种文化因素结合得越好,这种文化形式本身就越显得富有价值[6]。”
在唐代舞蹈中有一种健舞,即敏捷刚健、富有节奏。这种健舞多来自西域和周边少数民族。据文献记载,唐代的健舞主要有胡旋、胡腾、达摩支、拓枝、阿辽、竿舞、斤斗舞、绳伎舞、球操等。这些舞蹈对宫女健身起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宫廷专门用这些舞蹈来训练宫女的身材。这些健舞大多来自西域少数民族,甚至西亚的一些国家。有的健舞在魏晋时期已引进中国,但在唐代宫廷对这类舞蹈进行利用和改造是以往没有做到的。据《旧唐书》记载,武则天曾亲自排演了“舞之行列必成字”的“圣寿乐”,又称“字舞”,“上元圣寿乐,高宗武后所作也。舞者百十人金铜冠,五色画衣,舞之行列必成字,十六变而毕,有‘圣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万年,宝祚弥昌。’皆擂六鼓,杂以龟兹之乐,声振百里,动荡山谷。”(《旧唐书·音乐志》)其中“龟兹”,古西域国名,又作鸠兹、屈茨、归兹、屈支、丘兹等。在今新建库车县一带,自古新疆民族擅长舞蹈、音乐。武则天为了使“字舞”更有气魄、更美观,在排练中吸收了各种优秀的舞蹈。唐代诗人王建有过描述:“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丝,每遇舞头分两项,‘太平万岁’字当中。”这种体操是按队旋转,且走且舞排成字,参差高下如龙之宛转的“字舞”,排练时难度是很高的,因其气势恢宏,被后人称作唐代的大型团体操。
3 结 语
由上可见,马球也好,舞蹈、伎艺也罢,这些西域或别国引进的体育文化,在唐代传播中都进行了选择与改造,以适应唐朝自身文化的需要。一种异文化元素进入新的环境就被塑造来适应新的文化环境,所以分辩文化历史的两个过程——传播与修正,是解释文化与阐释意义的关键原则,唐代体育文化蓬勃发展,一方面是文化内部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多元文化的碰撞、融合、适应与整合,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唐型体育文化。
[1]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74-75.
[2] 谭光广,等.文化学辞典[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129.
[3] C·A·.托卡列夫[前苏].外国民族学史[M].汤正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67.
[4] 绫部恒雄编.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之克拉克特·彼得:文化传播主义[M].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文化室,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5] 孟慧英.西方民俗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18.
[6] 弗朗兹·博厄斯[美].原始艺术[M].金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On Communic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Physical Culture in Tang Dynasty
WANGJun-qi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63,China)
G812.9
A
1004-3624(2011)02-0110-03
2010-07-27
王俊奇(1956-),男,教授,主要从事体育文化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