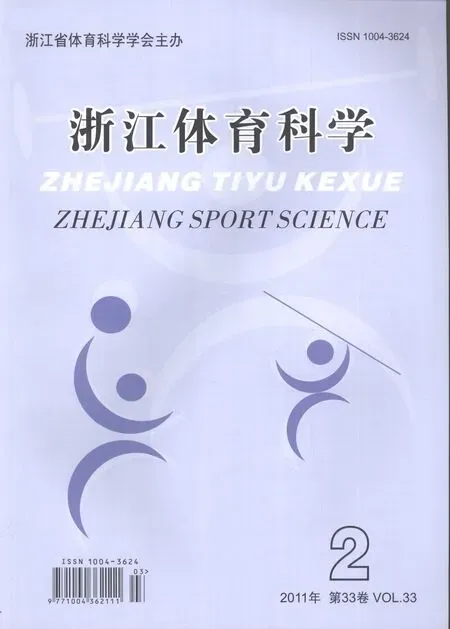我国农村体育现代化溯源
傅振磊
(绍兴文理学院体育学院,浙江绍兴312000)
我国农村体育现代化溯源
傅振磊
(绍兴文理学院体育学院,浙江绍兴312000)
运用文献资料和历史逻辑分析方法探索我国农村体育现代化起源问题。结果显示:在20世纪20、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通过发展乡村教育、促进乡村建设,将现代体育引入农村,并传播现代体育思想及其生活观念;共产党人将现代体育思想与我国农村社会现实相结合,传播现代体育,成立统一的体育管理组织,形成了苏区体育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与苏区体育运动使我国农村体育发生深刻变化,并呈现出某些现代化特征,共同开启了我国农村体育现代化之门。
农村体育现代化;乡村建设运动;苏区体育运动
Abstract:It researches the origination of rural areas sports modernization in China by the way of analyzing documents and historical logic.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drive of constructional rural areas leads modern sports into rural areas and spreads the modern sports idea by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The Communist Party connect the modern sports idea with our country reality,spread the modern sports and set up the unite sports organization.Furthering the Soviet Areas sports come up.Both the drive of constructional rural areas and the Soviet Areas sports change the rural areas sports,and the rural areas sports shows modernizing traits in China.They simultaneously open the door of rural areas sports modernization in China.
Key words:rural areas sports modernization;drive of constructional rural areas;Soviet Areas sports
0 前 言
在2010年第2期《浙江体育科学》杂志上,笔者提出了“中国农村体育现代化”问题,认为农村体育现代化属于我国近代社会历史上所存在的客观事实,是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深入展开,在我国农村体育领域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并表现出组织管理法治化与民主化、社会功能世俗化与生活化、体育设施多样化、体育技术传播知识化以及体育格局和谐化五个主要特征[1]。那么,我国农村体育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这些深刻变化的呢?由此便引发出另一个重要问题——我国农村体育现代化起源。通过梳理并分析相关文献资料发现,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体育开始传入中国,并在大中城市的部分学校里有所开展;军队中也施行了与西方体育有一定联系的“洋操”。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广大城乡的人民群众中仍以传统体育活动为主[2]。直到20世纪20、30年代,在“乡村建设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体育运动的引导与推动下,我国农村体育现代化才悄然兴起。
1 乡村建设运动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一部分知识分子精英的倡议与推动下,发起了“以挽救中国农村社会危机,进而挽救整个中国危机,并建立民主政治”为目的的乡村建设运动,西方现代体育也藉此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开始传播。然而,乡村建设运动又有三种不同意见:一是主张从教育农民入手,其代表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初主持的河北定县实验的主张与做法,此为“平民教育派”;二是从改良农业技术、提高农家收入着手,其代表是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与吴江农业推广实验区的主张与做法,此为“经济建设派”;三是从组织乡村自治着手,其代表是梁漱溟等在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实验中的主张与做法,此为“乡村建设派[3]”。在乡村建设运动实践中,三大学派都将西方现代体育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尤其“平民教育派”与“乡村建设派”在农村体育现代化建设方面成就斐然。
1.1 平民教育派的乡村建设运动
1926年,以晏阳初为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选择河北定县为乡村教育实验区,并在定县翟城村设立办事处,开展乡村建设各项工作。平民教育派认为,愚、穷、弱、私是我国乡村普遍存在的社会现实问题。为挽救农村危机,实现民族再造。根据以往从事平民教育的经验与教训,晏阳初提出了一整套解决这四大社会现实问题的方法,即对农民进行以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与公民教育为内容的“四大教育”。文艺教育包括文字教育与艺术教育两部分,培养农民的知识力,专攻愚;生计教育培养农民的生产力,专攻穷;卫生教育培养农民的强建力,专攻弱;公民教育培养农民的团结力,专攻私[4]。而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与公民教育的“四大教育”内容须通过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与家庭教育“三大教育方式”进行。学校式教育以文字教育为主,并注重个人的知识传授与基本训练;社会式教育以讲解与直观感受为主,并注重团体的共同教学;家庭式教育是中国特殊的一种方式,欲改善中国的生活方式,必须从家庭做起[5]。在卫生教育方面,通过社会式教育宣传卫生保健知识、身体锻炼方法,以改善农民身体“弱”的社会现实,达到提高农民的身体健康水平目的,而且,农民运动会这种现代体育形式也成为社会式教育的一种有效途径。
1927年2月,陶行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发起人之一)在南京开办了“晓庄中心小学”,并于1929年3月更名为“晓庄学校”。据说,晓庄学校开学时规模很小,一共只有13名学生,开学那天,从燕子矶出发,大家穿着草鞋,扛着帐篷,拿着绳索,到了一片荒坡的晓庄,搭起四座帐篷,向农家借了一张桌子,几条板凳,就此在炮火喧天革命紧张之际正式开学;在田野山林中,在农民队伍里,过他们教学做的生活,老师和学生都分住在帐篷里、农家破屋里,或者借助附近的乡村小学[6]。在成立初期,晓庄学校就十分重视对农民的改造。首先是成立民众学校,对农民进行识字教育;其次是设立中心茶园,对农民进行休闲教育,并且中心茶园配备了乒乓球、象棋等体育娱乐器材;再次是创办晓庄医院,对农民进行科学卫生教育;第四是成立晓庄剧社,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第五是联村自卫,将农民组织起来,开展防匪防盗的自卫活动[7]。从晓庄学校对农民的改造活动中可发现,作为西方现代体育之一的乒乓球成为平民教育派对农民进行休闲教育的内容,它是历史资料记载中,我国农村第一次接触的现代体育活动项目。
另外,平民教育派也十分注重乡村教育的传播。首先是在乡村学校教育中施行“导生传习制”,它源于陶行知的“小先生制”,要求在校学生或毕业生发挥“先生”作用,影响身边农民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其次是利用现代化工具向农民普及乡村建设知识,一是编辑出版农民教育报刊,《平民读物》与《农民报》是当时典型的两种农民报刊;二是利用广播无线电这一现代化传播工具为普及社会教育服务,播音材料包括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以及休闲教育等内容。他们为农村体育的技术传播知识化奠定了现代化基础。
1.2 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运动
1931年6月,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在山东成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并选定山东邹平作为乡村建设实验区,开始进行乡村建设实验。首先是设立村学乡学。它是梁漱溟以我国古代吕氏乡约为蓝本所设计的一种政教合一的乡村组织,有学董、学长、教员与学众四部分人组成,学董必须是村中或乡中有办事能力的人[8]。根据乡村建设研究院制定的《设立乡学村学办法》,其主要工作又分为学校式教育工作和社会式教育工作。在学校式教育工作中,村学乡学课程设置基本上与国民教育差不多,主要有国语、算术、自然、历史、地理、卫生、音乐、体育以及公民教育等内容,最大区别在于村学乡学所使用教材是根据乡村实际需要而自行编写的。在社会式教育工作中,村学乡学都有责任和义务倡导本村或本乡所需的社会改良运动,如:移风易俗、卫生健康教育,同时,兴办各项社会事业,如:兴办合作社、植树造林等[7]。由此可以看出,将国民教育的学校体育完整内容体系引入农村,并成为农民受教育的内容是乡村建设派所做出重的要贡献,而当时的学校体育课程设置已是一个以现代体育为主体的体系,包括田径、体操、球类和游戏等内容。
另外,乡村建设研究院还定期举办农民运动会以推动农村社会式教育工作。运动会设立项目有拔河、投掷、武术、篮球、射击、摔跤等,一般在每年的农闲季节举行。运动会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县为单位,全县所有的乡派队参加;另一种是以乡为单位,各村和村小学派队参加。有历史资料显示:1934年,乡村建设研究院曾在第九乡中学所在地吴家村举办过一次冬季农民运动会,运动会的比赛项目在村内村外两个场地上进行,村外场地是吴家村南的一片开阔地,四周是400m的跑道,中央竖一高杆,上面悬挂五颜六色的彩旗,投掷、长跑等竞赛项目在这里举行;村内场地设在乡学门前的农场上,比赛项目有拔河、武术和射击。比赛开始前,由各乡小学生表演运动操,唱《朝会歌》、《运动歌》等歌曲。比赛结束后,每个项目的前一、二、三名被请到主席台上照相、领奖。运动会会期一天,傍晚各村代表队结队返村[7]。由此不难看出,在形式和程序方面,乡村建设研究院所举办的农民运动会已具备相当高的现代化水平,并与现代体育竞赛非常相近。
山东邹平实验在当时产生过重大影响,其经验被称为“邹平模式”,并为其他一些实验区所效仿。无锡的黄巷、北夏与惠北等试验区也定期举办农民运动会,组织农民进行田径、篮球以及乒乓球等比赛。徐公桥实验区也积极引导农民从事文明健康的娱乐活动,实验区先后建成体育场、公园各一处,供农民平常业余游息之用,并定期举办民众运动会。在农民训练中,经济建设派的吴江实验区,也参照山东邹平实验区的村学乡学经验,将体育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根据上述论述,20世纪20、30年代所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发展农村教育传播现代体育内容,将现代体育知识与思想的种子撒播在农村;以中心茶园、农民运动会等社会式教育在农村传播现代体育生活观念,引导农民趋向文明健康的现代农村体育生活方式。乡村建设运动使我国传统、保守的农村第一次感受到了现代体育气息,并通过其遍及全国的、各地实验区的示范效应,由此而引发了我国农村体育的深刻变化。
在乡村建设运动中,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乡村建设研究院等社会团体成为农村体育活动的实际组织者与管理者,而非传统的农村封建家族、宗族势力集团,显示了其组织管理民主化特征;乡村建设运动倡导的农村体育面向全部农民,而非某些特殊群体,并以改善农民生活方式为己任,显示了其社会功能世俗化与生活化特征;以接受过专门村学乡学教育训练的“导生”为农村体育的传播者,并借助报刊、无线电台等现代化媒体工具传播农村体育,显示了其体育技术传播的知识化特征;尽管农民运动会的体育场地设施简陋,但也呈现出多样化,且东西体育活动和谐共处的特征。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乡村建设运动时期的我国农村体育都具备了现代化特征。
2 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体育运动
1917年,毛泽东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文章对体育的概念、目的、作用,在教育中的地位,体育锻炼的原则与方法等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提出体育之功效,能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勤体育则强筋骨,强筋骨则体质可变,弱可转强,身心可以并完;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李大钊在《“五一”纪念日对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一文中也阐述了他对现代体育的观点与看法,他认为西洋文明为动的文明,中国文明为静的文明,惟其动也故进取,惟其静也故保守,社会要发展必须“动”,而人的身心健康也要“动”。陈独秀也曾在其主编的《安徽俗话报》上积极宣传现代体育的意义和作用[9]。苏区农村体育发展则是共产党所倡导的现代体育思想与我国农村社会现实相结合的产物。
1927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于井冈山开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此后,又相继开辟了湘鄂赣、闽浙赣、洪湖湘鄂以及陕甘宁等革命根据地,这些革命根据地称为苏维埃区,简称“苏区”。为粉碎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提高军队战斗力,苏区军民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军事训练,这是当时苏区所面临的首要任务。而在军事训练的同时,基于军事、生活上的需要,苏区也开展了众多饶有趣味的体育活动——例如:爬山、赛跑、游泳以及篮球等。毛泽东身体力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亲自带头参加各项体育活动,包括冷水浴、体操、爬山、游泳、打篮球、跳高、跳远等,并亲自领导苏区军民修建大运动场;在当时举行的“八一”运动会上,周恩来负责指挥运动员参加比赛;在运动场地上也经常可以看到朱德、任弼时等打篮球。在苏区各地,工农群众还举行跳高、跳远、赛跑、游泳、秋千、篮球、足球、乒乓球及运动会等各种体育活动[2]。尽管当时苏区物质条件极差,但人民群众还是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地开辟了运动场地,制造了体育运动器材,为开展体育活动创造了必要条件,打篮球用的篮圈、打排球用的球网以及球都是苏区群众自己制作的,田径运动场则利用自然地形修建。1934年1月,毛泽东在《苏维埃区域的文化教育》报告中曾指出,群众的红色体育运动也是迅速发展的,现偏僻乡村中也有了田径赛,而且在许多地方都修建了运动场。
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民主政府不仅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卫生事业,也十分注意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并于1933年“五卅”运动大会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会”,作为组织和领导权苏区赤色体育运动的领导机构,它是革命根据地最早的群众体育组织,其成立后对苏区进一步开展群众体育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后来,还分别成立江西省、福建省以及瑞金县等省、区、县级赤色体育分会,并通过加入“赤色体育国际”决议[10]。根据资料统计,1931年至1934年,仅中央苏区所开展的重要体育比赛就有20余次,包括中央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运动会和各地方各系统的或基层的比赛,既有省、县、乡各地方单位的,也有军队的。
根据上述论述,在较早历史时期,共产党人就已接受并积极传播现代体育思想,并在其领导下的苏区,将现代体育思想付诸体育发展实践,引发了苏区农村体育的深刻变化。在苏区党和政府的组织领导下,成立了全苏区最早的、统一的体育管理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会,还分别成立了省、区、县各级赤色体育分会,形成了较完备的体育管理体系。在赤色体育会组织领导下,苏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群众体育活动和体育比赛。为满足苏区军民的日常生活需要,人们自己动手修建并制作了各种样式的体育场地器材设施,尽管有些简陋,但也表现出多样化、传统与现代共存特征。
3 结 语
乡村建设运动以发展乡村教育、促进乡村建设为目的,将现代体育引入农村,并藉此传播其现代体育思想与文明健康的生活观念,使我国农村体育发生了深刻变化,也使农村体育呈现出某些现代化特征;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体育运动则是现代体育思想与我国农村社会现实相结合的产物,以满足军事训练与社会生活需要为目的传播现代体育,并成立了统一的体育管理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会,也致使我国农村体育发生深刻变化,并呈现出某些现代化特征。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乡村建设运动与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体育运动共同开启了我国农村体育现代化之门。
[1] 傅振磊.中国农村体育现代化之商榷[J].浙江体育科学,2010,32(2):5-6.
[2] 崔乐泉.中国近代体育史话[M].北京:中华书局,1998:2-3,150-151.
[3] 刘豪兴.农村社会学[M].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 宋恩荣.晏阳初全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247.
[5] 晏阳初.晏阳初文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39-40.
[6] 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M].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1935.
[7]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90-91;261-269;315-316.
[8]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一)[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9] 陈晴.清末民初新式体育的传入与嬗变[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0] 谷世权.中国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2.
The Origination of Rural Areas Sports Modernization in China
FU Zhen-lei
(Depatment of PE,Arts and Science College of Shaoxing,Shaoxing 312000,China)
G812.42
A
1004-3624(2011)02-0004-03
2010-12-20
傅振磊(1973-),男,山东人,在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