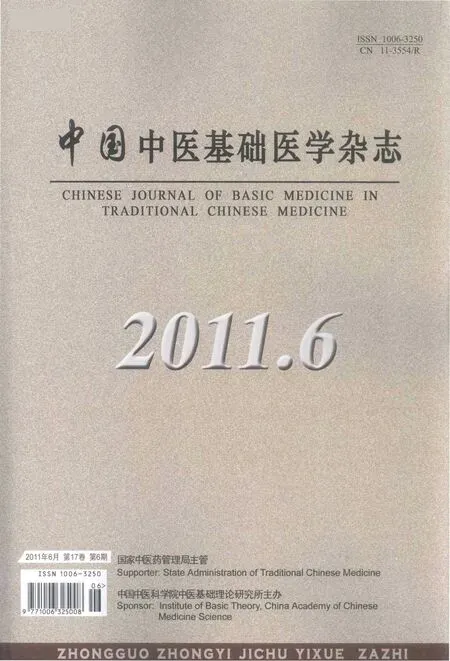郭雍疫病学术思想浅析*
李董男
郭雍(1102~1187年),字子和,河南洛阳人,自号白云先生。早年习儒,爱好理学,后攻于医,至晚年笃好《伤寒论》,精研仲景之学,著有郭雍《伤寒补亡论》20卷。所谓补亡,乃郭氏取《千金方》、《伤寒总病论》、《类证活人书》以及与其同时的名医常器之等人的学说,有合于张仲景论的即补入,并上郭雍自己的论述。笔者试析郭雍诊治疫病思想如下,请诸方家指正。
1 缩小伤寒范围
宋·庞安时、朱肱等人认为,无论伤寒、温病其起因都是冬季触犯寒毒,这一观点颇有影响。而郭雍在《伤寒补亡论》综合晋唐医家所论,提出了不同于此的观点:“初无寒毒为之根源,不得谓之伤寒,第可名曰温病”(《卷十八·温病六条》),即伤寒必须是伤于“寒毒”的,而温病未必伤于寒毒。
他认为,温病不止是1种而是3种:“雍曰:医家论温病多误者,盖以温为别一种病。不思冬伤于寒,至春发者,谓之温病;冬不伤寒,而春自感风寒温气而病者,亦谓之温;及春有非节之气,中人为疫者,亦谓之温。三者之温,自不同也。”他所论述的第1种温病即是自《黄帝内经》以来认识的“冬伤于寒,春必温病”者,属王叔和所论的伏邪之类;春季新感风、寒、温气而成温病是第2种,与巢元方《诸病》所论的冬温都属新感温病之类,但在病因和发病上又有所区别;春季感受非时之气,这属王叔和等所论的时气、时行范畴,郭雍将此也并入了温病之类。
有现代研究者据此认为:“郭雍提出了辨别伤寒与温病的根本依据,那就是有无‘寒毒之根源’。以此为伤寒与温病的划分,提出了较为清晰的界限。[1、2]”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准确。从郭雍自己的论述中,笔者发现其有自相矛盾之处:他所论的温病的第1种以及第2种的一部分皆是感寒邪而发的,只是因为发病时间在春季,就被命名为温病,而不是他宣称的“初无寒邪”才能命名为温病。有无“寒邪”并不是郭雍判别伤寒、温病的真正标准!
据此笔者推断,郭雍真实的目的是缩小伤寒的概念。他把伤寒限定为冬季感寒邪而即发,而把其他所有外感热病连同时气病都归于温病之列。他不仅指出,新感风、温等气及非时之气可以导致外感热病的发生,而不止是“伤于寒邪”,更是借此扩大温病研究的范围,缩小伤寒涵盖的内容。
同时郭雍指出,温毒发斑与伤寒发斑不同。《伤寒补亡论·卷十四·发斑十三条》曰:“此证是温毒发斑也,与伤寒发斑不同。盖温毒之毒本在里,久为积寒所折,腠理闭塞不得出。及天气暄热,腠理开疏,乃因表虚郁发为斑,是时在里之毒发在表,故可解肌而不可下也。伤寒之毒,初亦在里,久不能出。及春再感温气,腠理方开,随虚而出于表,遂见表证,而未成斑也。医者昧于表里之证,下之太早。时内无毒气可下,所损皆胃之真气。真气既损,则胃为之虚矣。邪毒者,乘虚而出、乘虚而入者。以先损之虚胃,而当复入之今毒,力必不胜,而胃将烂,是以其华见于表而为斑……故温毒之斑,郁发之毒也。伤寒之斑,烂胃之证也。”
2 细化温病证治
郭雍区分出伏寒温病、新感春温与时气病温三类:“不思冬伤于寒,至春发者,谓之温病;冬不伤寒,而春自感风寒温气而病者,亦谓之温;及春有非节之气,中人为疫者,亦谓之温。三者之温,自不同也(《伤寒补亡论·卷十八·温病六条》)。”这种分法对后世温病理论的发展很有启迪意义。我们分析可以发现,他的第1种分类源自《内经》;第2种春季自感成温者,即所谓的春温:“发热恶寒,头痛身体痛”,“既非伤寒,又非疫病”,乃“因春时温气而名温病”,虽然也属新感温病大类,但与王叔和的新感冬温有两点重要不同,其一是发病季节,其二是感受的邪气,这种新感春温之说在明代以后得到了汪机等人的传承;第3种实际上是《伤寒例》所论的时气病,郭雍认为这种疾病“长幼病状相似”,乃“温气成疫”之瘟疫,但他将四时的非时之气局限于春季,同时探讨了伏气、新感之轻重,大略“伤寒而成温者……而比之春温之疾为重也”。
事实上,郭雍所论3种温病不论病因病机如何,全部发于春季,这明显受到《黄帝内经》“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学说的限制,甚至限定的范围更小!如前所述,郭雍对“伤寒”概念的限定已经在事实上缩小了伤寒的范围,将之定位在冬季感寒而即发,但在这里他又将温病全限定于春季,那么其余诸季、诸病呢?
其实,郭雍所论远远不止这3种温病,在《伤寒补亡论·卷十八·温病六条》及《风温温毒四条》两篇中,除上述3种温病外,郭雍还论述了温疫、风温、温毒、湿温以及春月伤寒之温、四时温气等,并将疟、利、咽喉病、赤目流行也归于温病之列。如《活人书》又曰:一岁之中,长幼疾多相似,此温疫也。四时皆有不正之气,春夏亦有寒凉时,秋冬亦有暄暑时。人感疫疠之气,故一岁之中,病无长幼,悉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俗谓之天行是也。老君神明散、务成子萤火丸、圣散子、败毒散主之。雍曰:此谓春温成疫之治法也。若夏暑成疫,秋瘟成疫,冬寒成疫,皆不得同治,各因其时而治之。况一岁之中,长幼疾状相似者,即谓之疫。如疟利相似,咽喉病相似,赤目相似,皆即疫也。皆谓非触冒自取之,因时行之气而得也。”
同时,郭雍对寒疫、温疫的区分也与前代如《伤寒例》等不同:一是对于寒疫。《伤寒例》认为:“春分以后到秋分节前,天有暴寒者”为“时行寒疫”,而《伤寒补亡论·卷十八·伤寒温疫论一条》将时行寒疫仅限制于“冬日”;二是对于温疫。《伤寒例》认为:“冬伤于寒,发为温病”,“更遇温气,变为温疫”。而《伤寒补亡论》认为:“若夫一乡一邦一家皆同息者,是则温之为疫者然也,非冬伤于寒自感自致之病也。盖以春时应暖反寒,夏热反凉,秋凉反热,冬寒反暖,气候不正,盛强者感之必轻,衰弱者得之必重,故名温疫,亦曰天行、时行也。”上述的寒疫、温疫同属新感范畴,细析之后可以发现,《伤寒例》中的寒疫从春分到秋分长达半年时间,而郭雍将其限定于冬之一季;而《伤寒例》温疫影响范围小,而郭雍将其扩张为整个天行、时行病。
此外,郭雍还摘录了《伤寒例》与庞安时论述的新感冬温之病,甚至借来《活人书》所论“春月伤寒,谓之温病”。通过这样全面的论述可以看出,郭雍真正想说明的是,温病是包括除冬月感寒邪即发的伤寒之外,几乎所有外感热病(包括温疫或说天行)的重要概念。
可以说,郭雍所做的,正是数百年后温病学家们想做的,只是那时的他们有了更多发挥的空间。但如果没有晋唐医家的任意发挥,没有郭雍这样有智慧的学者为他们指明路径,他们的工作毫无疑问将变得艰难许多。
3 探讨疫病轻重
笔者发现,郭雍对伤寒热病、伏寒温病、时行疫气、冬病伤寒、新感春温等疾病在轻重上进行了细致探讨:“雍曰:伤寒时气,症类亦多,或名伤寒,或名温病,或曰时行,或曰温疫,或曰温毒。或以为轻,或以为重。”故需分辨清楚。他判断的基本原理是:“实时发者,必轻。经时而发者,必重也(《卷十八·伤寒温疫论一条》)。”以及“是则既伤于寒,又感于温,两邪相搏,合为一病,如人遇盗,何可支也”?
他主要在《伤寒温疫论一条》及《温病六条》两篇中,做出了具体判断:(1)“伤寒而成温者,比之伤寒热病为轻,而比之春温之疾为重也。”这里所谓的伤寒热病,应该指的是暑病:“后世以暑病为热病者,谓夏时之气热,最重于四时之热也(《卷一·伤寒名例十问》)。”(2)“故古人谓冬伤于寒,轻者夏至以前发为温病,甚者夏至以后发为暑病也。”(3)“大抵冬伤于寒,经时而后发者,有寒毒为之根,再感四时不正之气为病,则其病安得不重?如冬病伤寒,春病温气与时行疫气之类,皆无根本蕴积之毒,才感即发,中人浅薄,不得与寒毒蕴蓄有时而发者同论也。”(4)“仲景以为冬伤于寒,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盖初感即发,无蕴积之毒气,虽为伤寒,而其病亦轻。……伤寒冬不即发,遇春而发者,比于冬之伤寒为重也。”(5)“盖冬月伤寒,为轻。至春发为温病,为重。夏月热病,为尤重也。”(6)“又有冬不伤寒,至春感不正之气而病,其病无寒毒之气为之根,虽名温病,又比冬伤于寒,至春再感温气为病轻。”(7)“其不伤寒,至春触冒自感之温,治与疫同,又轻于疫也。”(8)《类证活人书》又曰:“治温病,与冬月伤寒、夏月热病不同,盖热轻故也。雍曰:此谓春温非伤寒者……朱氏注曰:春秋初末,阳气在里,其病稍轻,纵不用药治之,五六日亦自安。”
上面的论述中,时行疫气与冬病伤寒没有做出明显比较,只有一个间接论述:“伤寒之与岁露何如?雍曰:岁露者,贼风虚邪也。因岁露而成伤寒者,其病重而多死。四时伤寒者,因寒温不和而感也,其病轻而少死。上古之书论岁露,自越人仲景之下,皆不言及之。今虽有遇岁露而死者,世亦莫之辨,皆谓之伤寒时行也(《卷一·伤寒名例十问》)。”大略可以看出,郭雍认为冬月伤寒、时行疫气都不甚重。
综合来看,郭雍认为上述5种疾病轻重排名如下:最重者为伤寒热病(暑病),次重者为伏寒温病,轻重居中者为时行疫气、冬病伤寒,最轻者为新感春温。这种观点是有一定参考价值,也是笔者所见最早对外感诸病的轻重做细致研究的医家。但他认为时疫不重甚至轻于伏温这一点,似乎临床证据不足。
4 病机从毒立论
从病机方面,郭雍特别善用“毒”来解释,其中《伤寒补亡论》一书用“毒”字高达324次之多,使用“毒气”一词43处。如他创立的“毒气致厥”说,认为伤寒之厥“非本阴阳偏盛,暂为毒气所苦而然”,与《内经》气逆之厥不同。重点为“毒气扰经”,他说:“毒气并于阴,则阴盛而阳衰,阴经不能容,必溢于阳,故为寒厥。毒气并于阳,阳不能容,则阳盛阴衰,必溢于阴,故为热厥”,治疗应随毒气发展趋势因势利导,如“毒气随三阴经走下,不复可止。”
又如黄疸的毒血相搏说,《伤寒补亡论》[3]提出毒血相搏致疸之说,明确指出外邪不去久成热毒,在血脉中传流,与血相搏,为邪气败坏的血液不衄、不汗、不溺则郁而发为至黄之色:“巢氏黄病一论,未为该通,而诸家伤寒论中多从之。夫致黄之由非一,或误下,或火熏,皆能成黄,非止寒热谷气而已。大抵寒邪中人,久不能去,变为热毒。假春风发动表为可出之时,既动则不可复回,而腠理不开,无由作汗而出。郁而在里,终不能散,淫邪泮衍,血脉传流。其毒之重者,遇血相搏不能胜,为之变结。或如豚肝,或如墨色,此为邪气所败之血也。无以泄其邪,则血枯而人死。其轻者鼓血而上,随衄可出;涩者因促滑气而下,随溺可去。既不能与血相搏,又不能开腠理而生汗,上不可出,下不可去,乃散于毛窍之际,已失所舍,而无可定止,进退不能,郁为至黄之色,以待汗与溺而后通。此毒非不欲出也,犹人之行及门而无路也。医者疏通其道而指示之,不为汗,则为溺,未有不去之理。”余者不一而足。
在治疗上,“始觉不佳,即须救疗”以“折其毒热”,“必不可令病气自在恣意攻人”,若失治“邪气入脏,则难制止”。用药倡导“发散以辛甘为主,复用苦药”,因为“辛甘者抑阴气助阳气也,今热盛于表,故加苦药以发之。《素问》云:“‘热淫于内,以苦发之’是也。”服药不避暑夜早晚,及时调整剂量和服药周期等[4]。同时郭雍认为,伏寒温病、伤寒热病(暑病)、新感春温“其治法与伤寒皆不同。”以及“但传经,皆冬感也,皆以伤寒治;不传经者,皆春感也,皆以温气治之。”不可拘于伤寒时日,要随症施治。“又或有春天行非节之气中人,长幼病状相似者,此则温气成疫也,故谓之瘟疫。瘟疫之病,多不传经,故不拘日数,治之发汗吐下,随症可施行。”“其不伤寒,至春触冒自感之温,治与疫同”。其重要原则为:“大抵治疫尤要先辨寒温,然后用药(《卷十八·风温温毒四条》)。”应该说,郭雍之前的庞安时也是重点强调“毒”的。《伤寒总病论》一书“毒”字出现130次,多为“寒毒”、“热毒”、“温毒”、“阴毒”、“阳毒”和“毒气”,偏于病因方面,而郭雍所论偏于病机。
从后世中医外感热病包括疫病发展的整体走向来看,郭雍的做法虽仍强调了寒邪的重要性,也仍然是认为相当一部分温病是感受寒邪而发的,但是他对温病的重视,对于温病范围的扩大,对温病的3类分类尤其是伏邪、新感温病的探讨,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而以“毒”来解释疫病病机,对后世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 孙海云.庞安时医学上的成就[J].新中医,1982,(5):55-56.
[2] 张志斌.两宋时期的温病理论创新研究[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9,15(4):241-24,247.
[3] 宋·郭雍.仲景伤寒补亡论[M].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59:119.
[4] 王兴臣.论郭雍的伤寒学术思想[J].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91,15(5):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