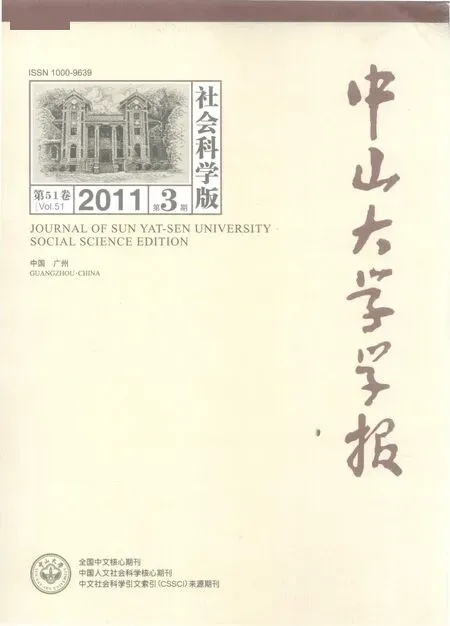鲍留云与《致富新书》*
吴义雄
鲍留云(Samuel Robbins Brown,1810—1880)是鸦片战争前后由马礼逊教育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设立的马礼逊学校的校长,是容闳等人在该校学习时的教师和到美国留学的资助人。在不少涉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作品中,他的名字被按照译音写作“布朗”或“塞缪尔·布朗”。但10余年前,香港学者李志刚先生就提出,应该在研究中使用其中文名“鲍留云”,根据就是,他在自己所编《致富新书》中署名为“合众国鲍留云”①李志刚先生在1998年香港浸会大学召开的“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讨会”上作了题为“鲍留云牧师在港对留学运动之影响及其对资本主义思想之引介”的报告。。近年来,相关出版物在谈及Samuel Robbins Brown时,已渐渐使用鲍留云这个中文名字。
《致富新书》是一部篇幅不大的政治经济学通俗读物。在笔者看来,它非常可能是最早的中文经济学教科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李志刚先生在10余年前曾寄给笔者一份《致富新书》的复印件,供笔者研究之用②在此谨向李志刚先生再次表示衷心的谢意!。近来,笔者对这份文献以及其他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甚感有进行专题研究的必要。本文拟对鲍留云之来华经历进行一些梳理,并结合《致富新书》刊行的时代背景,对此书进行初步研究,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正。
一
鲍留云于1810年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个新教徒家庭。他的母亲极具宗教热诚,是“美国最早且最好的圣歌作者之一”,被他的传记作者形容为“一位传教士母亲”③William Elliot Griffis,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Samuel Robbins Brown,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America,and Japan,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mpany,1902,p.15.。这种家庭氛围,对鲍留云无疑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在少年时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马萨诸塞州的孟森学校(Monson Academy)度过他的中学时代。容闳和后来他所促成的中国幼童留美,正是在这所学校就读的。鲍留云在离开学校后,即开始他的教书生涯,以此作为谋生手段。同时,他还继续坚持学习。经过努力,他进入耶鲁大学,并在1832年从这所著名的大学毕业①鲍留云的早期经历见 William Elliot Griffis,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Samuel Robbins Brown,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America,and Japan以下有关鲍留云生平的内容,凡未另注者均以该书为依据。。
耶鲁毕业生的身份并未使鲍留云感到满足,据说,纽黑文的寒冷气候也使他健康状况不佳,故他在离开耶鲁后,南迁到南卡罗莱纳州,进入哥伦比亚神学院(Theological Seminary at Columbia)学习了两年。在这期间,鲍留云依靠在巴汉维尔青年女子学院(Barhamville Young Ladies Seminary)教授音乐获得经济来源。他的学生中,有后来来华的美国圣公会主教文惠廉(William Boone)的妻子,以及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母亲②William Elliot Griffis,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Samuel Robbins Brown,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America,and Japan,pp.51—52,61,117,127—133.。在这两年中,鲍留云也恢复了健康。之后,他北上纽约,担任纽约聋哑人学校的教师。同时,他又进入当时刚创办不久的协和神学院学习,成为首届学生之一。他在协和神学院的学习经历,为他后来在中国和日本的事业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1838年,鲍留云从协和神学院毕业后,即向传教机构美部会申请前往中国。其时,美国尚未从1837年的经济危机中恢复,而美部会之前已经向中国陆续派遣了几名传教士。故他的愿望暂未实现。鲍留云继续在纽约聋哑人学校教书,同时等待机会。
此时,广州的“马礼逊教育会”已经成立并开始运作。1837年1月,该会分别致函耶鲁大学和“英国海外学校协会”(British and Foreign School Society),请他们代为物色教师,以便在中国开办学校。该会的成员之一、美国商人奥立芬(David Washington Cincinnatus Olyphant)在回美国期间,拜访了耶鲁大学的三位教授斯利曼(Silliman)、古德列支(Goodrich)和吉布斯(Gibbs)。这三位教授对马礼逊教育会的事业深感兴趣,故奥立芬当即请他们作为寻求教师的受托人。他们很快找到了正在纽约聋哑人学校教书的鲍留云,确定请他到中国做马礼逊学校的教师③William Elliot Griffis,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Samuel Robbins Brown,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America,and Japan,pp.51—52,61,117,127—133.。
鲍留云在1839年到中国,在广州和澳门、香港等地活动,其主要职责是担任马礼逊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他在长达8年的时间内开创了基督教在华传播史和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项重要事业,直至因各种原因,在1847年与妻子一道,带着容闳、黄胜和黄宽离开中国,回到美国。这段经历已经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者经常讲述的经典故事。而鲍留云夫妇当年携去美国的容闳等人日后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的积极影响,也使得鲍留云或布朗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中外各种史书之中。对这些内容,本文已不必赘述。
鲍留云在回美国后,由于其夫人健康方面的原因,没有再回中国。但他继续为马礼逊学校尽力。他先将容闳等三人送到孟森学校安置好,随后在几个城市作了几场以中国为主题的演讲,为此时仍在香港开办的马礼逊学校筹集资金。1848年,他开始在纽约州的罗马学院(Rome Academy)担任教职。1851年春,纽约州奥本(Auburn)附近的一个归正教会“沙滩教会”(Sand Beach Church)请他担任牧师之职,他“愉快地接受了”④William Elliot Griffis,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Samuel Robbins Brown,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America,and Japan,pp.51—52,61,117,127—133.。鲍留云在1838年前往中国前夕,就在纽约第三长老会受按立为牧师,故此次到归正会任神职也可以说实现了自己原来的愿望。他在此教会任职至1858年。在此期间,他参与创办美国最早的女子大学埃尔迈拉女子学院(Elmira Female College),一度担任筹备委员会的主席,从而在美国女子教育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⑤William Elliot Griffis,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Samuel Robbins Brown,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America,and Japan,pp.51—52,61,117,127—133.。
1858年,美国与日本签订《江户条约》(《日本国美利坚合众国修好通商条约》),为美国在日本的传教事业打开了道路。当年底,一直有志于从事传教事业的鲍留云向美国归正会海外传教差会申请到日本做传教士。1859年,鲍留云携带家眷,开始了到日本的传教之旅。此后20年,鲍留云都在日本传教,他在神奈川和长崎从事传教活动,并运用他在教育方面的经验和热情,在长崎开办了传教学校。在这漫长的时间内,鲍留云精通了日语,并将《新约》翻译成日文①William Elliot Griffis,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Samuel Robbins Brown,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America,andJapan,pp.137—324,142—143,235—236,291,292—294,308.。
从时间上来看,鲍留云作为传教士,大部分时间是在日本度过的。但他和中国的联系并未完全中断。他继续关注着以前他在澳门和香港所教的那些学生,为容闳、黄宽、黄胜三人在美国的留学生涯提供了关键性的帮助,晚年还关注容闳发动的中国幼童留美事业。在赴日途中,他再次访问了香港,凭吊当时业已关闭数年的马礼逊学校的故地。在那里见到了以前的学生容闳和黄宽。他还访问了厦门、上海等地②William Elliot Griffis,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Samuel Robbins Brown,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America,andJapan,pp.137—324,142—143,235—236,291,292—294,308.。此后,他长期保持着和这些学生的联系,其间,他曾对美国的排华风潮表示不安和责难③William Elliot Griffis,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Samuel Robbins Brown,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America,andJapan,pp.137—324,142—143,235—236,291,292—294,308.。1877年,他到南洋及中国沿海地区旅行,与阔别多年的学生们相聚。他在香港上岸时,几个在政府任职的过去的学生迎接他,在黄宽的主持下,为他在广州的小住作周到的安排。他在香港再次探访“马公书院”(马礼逊学校)的旧址,对着当年手植的大树发出不胜今昔之慨。他又到澳门,去看初办马礼逊学校时的旧居,“从废墟上带走一片旧瓦以志怀念”④William Elliot Griffis,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Samuel Robbins Brown,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America,andJapan,pp.137—324,142—143,235—236,291,292—294,308.。他在前往上海的途中路过厦门,发现这里的海关也有他过去的4位学生在服务。这些学生为了报答昔日的恩师,为他安排了一次舒适的旅行,使他得以到芝罘、天津和北京观光。他在北京见到了丁韪良。他在上海时又遇到4位过去的学生,他们为了表达感激之情,送给他一面精美的银匾⑤William Elliot Griffis,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Samuel Robbins Brown,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America,andJapan,pp.137—324,142—143,235—236,291,292—294,308.。
鲍留云在日本又继续做了几年传教士,在1879年返回美国。次年,他在自己的祖国病逝。在去世之前,1880年1月和2月,他作为容闳的客人,在华盛顿住了一段时间。其时,容闳还在为中国留美幼童作最后阶段的工作⑥William Elliot Griffis,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Samuel Robbins Brown,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America,andJapan,pp.137—324,142—143,235—236,291,292—294,308.。而追根溯源,鲍留云在澳门和香港的事业未尝不可以说是中国幼童留美的远因。
二
鲍留云作为一个教育家,他从教的时间前后延续了半个世纪;作为传教士,他在中日两国活动的时间也有近30年。但与那个时代从事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多产的西方人相比,他留下的作品并不多。
鲍留云在1847年回美国之前,曾经撰写过6篇较长的马礼逊教育会和马礼逊学校的年度报告,分别发表在英文月刊《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第10—15卷。这些报告,在今天是研究马礼逊教育会和马礼逊学校最为直接的史料。鲍留云在这些报告中就教育问题所作的评论,也可以作为研究他的中西文化观念和教育理念的资料。在这份刊物上,还可以看到他为1843年去世的马礼逊之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的葬礼所写的长篇布道辞⑦S.R.Brown,“The Memory of the Righteous:Funeral Sermon on the Death of J.R.Morrison”,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2,pp.456—464.。此外,他还在《中国丛报》发表了一些翻译作品。他将耶稣会士M.Bohet之《中国札记》翻译成英文,分5次发表⑧“Character,Custo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hinese”,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9,pp.284,399,483,617;vol.10,p.65.。
在回美国之后,鲍留云曾在美国亚洲学会会刊上发表了一篇长达40页的论述中国文化的论文,系统阐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观点,是比较难得的一篇文献。从整篇文章来看,鲍留云对于中国文化的基本认识是比较负面的。这与当时包括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内的多数来华西人的思想倾向是吻合的⑨S.R.Brown,“Chinese Culture:Or Remarks on the Causes of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Chines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2(1851),pp.167—206,183.。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文章的一个脚注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资料。在谈到中国地理书的贫乏时,鲍留云加了一个脚注,其中说:
1840年,著名的林钦差从笔者这里取得一部慕瑞(Murray)的《世界地理大全》,请他的私人秘书,一位从美国传教士学习英语的中国青年将其部分翻译为中文。在林被流放伊犁后,他将这些译文分为两卷出版。(10)S.R.Brown,“Chinese Culture:Or Remarks on the Causes of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Chines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2(1851),pp.167—206,183.
从这段话可以了解两个情况:其一,林则徐当年是从鲍留云手上得到英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的英文原本的。其二,将其译为中文的是跟随美国传教士学习英文的“中国青年”。在当时林则徐的翻译班子里,符合这一条件的是《劝世良言》作者梁发的儿子梁进德。因此,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对“开眼看世界”的先驱林则徐在广东的活动细节作进一步了解。
正如上文提到的,鲍留云在日本期间,其最大成就是将《新约》翻译成日文。此外,他还著有《日语会话》、《日语英语学习精通法》等西人学习日语的参考书。此外,日本东京基督教团出版部在1965年还出版了《鲍留云书简集:幕末明治初期宣教记录》一书,乃为后人所编。
本文将要重点讨论的《致富新书》,目录卷下端题“香港飞鹅山书院藏板”,内封题“道光二十七年刊”。所谓“飞鹅山书院”即在香港的马礼逊学校,或又称为“马公书院”。可知该书刊刻于鲍留云即将返回美国的1847年。《致富新书》例言下端题“合众国鲍留云易编”。所谓“易编”,当为“译编”之意。
既然是译编,其所据原本是何书。这是需要加以考证的问题。鲍留云在这篇例言中说:
中华选家,多选文章诗赋抄刻,其余各体,概置弗录。吾合众国,选刻《致富新书》一本,益人良深。余到中华有年,历览群书不少,而与吾国《致富新书》之义相同者,目所罕睹。故弗敢自秘,不辞辛苦,译为唐书,愿人知所重焉。①鲍留云:《致富新书·例言》,香港飞鹅山书院藏板,道光二十七年刊。
他又说:“《致富新书》系合众国贤人杰士所作。”②鲍留云:《致富新书·例言》,香港飞鹅山书院藏板,道光二十七年刊。从上述这些信息来看,显然,鲍留云此书是将美国的一本著作翻译编辑而成的。他并没有告诉读者,这位“贤人杰士”是谁,更没有在书中介绍这部《致富新书》的英文名称。不过,笔者检索著名的图书目录数据库worldcat(世界图书馆界联合组织OCLC之5万余图书馆联合目录),发现Samuel Robbins Brown项下《致富新书》条目的作者栏,标有“John McVickar”和“Samuel Robbins Brown”。这意味着,该项目录制作人认为,鲍留云此书翻译的是John McVickar的著作。该目录没有显示认定《致富新书》原作者为杰克·麦克维卡(John McVickar,1787—1868)的原因。但其如此标注,说明编者应该有一定的理由。在自己未掌握相关线索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应该重视该目录提供的信息。但有些情况则应该加以辨析。
麦克维卡是19世纪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神职人员。他1804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811年,他成为纽约美国圣公会的一位教区长。1817年,他被聘任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麦克维卡在教会内贡献颇多,除长期献身于教会事务外,还是一位教会历史学家③有关麦克维卡的简要生平,可见“美国名人网”上的资料。网址:http://www.famousamericans.net/johnmcvickar/。一部美国经济学史著作指出,麦克维卡是“一位早期重要的经济学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经济学,是一本早期教科书《政治经济学大纲》的作者……麦克维卡是哥伦比亚大学最后一位道德哲学教授和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讲授自由贸易的学说”④Lars Magnusson,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 in America:1822—1890,London,Routledge,1999,p.9.。
笔者查阅了可以见到的麦克维卡的两部经济学著作。一部是他出版于1825年的《政治经济学大纲》⑤John McVickar,Outlines of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Wilder & Campbell,1825.,另一部是出版于1833年的《政治经济学导论》⑥John McVickar,An Introductory Lecture of Political Economy,London:John Murray,1833.。其中,《政治经济学导论》是他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一次演讲的讲稿或演讲记录。经过比照,笔者发现这篇演讲稿的内容与《致富新书》的结构完全不同,内容也相对集中于对经济学某些问题的评论,《致富新书》中的很多内容,这篇演讲辞中都没有。当然,二者提到的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则是相似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则是一部比较正规的经济学著作或教科书,它由四部分组成:一是经济学的定义与学说史;二是财富的生产;三是财富的分配;四是财富的消费。按鲍留云的说法,他译编的是美国人的“致富新书”,如果该书的作者是麦克维卡的话,那中文《致富新书》的英文母本很可能就是这部《政治经济学大纲》。
但这里仍然存在两个问题,需要略加说明。其一,《政治经济学大纲》的封面页明确标明,该书是“包含在大英百科全书之爱丁堡附件中关于该主题的文章的翻印(republication)”。而所谓“大英百科全书之爱丁堡附件中关于该主题的文章”,其作者是英国经济学家麦库罗奇(John Ramsay McCulloch,1789—1864),曾先后任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教授,著有经济学著作近30种①有关麦库罗奇的情况,可见:“John Ramsay McKulloch”,http://homepage.newschool.edu/~ het/profiles/mcculloch.htm。因此,该书的主要学术贡献应该是来自麦库罗奇的。即是说,《致富新书》可能反映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的思想。不过,《政治经济学大纲》的封面还标明,该说还包含“解释性与批判性注释和关于这门科学的提要”,这个部分,应该是麦克维卡的贡献,否则,所谓“合众国贤人杰士”之作就完全谈不上了。其二《政治经济学大纲》是一部188页的著作,而中文的《致富新书》只是一本50多页的小册子。对照二书可以发现,二者在结构上也不相同。如果鲍留云未在署名时强调《致富新书》是“易编”之作,则很容易觉得二者之间不存在什么关系。
当然,笔者并非要通过上述考证,来否定中文版《致富新书》与麦克维卡《政治经济学大纲》抑或其他作品之间的联系。下文将会谈到,《致富新书》的一个突出思想就是“自由贸易”,而这恰好也是麦克维卡的经济学思想的重要部分。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政治经济学大纲》和麦克维卡的其他作品是鲍留云编译《致富新书》的范本或依据,他一定还是花费了很大的力气进行改编的工作。因此,如果《政治经济学大纲》是《致富新书》的母本,则鲍留云的“易编”基本上是一次改写。这不仅可以从该书的篇幅和结构得到初步的证明,还可以从它的内容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三
鲍留云的传记作者格里斐斯(William Elliot Griffis)说:“看到(中国)需要有一本论述比孔孟之书所言晚一两千年之事的经济学教科书,鲍先生写了一本关于这一科学的入门书,该书乃是他翻译为中文的,1847年在广州出版。”②William Elliot Griffis,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Samuel Robbins Brown,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America,and Japan,p.90.显然,说该书“在广州出版”是一个错误。但这段话告诉我们,鲍留云译编该书乃是为了向中国人提供一本经济学教科书,则可能指出了他的著书目的。
查马礼逊学校(飞鹅山书院)历年的报告,均未发现有开设经济学课程的记录。而且,鲍留云在《致富新书》刊行后不久,即返回美国,即使有在学校开设这门课程的想法,也已来不及实现。但至少可以说,鲍留云希望将《致富新书》当作该校学生以及其他中国人了解西方经济学常识的普及性读物。
在《致富新书》卷首,有一篇中国人所作的序,作者未具其名。按序中所言,作者应该是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来自外地的文人,至作序时,已在香港或者附近逗留5个月。其中说道:“外国重文人之学,他邦求识字之人。聘黄夫子而谈经,请唐先生而论道。”又云:“问字频来,借书时至,不愧西土名儒。幸为东国贤师,摘叶抽词,粲花著论。《致富》番书,译为唐卷。全稿授我,索我俚言。”③佚名:《致富新书序》,《致富新书》卷首。从这些句子可见,这位文人与鲍留云之间在文字上应该有比较多的交往。这些话也间接说明,鲍留云译编《致富新书》的工作主要是在1846年进行的。鲍留云将整个书稿交给这个人,请他作序,证明鲍留云对他是很信任的。所谓“摘叶抽词”,似乎也说明,他了解鲍留云并非将所依原著完整地翻译,很可能在译稿完成后还进行了删减的工作。至于他对鲍留云帮助到何种程度,现在缺乏更多的资料,难以判断。但当时西人将西文作品译为汉语或以汉语著书,多在文字上依靠中国文人,而且多数是像这位序言作者那样不知名的下层文人。这位自称“频年失志”、“半年寄迹”的作者,也很可能在《致富新书》文字的组织、措辞的修订等方面,帮助过鲍留云。
《致富新书》共56叶,不分卷,按内容分为19篇,分别为:《论用银格》、《论百工交易》、《论商事》(二则)、《论贸易》、《论工艺》、《论农工商贾》(二则)、《论土地》、《贫富分业》、《论用银益人》、《论物贵重》、《论市价》、《论平贱》、《公务》、《学业》、《贫约》、《并处世良规》、《论用银》、《并用银例》。全书虽不足2万字,却论述了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商品价值与价格、经济与政治关系等内容,基本上涉及了当时西方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方面。鲍留云在书中对这些方面的常识,以尽可能平易的汉语,进行了介绍。鸦片战争前后来华西人的类似著述,尚有英国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的《生意公平聚益法》、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的《贸易通志》。但前者主要讨论商业道德问题,后者则主要宣扬自由贸易的观念,并论及中外贸易的历史、现状以及商业制度等问题。就经济学内容的全面性而言,这些作品都不及《致富新书》。
《致富新书》这本小书,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1)该书尽量用当时中国人可以理解的语言,来介绍西方经济学知识,从其文中可以经常看到比较地道的遣词造句习惯。这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那位南游文人的帮助,已不可考。书中所列举的论据,也有不少与中国相关。如书中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用“银”这个词来译称广义上的货币①鲍留云:《致富新书·论用银格》,第6—7页。。在称呼美国时,也按当时中国人的习惯称为“花旗”②鲍留云:《致富新书·论贸易》,第17,16—17页。。在论述通商之利时,作者写道:“故中华之邦,与东洋之国,使无海以通之,将见洋参洋毡,其价十倍……”他还以英国对华通商,作为自己的论据。其中还引用“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样的中国成语③鲍留云:《致富新书·论商事·其二》,第14—15页。又如:《学业》篇中讲到学术于教育的重要性,也举中国、美国为例,见第47页。。在讲到农业的重要性时,他引用了《尚书》中的“三年耕,而有一年之食”等语④鲍留云:《致富新书·论农工商贾》,第22页。。他还在书中加入自己所处环境的因素,如在《论农工商贾》中说:“粤东城中,文人叙会之区,商贾往来之地。近悦远来,群贤毕至。所以天下至难得之物,亦得而有之,何其幸也!”⑤鲍留云:《致富新书·论农工商贾·其二》,第25页。显然,这些都非“合众国贤人杰士”的原书中所有。在强调国际贸易的必要性时,他还说道:“夫中国有余茶,英国有余布”,理应互通有无。以他所熟悉的中英通商情形作为自己的论据⑥鲍留云:《致富新书·论贸易》,第17,16—17页。。这些均表明,《致富新书》作为译编之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鲍留云改写而成的。
(2)该书介绍了一些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如第一篇《论用银》,主要介绍货币的功用这种基本知识。第二篇《论百工交易》则阐述社会分工、各司其业的原理,在这一点上将“各务一业,交相为易,互有益也”的文明社会与“躬耕南亩,自灌西园”的“野人之邦”相比照,论述“列国之中,一人而学百工,则百工一无所成”,而“吾人各务一艺,则精于一艺,故器多有所成,而民亦多有所用”这样的道理⑦鲍留云:《致富新书·论百工交易》,第8页。。《论工艺》则强调技术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⑧鲍留云:《致富新书·论工艺》,第19—20页。。
《论土地》、《论贫富分业》、《贫约》三篇,则是针对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经济和道德观念的。《论土地》的中心思想是反对均田地。鲍留云认为,土地平均,本来是很理想的状态,“上帝之造土地业,本不欲使富者骄傲其有余,贫者衣食之不足”,“然所难者,不知将何法而土地可以齐一也。夫尔亦原无田宅之福命,而欲坐享乎田园,虽虔求于上帝,上帝许之乎!”⑨鲍留云:《致富新书·论土地》,第27,27—29页。他认为“土地平分,不独无益于天下,而且反害于天下”,原因在于,是否拥有土地,在于人之勤俭与骄奢之别,土地买卖由此而起,无法防止。若强行禁止土地买卖,则将使“勤俭之风息,滥用之习生。此弊正等于野民”,“然野人之风,吾国岂能为乎?”在这里,他将土地是否均平上升到文明与野蛮之别,将是否保有土地与人们是否勤俭直接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土地私有及土地集中的现象辩护⑩。与这一观点相联系,《贫富分业》则主要论述不可均贫富。作者的论据同样还是,贫困的形成乃由于“骄侈怠惰之习”,均贫富则将使“勤者必学惰,惰者不肯勤”,财富无由蓄积,终成贫穷之世界,如土耳其、亚非利加者流①鲍留云:《致富新书·论贫富分业》,第30—31,31—32页。。他也反对将富人财富之一部分用于济贫之主张。他认为富人多余之财可以用来组织生产,创造财富,并给予受雇佣者以工作生财之机会;而用于散财济贫,则不过周济少数人而已,“贫者多矣,焉得人人而济之……不如用之以食农工商贾可也”②鲍留云:《致富新书·论贫富分业》,第30—31,31—32页。。《贫约》篇则专门讨论慈善济贫的问题。鲍留云承认济贫的道德价值,慈善行为乃“富者得于上帝独厚,殆以施济而表上帝之恩焉。此即仁人之心也”。但他又认为,在很多情况下,济贫适足以养惰,使仰给者“怠惰成性,习惯自然,又何以养父母,何以畜妻子乎!”对那些人习惯于依赖别人者来说,“不施胜于施也”③鲍留云:《致富新书·贫约》,第49—51页。。
与以上观点相联系的是书中表达的财富观念。在《论用银益人》这篇文字中,作者认为,富人将生活所需之外的财富用于济贫固然不对,而将其“收于钱库之中,惟恐人攘之”的“守钱虏”,或是将其用于追求奢华生活的挥霍者,都是无益有害之人,因为他们没有善用财富,或藏之使其等于“泥土、石块”,或滥用之使其成为“无益之费”,均未能将其用于创造新的财富,为社会做出贡献。他认为值得赞扬的是将钱财“用之以治农,用之以食工,或放账以取利,或贸易而经商”的“节用之人”,他们对财富的使用“真不虚费矣”④鲍留云:《致富新书·论用银益人》,第33—35页。。值得指出的是,在《致富新书》的末尾,又有《论用银》一篇,却与以上主张有些矛盾。作者再次指责那种“蓄财不散”的“守钱奴”,指其“既不利于己,又无益于人,且银愈多而愈戚矣”,认为正确的态度是“财得之有道,用之有方”。但他随之列出了“用银之例”4条,分别是备家用、救施贫穷、养瞽者并教愚蒙、银不可过重⑤鲍留云:《致富新书·论用银》,第55页。。这些,似乎在提倡一种乐善好施的理念,与上文所述的经济和财富观念直接冲突。笔者未能从文中找到发生此冲突的原因。也许前面所述的价值观、财富观,乃是那位“合众国贤人杰士”原书中的思想,而这最后一篇《论用银》中的观点,则是鲍留云这位传教士自己的理念。
《致富新书》介绍价值和价格学说的有《论物贵重》、《论市价》和《论平贱》这几篇。《论物贵重》以金、银、铁三种物品之价值为例,铁器远较金银为有用,但价低于金银,是因为以下这些因素:首先,金银较铁远为稀缺,“市价之低昂,由器物之多少而定也”;其次,亦因金银之获取,远较铁之获取为艰难,故其“盖以功而定价也”,这就表达了类似于“物品包含劳动量多少”的价值学说;再次,物品的价值还要看其是否有用,“使物无所用,功虽多,亦奚以为?”总之,“苟为有用之物,且精华可爱,则人人好之,而竭力以求。若物不用力而得之,其用虽大,其物虽美,亦无所贵。夫铁之用,胜于银千余倍。至于相换之时,银又重于铁约千倍,盖所换者功也”⑥鲍留云:《致富新书·论物贵重》,第36—38页。。其中,鲍留云着重强调的,还是“物之轻重,以其功之多少而定”的价值观点。应该说,他在此还是以比较简明的语言,将有关商品价值的理论作了基本的说明。《论市价》则主要讨论物品的价格问题。鲍留云主要以弓与箭的市场关系,来说明商品的价格,主要受供求关系的影响。按他的说法,弓一旦紧缺,势必因“物罕为奇”,而“弓愈少,而买者愈多,则价愈高矣”,反之则其价贱。而且,由于买弓者多,“而卖者少,致令为弓者日多,此日弓有余而卖者多,则必减价方有人售,由是弓价日贱,可比常价而更贱矣”⑦鲍留云:《致富新书·论市价》,第39—40页。。《论平贱》则着重说明何者为“平”,即购买什么样物品合算。按作者的说法,价贱不等于“平”,“平与贱,则有异焉”。衡量其物是否“平”,还要考虑其精粗美恶,一味求价贱之物,“不智之甚也”,往往造成适得其反之后果⑧鲍留云:《致富新书·论平贱》,第41—42页。。
《致富新书》中还有几篇论述与经济相关的问题。如《公务》篇主要讲述公民纳税赋与国家政权之关系,说明官府之优劣对于社会秩序及民生之重要影响。《学业》篇则主要论述提倡学术,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对于开启大众智慧,提高民众教育,增强其谋生治世能力的重要性,劝告说:“诸君子学足于己,宜教于人,淑己即以淑人,善身因以善世。而为治者,急宜设学校以广教化也。”①鲍留云:《致富新书·学业》,第48页。鲍留云在此并未说明“学校”的概念,但前文所论,均将学识与经济活动相联系,注重实用的特征很明显。联系到他自己此时担任马礼逊学校校长、作为西方教育引进中国者的角色,可以判断他要提倡的是西方近代的教育。《论求财》倡导一种积极进取、奋发向上、追求个人财富的价值观。该书还列出《处世良规》5条,提倡务勤劳、尚节俭、节制、立志、常怀满足感恩快乐之心②鲍留云:《致富新书·处世良规》,第54页。。这些,都可以说是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总结。
(3)鲍留云针对中国社会当时仍存在的农本商末的观念,阐述农、商平等的思想。他在《论商事》中说,商人不事生产,似乎不如躬耕收获的农夫,也不如“制成器用”的织者,“羁迹市廛,留心货利,似无所用焉”,但实际上,“为商者,以父母之国,所产之货,而远适他邦,即有关河之阻,不辞转运之势”,其功不可没,“是商者,殆亦如农者之种粟,织者之织布,贵相似也”,“故为商之事,岂可忽乎!”书中还有多处论述这种农、商平等的思想。至于有人对于商人获利持有异议,鲍留云说:“然既有利,则富其人,并富其国矣,何议之有!”③鲍留云:《致富新书·论商事》,第11—12页。他反复说明,不应对商人贱买贵卖的逐利行为加以指责,指出商人“利于己则利于国矣”,“通商之事,虽为利己之计,实为利国之计矣”④鲍留云:《致富新书·论商事·其二》,第12,12—13,14,12,14—15页。。
鲍留云在书中,以较为温和的句子,劝告官员们不要干预商事,正如他们也不应干预农事。“商之为商,犹农之为农。农不可戒,商亦不可戒也。夫农也,度其土田,宜种十顷之豆,可树百本之桑,农自图之。抑商也,以海洋为土田,以舟船作耕具,往也布而归也茶,商自度之。农商之获虽殊,而其益则一也。”⑤鲍留云:《致富新书·论商事·其二》,第12,12—13,14,12,14—15页。这种商、农并重的观点,显然是针对中国重农抑商的观念和政策的。他进而提出:“若官长禁戒之,权不由于商,则可市之物而不得市,不可市之物而不敢市,则所获者寡矣,而国用亦因之寡矣,自是而财利日见其不足矣……故禁商旅之事,岂非不智之甚哉!”⑥鲍留云:《致富新书·论商事·其二》,第12,12—13,14,12,14—15页。这种言论,是当时中国人自己难以公开宣扬的。
(4)《致富新书》重点宣扬的一个观点,就是“自由贸易”的主张。以上所述该书关于重商的观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为阐述这一论点服务的。该书之《论商事》、《论贸易》、《论农工商贾》等篇,均以阐述此观点为主,占全书1/4以上的篇幅。鲍留云强调,从事贸易的商人“以本地之土产,往易异国之土宜”,“我国多本无之物,一旦而取给不穷,皆商人为之也”⑦鲍留云:《致富新书·论商事》,第11—12页。。希望清政府“于远方之人,则当怀柔之”⑧鲍留云:《致富新书·论商事·其二》,第12,12—13,14,12,14—15页。。
这种自由贸易的主张,很明显是针对在鸦片战争之后被迫打开国门,但对外封闭的心态依然存在的清朝官员。以上所引鲍留云将农、商相提并论的言论,其中所谓“往也布而归也茶”,不难从中体察到,他在谈论“商”时,心目中的对象是贩运布匹到中国又购买茶叶回国销售的西方商人。所以他在论述禁商之不智后强调:“又非不智已也,且违上帝之法,罪莫大焉!上帝创造万国,列国之地气各殊,所以列国之物产大异,欲人交相为易,有无相通。故上帝疏通致远,造次大洋而小海,而各国之人,藉大舟以往来,惟托上帝之鸿恩也。”又谓:“上帝之造天地,有地必有海,一定之数也。”而上帝造海,即是希望各国通商往来,“非若无智之徒,谓造此以别各国,分疆界,尔为尔,我为我,以致结怨为仇也”,“天下无不可亲可爱之人,所以易土产,通货财,互助以利用,增其快意,厚其安居,而人益乐其生焉”⑨鲍留云:《致富新书·论商事·其二》,第12,12—13,14,12,14—15页。。鸦片战争时期,御史曾望颜曾提出《封关禁海议》,被译为英文,在西人媒体上广为刊载。故鲍留云为商人和商事辩护,并非无的放矢,实际上也是为西方在华通商利益辩护。
《致富新书》中有《论贸易》一篇,专门论述国际贸易的重要性。鲍留云再次以中国人熟悉的语言,阐述国际贸易的必要性,指出英国之“余布”与中国之“余茶”“若有无不能相通,斯所积者,亦终于无用耳”,而且还会导致“百弊丛起。此贸易不通,势必至此”。只有让华茶和英布自由地相互“以其所有余,补其所不足”,才能相互为用,共同得益①鲍留云:《致富新书·论贸易》,第16—17,18,17—18页。。不仅西方国家需要中国的茶叶等物,中国实际上也在用西方的产品。“中国所用之洋货,固非中国自造之也。舍贸易又何以得哉!”②鲍留云:《致富新书·论贸易》,第16—17,18,17—18页。
在就自由通商问题作出以上论证后,鲍留云犹嫌不足,又在《论农工商贾》中再次论述通商的重要性。这一篇文字开头是讲述社会分工的道理,也承认农业之重要,说“先有农而后有商贾百工”,“故农为百工之首也”③鲍留云:《致富新书·论农工商贾》,第22,22—26页。。然后他很快笔锋一转,说“然所重者,又不止此也”,工与商亦不可或缺。但他着重论述通商在经济生活中的关键性作用,尤其是为英美等西方各国对华通商辩护④鲍留云:《致富新书·论农工商贾》,第22,22—26页。。其言论这里不再繁琐征引。
针对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内有人企图实行严格的易货贸易,以防止鸦片流入、白银外流、商欠频发等弊端,鲍留云认为这违背了通商贸易的规律,加以斥责:“乃有总角之童,未识贸易之道,则以换物为贸易。不知换物之益,徒益于一己,不能益于一国也……夫两国相易,其货各有不同”,中国与西方贸易互利,货物繁多,交易过程复杂,实际上无法采用易货的方式⑤鲍留云:《致富新书·论贸易》,第16—17,18,17—18页。。
以上是笔者对《致富新书》内容的简要总结。这四个方面只是一个大致的归纳。《致富新书》的主要内容及其值得注意的方面,基本上如此。当然,笔者的总结可能还有不够全面细致之处,可能需要再作深入的讨论。
四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作为一部政治经济学的简明读物,《致富新书》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它虽然没有全面、细致地论述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也缺乏理论的深度,与作为英美经济学思想发展结晶的《政治经济学大纲》远不能相提并论,但毕竟是现在已知最早的以中文写成的政治经济学作品,并且很有可能是作为马礼逊学校的学生读物来写的,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教科书的性质。书中阐述的经济学思想观念,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或者以当时西方经济学的程度来衡量,都还比较简单浅显。但对于当时极少接触西方经济学说的中国人来说,这些都是很新鲜的知识和思想。它的刊行,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上,应有相当的标志性意义,很值得我们重视。
但是,这只是我们今天历史研究者的看法。在当时,《致富新书》并未引起中国人的注意。翻阅当时的历史文献,基本上看不到有谁提到过这本小书。从19世纪中期中国社会的思想状况来看,这也不奇怪。当时中国著名的学者魏源的《海国图志》和福建巡抚徐继畬的《瀛环志略》,也在很长时间内为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所遗忘和漠视。不同的是,魏、徐之作毕竟在19世纪后期为追求改革的知识分子所瞩目,而《致富新书》则似乎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直到历史学者将其发掘出来。
《致富新书》和《海国图志》、《瀛环志略》还有一个相似之点,即它后来在日本学界得到了注意。明治八年(1874),该书被翻译成日文本的《致富新论译解》出版。翻译者是中岛雄和赞井逸三,他们除翻译外,还加了注解,按照该书序言之说,是“原于合众国人鲍氏之说,旁引曲证”⑥佐濑恒:《致富新书》日文版序,见中岛雄、赞井逸三:《致富新论译解》卷首,明治八年,东京松柏堂发卖。,可见在注解方面下了较大的工夫。该书分为3卷,共84叶。当时,鲍留云已经在日本传教10余年,但他并未将当年在香港刻印的这本小书用日文重写,却由两位日本人将其翻译。从佐濑恒写的序言中,笔者未发现译者和鲍留云有何接触。佐濑恒的这篇序言是很值得一读的。作者在其中很有激情地讲述了西方国家在日本的经济渗透,如何迫切地使人们要思考“所以兴工业而富邦民”这一重大问题,提出要重视西方“经济之术、所以致富之道”⑦佐濑恒:《致富新书》日文版序,见中岛雄、赞井逸三:《致富新论译解》卷首,明治八年,东京松柏堂发卖。。值得一说的是,这篇序言中已经有数处使用“经济”一词。而中国人采纳近代意义上的“经济”这一词汇,则是20世纪初的事情了,系统引进西方的经济学说,也较日本落后数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