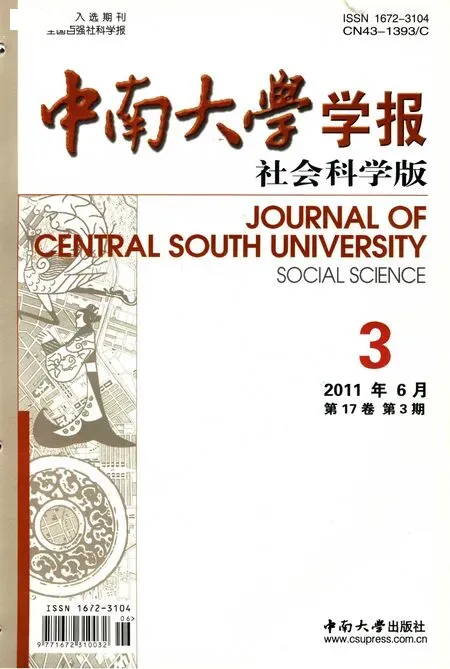休谟“旁观者”的同情理论探微
孙海霞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江苏 南京,210046;黄山学院社科系,安徽 黄山,245041)
欧洲文艺复兴后,对道德合理性的重新论证有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条方法理路。英国思想家休谟以其人性论为基础,以基于习俗与习惯的经验主义方法为依据,构建了他的道德情感学说体系,论证同情作为道德基础的地位与作用。麦金太尔看到休谟对道德合理性论证的努力,但他同时认为休谟在道德合理性论证上是失败的,认为休谟的同情原则在理论上只是一种“哲学上的虚构而已”。[1](63)我们认为这一评价是有失偏颇的。在休谟那里,作为道德基础的同情原则是基于“旁观者”立场的同情,它克服了个体同情的相对性、差异性,具有普遍性和权威性。休谟基于“旁观者”立场的道德同情理论在西方伦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性是情感的奴隶”:同情原则的人性基础
人性的设定本身是构建道德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前提。休谟把人类一切精神统称为“知性”,并区分为“印象”和“观念”两个部分,分别构成经验和理性的对象。印象相较于观念而言,具有优先性,印象是观念的原因。情感、欲望和情绪则作为印象的组成部分,与观念、理性相对,是行为的直接推动力。休谟摈弃同时代理性主义伦理学派的习惯看法,反对把更多理性的盘算和深谋远虑归之于人性,强调情感是道德行为的推动力,主张道德导源于情感,而不是理性。
道德导源于情感,而不是理性,情感是道德的基础,这是休谟道德理论的核心主题。为此,休谟提出“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2](453)休谟承认理性在几乎所有道德规定和道德推论中都是发挥作用的,但他同时强调理性的作用是有限的。在休谟看来,理性包括观念的比较和事实判断两种,它们能揭示和发现关系,但道德感却不在于这些关系的揭示与发现。理性的逻辑推导或事实判断能够帮助人们形成观念上的意见,却不能形成道德区别,不能直接影响人们的实践行为。理性关涉事实判断,关乎真伪,而道德属于价值判断,关乎善恶。因此,道德不可能导源于理性。单独的理性并不足以产生任何道德的谴责或赞许,不能成为道德行为的直接推动力,“理性给我们指示行动的诸种倾向,人道则为了有利于那些有用的和有益的趋向作出一种区别”。[3](138)因此,道德以情感为基础,它并不是理性判断的结果。
情感作为道德的基础,最直接的表现是道德的善恶区分与人的苦乐感直接相关,给人带来快乐感受的是值得赞许的,是善的;给人带来痛苦感受的是被谴责的,是道德上的恶。休谟指出,人们之所以能够形成对行为夸奖或责备、赞许或谴责的一致性,形成关于道德善恶的区分,就在于人性中蕴含着一个最强大的原则即同情原则。同情使人们产生对他人快乐或痛苦的共感,并因此激发人们或善或恶的道德评价,激发人们的道德行为。
二、“旁观者”的同情:同情作为道德基础的内涵
在休谟那里,“同情”是一种自然的情感,也被称为“仁爱情感”、“人道情感”、“道德感”,指“与他人的同胞感(a fellow-feeling with others)”,[3](70)意味着一个人的幸福或苦难的感觉,总是别人在某种程度内能感到的。正是基于同情,人们实现了情感间的共通、共鸣和相互传达,形成对行为的赞美或谴责。①
共通性是同情的不可或缺的因素。罗尔斯指出,休谟的同情使得我们具有“关于另一个人的感情的观念,那个观念活跃到足以成为在我们的内心的相同的情感”。[4](117)也就是说,在休谟那里,作为道德基础的同情就是一种“共鸣的情感”,是全人类所“共通的情感”,它导致共通性的感觉。而其共通性的基础就在于人们“必定对凡是有用于和有助于人类的东西、而非对有害的和危险的东西做出一种冷静的优先选择”。[3](124−125)同情是人们在人类的幸福和社会公共福利问题上形成的共通感。同情使得人们做出一般性的道德判断成为可能。
普遍性是同情的第二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休谟指出,没有人是与他人的幸福和苦难绝对地漠不相关的,他人的幸福或苦难总是在我们心里自然产生一种快乐或痛苦。同情是人人共有的情感,它可以扩展至全人类,甚至使“最遥远的人们的行动和举止按照它们是否符合那条既定的正当规则而成为赞美或责难的对象”。[3](125)同情意味着对人类幸福和社会公共福利的自然趋向是人类从古至今的普遍追求,是存在于一切人之中的普遍能力。
休谟指出,惟有具备共通性和普遍性、综括力这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才属于他所说的同情,惟有这样的同情才使其成为一般的道德基础。但是不难发现的是,人们对于与己相似的人、与己亲近的人、在文化或语言方面与己相似的人通常会给予更多的同情,同情也存有偏私性、特殊性。如果人们从这样的特殊性出发来考察人们的性格和人格,那么人们连互相的交谈都会成为问题,更不可能形成一般性的判断。为此,休谟指出,生活中人们总通过经验改正情绪,使得人们依据“稳固的”、“一般的”观点对事物做出较稳定的、一般性的判断。[2](624)同情的偏私性、特殊性需要得到改正。一般性、普遍性的观点要求人们同情受到行为者行为最直接影响的那群人,并且忽略我们自己的特殊利益,也就是要求人们以一种“旁观者”的观点和立场做出判断。作为道德基础的同情是“旁观者的人道感受”,[3](82)是一种基于“旁观者立场”的同情,它克服了同情的偏私性,是建立在对人类幸福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共通感觉基础上的、以人类幸福和社会公共福利为判断依据的立场和观点,具有普遍性、一般性。
三、效用原则:同情作为道德基础的作用体现
在人性趋乐避苦的基本假设下,休谟指出同情是基于一种苦乐感,带来快乐感受的将受到赞许,而带来痛苦感受的则会遭到谴责。快乐和痛苦感受得以发生的源泉和原则是:对他人或社会有用、对我们自己有用、直接令我们自己愉快、直接令他人愉快,归结起来即是效用原则或愉快原则。效用原则是基于一种外在考察,而愉快原则是一种内在感受。令人愉快的常常是因为给人以效用感受,因此,区分善恶的苦乐感受的源泉归结起来就是效用原则。在休谟看来,效用原则是道德价值评判的基础和基本依据。那种对人类的幸福或苦难的同胞感即基于“旁观者”立场的同情,就是对公共利益和社会效用的感受,坚持效用原则就是确定对公共利益和效用的反思产生敬重或道德赞许,“一般而言,有用性这个因素具有最强大的效能,最完全地控制着我们的情感”。[3](55)这样,同情原则获得了客观的社会性依据,社会效用、公共利益成为道德之最高价值所在。
休谟通过完整阐述道德的源泉和原则体系,揭示了同情在道德决定中的基础作用,他说:“我们必需完全说明效用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从人类本性中最著名最公认的原则推演出来。”[3](64)具体来说,对于“对他人或社会有用”的品质,无论是“自然的道德”(比如仁爱),还是“人为的道德”(比如正义),其道德价值在于它们所具有的公共效用性,令人们感到愉快,抓住了人们的某种自然感情即同情,自然地会受到普遍赞许和尊重;对于“对自己有用”的品质,其道德价值主要不是因为它们自身直接具有的有用性趋向,不是因为“对自己有用”,而是因为“令他人快乐”,因为同情会让人们关注他人的幸福和苦难;而对人类的幸福或苦难的同胞感,也使得那些“直接令我们自己愉快的品质”因其能够直接传达给那个拥有它们的人以快乐而获得道德价值;至于“直接令他人愉快的品质”,其本身恰就是德性的本性所在,因为“德性的本性、其实德性的定义就是,它是心灵的一种令每一个考虑或静观它的人感到愉快或称许的品质”,[3](114)德性之所以令人赞许恰是它令人愉快的属性。显然,以上与道德的源泉或原则相对应的、有价值的品质都是藉着同情情感而被推崇为德性的。这样,基于“旁观者”立场的同情在个体的特殊利益与社会普遍效用之间架起了桥梁,为公共效用原则的实现提供了基础和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休谟效用原则中的效用并不是指一种实际的结果,而是一种关于效用的经验感受。休谟主张把目的圆满实现所依赖的各种外在的“幸运的条件”与人的“善良的心理倾向”分开。幸运地实现了目的的行为给人较强的快乐,并且引起“较为生动”的同情,但并不因此就是“更善良的”。[2](628)休谟明确主张要依据动机而不是依据结果来进行道德评价。他说:“任何一个对象就其一切的部分而论,如果足以造成任何令人愉快的目的,它自然就给我们以一种快乐,并且被认为是美的,纵然因为缺乏某种外在条件,使它不能完全有效。”[2](627)这种对动机的考察是建立在基于“旁观者”立场的同情基础上的,是借助“想象”看其是否自然地倾向于有益社会,休谟指出:“想象有一套属于它的情感……这些情感……与情感对象的真实存在无关。当一个性格在每一方面都适合于造福社会时,于是想象便容易由原因转到结果,而并不考虑还缺着使原因充分发挥其作用的某些条件。”[2](627)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休谟还饶有兴趣地列举“树由果知”的例子:一颗桃树比另一桃树好,是因为它结出更多更好的果实,尽管它的桃子在完全成熟之前已遭蜗牛或害虫所毁坏,对它的称赞也是一样的。[3](79)休谟从动机考察效用的道德评价理论,突出了同情作为道德基础的作用。
四、同情的客观实存性及个体同情程度差异性的矫正
同情原则是客观实存的。“一切事物总是呈现给我们以人类的幸福或苦难的景象,并在我们胸中激起快乐或不安的同情活动。在我们的严肃的工作中,在我们的轻松的消遣中,这条原则一直发挥着它的能动的效能。”[3](72)休谟指出,没有人会如此漠不关心其同胞的利益,以至觉察不出由于行动和原则的不同倾向而造成的道德的善恶区别,同情的程度“可以是争论的主题”,但同情的“实存的实在性”必定是每一种理论或体系都予以承认的。正是基于客观实存的同情,正常的人们总是给予社会的幸福以优先的选择。
同情具有客观实在性,但个体同情程度确实存在着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直接地与人们的想象有关。想象又与人们的经验与经历相关,想象“若非有相应的印象为他们现行开辟道路,都不能出现于心中”。[5](21)个体受制于经验与经历,会产生不同的同情感受。不过,同情感的这种差异“不在于对象本身,而在我们对它的位置”,[3](79)因此,个体同情感的差异性并不影响行为本身的价值。而人们对行为的道德价值的判断也并不是基于这样一种具有差异性的特殊个体的同情,而是基于具有普遍性的“旁观者立场”的同情。
但是,要做出正确的善恶判断,必须坚持具有普遍意义的善恶标准,坚持“旁观者”的普遍性立场。人们应当矫正个体同情可能存在的差异性、特殊性,克服情绪、情感上和知觉上的不平等性,否则,人们不可能进行任何的思想或讨论。为此,休谟提出矫正的两条途径,对现代伦理学发展具有重大启示意义。其一,通过语言的规范来克服个体同情的差异性。“一般的语言,既然是为了一般的用途而形成,就必须根据某些更一般的观点来铸造,必须附带契合于社会的一般利益所产生的情感的称赞或谴责的辞藻。”[3](80)语言是交往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本身往往就包含着谴责或赞许的情感,因此,一方面,我们对于人们品质的判断和讨论中,必须努力克服语言中不可避免的差异障碍,加强文化之间的沟通,使得我们的情感变得更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另一方面,个体同情差异性的克服要求克服语言自身的歧义性,增加其普遍和一般性的意义。对语言进行规范,是对行为规范的一种要求。由此,“休谟已经意识到语言对于道德能力和道德社会构建的重要性,虽然他的阐述还显得单薄和概略”。[6](93)其二,通过交流来克服个体同情的差异性。同情虽然是人人具有的一种自然情感,但也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每个人遭遇的社会境况不同,其所持有的立场和观点就会不同,因而造成个体同情感的差异性。为此,休谟提出通过社交和谈话,加强情感的交流。他说:“在社交和谈话中,情感的交流使我们形成某种我们可据以赞成或反对种种性格和作风的一般的不可变更的标准。”[3](80)通过交流,增进对别人的理解,才能在双方间建立更加“活泼”的同情,从而有利于矫正不平等的因素,坚持一种基于一般有用性的对于恶行和德性的一般标准。交流可以增进同情,而增进的同情反过来又促进交流的进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实用主义者查尔斯·霍顿·库利把同情不仅作为一个人道德水准的标志,也作为一种不可缺少的社会力量,要求人们增进自己的同情能力。[7](97)基于同情共感,关注人类普遍幸福,增进彼此的理解,正是现代商谈伦理学内涵的伦理要求。
五、休谟以同情为基础的道德情感理论的意义及其遭遇的困难
休谟的道德同情理论直接来源于莎夫兹伯利和哈奇逊,但后两者对同情共感的内涵及其作用机制均未做出系统的回答与阐述。休谟论证了同情共感作为道德基础的地位和作用,建构了较为完整的道德学说体系。他反对同时代理性主义者“把动机过于简单化,接近于曲解的程度”,[8](675)克服了理性主义研究的抽象性,把经验主义的方法引入精神科学和道德领域研究,进行道德合理性论证,更加注重丰富而充满生命力的现实道德生活世界,克服了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规则主义的单调和无情,指出理性在道德中的有限性,强调情感的基础性作用,从而通过还原人性的丰富性,使得道德更具生活气息,让人倍感亲切。
休谟强调同情的道德基础作用,使得道德自身充满激情,充满感染力,有利于个体获得完满的德性,获得一种符合人的本真需求的快乐,有利于人们保持一种对道德的敬畏。人们注意到,随着理性主义在现代社会片面的发展,常识理性的利益算计霸权导致情感衰落,人们追逐娱乐,寻求纯粹感官的刺激,最终导致道德权威的丧失。[9](114)而从同情理论出发,德性不再是冷漠的利益算计,而是充满激情的行为实践,道德因而充满魅力。忽视或否定人自身所具有的这种自然情感,道德就会失去生命力和权威性,“熄灭一切对德性的火热的情和爱、抑制一切对恶行的憎和恶,使人们完全淡漠无情地对待这些区别,道德性则不再是一种实践性的修行,也不再具有任何规范我们生活和行动的倾向”。[3](24)
通过对同情共感理论的论证,休谟表达了对人类生活方式的深刻思考。休谟承认自爱也是人性的组成部分,但他反对夸大自爱在人类道德行为中的作用,认为把自爱作为人性基础,以个体权利为中心,必然导致实践中人们日益陷入自我中心境地,成为彼此孤立的“单子”式的个体,造成人际关系的淡漠。而人人共有的同情感,表达的是对他人幸福或苦难乃至整个人类幸福或苦难的关切,它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交流。社会交往是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一种本能,它本质上就是一种情感交流。人与人之间就应是这样一种相互关切、充满情谊的关系。
现代哲学人类学奠基者舍勒指出“草率地对待感情事物和爱和恨的事物”是现代人所犯的一个过错,[10](56)他认为主观的情感也能把握对象关系,并对人的生命和生存产生重大影响。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休谟道德同情理论,是对理性与情感在道德中地位的再思考。正如休谟指出的,理性有它的有限性,在道德领域,我们应当重视情感的作用。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同情作为一种情感,其自身的经验性、主观性决定了休谟以同情为基础的道德情感理论必然遭遇理论和实践上的困难。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在以趋利避害作为基本人性假设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同情来根本解决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个体同情程度的差异性会损害同情原则的普遍性、权威性。人人虽共有同情感,但每个个体的经验和经历不同,个性也存在着差异,一个人在生活中常常不可能达到对另一个人的完全理解,从而造成基于“旁观者”立场的同情原则在道德实践中的困难。但是,我们不能否定的是,一个理论的价值往往并不在于它的完美性,而在于它能够给世人以启示,其理论上存在的缺陷恰恰构成后来者理论发展的起点。实际上,休谟的道德情感理论不仅被紧随其后的亚当·斯密直接继承和发展,现代情感主义伦理学也把休谟作为自己的理论溯源。
注释:
① 值得注意的是,休谟的“同情”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理解的“怜悯”的同义词。怜悯往往是他人痛苦在个体内心激起的反映。怜悯可以产生友善的行为,但这种有益和善良的感情有时却是建立在对对方自尊心的无情打击的基础上的,被怜悯者常常觉得受到侮辱。但在休谟的意义上,同情不同于怜悯。在休谟那里,怜悯只是由同情产生的一种情感反映。
[1]麦金太尔. 追寻美德: 道德理论研究[M]. 上海: 译林出版社,2003.
[2]大卫·休谟. 人性论·下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3]大卫·休谟. 道德原则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4]约翰·罗尔斯. 道德哲学史讲义[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3.
[5]大卫·休谟. 人性论·上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6]Paul Russell. Freedom and Moral Sentiment [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7]查尔斯·霍顿·库利.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8]乔治·霍兰·萨拜因. 政治学说史(下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9]R. W. 费尔夫. 西方文化的终结[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10]马克斯·舍勒. 爱的秩序[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