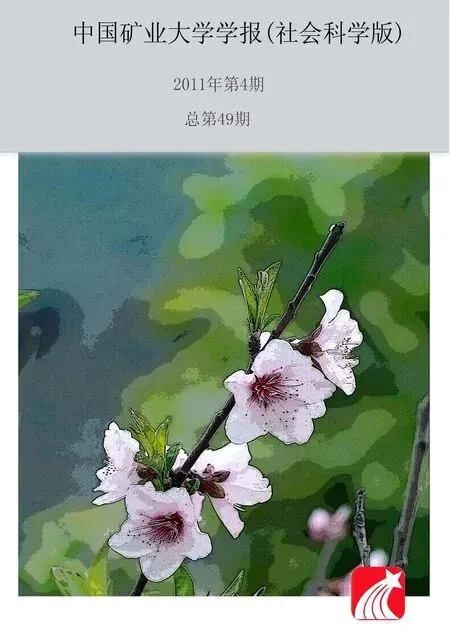宋濂的散文艺术与绵延意识
张思齐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宋濂的散文艺术与绵延意识
张思齐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宋濂是由元入明的文学家,为明代文臣之首。《阅江楼记》是宋濂的名作,其结构孕育着八股文的胚基,其文气即作者强烈的历史意识。宋濂的散文艺术,上承宋人王禹偁,下启清人刘曾。宋濂不同于王、刘之处在于他那特别强烈的绵延之感。在绵延中,过去、现在和将来互相渗透浑然一体。绵延是不可量度的精神活动,而文人在此活动中快乐无比极其幸福。中华民族文化的绵延是宋濂最为关心的问题。宋濂对历史的把握是一种带有其个性特征的时间感,它从根本上决定了宋濂散文的文本品质。
明代文学;宋濂散文;绵延意识;比较研究
宋濂(1310—1381)是站在历史交合点上的伟大的文学家。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国,取代元朝,国号大明,改元洪武,建都南京,并以其故乡凤阳为中都。这一年,宋濂已经五十九岁了。入明之后,宋濂只生活了十四年。宋濂享年七十二岁,他的一生之中,有五分之四强的时光是在元朝度过的,而在明朝度过的时光仅在其生命历程的五分之一弱。明朝开国之前,宋濂即已进入智囊团以辅佐朱元璋。《宋文宪公年谱》卷上:“[元至正]二十二年壬寅,先生五十三岁。……八月,进讲经筵,明太祖召先生与孔克仁讲《春秋左氏传》毕,先生进曰:‘《春秋》,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告归省亲。有白金文绮之赐,且曰:‘卿之诚慤,朕素知。’故有是赐。”[1]2707入明之后,宋濂仍得朱元璋信任,一路官运亨通。明初,宋濂应朱元璋之召,前往应天(今江苏南京)任江南儒学提举,兼授太子经书。不久,宋濂改官起居注,与刘基常侍朱元璋左右,以备顾问。洪武二年(1369)宋濂充任总裁官,修《元史》。待《元史》书成之后,宋濂升任翰林学士。之后,宋濂历任国子司业、礼部主事、赞善大夫。洪武六年(1373),宋濂升任侍讲学士。洪武九年(1376),宋濂进学士承旨。后来,宋濂以老致仕。
朱元璋的统治以严酷的专制独裁而著称于史籍。从朱元璋建立明朝起,文学进入了一个惨淡的时代。在这惨淡的时代里,多数文人都在痛苦中挣扎这种情况延续了一百二十年。其间居于皇位者有太祖、惠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代宗、英宗(二度为帝)和宪宗,一共九帝。至于年号,则由洪武、建文、永乐、洪熙、正统、景泰、天顺而至成化,一共九朝。直至1488年,明孝宗朱祐樘登基,改元弘治,这一情况才得到根本的扭转。从此,明代文学进入了复兴时期,蓬勃地向前发展了。宋濂在明代初期的文人中乃是境遇最好的,史称开国文臣之首。《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濂状貌丰伟,美须髯,视近而明,一黍上能作数字。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四方学者悉称为‘太史公’,不以姓氏。虽白首侍从,其勋业爵位不逮基,而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2]2512由此可知,宋濂之所以在明代文人中处境最好,不是因为他逢迎了朱元璋,而是因为他人格高尚,道德高尚,学问高深,识见高明。宋濂是一位积极入世的文人。元至正中,他因人推荐获授翰林院编修。然而,面对高官厚禄,宋濂坚辞不受,表现出了极大的民族气节。入明之后,宋濂进入朝廷,凭借丰厚的学养,获取崇高的职位,作为朝廷思想库的重要成员,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知识分子的能动作用,因而他能在元明易代这一特殊的历史格局中,洞见政治走向,顺应时代潮流。
由于常侍朱元璋左右,宋濂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朱元璋的文化专制主义。在明初文学整体惨淡的情况下,宋濂的文学创作犹如孤挺花,峭立石头危岩之上,一枝独秀。于是广大文人有了风向标,他们也就悄悄地行动起来,努力经营文学的事业,从而为文学在明代中期的复兴做了准备。这就告诉我们,宋濂的文学必有其过人的地方。研究宋濂文学的独特性,乃是一项饶有趣味的工作。为了切入这一工作,我们不妨由细微处着手,就其典型的文章加以解剖,庶几洞见出宋濂文学创作之本真面目。惟有如此,方能返归大略,庶几寻觅出规律性的认识来。
在宋濂的大量散文作品中,《阅江楼记》是较为重要的一篇作品。解剖麻雀,可知一切鸟雀。观察滴水,可见普遍规律。为着研究的方便,兹录如下:
金陵为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类皆偏据一方,无以应山川之王气。逮我皇帝定鼎于兹,始足以当之。由是声教所暨,罔间朔南,存神穆清,与天同体,虽一豫一游,亦可为天下后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狮子山,自卢龙蜿蜒而来,长江如虹贯,蟠遶其下。上以其地雄胜,诏建楼于巅,与民同游观之乐,遂锡嘉名为“阅江”云。
登览之顷,万象森列,千载之秘,一旦轩露。岂非天造地设,以俟大一统之君,而开千万世之伟观者欤?当风日清美,法驾幸临,升其崇椒,凭栏遥瞩,必悠然而动遐思。
见江汉之朝宗,诸侯之述职,城池之高深,关阨之严固,必曰:“此朕栉风沐雨,战胜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广,益思有以保之。
见波涛之浩荡,风帆之下上,蕃舶接迹而来廷,蛮琛联肩而入贡,必曰:“此朕德绥威服,覃及内外之所及也。”四裔之远,益思有以柔之。
见两岸之间,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肤皲足之烦,农女有斫桑行馌之勤,必曰:“此朕拔诸水火而登于衽席者也。”万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
触类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楼之建,皇上所以发舒精神,因物兴感,无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阅夫长江而已哉?彼临春、结绮,非不华矣;齐云、落星,非不高矣。不过乐管弦之淫响,藏燕赵之艳姬。一旋踵间而感慨系之,臣不知其为何说也!虽然,长江发源岷山,委蛇七千余里而始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时,往往倚之为天堑。今则南北一家,视为安流,无所事乎战争矣。然则,果谁之力欤?
逢掖之士,有登斯楼而阅斯江者,当思圣德如天,荡荡难名,与神禹疏凿之功同一罔极,忠君报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兴耶?
臣不敏,奉旨撰记,故上推宵旰图治之切者,勒诸贞珉。他若留连光景之辞,皆略而不陈,惧亵也[1]780。
《阅江楼记》是明代散文中的名篇。在今人所编的各种选本中,容易觅得这篇文章。然而,各本所录,分段各有不同,标点也有差异。笔者所录,文字依据今人所编《宋濂全集》。不过,根据这篇文章的内在逻辑,笔者将之重新分段,并且调整了标点符号。在分析这篇文章之前,委实有考订文字之必要。在“农女有斫桑行馌之勤”一句中,“斫”字不妥。程敏政编《明文衡》卷二十九录有《阅江楼记》,该句作:“农女有捋桑行馌之勤。”斫,用刀斧砍劈。捋,以手握物,向一端滑动。这正是采摘桑叶时的动作。此可以经书为证,《诗经·周南·芣苢》第二章:“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3]农民栽培桑树,主要是利用桑叶来养蚕。桑树的叶、果、枝、根和皮固然可以入药,但是人们捋桑叶,采桑椹,折桑枝,刨桑根,取桑皮。一般说来,人们是不砍斫整个桑树的。桑树的木材也可以做成各种器具,但是那须是生长在深山老林需要数十年才能够长成的大桑树,偶一砍伐之,而不是种植在田间的成片的桑树。田间种桑,追求的是产量,一般采用矮树作业法。既然大桑树不在田间,也就不需要农女行馌了。行馌,给田间耕作的人送饭。倘若有某位砍伐大桑树的壮汉,那么他自己会带着干粮前往深山老林,不必依赖农女行馌。
《阅江楼记》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在最后一段里,作者交代了写作的原委:“臣不敏,奉旨撰记。”原来这是一篇应制之作,亦即宋濂奉皇帝之旨意而撰写的文章。既然是奉皇帝的旨意而撰写文章,那么作者就不得不歌功颂德了。但是,假如一味歌功颂德,那么就会成为一纸虚文。深谙个中究竟的宋濂,抓住这个机会,发挥文章的教化功能,企图在歌功颂德中表达自己的政见。有境界的应制诗文,都是这样借题发挥的。自己的政见,借皇帝之口说出,其作用就会巨大,其传播就会广远。一般说来,应制之作,官气浓郁,大都堆砌着刻板的套话,因而陈词滥调充盈其间,从而文气迂腐而可读性较小。宋濂的《阅江楼记》却不是这样,它朝气勃勃,层层深入,传达了盛世之君须忧国忧民这一主旨。这篇文章,其意殷殷,丝丝入扣,它传达出一代忠臣须辅佐君王并且像对待父母兄弟那样关注民生的衷情。因此,《阅江楼记》虽然是代皇上立言,传递出来的其实是作者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事实上,朱元璋执政之后,逐步纠正文化专制之偏颇,逐步启用一批批文人,逐步重视文教建设。从这一系列政治趋向的变动来看,宋濂的确较好地发挥了高级知识分子的国家思想库作用。因此,宋濂《阅江楼记》的中心思想是:君臣一体,关心国家;君臣一体,关注民生;君臣一体,建设新生的政权。范仲淹(989—1052)在《岳阳楼记》里写道:“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4]士人立于朝廷,应当爱君如爱父,爱国如爱家,爱民如爱子,因为这三者本来就是相互依存的。在天下大治的情况下,君主、国家和民众乃是三位一体的存在;父母、家庭和子女也是三位一体的存在。自古以来,爱君者必爱国,爱国者必爱民,没有哪一个人是以君为心而不以民为心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出了表率,广大群众自然就会效法他们。幸甚至哉!范仲淹在三百余年之后遇到了知音,这位知音不是别人,就是宋濂。比较这两篇文章之后,我们有理由认为,宋濂的《阅江楼记》堪称范仲淹《岳阳楼记》的明代版本。
宋濂《阅江楼记》的结构是八股文的胚基,这是值得注意的。宋濂《阅江楼记》一文的突出特点,就是文章的结构非常巧妙。笔者将《阅江楼记》分为八段。这八段并非笔者随意所作的划分,而是因为其文脉本来就是如此,只能如此划分。所谓文脉,乃是古人的说法。借用今日之术语,文脉就是一篇文章的内在逻辑。只要稍加对比,就可以看出它们大致对应于八股文的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阅江楼记》的三段排比文,写得非常好。它们均以“见……”而起笔,从而描摹出皇帝在阅江楼上因览物而浮想联翩的神态。它们均包含一段言语的吐纳(utterance),以“此朕……”发出感叹。这些感叹,乃是皇帝的心理呢喃,不一定自口中说出来。它们均以一段推设作结,以“益思有以……之”收束。也就是说,心理呢喃反映了皇帝的构想,而这一构想并不停止在计划阶段,而是就要很快付诸实施的。从历史记载上看,朱元璋的确有即知即行的特点。在施政方面,朱元璋一贯具有雷厉风行的作风。宋濂《阅江楼记》与一般八股文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八个部分安排比较灵活,排比段落出现在文章的中间,而不是后半部。如果机械地写作,那么第六段也应该使用排比的句式,但是宋濂没有这样做。《阅江楼记》的第六段最长,采取单句散行的句式,这就为充分地展开论说提供了方便。诗歌与散文的区别有很多,但是最根本的是观念方式的区别。散文的观念方式与诗歌的观念方式相对立。在诗歌中,关键的是形象。在散文中,关键的是用作内容的那种单纯的意义。因此,就散文而论,观念就成了认识内容的单纯手段。在《美学》第三卷第三章中,黑格尔指出:“所以一般地说,散文的规范是精确、鲜明和可理解性,而用图像比拟的方式则较不精确鲜明。”[5]这就是在《阅江楼记》第六段里宋濂有意识地采用单句散行的句式之根本原因。不过,由于《阅江楼记》从整体上说具有八股文的雏型,同时它也是全文的重心所在,所以宋濂把它写得美轮美奂,文采斐然。八股文是一种综合的文体。八股文几乎囊括了中国文学的所有文类。从句式上说,八股文融骈文和散文为一体。从音韵上说,八股文融韵文和散文为一体。不管是哪一种融合,散文都是八股文的基质。这就是为什么在文体学上人们一般把八股文归于散文的原因。而且,具有境界的八股文也被人们看作优秀的古文。《阅江楼记》第六段就是点染著诗情画意的散文,其中也有一些描绘。为了获得历史的厚重感,在《阅江楼记》第六段中,宋濂特意穿插了若干典故。临春、结绮为阁名。南朝陈后主修建临春阁和结绮阁,经常在那里欣赏歌儿舞女的表演。后来隋兵攻入金陵,这两座阁,焚于战火。齐云楼为唐代曹恭王所修建,位于旧吴县的子城之上。元朝末年,朱元璋率兵攻克平江,活捉张士诚。躲在齐云楼里的张士诚群妾,尽焚于楼中。落星楼为三国吴主孙权所修建,位于今江苏省南京市东北。宋濂提及这些名阁和名楼,乃是为了与阅江楼作一番对比,从而彰显朱元璋的宏才大略。这也告诉我们,八股文的结构也是一般论说文所应当遵循的一种形式安排,它可以有某些变通,也可以有某些省略。这还告诉我们,大凡精心结撰的议论文,其结构往往与八股文暗合。宋濂《阅江楼记》一文,昭示了明代文学的走向。这是因为,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极盛时代,而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是八股文。八股文是明代最为重要的文章形式,它支配着文人们(literati)的实际生活,它不仅参与了明代的政治生活,它还集中地反映了明王朝的国家态势,那就是大一统,灿灿乎明代君臣追求国体光明正大,洋洋乎明代君臣渴望把事业做大做强。
宋濂《阅江楼记》层次分明而又一气贯注。这贯注全文的一气就是宋濂对历史的特殊感受,即历史乃一绵延体。我们知道,时间与绵延是一对相互依存的范畴。我们看到,时间与绵延是贯串在宋濂《阅江楼记》里面的一条哲理红线。《阅江楼记》中有多处言及时间与绵延,比如,“自六朝迄于南唐”,“千载之秘”,“开千万世之伟观者”等。雄伟壮丽的阅江楼巍然耸立在长江边的狮子山上。登楼之人,见滔滔江水,非常容易产生历史的联想。历史事件在时间中运行,历史文献在时间中被书写,江水在河道中前行,沙石在流水中被淘汰。时光在流逝,江水也在流逝。人们常说,时光如流水。在《论语·子罕》中,孔子的门人记录了夫子站在江边而兴叹的情形。孔子感叹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6]在《论语新解》中,钱穆指出:“不舍昼夜者,犹言昼夜皆然。年逝不停,如川流之长往也。或说:本篇多有孔子晚年语,如凤鸟章,美玉章,九夷章,及此章,身不用,道不行,岁月流逝,迟暮伤逝,盖伤道也。或说:自本章以下,多勉人进学之辞。此两说皆得之。”[7]人们常常说历史的长河。这是带有隐喻性质的一个词语。此语本身就告诉我们,时间与绵延与江河流水之间的关系,乃是何等紧密。
狮子山是一座绵延起伏的山,它像一条蜿蜒的长龙昭示着时间的绵延。在这里,地形地貌的蜿蜒舒展与历史事件的绵延流逝互为补充,勾勒出一幅幅史诗般的画卷。在这里,空间和时间形成了对立的统一。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江南二江宁府江宁县:“狮子山,府西北二十里,亦曰卢龙山,晋元帝初渡江,见此山绵延,因以拟北地卢龙。《志》云:山在城西北隅,周回十二里,西临大江。明初陈友谅趣建康,太祖亲总大军驻狮子山。友谅犯江东,憍转向龙江,至山下登岸立栅。太祖率诸军大战,友谅败走。寻建阅江楼于此。《金陵记》:狮子山在金川门外。”[8]狮子山,又称卢龙山,即卢龙塞,位于今江苏南京市西北。朱元璋亲督军卢龙山,事在元至正二十年(1360)夏五月。陈友谅(1320—1363)系元沔阳(今湖北仙桃市)人,本为渔家子,曾经担任过县吏。元朝末年,布贩出身的徐寿辉(?—1350)利用白莲教,组织起义,以红巾为号。这就是著名的红巾军起义。至正十一年(1351)十月,徐寿辉建国称帝,国号天完,年号治平。陈友谅见元朝大势已去,便加入天完红巾军,以战功卓著而升元帅。待到自身的势力雄大之后,陈友谅便开始杀戮诸将。至正二十年(1360年)五月,陈友谅杀害徐寿辉,自称皇帝,国号大汉,年号大义,尽有江西、湖广地。在明朝的开国者看来,这实际上是一股封建割据势力。为了建立明王朝,朱元璋必须消灭陈友谅的势力。这就是朱元璋在陈友谅称帝的当月便亲自督军于卢龙山的原因。朱元璋歼灭陈友谅的战争,乃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殊死搏斗,它一共持续了三年零三个月。陈友谅战败,事在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八月。《明史》卷一《太祖本纪一》:“八月壬戌,友谅食尽,趋南湖觜,为南湖军所遏,遂突湖口。太祖邀之,顺流搏战,及于泾江。泾江军复遮击之,友谅中流矢死。”[2]8此后,朱元璋逐渐削平其他割据势力。五年之后,大明王朝终于建立。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他要修建高楼崇阁,以缅怀峥嵘岁月,纪念赫赫战功,表彰有功之臣,振起全国民心。于是朱元璋下诏建造阅江楼,并亲自撰写了《阅江楼记》,又命众文臣各写一篇《阅江楼记》。本来题名为《阅江楼记》的文章有许多篇,然而只有朱元璋的《阅江楼记》和宋濂的《阅江楼记》流传下来。其他各篇《阅江楼记》都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渐次淘汰了。朱元璋的《阅江楼记》得以保存,因为他是皇帝。宋濂的《阅江楼记》之所以得以保存,乃是因为文章本身写得好。宋濂《阅江楼记》在民间广为传诵,后来还入选著名的选本《古文观止》。然而,历史似乎对人们开了一个大玩笑。这就是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所谓阅江楼,有记无楼;斯《阅江楼记》,无楼有记。人们在一篇又一篇的《阅江楼记》中所描写的阅江楼,只不过是一种文学性的想象罢了。这是因为阅江楼根本就没有修建起来。朱元璋所写的那一篇《阅江楼记》,一千二百余字,大抵雍容华贵。然而,朱元璋《阅江楼记》,自然与大多数帝王之作一样,四平八稳,新意无多,足以记事,难以感人。这篇文章载《眀太祖文集》卷十四,该文集由明代文人姚士观等人所编校。
《明太祖文集》卷十四尚有《阅江楼记序》一篇,录如下:“朕闻昔圣君之作,必询于贤而后兴。噫,圣人之心幽哉!朕尝存之于心,虽万千之学,犹不能仿。今年欲役囚者建阅江楼于狮子山。自谋将兴,朝无入谏者。柢期而上天垂象,责朕以不急。即日惶惧,乃罢其工。诚令诸职事妄为《阅江楼记》,以试其人。及至以记来献,节奏虽有不同,大意比比皆然,终无超者。朕特假为臣言而自尊,不觉述而满章,故序云。”[9]卷十四朱元璋的这篇序文告诉我们七个事实。第一,朱元璋欲修造阅江楼,以纪念战功。这是他的初衷。第二,朱元璋命群臣各作一篇《阅江楼记》。这是他的权术。本来,楼堂馆所阁记这一类的文章,大多写在建筑竣工之后。君不见,工程竣工,首长率领各位官员,浩浩荡荡,预为参观,文人才子,纷纷属笔。否则,未睹其物,如何写作记文呢?第三,为了调动群臣写作记文的积极性,朱元璋带头写作记文。由于皇帝亲自动手写文章,所以任何大臣都无法推诿了,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去写作记文。由此可见,朱元璋为了实施他的权谋,达到了处心积虑的地步。朱元璋为了让人们相信他是真心实意地要修建阅江楼,便下达命令,调集各监狱中的囚犯,去充当劳动力,平整地基。第四,朱元璋这一次弄权术,目的是要考察群臣对大兴土木修建楼堂馆所阁的态度。第五,待到群臣表态之后,朱元璋突然宣布停工。为此,他还编造了一个理由:上天托梦给他,告诫他不要着急,这一类工程,以后再修建。第六,朱元璋给群臣之作文打分。他打的分都不高,这是因为在他看来群臣所作之文,都不好。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朱元璋认为群臣之作文都不好呢?那些文章的缺陷是什么呢?原来,朱元璋认为,群臣在他们的文章中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见解。第七,朱元璋在评判文章的时候。坚持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他下令修楼也好,他下命作文也好,都围着一个目的,那就是建设和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于是我们看到,《阅江楼记》具有宏大的写作背景。由兹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提出来的那个文学批评的著名命题:“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0]欲文章之不朽,岂能脱离主旋律乎!
在这篇文章的后面,还有一段文字:“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皇帝坐东黄阁,询臣某曰:‘京城西北龙湾狮子山,扼险而拒势,朕欲作楼以壮之,雄伏遐迩,名曰阅江楼。虽楼未造,尔先为之记。’臣某谨拜手稽首而言曰:‘臣闻古人之君天下,作宫室以居之,深高城隍以防之,此王公设险之当为,非有益而不兴。土阶三尺,茅茨不剪,诚可信也。今皇上神谋妙算,人固弗及,乃有狮子山扼险拒势之诏,将欲命工。臣请较之而后举。且金陵之形势,岂不为华夷之魁?何以见之?昔孙吴居此而有南土,虽奸操忠亮,卒不能擅取者,一由长江之天堑,次由权德以沾民。当是时宇内三分,劲敌岂小小哉?犹不能侵江左,岂假阅江楼之拒势乎?今也皇上声教远被遐荒,守在四夷,道布天下,民情効顺,险已固矣,又何假阅江楼之高扼险而拒势者欤?夫宫室之广,台榭之兴,不急之务。土水之工,圣君之所不为。皇上拨乱返正,新造之国,为民父母,协和万邦,使愚夫愚妇无有谤者,实臣之愿也。臣虽违命,文不记楼,安得不拜手稽首,以歌陛下纳忠欵而敛兴造、息元元于市乡。乃为歌曰:天运循环,百物[百物祯颁。真人立命,四海咸安。臣歌]圣德,齿豁鬓斑。亿万斯年,君寿南山。’”[9]卷十四不少人误以为这一段文字也是朱元璋《阅江楼记序》的一部分。这是错误的。这一段文字,在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中特地高一格书写,以表明它与其前朱元璋《阅江楼记序》有所不同。这实际上是编者所加的一篇按语,用以说明朱元璋《阅江楼记》和《阅江楼记序》的写作原委。从这篇按语中,我们也可以明白各位大臣写作《阅江楼记》的原委。从这篇按语中,我们还可以明白那一桩因为阅江楼而发生的文坛公案:有记无楼。这篇按语由皇帝与“臣某”的对话构成。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位“臣某”究竟是谁呢?某,在古代汉语中有两种用法,一是指代不明的人物、事物、时间或地点;一是自我的谦称。比如,张某、李某,就是姓张、姓李的人言及自己的时候所用的谦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明太祖文集》提要:“《明太祖文集》二十卷,明巡按督学御史姚士观、南京户部督储主事沈鈇仝校刋,两江总督采进本,分十八类,曰诏,曰制,曰诰,曰书,曰勅命,曰策问,曰勅问,曰论,曰乐章,曰乐歌,曰文,曰碑,曰记,曰序,曰说,曰杂著,曰祭文,曰诗。……焦竑《国史经籍志》列《太祖文集》二十卷,又三十卷。此本卷数与竑所列前一本合,当卽竑所著录欤。其刻在万历十四年,编次不知出谁手。目録之末,有姚士观等跋语。乃据旧本刻于中都,亦未能详考所自来也。考朱彛尊《明诗综》载有太祖神凤操一首,而集内无之,则亦未为赅备。然所谓三十卷者,今未见传本,其存佚均未可知。近时诸家所藏弆,大抵皆即士观等所刻。今亦据以著录,存有明一代开国之著作焉。”[11]另据《江南通志》卷九十学校志记载,万历十六年(1588),池州知府姚士观,将当地的为实书院改为储才书院。由此可知,姚士观为明末吴中名士,他绝无与朱元璋对话之可能。在前引按语中“臣某”只能是明初的“某臣”了。笔者认为,这位“臣某”其实就是宋濂。宋濂虽然写了一篇流传至今的《阅江楼记》,但是他并不主张大兴土木修建楼堂馆所阁。虽然,秉持类似主张的重臣不止宋濂一人,但是秉持类似主张而又与撰写《阅江楼记》相关因而与皇上对谈的大臣却只有宋濂一人。宋濂生性崇尚简朴,康熙年间所修《浙江通志·宋濂传》:“日本遣使求文,以百金为献,却不受。上以问,濂对曰:‘天朝侍从之官,而受小国金,非所以崇国礼也。’四夷朝贡,必令其使问宋先生安否。”[1]2308明太祖朱元璋固然有为政专制的一面,但是他生活作风简朴,严厉惩办贪官,这也是名著史册的。朱元璋之所以下令停建阅江楼,还是他从全国财政大局考虑的结果。经过深思熟虑后,朱元璋认为应该首先解决紧迫的军国大事。至于修建楼台馆所阁,这一类事情实在应该缓一缓。比如,朱元璋认为应该集中财力人力修建南京和中都凤阳的城墙。而且,由于耗费巨大,事实上后来连中都凤阳的城墙也停建了。
吾师顾易生先生指出:“金元的诗文批评,基本上沿袭宋的余风。”[12]诗文批评如此,诗文创作亦然,而且这一基本格局尤其得到有明一代文人的认同。在宋濂的心理流中存在着强烈的绵延意识。在《阅江楼记》与文类承传的关系中,我们也能看见宋濂的心理流所激起的层层波澜。在宋濂的《阅江楼记》一文中清晰地存在着的作者感觉、物体意象、文体表象和历史观念等组成的表层心理。其实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宋濂的意识外壳。它们犹如河面上结成的冰壳。宋濂的心理流在冰盖下面流淌。贯串于宋濂《阅江楼记》字里行间的还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能量之流,这才是作者意识的真正本质。这一道能量之流才是宋濂的真正自我,或曰基本自我。宋濂对历史的把握乃是一种时间感。在宋濂看来,中华文化的道统绵延不断,中国文学的传统也绵延不断。在他看来,不管人们记得起来与否,明朝的正统文人和作家应该是直接承接宋代的文学传统的。诚然在宋朝和明朝之间曾经横亘着一个元朝(1279—1368),然而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这个横亘着的障碍物就被挪开了。在今人看来,元代亦有元代的文学。在明人看来,事情却不是这样。明代正统文人认为,元代九十八年充其量不过是历史长河的一道支流罢了,因而元代文学不过是宋代文学的余风罢了。明代正统文人认为,明代文学应该绍继的是宋代文学而不是元代文学,巍巍然三百二十年的宋代文学与在他们看来应该永远存在下去的明代文学乃是一个整体。有趣的是,宋濂《阅江楼记》的文本存在正是如此。从文本的质地(texture)来看,宋濂的《阅江楼记》显然脱胎于北宋王禹偁的《待漏院记》。为便于比较研究,兹录王禹偁《待漏院记》如下: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岁功成者,何谓也?四时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气矣。
圣人不言,而百姓亲、万邦宁者,何谓也?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敎矣。
是知君逸于上,臣劳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数也。是不独有其德,亦皆务于勤尔。况夙兴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犹然,况宰相乎!
朝廷自国初由旧制,设宰臣待漏院于丹凤门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阙向曙,东方未明,相君启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哕哕銮声。金门未辟,玉漏犹滴。彻盖下车,于焉以息。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
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来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畴多芜,何以辟之;贤人在野,我将进之;佞臣立朝,我将斥之;六气不和,灾眚荐至,愿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诈日生,请修德以厘之。忧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门既启,四聪甚迩。相君言焉,时君纳焉。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则总百官,食万钱,非幸也,宜也。
其或私雠未复,思所逐之;旧恩未报,思所荣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车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势,我将陟之;直士抗言,我将黜之;三时告灾,上有忧色,构巧词以悦之;郡吏弄法,君闻怨言,进谄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门既开,重瞳屡迴。相君言焉,时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则死下狱,投远方,非不幸也,亦宜也。
是知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复有无毁无誉,旅进旅退,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者,亦无所取焉!
棘寺小吏王某为文,请志院壁,用规于执政者[13]。
如此分段,由笔者所为,标点亦然。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冬,王禹偁写下了这篇《待漏院记》。那一年,王禹偁任大理评事,年仅三十四岁。所谓待漏院,就是古代为方便百官到皇宫上朝所设的休息场所。王禹偁写作这篇文章的目的,乃是借待漏院为引子,就宰相的职能与为人,论述了他自己的看法。在封建社会中,宰相位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负责处理国家运转的日常事务。《待漏院记》一文的重点,就是分析各类宰相的品行和心理活动。称职的宰相必须达成对皇上负责和对百姓负责的一致性。一位好的宰相,既要让皇上满意,又要关心民生。唯有如此,才能岁稔邦宁,开启一代太平盛世。王禹偁《待漏院记》由八段构成,首二段结构对称,好比一根绳子的两股绞线,形成排比。第三段提出论述的中心,即宰相的职能。第四段将宰相的职能与待漏院这一特殊的空间环境联系起来,从而将论题具体化。第五段和第六段为全文的重心所在,作者描述分析了各类宰相的心理活动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这两段字数基本相同,结构完全对称,好比一根绳子的两股绞线,形成排比。第七段为全文的理论升华部分,论述宰相的好坏关乎一国之政这一道理,并谴责了那些尸位素餐、碌碌无为、只知保全个人禄位的庸俗宰相。第八段,交代写作的缘起,并收束全文。显然,在王禹偁的《待漏院记》中也孕育着八股文的胚基。
宋濂《阅江楼记》上承宋代王禹偁的《待漏院记》,下启清代刘曾的《汉关夫子春秋楼记》。宋濂不同于王禹偁和刘曾之处,在于那特别强烈的绵延之感贯串于全篇文章之中。简言之,在宋濂看来,就宇宙而论,惟有绵延才是真实的时间;就文学而论,惟有中国文学的绵延才是真实的存在。在绵延中,过去、现在和将来,互相渗透,浑然一体,并没有分明的界限,因为绵延乃是不可量度的精神活动,而文人在此活动中乃是快乐无比、极其幸福的。
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真是一个伟大的绵延体。2001年,阅江楼终于建成。2002年狮子山阅江楼风景区已对外开放。阅江楼与黄鹤楼、岳阳楼和滕王阁合称江南四大名楼。阅江楼应该怎么修?阅江楼的体制应该如何定?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今人的主要依据就是宋濂这篇《阅江楼记》。明人设想的阅江楼主要用于表记战功。今天的阅江楼主要用于旅游。一国旅游之兴,标志着该国的兴盛。国内旅游之兴,其基础在于经济实力。国际旅游之兴,其基础在于综合国力。而今,节日众多,假期变长,这说明中国变得强大了,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了。这也是中华民族历史绵延的一种表征。倘若宋濂得见其记叙中的阅江楼,早已人来人往,游客如云,当会何等欣慰!
[1] (明)宋濂著.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2] 中华书局编辑部.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
[3] 程俊英,蒋见元译注.诗经[M].长沙:岳麓书社,2000:7.
[4] 四川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宋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24.
[5] (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61.
[6] (春秋)孔丘著,杨伯峻今译,刘殿爵英译.论语(中英文对照)[M].北京:中华书局,2008:150.
[7] 钱穆.论语新解[M].成都:巴蜀书社,1985:224.
[8]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160.
[9] (明)·姚士观.明太祖文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长沙:岳麓书社,2002:1566.
[11]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Z]北京:中华书局.1965:1464.
[12] 王运煕,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上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275.
[13] 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16.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ong Lian:His Art of Prose and His Consciousness of Duration
ZHANG Si-qi
(College of Litera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Song Lian,a writer living in an era of the Yuan Dynasty(1271—1368)changing into the Ming Dynasty(1368—1644),is regarded as the first master of the Ming literati.An Account of the Tower Overlooking the Yangtze is a masterpiece by Song Lian.Its structure is the embryo of the eight-part essay and its literary vigour is the author’s strong consciousness of history.Song Lian’s art of prose is a continuation of that of Wang Yucheng who lived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that of Liu Zeng who lived in the Qing Dynasty.Song Lian distinguishes himself from both Wang and Liu in that his sense of duration is extremely strong.In the duration,the past,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are mingled into an integral whole.The duration is a sort of spiritual activity immeasurable in which the literati feel extremely joyful and boundlessly happy.Song Lian most concerns himself with the dur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Song Lian approaches the history with an individualized sense of the time,which decides the textural quality of his prose.
the Ming literature;Song Lian’s prose;duration consciousness;comparative study
I207.62
A
1009-105X(2011)04-0119-07
2011-09-0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BZW020)
张思齐(1950-),男,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