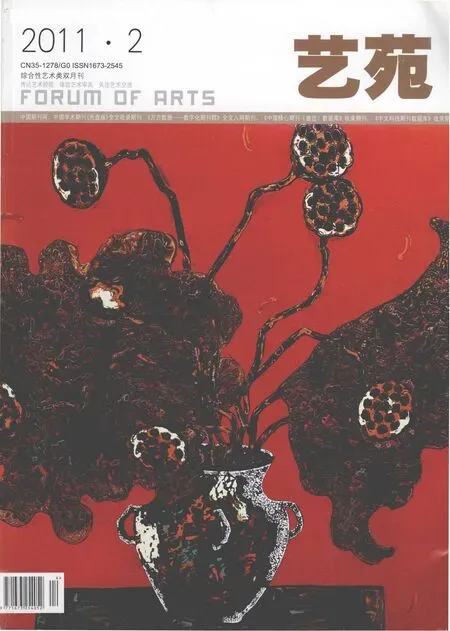人类精神生态的症结与出路——易卜生后期戏剧的深生态学解读
文/汪余礼
如果说,“要真正解决生态问题,不仅仅是要解决自然生态问题,更为根本的还在于要解决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方面的问题”[1](P46),那么易卜生后期确已意识到这一点,并在戏剧中持续而深入地探讨人类“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方面的问题”。作为一位以“描写人类”为己任、以“实现我们每个人真正的自由和高贵”为使命的艺术家,易卜生尤其注重对人类精神生态的洞鉴与审思;而且,他在戏剧中所作的探索具有鲜明而强烈的现代性,至今仍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与深思。因此,本文拟从深生态学的角度观照易卜生后期戏剧,发掘其中所内蕴的洞识与智慧,以期为我们今天从根基处反思生态危机、建构生态文明提供思想触媒与智力资源。
综观易卜生后期10部戏剧,每部作品对人类精神生态的洞鉴与审思各有其特殊性,不便概而言之;因此,下面笔者拟本着宏观与微观、普遍与特殊相结合的原则,尽量准确地加以论述。
一、群鬼的纠缠与蛮性的遗留
在易卜生后期戏剧中,经常出现的、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意象是“鬼魂”或“死人”,与之对应反复出现的意象是“阳光”或“日出”;由此可以切入易卜生后期戏剧的核心意蕴。
首先不能不提到的是《群鬼》。这部发表于1881年的作品,对于当时人们所受的精神禁锢作了极为深刻的揭示,直到今天仍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剧中海伦由母亲和姑姑做主嫁给阿尔文中尉后,不久发现丈夫是个荒淫无度的酒鬼,她难以忍受那种可耻的生活,希望借助曼德牧师的帮助跳出苦海。但曼德牧师告诉她“你的义务是低声下气地忍受上帝在你身上安排的苦难”、“心甘情愿地忍受束缚”。此后海伦忍辱负重,一面为丈夫做善事撑面子,一面为儿子挣学费铺前程。但她丈夫阿尔文并不因此有所收敛,反而“索性把丑事闹到家里来了”——引诱女佣乔安娜并致其怀孕。就在曼德牧师一再把她“深恶痛绝的事情说成正确、合理的事情”之后,海伦开始了自己的反思:
因为有一大群鬼把我死缠着,所以我的胆子就给吓小了。……我几乎觉得咱们都是鬼,曼德牧师。不但咱们从祖宗手里承受下来的东西在咱们身上又出现,并且各式各样陈旧腐朽的思想和信仰也在咱们心里作怪。那些老东西早已失去了力量,可还是死缠着咱们不放手。我只要拿起一张报纸,就好像看见字的夹缝儿里有鬼乱爬。世界上一定到处都是鬼,像河里的沙粒那么多。咱们都怕看见光明。[2](P253)
这里阿尔文夫人的反省是相当深刻的,她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死鬼和活鬼们——各式各样陈旧腐朽的思想和信仰以及信守这些死东西的人——如何死缠着自己,令她几近窒息而无力反抗。具体说来,在剧中,对她毒害最深的“死鬼”是源于基督教会及其牧师的一些道德信念,如“做老婆的不是她丈夫的裁判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只能尽自己的义务,没有权利享受幸福”、“女人嫁后应该靠紧自己的男人,低声下气地忍受上帝所安排的苦难”[2](P238),“人生在世不应该追求幸福,而应自觉忍受苦难以求赎罪”、“女人嫁后应从一而终,绝不应该希求改嫁”、“女人应始终牢记为妻为母的义务,而不应追求个人的快乐”,等等;对她钳制最狠的“活鬼”则先后有阿尔文和曼德牧师,后者在海伦想走出鬼窟时不但不理解她合理的愿望,反而用基督教会的那些律条,把她说成是“罪孽深重的人”。作为一个比较胆小的女人,海伦半信半疑地守着传统的教条、牧师的劝告。为了残存的那点希望(把儿子培养成人),她包容着最难包容的丑事,忍受着最难忍受的痛苦,但最后那点希望还是破灭了。她儿子欧士华遗传了阿尔文的梅毒,在一个黑夜里突然发作,肌肉松弛,眼神呆滞,嘴里平板地重复着“太阳、太阳”,庶几成了白痴。海伦、欧士华的悲剧有力地映现出在“覆盆不照太阳晖”的环境中“群鬼”是如何戕害人的精神与生命。
在人类的潜意识深处,比宗教律条更古老、更普遍、也更制约人健康发展的是各种各样的“蛮性”。所谓“蛮性”,是指人在进化过程中没有蜕掉的动物性、野性、兽性。最初,原始人类在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中打败其他动物,顽强地活了下来;而他们在求生过程中所积累的竞争经验则代代相传,化为后人心灵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并在后人生存竞争的过程中得到丰富、强化和深化。于是我们看到,历史上多数人自觉不自觉地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演绎了一幕幕恃强凌弱、互相残杀的悲剧。而只有极少数目光深邃、智慧超群的人,看出这种“蛮性”最终可能使人类走向毁灭,于是便以种种形式点拨、警醒“愚昧的世人”。易卜生正是这样一位深切关怀人类命运而又极富远见卓识的艺术家,他在1883年之后创作的《野鸭》、《罗斯莫庄》等作品对人类心灵深处的蛮性所作的洞鉴与解剖,尤为发人深省。
1884年,易卜生发表了《野鸭》,此剧艺术视野远超前作,在易卜生戏剧生涯中具有开拓新境、承前启后的关键意义。大体而言,《野鸭》对人类精神生态的揭示是在四个向度上展开的:以威利形象刻画出社会上那些信奉丛林法则的“强者”的性格与命运;以艾克达尔、雅尔马形象剖露出被损害的“弱者”的生态与心态;以格瑞格斯和瑞凌形象展现出“拯救者”的思维与行径;以海特维格形象呈示出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生态人”的性情与观念。在剧中,威利是个非常精明狡诈的木材商,多年前他欺骗了合办林业公司的朋友艾克达尔,致使后者锒铛入狱,从此跌入人生的低谷。而且他骗过的人不在少数。他儿子格瑞格斯对父亲骗人害人的行径极为不满,曾当面指责他:“我一想起你从前干过的事情,眼前就好像看见了一片战场,四面八方都是遍体鳞伤的尸首。”这暗示出:威利骨子里是个信奉“丛林法则”的家伙,或者说在他身上有着非常浓厚的“蛮性的遗留”。就事实而言,他过去的斑斑劣迹不仅导致很多人倾家荡产,也给他人的精神心理带来了严重的创伤。被他蒙骗过的老艾克达尔,从监狱里出来后就像一只挨了子弹的“野鸭”,“一个猛子扎到水底里,再也冒不起来了”。其子雅尔马则生活在虚幻的梦想中,精神渐趋麻木——就像那只养在水槽里的野鸭,年深月久后,翅子再也飞不起来了。而威利在害人后日子过得也并不逍遥——他的眼睛快要瞎了,亲生的儿子又坚决反对他,拒绝跟他合作,这样他几乎是走到穷途末路了。易卜生写到威利的眼睛快要“瞎”了,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其内在本质与命运的一种隐喻。质言之,威利也是一只扎在水底看不见广阔前景的“野鸭”。
到了《罗斯莫庄》(1886年出版),易卜生对人心深处“蛮性的遗留”探掘得更为深入了,同时也对之进行了更为严厉的审视。这种探掘与审视主要是通过塑造吕贝克形象来实现的。在该剧中,吕贝克是一个蔑视传统习俗、崇尚自由解放、意志坚强、思想新锐的女性。她就像“北方山头峭壁上的一只鹰隼”,目光炯炯,行动果敢,比男人更具有攻击性。来到罗斯莫庄后,她很快拿定主意要除掉罗斯莫的妻子碧爱特,并得到罗斯莫的爱情。她一面以她的漂亮、性感、热情以及一套套的自由观念、解放思想感染、影响罗斯莫,另一面则设法取得碧爱特的信任,以至几乎可以牵着她的鼻子走。如其所愿,碧爱特后来被她“引上迷惑的道路”,跳进水车沟自杀了。这是一桩无法回避的罪孽。事后吕贝克虽然希望能顶着罪感继续前进,但她在与罗斯莫相处的日子里,逐渐受到后者人格的感染,良心上越来越难受。当原先想要的幸福即将来临时,她却不能不悲哀地承认“我的历史把我的路挡住了”。最后,她决定以自惩洗刷自己的罪恶。通观全剧,就吕贝克的生命历程而言,正是她以前“蛮性的发挥”挡住了她后来通往幸福的道路。易卜生以深邃的目光看到了那种“蛮性”黯淡的前途,也隐示了人类精神发展的正确方向,这是我们不能不“睁眼看清楚”的。

从根本上说,人若任性耍蛮、依循丛林法则行事,实质就像“野鸭”一样盲目,像吕贝克一样自己挡自己的路。人类如果不能走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则不但不可能进化、实现可持续发展,还有可能发生“退化”。聂珍钊先生曾说,“丛林法则是动物界维护秩序的自然伦理,它只适用于没有理性的动物界。……如果我们人类接受了丛林法则,我们就会变为野兽,不再为人。”[3](P89)而挪威皇家科学院院士何莫邪先生,出于对19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种种“怪现状”的洞察与忧思,甚至提出了一种“退化论”。总之,人类是否能超越丛林法则,实质上关涉到人类自身的前途与命运,在当代尤其应该引起人们的警醒与深思。
二、魔性的涌动与酷烈的自审
与“蛮性”紧密相关的是“魔性”。“蛮性”主要具有破坏性,“魔性”则既有破坏性,又有创造性;“蛮性”存在于几乎每个人潜意识的深处,“魔性”则主要存在于那些天赋优厚、才华杰出者心灵的深处。这两者有时会混在一起,互相推助,兴风作浪,产生出极为可怕的破坏力量。易卜生后期戏剧对此亦多有探索,并以立象反照、艺术自审等形式对其进行了极为深邃的反思。
在《罗斯莫庄》出版后第四年(1890年),易卜生写出了《海达·高布乐》。剧中的海达,年少时喜欢“骑着大马,跟着将军在大路上飞跑”;出嫁时,带着两把手枪来到泰斯曼的新家。这隐示出,她从小所接受的熏陶,乃是“征服者”的人生观和贵族的荣誉观。嫁给一心钻研学问的泰斯曼后,她百无聊赖,在心里梦想着曾经热恋过的艾勒达·乐务博格,但又不敢有所行动。而她原先很瞧不起的泰遏(即爱尔务斯泰太太),不但成功地使乐务博格改邪归正,并且与他合作完成了一本书。这一切使得海达又嫉妒又恼恨,便设法烧掉了他们合写的书稿,并激励乐务博格去自杀。这就显露出海达性格中的一种重要因素——魔性。
易卜生说:“海达身上的魔性因素在于:她想要把她的影响力施加到某个人身上,而一旦这种愿望实现,她就会鄙视他。”[4](P449)从剧本实际来看,这只是点明了海达身上魔性因素的一个方面。除了平日里不可遏制地涌出一些恶意冲动之外,她还“对于毁灭有大欢喜”。“对于海达来说,自杀宛如一幅完整的英雄主义图画,一幅‘完美’的图画。出于这个原因,她给了乐务博格一把自己的手枪,仿佛这是记忆的信物,要求他保证让自杀‘完美地’发生。”[5](P150)同样出于这个原因,海达最后用剩下的一枝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把乐务博格没有做好的事情“完美地”做到了。对此,马丁·艾思林认为:“海达的自我实现,由于许多外在的、超出她控制能力的因素,而悲剧性地成为不可能。……她的破坏性,仅仅是她的误入歧途的创造性,以及真我未达身先死的悲剧性失败。”[6](P36)这里,艾思林的分析大体是中肯的,但他忽略了海达内心的魔性——这一点易卜生自己在札记和书信中曾反复提到。正是由于海达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魔性冲动,使她害死了别人,也走向了自戕。茨威格说:“魔性在一些人身上就像发酵素,这种不断膨胀、令人痛苦、使人紧张的酵素把原本宁静的存在迫向毫无节制、意乱神迷、自暴自弃、自我毁灭的境地。”[7](P130)这话用在海达身上,可谓一语中的。而易卜生之所以着力刻画出海达身上的“魔性特质”,正是为了“从身上刷掉它们”,以便实现“灵魂的净化”。
紧接着,在《建筑大师》中,易卜生对艺术家-创造者心魂中的“魔性”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洞鉴与审思。在该剧中,主人公索尔尼斯身上的魔性,一方面使他不由自主地向着心目中的目标驰骛不止,另一方面又使不由自主地倾向于控制和压迫他人。作为创造者之魂,索尔尼斯体内的山精与妖魔既有创造性、建设性的一面,又有叛逆性、破坏性的一面。尼采在《权力意志》中说:“最强者,即具有创造性的人,必定是极恶的人,因为他反对别人的一切理想,他在所有人身上贯彻自己的理想,并且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他们。”[8](P112)这话未必是真理,但用在索尔尼斯身上倒也比较贴切。确实,在索尔尼斯的人生履历中,既有显明的恶迹,比如残酷地把老布罗维克踩在脚下,又严厉地控制着他的儿子,使之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也有隐在的恶意,比如一心盼望艾琳家的老房子被大火烧掉,以便他的建筑事业可以起步。最后索尔尼斯在希尔达的鼓动下登上塔楼,终于把持不住掉下来摔死了。这一结局,表面上看是“恶有恶报”,但其实也可以看作是索尔尼斯的自审自裁。他虽然恶迹斑斑,但良心未泯;他为自己过去的行为感到痛苦,但又深知自己体内的魔性是自己把握不了的——只要还活着,就免不了要操控他人。最后,他明知必死而登上塔楼,在某种意义上是他自身的神性对魔性的超越,是有限者向无限者的皈依。
此后第四年(1896年),易卜生在《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一剧中再次探索、审判了创造者潜藏有魔性的灵魂。但与索尔尼斯不同的是,银行家博克曼在挪用银行巨额存款、杀害女友爱情生命后被捕入狱,在随后漫长的13年里他一遍又一遍地审查自己的动机与行为,“自己当原告,也当被告,并且还当审判官”,但得出的结论是:“我没有任何罪,只是对不住我自己。”他觉得自己唯一的错误在于出狱后没有“从头做起,重新爬上高峰”,“铲除中途的一切阻碍,爬得比以前更高”——像浮士德那样“自强不息”,把创造和破坏进行到底。这是一个至死忠于自我野心、顽固地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心中的“魔性”较之索尔尼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曾经叱咤风云,是“天才英纵的一代豪杰”;但他无限制地自我扩张分明给很多人带来了无可挽回的灾难。最后他在雪夜里被一只“冰冷的铁手”击中而死。哈罗德·克勒曼认为:“在这个结论和忏悔中,易卜生宣布了他最深刻的服罪之感。”[9](P236)不管这是否隐示了易卜生本人的“忏悔”与“服罪”,但至少表明了艺术家对魔性灵魂的严肃审判。
魔性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确属我们人类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歌德曾说过:“具有魔性的人物往往会发挥出令人不可置信的力量,在一切事物上面甚至在天地间都具有无与伦比的威力,影响之大,简直没法形容。即使是集结起所有的道德力量,也不是他的对手。”[10](P515)这暗示出魔性力量与道德力量往往是对立的,或至少是交错的。一般而言,魔性如能得到理性有效地调控,可能会转化为创造性的力量;如果冲破理性的控制,不能自已地爆发出来,轻则伤人伤己,重则可能对人类的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造成极大的伤害——就在《海达·高布乐》发表前一年,希特勒出生,40年后他便以巨大的魔性力量不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也毁灭了他自己。在此我们不能不惊叹易卜生高度的敏慧,他对于时代潮流中那股阴冷的暗流仿佛已感到丝丝凉意,便预先表现了出来。惜乎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玩偶之家》演出剧照
三、精神的变革与新生的曙光
如果说人类要是放纵自身的“蛮性”、“魔性”最终很可能导致自我毁灭的话,那么人类必须在深刻反省的基础上调整、改造自我,并寻求新生之道。易卜生在《〈海达·高布乐〉创作札记》中已经提到:“新的空间必须被清理出来,以便人类的精神能够发生伟大的转变,因为它已经误入歧途。人类的精神已经误入歧途。”[4](P447)在1897年夏致米莱夫斯基伯爵的信中,易卜生再次说:“人类的发展从一开始就脱离了正确的轨道。”[11](P329)那么,在易卜生看来,人类的精神应该发生怎样的变革,才能走上正确的轨道,实现永续健康发展呢?
易卜生后期戏剧在透视、剖析人类精神中种种病态的同时,对这一问题有着越来越深入的思考。在《野鸭》中,易卜生对“拯救者”格瑞格斯已隐隐有所批评。格瑞格斯的“拯救”计划之所以失败,不只是由于他行事鲁莽,更主要的是:他的内心被“理想的要求”所充满,对人对物缺乏真挚的爱心;换言之,他的理念是热的,而情感是冷的。即便在海特维格自杀后他也没有感到震惊与痛苦,而只是急于为自己开脱罪责。如果他心里对人对物有同情的理解,能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那么他就不会对雅尔马说出那个致命的真相,也不会劝海特维格“牺牲掉自己最心爱的东西”。可能正是基于对格瑞格斯型人物的反思,易卜生随后在《罗斯莫庄》中把灵魂拯救的希望寄托在“真爱”上,隐示出“如果真情、真爱的确能提高人的心智,那倒是人间一桩最光荣的事情”的思想。到了《海上夫人》,他在这方面的探索更集中、认识也更明确了。
《海上夫人》(1888年出版)不只是一部探索女性心理的戏剧,而更主要地是一部探讨人类命运与前途的戏剧。易卜生在1897年曾表达过一种奇怪的观点:“人类在幼儿时应该从海洋生物开始进化。”[11](P329)而在此剧中,海上夫人艾梨达表达过类似的想法:“假使人类一起头就学会在海面上——或者甚至于在海底——过日子,那么,到这时候咱们会比现在完善得多——比现在善良些、快活些。”怎么理解这种观点呢?从第二幕来看,海上夫人曾常常观赏“鲸鱼、海豚、海豹什么的在赤日当空的时候趴在礁石上取暖”,她可能由此认为海洋生物性情温和善良,不像陆地生物那样依循丛林法则生活,养成了种种劣根性。而从全剧整体来看,房格尔大夫具有大海般开阔的心胸,待人热诚,对妻子艾梨达更是爱护有加;陌生人则像某些陆地动物一样性狠好斗(他杀过船长),对艾梨达也并无真挚感情。虽然陌生人的神秘、冷酷、强硬一度对艾梨达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吸引力,但他的意志最后还是败给了房格尔的真情。最后让艾梨达心意发生转变的,正是房格尔大夫的真爱。可以说,只有真情感以及随之而来的真道德(“爱”与“善”),才能给人带来更长久的幸福与快乐,因而也是更有力量、更有前途的。由此也就可以理解,艾梨达(以至易卜生)那种奇怪观点的实质在于:以善良之心与周围生命和谐相处,才是人类进化的正确轨道。
在《建筑大师》中,索尔尼斯曾痛悔自己压制了艾琳的才能——“把孩子们的灵魂培养得平衡和谐、崇高优美,使它们昂扬上升,得到充分发展”;到了《小艾友夫》,易卜生就把关注的焦点转到“培养孩子”了。剧中男主人公阿尔莫斯在经过一番反省之后,意识到自己以前的过失造成了儿子小艾友夫的残疾,决定不再埋头写作《人的责任》,而“要在自己的生活中间实行‘人的责任’”。他下定决心,“要培育孩子天性中一切善良的幼芽——让它们开花,让它们结果”。但妻子吕达贪图欢爱,讨厌儿子,狠心地说“我但愿没生这孩子”。后来,感到自己多余的小艾友夫跟随着鼠婆子,落到海里溺死了。孩子死后,吕达的精神变得特别紧张,还经常出现幻觉——她老是看见小艾友夫在海底仰脸躺着,“睁着两只大眼睛”。为了赎罪,也为了填补爱的对象(阿尔莫斯)失去后留下的空缺,她决定“把海滩上那些苦孩子都带到家里,当作亲生儿女看待”。后来阿尔莫斯受到感染,决定和吕达一起,好好培养那些苦孩子。从总体来看,该剧是易卜生探索“人的精神如何向善转变”或“变化的规律”的一个尝试。正如柏拉图在《斐德罗篇》借苏格拉底之口所说的那样,“爱欲是一种普遍又令人极为费解的力量,既能破坏又能寻求善”[12](P167),吕达强烈的爱欲虽有破坏性,但最终促使她走向了善道。作为一个浑身散发着活力的女人,吕达一度把爱欲的满足视为生活的第一要义,多年前“她儿子的残废是由于她浸淫于性事而忽视了照顾他;小艾友夫最终的死,是因为他的妈妈希望他消失”[6](P36);但也正是由于强烈的爱欲,她在丈夫离开之时感到需要“想法子找点东西,找点性质有点像‘爱’的东西把内心填补起来”,这使她最终走出了恐惧,走向了充实,也可以期冀“宁静安息的日子”了。如果说歌德认为“凡自强不息者终究会得救”,那么易卜生很可能认为“凡爱欲不泯者终究会得救”。
最后,易卜生在其戏剧收场白《当我们死人醒来时》反省了世间种种“活死人”的荒谬性,肯定了爱情对于生命的根本意义,并进而暗示了“死人”走向新生的可能性。该剧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易卜生的集大成之作,它对人类精神生态的描写至少包含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由鲁贝克创作的半身人像(里面隐含了好些“神气十足的马面,顽固倔强的驴嘴,长耳低额的狗头,臃肿痴肥的猪脸”)和“复活日”雕像的底座(“从地面裂缝里,钻出一大群男男女女,带着依稀隐约的畜生嘴脸”)来体现,这些形象凸显了人心中的“蛮性”;第二个层次,由鲁贝克艺术灵感的源泉爱吕尼来体现,她在配合鲁贝克完成“复活日”之后,就毅然出走,“在全世界走过很多地方、颠倒过各种各样的男人、杀死了两个丈夫、弄死了很多孩子”,这隐喻着艺术家或创造者心中的“魔性”;第三个层次,由鲁贝克早年的艺术追求、创作状态来体现,那时他感觉自己肩负有神授的使命,把全部生命都投入到艺术创作中,而竭力克制自己的欲望,像圣徒一样生活,这隐示出人心中的“神性”;第四个层次,指鲁贝克由精神走向肉体,由圣洁走向世俗,盖别墅,建公馆,娶美人,过起富裕奢华、轻松愉快的生活,但在“快乐逍遥的生活”中,他感到越来越空虚、疲倦、烦躁,这表现出人的“常性”;第五个层次,指鲁贝克和爱吕尼醒悟到自己已经成了活死人后,开始追求新生,追求某种既接近艺术又接近宗教的生活,这是对人的完整而自由的新生命的隐喻。
在该剧末尾,吕贝克和爱吕尼攀上山顶,手挽着手,要走上“乐土的尖峰”,走上“朝阳照耀的塔尖”,并在那儿举行婚礼;但不久,他们就像布朗德一样葬身于雪崩了。这个结局并非表明他们最后的抉择是错误的,而是要反衬出一种新的人生理想。这种理想的实质在于,肯定爱对于人生的根本意义,并在审美与信仰中走向“第三境界”。现实生活有太多缺憾,这使得审美成为必需。审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特殊的“有意识的自欺”(康拉德语)。鲁贝克明知爱吕尼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最纯洁、最理想的女人”了,但仍然把她看成是“梦想中的女人”;他甚至明知对方已经“死”了,但仍然认为她是“自由鲜活”的,“生活依然像从前一样热烈地沸腾跳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当前的人与生活艺术化了。而信仰,本质上是一种超越性的情感。最后鲁贝克与爱吕尼携手同行,弃绝一切向着他们心中“朝阳照耀的塔尖”靠近,正是在两心相爱的过程中复活“信仰”:信仰真爱,信仰某种超越性的生命境界。他们明知这样做必然陨命,但恰恰是要通过这种行为来证成他们的信仰。在1887年的一次讲话中易卜生指出:“诗歌、哲学和宗教将融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新的范畴,并形成一种新的生命力,对此我们当代人还缺乏明确的概念。……我特别相信,我们时代的理想——尽管已经崩溃瓦解——将朝着我在《皇帝与加利利人》一剧所指明的‘第三境界’发展。”[13](P56)由此来看,最后鲁贝克与爱吕尼的选择并不是要“逃避现实”,而是体现出一种否定既有种种理想的倾向;他们藉着审美与信仰走上“朝阳照耀的塔尖”,乃是要显现出一种新的理想、新的境界。这种理想境界,基于对整个人生与艺术的哲学美学反思,同时又融入了宗教的因素(易卜生反教会但并不反宗教),将“构成一个新的范畴和新的生命力”,对于今天以至未来的人们都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综上,易卜生后期戏剧对人类精神生态的洞鉴与审思大体是沿着两条路线进行的:一是多方位、多层次地揭示人类精神生态的症结,其中既包括过去的种种旧思想旧道德及其信守者(“群鬼”)对于现代人的纠缠与钳制,也包括人类本性中潜伏的具有破坏性的“蛮性”与“魔性”;二是在“人类精神误入歧途”之后努力探索人类精神发生变革、走向新生的可能性,这主要是发掘人类灵魂中“一切善良的幼芽”和隐隐存在的“神性”,并暗示一条基于“善”和“爱”,通过“审美”与“信仰”走向“第三境界”的新道路。毋庸置疑,易卜生后期戏剧的这些探索对于我们今天从根基处反思生态危机、建构生态文明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简言之,过去社会通行的崇尚强悍、肯定霸道的价值观念,弱肉强食、胜王败寇的丛林法则,容易诱发人类的蛮性与魔性,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人类的精神生态、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而要走出歧途,必须重新确立善良、爱愿、审美与信仰的根本性价值,让人类本性中一切健康美好的因素发挥出来,这样才有望迎来高度和谐、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