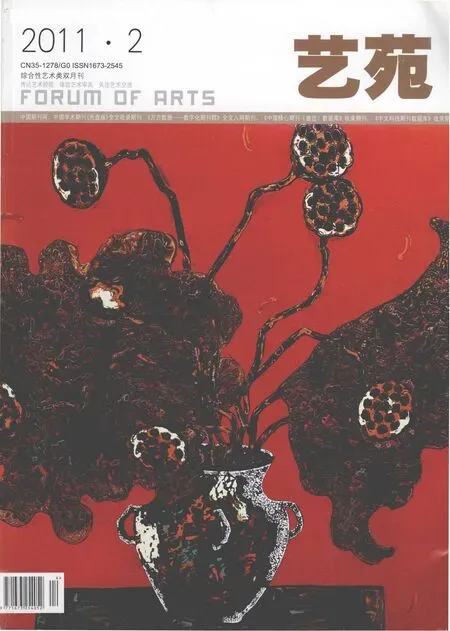试论港产英雄类电影的人物形象——从跨文化形象学角度说起
文/许昳婷
在跨文化视野内研究形象学,并非仅是简单地描述研究对象的形象特征,更重要的是在特定的知识框架中阐释和分析形象的意义。西方有史可考的中国形象在1250年前后出现,在此后的近八百年中,呈现了或美好或恐怖的多重变化。但无论如何,这种动态结构永远是为西方的社会价值体系服务的,“中国”这一地理文化概念始终是西方确立的他者。跨文化形象学研究中涉及的中国形象研究主要是关于西方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在这一类问题中,对西方现代性霸权究竟怎样影响了中国的本土形象定位、中国的自我形象和自我想象经历了何种变迁,以及中国在与西方的交流互动中如何进行主体性身份建构等的探索和追问,始终是值得关注的。
港产英雄类影片自李小龙《精武门》等作品肇始,塑造了黄飞鸿、霍元甲、陈真、叶问等一系列个人英雄形象。这些英雄人物多生长在清末至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的几十年间,在家国危亡之际,他们担负起了反抗外辱、启迪民智、强健民体的重担;他们功夫了得,具有侠义之气,在与外国人的对抗中历尽艰险最终取胜,把中国引向光明的未来。这类影片的叙事策略和人物形象都有一套特定的、类型化的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当代中国人对于自我形象的塑造,表现了中国人自我想象中的强国形象。援用跨文化形象学的方法,其优势就是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宏观视野。在案例研究中,如何在这一宏观视野中分析具体的问题,则需要甄别文化生产及其意识形态的差异。因此,“中国”和“港产”就构成了一对具有张力的符号。形象是“中国”的,“产地”却是游离于“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边际地带——香港的政治与文化属性正是处于跨界意义上的临界点。同时期大陆和台湾的英雄类影视作品与港产的极不一样。或许,因为同处于一个政治疆域内,关于港产英雄类电影中国想象的研究可以让我们走出“中原中心”甚至“北京中心”的第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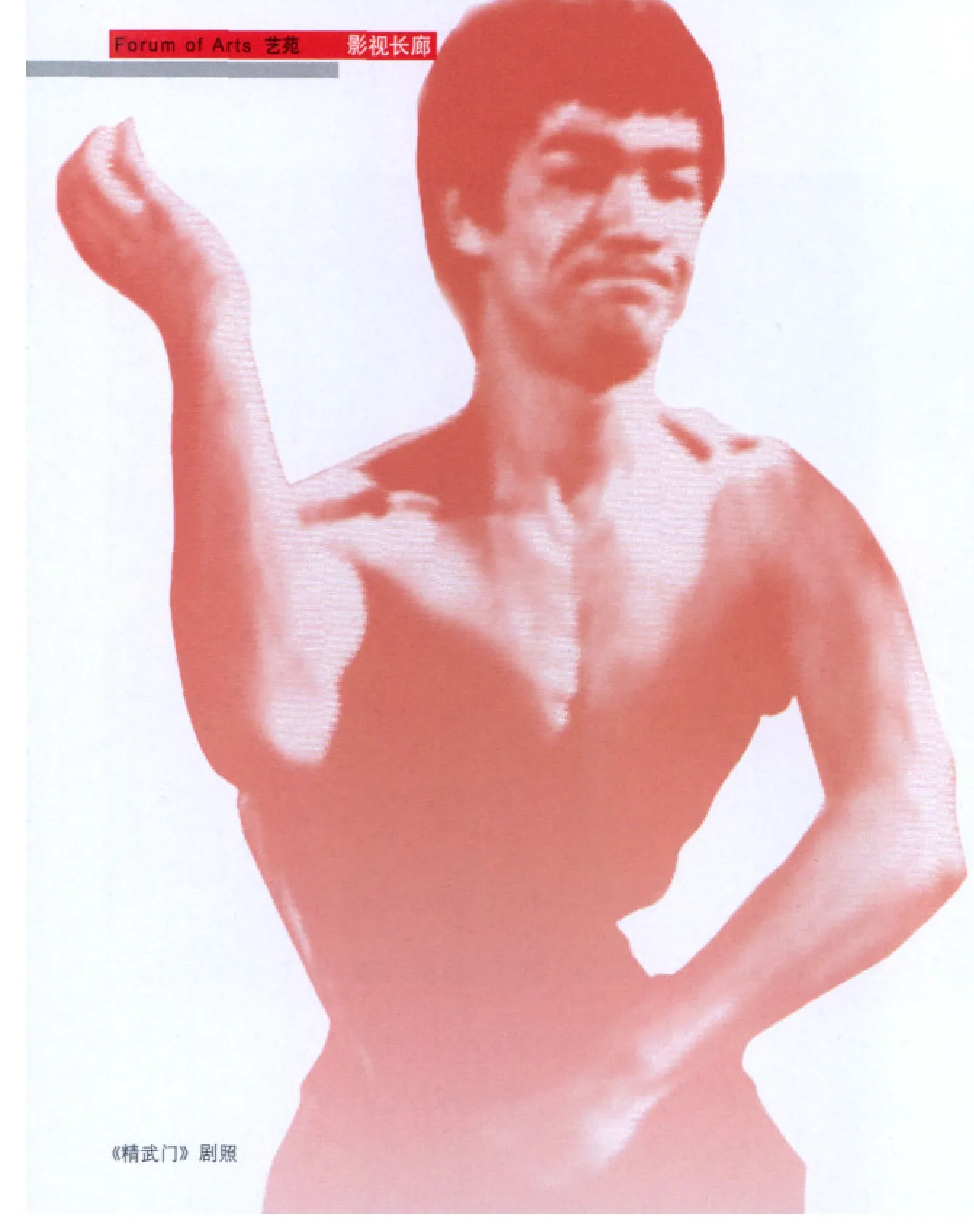
一、港产英雄类电影的人物形象模式
绝大多数港产英雄类电影以敌人的挑衅或中国人受辱为开端,以中国人得胜、外国人或侵略者完败为结局,这其间突出个人英雄的反抗历程,着重表现与敌人打斗的场面。这样的个人英雄通常具有高强的功夫,能够以一敌百,甚至能够以血肉之躯抵抗西方的洋枪洋炮。在个人英雄的影响以及拯救家国危亡的爱国口号感召下,一些非英雄的草根平民也迅速成长并扛起反抗的大旗,与英雄一起并肩战斗。在同仇敌忾的强大民族凝聚力的震慑下,原本高傲自大的敌人通常都会以惨败结束自己的一生。英雄、平民和敌人构成了这类影片的主要人物群组,共同谱写了一部中国人自我想象的民族国家寓言。
1.天生的英雄
港产英雄类电影中的个人英雄,如黄飞鸿、霍元甲、陈真、叶问等,通常习武多年,武艺高强,正义凛然,似乎天生就具有英雄的气质,或者说,他们从影片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拯救一切的英雄身份,是天生的英雄。
李小龙主演的《精武门》中陈真面对师父霍元甲去世的噩耗,没有像师兄弟们那样以平静的心态暗中调查,而是强烈质疑胃病和感冒导致师父死亡的荒谬诊断。他一身白衣的装扮与其他师兄弟深色的传统习武之人的装扮完全不同,在影片中亦经常呈现个人与群体分立的站位,突出其与众不同的身份特征。陈真作为一个突然归来的“闯入者”,打破了师兄弟们僵化、固守的习武信条,面对日本人的挑衅再也不退让妥协,而是奋起反抗,在个人复仇的同时也报了家国受辱之仇。甄子丹主演的《精武风云·陈真》中的陈真在法国时作为华工参加一战,领导战友冲出重围,体现了绝佳的英雄气质,这也就预示了他回国后势必成为抵抗侵略的领导者。可以说,这一类英雄的身份是先在的、固定的,是影片中的灵魂。
但是,这些英雄们在一开始并未想过要成为英雄,甚至也没想过要用自己的功夫保家卫国。高强的功夫、强健的体魄标志着他们具备英雄的能力,但往往直到某些事件发生才彻底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使他们具有身为英雄拯救天下的意识。《叶问》中的叶问为人低调谦和,不愿意和陌生人切磋武艺,像个不问世事的隐者。中日战争爆发,佛山沦陷,他只得带着妻儿移居废屋,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正是这种转变使他亲眼目睹了中国人被羞辱、惨死在日本道馆的事实,才下决心痛击日本人。当他站在擂台上与三蒲决一死战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公共视野下的英雄,他不仅是为自己、为中国功夫而战,更是为中华民族而战。如此说来,这样的英雄身份是被时代和环境赋予的,在周围人们的影响或刺激下确立,有一个获得——觉醒——认同——发扬的过程。
这类天生的英雄是影片的主角,有着普通人的情感甚至是性格缺陷,但他们具备英雄的能力和气质,总能在最关键的时刻觉醒并挺身而出,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主要力量。
2.非英雄、小人物的成长史诗
在这类电影中,和英雄联系最为密切、可以和英雄并肩战斗的,往往是一些普通人或小人物。他们多出身低下,生活贫困,有着各种各样的小缺点,如胆怯、圆滑、贪心等,也可能与英雄之间存在矛盾和误解,或者在与英雄的合作/镇压、与敌人的反抗/妥协中呈现暧昧不明、摇摆不定的多重身份,但他们同样具备爱国激情,他们的某些“反革命”行为往往是身不由己或用心良苦的。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他们不断成长、不断觉醒。最终,他们的身份由混沌多元变得单一纯粹,倾向英雄与正义的一方,成为保护英雄、保障胜利的关键性人物。
《精武风云·陈真》中的警察黄昊龙在枪战中贪生怕死,面对外国上司却圆滑地邀功请赏、阿谀奉承。他看似“走狗”一般在夹缝中苟且偷生,可是他深知陈真的真正身份,总是暗中保护陈真。当他难以忍受西方强权的压迫性力量时,终于对洋上司爆发,说出了“欺负我们的外国人最终只能滚蛋”的豪言壮语,颠覆了以往胆小怕事的形象,带着兄弟们炸掉日本军部的壮举更是将自己的身份明确转换至革命者反抗者一方,成长为辅佐陈真的幕后英雄。《叶问》中的李钊最初是个蛮横但不失可爱的小警察,后为了生计不得不投靠日本人,为叶问等人不齿。可就是这样一个“叛徒”,面对日本人的逼迫,多次用错误的翻译为叶问躲避灾难,并最终夺下日本军官的手枪,保护了叶问的生命。在他的身上,始终有善良和正义的一面,他所说的“我也是个中国人”恰恰昭示,不管身份具有何种多重性,他始终会倾向本土国族认同的一方,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由此可见,这类电影中的草根平民多在英雄感召下不断觉醒、奋起反抗。他们的认同过程恰好和天生的英雄从个人能力到思想意识的成长路线相反。在多重身份的纠缠中,被边缘化的小人物在思想上始终指向“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但是某些外部环境导致他们不能或不敢反抗侵略者的强权话语,英雄人物的崇高行为和社会正义力量的呐喊促使他们完成了从思想到行动的蜕变,最终成为革命的行动者。
3.脸谱化的敌人
在英雄类影片中,能和英雄产生激烈矛盾冲突的,通常都是外族侵略者。这类人物通常具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鄙视落后的中华民族。他们狂妄、残忍,肆意挑衅中国人,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多先占据上风,但是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外族侵略者最终总会惨败,甚至丧失性命。
在影片中,骄傲自大的日本人多以极端过分的行径(如“赠送”给中国人“东亚病夫”的牌匾)侮辱中国人,随着英雄反抗激情的爆发,中国人与侵略者共同成为公共视野中的主角。英雄与敌人的每一次交锋,都被置于了“被看”的地位——手无寸铁的中国人共同为英雄摇旗呐喊或默默祈祷,侵略者则共同拿起武器打击中国人。于是,英雄与敌人的对决也就不可能仅是个人恩仇,而是成为各自国家和民族的代表,具有了意识形态上的荣誉抑或耻辱的话语意义。可是在这种以一敌多的情势中,看似强大而众多的侵略者似乎并未占据明显优势——就群体性敌人来说,他们多经验贫乏、武艺不精,如虹口道场中的武士们,穿着同样的道服,在影片中几乎没有任何特写,毫无个性可言。他们仅仅是机械化地听从上司的命令去和英雄短暂交手,或者也可以说,他们为陈真、叶问等英雄构建了展现强大个人能力的舞台,是被中国人打得落花流水的群体性符号,为敌我个人对决做了极好的铺垫,成为敌人/侵略者卑鄙无能的隐喻。

《叶问》剧照
比群体性敌人更高层次的,是有能力、有权力、有野心和英雄一对一进行决斗的“高级敌人”。他们狂妄自大,坚信自己一定取胜,但通常也有可敬的气质——对英雄怀有尊敬之心,期待与英雄个人的、公开的、平等的高下对决。如《精武风云·陈真》中的力石猛命令放走已被抓捕的陈真,要与其平等地决斗、亲手报杀父之仇;《叶问》中的三蒲更是将叶问看做真正的高手,警告他的手下暗杀是可耻的行为。但是,对英雄怀有尊敬之心的逻辑前提,是他们将自己视为了逢战必胜的超级英雄,用“全中国都知道我赢”(《叶问》三蒲语)来实现征服英雄、征服中国的野心。尽管他们对英雄个体怀着一定程度的尊重,但是欺压广大民众,肆意烧杀抢掠的残酷行径使他们始终带有非正义性的身份符码,最终的失败也就在所难免。
值得注意的是,敌人/侵略者看似强势,可是在影片中并未着力塑造他们的形象,而是主要呈现强权压迫下的一种整体性氛围,即敌人/侵略者带来的恐慌与屠戮。但是,这种整体性氛围终究会被英雄的凛然正气所打破,以脸谱化的手法塑造的狂妄自大的敌人/侵略者不过是没有智谋、一味蛮干的“纸老虎”,英雄会使他们一败涂地。正义善良的中华民族始终是这套叙事话语的主体,是这类影片的决定性视角。
二、港产英雄类电影折射的中国形象和自我想象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人用洋枪洋炮将中国的大门轰开,直至1945年中日战争结束之前的近百年间,中国的对外战争几乎从未取得过彻底胜利。这段屈辱史是中国人内心难以抚平的伤痕,也是电影艺术中经常表现的对象。百年的历史呈现了多重矛盾,而港产英雄类电影亦体现了被放置于世界先进思想文化浪潮中的中国所表现出的时代张力,是西方想象与本土建构相互作用的产物。
港产英雄类电影以李小龙《精武门》等作品为滥觞,近半个世纪来不断发展壮大。李小龙祖籍广东,生于美国,长于香港,后又在美国达到其事业巅峰。身份的多重性与被边缘化的地位,促使其希望建构一种全新的自我形象,而其作品中功夫高强、有正义感、不屈不挠的中国人形象,符合西方人对传统东方神秘侠文化的想象。侠客成为拯救中国的民族英雄——这也成为西方殖民/后殖民语境下中国人自我想象的重要部分,是之后迅速崛起的港产英雄类电影几十年来共同遵守的叙事范式。在这种范式中,英雄与中国功夫成为中国形象的套话,但是这种中国形象的建构方式有不少值得思考之处:
首先,这类电影呈现了中国人在遭受外族入侵时顽强奋斗的精神。狂妄自大的侵略者视中华民族为“东亚病夫”、“劣等民族”,他们的侮辱与嘲笑成为彻底激发英雄斗志的导火线,英雄的反抗也就被赋予了复仇的意义——在战胜敌人时,英雄通常会毁掉敌人“赠送”的侮辱性牌匾、或者报复性地羞辱这些敌人,如让敌人吃掉写有“东亚病夫”的纸张等。同时这样的叙事逻辑表明,敌人到中国肆意屠杀、欺压民众,他们的惨死是罪有应得的。当敌人被英雄痛击的时候,每一位中国观众都会产生强烈的爱国共鸣,认同影片中英雄的行为,从而彻底否认强权话语赋予中国的负面意义,树立起正义、光明的中国形象。但是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视角忽略了对复仇方式合理性的思考,甚至颠覆了传统儒家文化及侠文化中以德报怨、仁义至上的理想人格范式。或许,这其中的逻辑就是德里达关于两元对立关系中话语的“rein scription”,即受压迫者的反抗常常受制于权力自身的自我复制与再生产,重复并强化了霸权的逻辑。如此地循环,值得深思。
其次,这类电影呈现了中国功夫、长刀短剑与西方坚船利炮之间的奇妙关系。如果说历史上西方的坚船利炮摧毁了冷兵器时代中国人征战四方的优越感,那么影片中的呈现却与史实恰恰相反,中国人的神奇功夫不仅可以躲过侵略者强劲的炮火,甚至可以飞檐走壁地奔赴敌人阵地将他们全部消灭。由此说来,坚船利炮不过是神奇功夫的衬托,英雄绝不可能被先进武器所战胜,西方视野下所谓蒙昧落后的中国人恰恰是不可战胜的强者。可是,这种看似振奋人心的中国人形象却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西方的“黄祸”恐慌——19世纪末期,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与经济掠夺使他们在胜利中隐约感到某种恐慌,害怕中国人总有一天会采取报复行动——这是西方文化集体无意识深处关于异域的恐惧[1](P356),而个人英雄是这种恐惧的制造者。于是,这也就造成了英雄身份的裂隙:一方面,这种英雄形象符合西方人对神奇中国功夫的幻想;另一方面,也印证了西方对中国的恐惧性想象。也就是说,这种个人英雄形象的塑造究竟站在何方话语立场,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精武风云·陈真》剧照
由此说来,港产英雄类电影始终在西方想象与本土建构中努力探索,创作者希望建构起独立自强的中国形象,可是又不自觉地受到西方强权话语下中国形象的影响,并且运用这个“他者”进行建构当下中国文化身份的尝试。在这种跨文化的艺术实践中,西方强权话语在不平等的交流空间内始终保有优势,港产英雄类电影中的国人形象塑造也就难以摆脱西方视角对中国的想象。面对西方文化的覆盖性冲击,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总是想要着力凸显某种可以纾解这一焦虑的民族文化认同意识,可是却在不期然间更为顽强地证明了由西方提供的这一视觉结构的超级魅力,本土始终被现代知识分子呈述为殖民主义话语所期待的景观[2](P17)。所以,尽管西方文化在中国本土并不总是呈述为消极意义,但港产英雄类电影未能明显地超越或者凸显自我主体性,甚至可能会形成自我“他者化”的危机,更加丧失自我的主体性地位。
三、小结
港产英雄类电影以激动人心的故事情节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武打场面在今天的大众文化消费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这类电影主要塑造了英雄、草根平民以及敌人等几类人物,表现了中国人的自我形象和自我想象。但是,面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并不平等的动态关系,这类影片中的中国形象建构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西方强权话语的影响,依旧没能建构出完全独立的主体身份,“我是谁”依旧是当下语境中值得思索的问题。
[1]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周云龙.越界的想象:跨文化戏剧研究(中国,1895-1949)[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