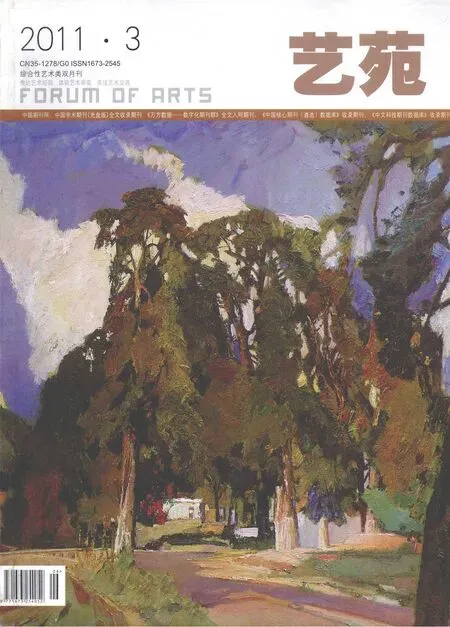让“空间”衍伸出更多意义——评福建人艺实验版《雷雨》
文/蔡福军
《雷雨》是中国百年话剧最优秀的几个收获之一。北京人艺版《雷雨》的登峰造极让照搬照演走向了末路。如何在曹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再呈现这部作品?陈大联改编的福建人艺实验版《雷雨》(以下简称新《雷雨》)让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有这样的勇气面对经典的挑战,有这样的才智对《雷雨》这样地审视、改造、提高。陈大联一定是《雷雨》的崇拜者和痴迷者,他的改编不是亵渎经典,不是青春逆反般的刻意求新、求怪;他努力注入时代的元素,让《雷雨》以更妥帖的方式活在当下。
电影《大话西游》大热之后,理论家突然踌躇起来:难道后现代社会已经来临?反中心、反连续性、反历史主义、拼贴、反深度、黑色幽默……这些后现代理论名词纷纷在电影中得到印证,这部电影及其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熟知这些理论名词并非难事,能够将这些名词背后的深意真正贯彻到剧本当中,才是真正见功夫的事情。尽管新《雷雨》中随处可见布莱希特“间离”效果这样现代主义的形式,但从整体上而言,它却深得后现代“空间”理念精髓。陈大联找到了一个大空间,重新容纳了《雷雨》的人物,在新的空间里,人物的内心也开始发酵,生出新意。大空间里一个是舞台空间,一个是理念空间。
新《雷雨》解放了舞台,也极大限度地解放了空间。新《雷雨》让周家、鲁家分坐两边,每个人前面都有一面鼓以及铃铛、三角等打击乐器。这些人坐在舞台的边缘,当剧情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或进入舞台中心,进行“正式”地表演;或站立,与中心舞台呼应;或敲击身边的打击乐器与中心舞台配合。方形的中心舞台与布满擂鼓的边缘舞台之间,形成一个统一的空间。演员的全面介入,舞台空间的放大使得舞台没有了“中心”。空间被连接的同时也被敞开了:“幕后”、“台前”的泾渭分明被打破了,每个人都在参与演出,每个人都在台前,每个演员都神经紧绷。因为下一秒,他们或许要步入舞台中央,或许要敲击眼前的乐器。地面舞台已经形成一个整合的、庞大的演出空间,舞台后方字幕的参与使得这个空间从平面走向立体。字幕的出现本来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哪个地方戏演出不需要字幕的辅助?问题不在字幕本身,而在于字幕的功能。新《雷雨》的字幕不是显示唱词,而是同时具有补充剧情、渲染中心舞台演出的情绪氛围、交代出场人物关系等功能。这样,平面舞台的演出必须要辅以字幕这个空间舞台才能够完满。因为此,新《雷雨》的灯光惊人的简约,也惊人的复杂。简约在于几乎没有绚丽多彩的色泽搭配,大量白色追灯单调得让人窒息——这正是这个剧需要的感觉。复杂在于人物空间转换迅速,舞台流动性强。中心舞台与边缘舞台之间的快速切换、游走令人眩晕。新《雷雨》的舞台空间只有配上具有特殊功能的字幕、独特的灯光才能算一个完整的空间。
锣鼓经的使用是这个剧的一大亮点。没有笛、箫、唢呐之类的吹奏乐器;没有二胡、三弦、琵琶之类的弦乐器,新《雷雨》只选择古典戏曲中的打击乐器锣鼓经。为什么不是用管弦乐器而是用锣鼓经?导演的用心耐人寻味。可以肯定的是,锣鼓经的使用十分符合《雷雨》这个戏的精神氛围:压抑的豪宅里面,雷雨将至,闷气弥漫,所有人都想开窗透透气,周朴园却保留关窗的习惯。锣鼓像炸响的阵阵雷鸣,不仅仅响彻在空中,更是强烈地在每个人心中擂起。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惊雷,当惊天的秘密被戳穿,导火线被点燃,几个惊雷链锁似地同时爆炸,成就了惊天地的闷响,也成就了《雷雨》的经典。锣鼓经的使用也给这个戏增加了节奏感,尤其是人物内心最冲突、矛盾最激烈的时候,锣鼓经的渲染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周萍面对父亲的拷问、繁漪被迫喝下药……这些场景中锣鼓大放异彩。这个戏并没有像戏曲那样,用严格的锣鼓点来展示程式,却深得其中韵味。锣鼓、舞台、演员、灯光、字幕形成了多重的,却又是整合的立体空间,彼此相得益彰,这正是新《雷雨》在舞台空间上的突破。只是字幕的使用还不够到位,仍有提高的空间。
理念空间里,令人新奇的是该剧的叙事方式。新《雷雨》拿掉了鲁贵的戏份。鲁贵原本是穿针引线的人物,他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他的叙事功能是捋顺人物关系,埋下伏笔,将冲突像阵势一样明晰地摆开,他敲响了战鼓,交战方扬鞭策马,残酷的短兵相接就要发生。他发现了周萍、繁漪的乱伦关系、周萍与四凤之间的特殊关系、繁漪将要驱逐四凤、侍萍的身世、对四凤做下人的态度,及她即将到达周公馆等。将这个人物抽掉仿佛珍珠掉了链子,有可能出现一盘散沙、观众无法理解的局面。冒着这样的风险,新《雷雨》尝试将鲁贵的叙事功能交给全新的舞台呈现样式——自我陈述、屏幕上的说明。第一幕所有的演员上来讲述这个角色的作用、意义和象征。演员自己陈述演出角色的意义,这是一个新鲜的做法。但交代了人物自我,并没有交代人物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屏幕做了一定的补充。屏幕上显示了周冲、四凤触电身亡等片段,让故事在一定程度上顺下来。总的说来,看明白这个戏要大致了解《雷雨》,还好,高中语文教材里有《雷雨》选段,大部分观众没有欣赏障碍。
失去了鲁贵,就失去了情节叙事的线索,失去了一以贯之的理性逻辑。没有了往常的“悬念”,而以新鲜的冲突代之。新《雷雨》将故事片段有限度地打乱,重新拼贴、组合,以达到全新的效果。我将新《雷雨》大致分为以下16个片段:1.希望;2.走与留;3.三重对峙;4.来·梦魇;5.经不起追问的罪;6.两对母子;7.痛苦无法抉择;8.春梦;9.逼药;10.不合时宜的纯真;11.走还是留;12.侍萍重生;13.劝归;14.夜会;15.总爆发;16.尾声·希望。
看似一片混乱的片段拼贴,其实是用心良苦、匠心独运。根本性的区别在于将历时的叙事顺序改换为共时的空间逻辑。具体地说,空间逻辑在剧中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情绪逻辑、空间运动与空间人物并置关系。细看此剧,片段的情绪组合颇有规律——遵循激越、低沉交替的情绪逻辑。四凤与周冲的“希望”片段是柔和的、梦幻般的;紧接着周萍与繁漪的“走与留”片段就充满了剑拔弩张的紧张感;在经历了周朴园逼繁漪喝药的“逼药”之后,周冲来四凤家劝说的“不合时宜的纯真”又重归舒缓。这种情绪逻辑起伏有致,让观众的情绪可以一张一弛,恰到好处。
从空间运动来说,新《雷雨》以周朴园家为空间的中心,围绕着这个中心,上演着“来”、“留”、“走”三种空间运动方式,这些也是戏剧冲突的发力之点。侍萍、鲁大海的“来”,周萍、繁漪、四凤则焦灼在“走”与“留”之间。片段的许多组合方式恰恰以此为依据。总体而言,新《雷雨》还是遵循原来故事的顺序,在调整的尺度上,陈大联左右权衡、小心翼翼。一些经典片段甚至是全盘保留,一字不删,一丝不改,有些地方甚至让人觉得有点“保守”了。这样的顺序让人很容易认出这就是《雷雨》。新《雷雨》剪截旁支,将最具有戏剧冲突的片段呈现在舞台上。因为遴选的细致,冲突犹如一个个爆炸点,强烈而又持续不断。因为有了空间逻辑,舞台呈现也就不是毫无规则的凌乱和随意。

《雷雨》剧照 摄影:王士捷

《雷雨》剧照 摄影:庄 文

《雷雨》剧照 摄影:陈世荣
最为重要的还是空间人物的并置关系。空间的重新组合不但没有损害《雷雨》本身的深刻,反而为《雷雨》敞开了一些新的可能性。这个戏最用心力、最具创造性的地方也在于此。在对《雷雨》每个人物、每个场景,甚至每句台词都烂熟于心的时候,如何根据人物之间可能的关系进行重新组合?这样的组合有什么作用?陈大联肯定为此绞尽脑汁。
在我看来,新《雷雨》在许多地方的组合都是非常成功的,让人猛然发现,原来还可以这样!空间人物的并置有四种模式:复杂化、简单化、多重声部、重复。在一个场景中增加原来剧本中没有的人物,是将人物关系复杂化;抽掉原剧中本来有的人物是简单化;多重声部是中心舞台的人物与原剧一样,但是边缘舞台同时发出声音介入中心舞台;不断重复一些场景则是重复。这四种方法让新《雷雨》有了新面孔。将繁漪与周冲、侍萍与四凤两对母子(女)同时放在舞台上是将人物并置复杂化,这样的做法颇为有趣。两对母子(女)既互相对峙又彼此有关联——周冲向繁漪说出喜欢四凤、侍萍又因为繁漪的说辞让四凤离开周公馆。看似独立的两对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交集,交集之中产生了新的意味,也让人更清晰、更直观地了解人物之间的冲突。新《雷雨》让周萍、繁漪、四凤都有机会单独在舞台上面临两难的抉择,这是简单化处理的方法。把其他人物放置在周围,聚光灯打在这个人物身上。周萍在繁漪、四凤之间徘徊,在走与留之间抉择,他内心的苦痛没有言语,只有锣鼓经的渲染和他一个人在舞台上焦灼。繁漪同样在乱伦的罪恶与无法割舍的感情之间踌躇,给她一个独立的舞台空间,让大家发现这个伤得最深的女人咀嚼着从心里流出来的血。四凤在周萍与母亲之间犹豫,她深爱着母亲,更舍弃不了周萍,因为她已经怀有身孕。痛苦不仅仅属于她,她那知道一切罪恶的母亲心灵已经崩溃。因为中心舞台与边缘舞台界限模糊,多重声部在这个戏中随处可见,在许多地方效果甚佳。例如周朴园与侍萍回忆三十年前一些生活细节的时候,让边缘舞台的周萍、四凤站起来说。这样处理的好处有两方面:一方面,两个年轻人的对白,让人立刻回到三十年前他们青春洋溢的美丽,他们的温情与爱恋;另一方面,意味着他们的悲剧将在下一代重演,甚至因为乱伦关系加剧了当年的悲剧。周冲与四凤充满纯真、希望的对白几次穿插在剧情之中。这样的重复让新《雷雨》过于紧张的弦松一松,也让过于压抑、颓废、黑暗的氛围能见到一些亮色。新《雷雨》复杂化、简单化、多重声部、重复等空间技术的使用真正为《雷雨》打开了一片空间,将原著中潜藏着的许多可能性的冲突挖掘出来,赋予《雷雨》崭新的生命。
空间理论为后现代主义者们津津乐道。索绪尔将语言分为共时、历时状态,后现代主义者喜欢将历时状态共时化。把一堆在不同时期的关系项按照一定的原则放置在同一共时空间中,让彼此的关系比照出更多的新意来。也许陈大联并不深谙后现代时髦的理论,但是他用实践将这些时髦的词汇变成了活生生的舞台呈现。新《雷雨》与时代契合了,《雷雨》常演常新,这也许曹禺先生百年诞辰最感欣慰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