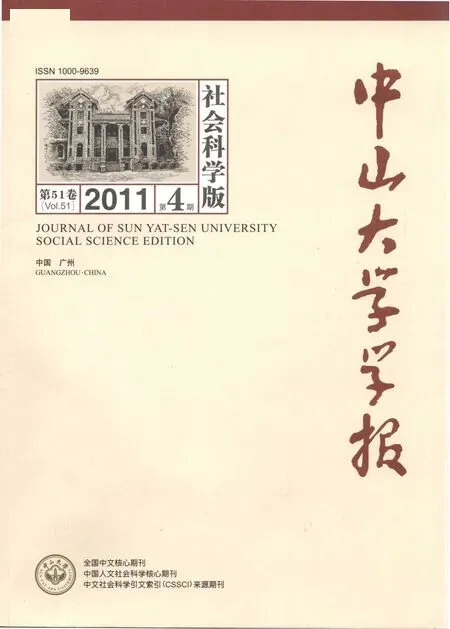激进权智与温和权慧:孟子经权观新论*
杨海文
傅伟勋的《儒家心性论的现代化课题(上)》提出了证立孟子性善论的十大论辩,同时指出:“儒家则自孟子以来早已把握到‘心性论在先,伦理学在后’的道理。”①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254页。孟子建构自身思想体系,“心性论在先”就是首先逻辑地确立了“仁且智”的理想人格,“伦理学在后”就是随后现实地践履着“经而权”的伦理智慧。《礼记·丧服四制》有言:“夫礼……有恩,有理,有节,有权,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义也,节者礼也,权者知也。仁、义、礼、知,人道具矣。”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94页。按,柳宗元《断刑论下》云:“果以为仁必知经,智必知权,是又未尽于经权之道也。何也?经也者,常也;权也者,达经者也:皆仁智之事也。离之,滋惑矣。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是二者,强名也。曰当,斯尽之矣。当也者,大中之道也。离而为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偏知而谓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谓之仁,不仁者也。知经者不以异物害吾道,知权者不以常人怫吾虑。合之于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柳宗元:《柳河东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第41页)人情、人道烛照下的“恩者仁也”、“权者知也”,又昭示了经权与仁智紧密相关的思想史传统。孟子“经而权”的伦理智慧,既倡导“背反于经”的激进权智,又强调“返归于经”的温和权慧,同样旨在把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精神真切地落实在每一个道德实践主体的人伦生活之中。
一、以权抗礼:小叔子为何要救嫂子
明代著名文人徐渭的《四声猿·女状元辞凰得凤》第一出有句唱词:“此正教做以叔援嫂,因急行权;矫诏诛羌,反经合道。”③徐渭:《四声猿》,《续修四库全书》第176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第224—225页。读过《孟子》的人,也都会对下面这段话留下深刻印象: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7·17)①此种序号注释,以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为据。下同。
孟子十分看重权变,曾说:“权,然后知轻重。”(1·7)“执中无权,犹执一也。”(13·26)其中,“执中无权”是孟子对子莫践履伦理规范的评价。子莫既不像杨朱那样为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不像墨子那样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而是执中。孟子则认为,子莫虽然执中,本质上还是杨、墨那种不讲权变的执一。援嫂以手之“权”与执中无权之“权”又有所区别,《朱子语类》卷56指出:“‘执中无权’之‘权’稍轻,‘嫂溺援之以手’之‘权’较重,亦有深浅也。”②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331页。轻就是温和,重就是激进。换句话说,孟子“经而权”的伦理智慧包括温和、激进两个层面,背反于经的激进权智又最为人们津津乐道。
以上对话,淳于髡向孟子抛出了一个两难问题:如果小叔子严格遵守“男女授受不亲”之礼,他就绝对不能伸手去救嫂子;如果小叔子伸手去救嫂子,他就违背了“男女授受不亲”之礼。孟子如何破解这个两难选择呢?
战国中期,礼乐文明越来越崩坏。孟子力图在合法化认同与创造性转换的基础上,重新恢复礼乐文明固有的政治—伦理统制功能。要是没有碰到嫂子溺水这类突发事件,孟子必然要求道德实践主体遵守“男女授受不亲”之礼。《礼记》就说:
子云:“好德如好色。诸侯不下渔色。”故君子远色以为民纪。故男女授受不亲。御妇人则进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与同席而坐。寡妇不夜哭。妇人疾,问之,不问其疾。以此坊民,民犹淫泆而乱于族。(《坊记》)③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622,1462页。
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嫂叔不通问。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于捆,内言不出于捆。女子许嫁,缨。非有大故,不入其门。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曲礼上》)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240页。
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授,则女受以篚。其无篚,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内,不啸不指;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内则》)⑤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622,142页。
日常生活中,男女之间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未尝不可。现在的问题却是:嫂子落水了!“男女授受不亲”,“嫂叔不通问”,小叔子救还是不救?郑玄注上引《礼记·曲礼上》云:“皆为重别,防淫乱。”⑥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240页。小叔子也是道德实践主体,如果他此时此刻还泥守男女大防,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嫂子溺水而死,他真的可以这样做吗?孟子正告淳于髡:要是小叔子这个时刻不奋不顾身地去救嫂子,他就是豺狼,就是禽兽!小叔子必须置礼节于不顾,奋不顾身地去救嫂子!从孟子这一回答看,大凡突发事件,激进权智就得出来发挥自身的大作用。
小叔子不救嫂子,有其“礼”的依据;救嫂子,则是“权”的体现。礼与权何以会存在如此明显、严重的冲突呢?先看以下几段话:
礼作于情。(郭店简《性自命出》)⑦荆州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79,194页。
礼因人之情而为之。(郭店简《语丛一》)⑧荆州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714页。
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礼记·坊记》)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618,1694页。
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訾之者,是不知礼之所由生也。(《礼记·丧服四制》)②阮元校刻:《十三经 注疏》下册,第1618,1694页。
礼者,实之华而伪之文也。(《淮南子·氾论训》)③高诱:《淮南子注》,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223页。我们的思想史传统认为:圣人源于人之常情,制作了礼乐规范;“为之节文”是礼乐规范的表达形式,亦即以书写方式固定下来且代代相传。圣人制作礼乐规范的主观愿望就是试图为实际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形立法,假如它真的面面俱到了,道德实践主体只要依照条文化了的礼乐规范,就可自在地展开自己的伦理生活。但是,圣人果真能为实际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形都立法吗?
《孟子》有两章提到“仁且智”(3·2,4·9)。其中讨论周公的一章,陈贾问:“然则圣人且有过与?”孟子答:“周公之过,不亦宜乎?”(4·9)《河南程氏遗书》卷4云:“夫管叔未尝有恶也,使周公逆知其将畔,果何心哉?惟其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则其过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过,不亦宜乎?’”④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1页。周公是圣人,圣人也有过失,圣人不是无所不能的。圣人制作礼乐规范,同样不可能完全穷尽实际生活中会出现的所有情形!否则,孟子、淳于髡时代,礼乐规范为何没有明确指示小叔子该不该救嫂子呢?正因没有明确指示,小叔子陷入了两难:救嫂子,就违反了礼;不救嫂子,就背离了情。违反了礼,仅仅算不上君子;背离了情,却形同禽兽,简直不是人了。既有的礼乐规范解决不了礼与情之间明显、严重的冲突,这为孟子让小叔子以权抗礼提供了极富思辨张力的理论空间。
权变智慧帮孟子消解了淳于髡那个两难问题,可促使小叔子以权抗礼的终极根源又是什么呢?《孟子》有两个有名的落水故事:一个是“孺子将入于井”(3·6),另一个就是“嫂溺援之以手”(7·17)。救不救小孩,并未涉及到以权抗礼,但孟子不容置疑地指出:道德实践主体一看见小孩子即将掉进井里,就会毫不犹豫、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去救他;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先天、内在地具有怵惕、恻隐、不忍人之心,没有此心,不啻于非人。依据孟子道性善、言本心的心性论,救小孩的理由,其实也正是救嫂子的终极根源;小叔子以权抗礼、援之以手是根据人道原则做出的道德决定,这一人道原则就是贯穿于孟子思想体系之中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
圣人制礼作乐,源于人之常情。在孟子看来,人类最根本、最普遍的常情就是怵惕、恻隐、不忍人之心。以上两个落水故事,人们都是本着这一人之常情才出手相救。从常情的角度看,他们救人,不仅没有违背圣人制礼作乐的初衷,反而是对礼乐规范最真切的践履。圣人规定了“男女授受不亲”、“嫂叔不通问”,他们又是否能够从小叔子救嫂子的行为中,看出这个普通人以权抗礼的善良用心呢?倘若觉察到了,圣人又是否会意识到他们这个创作集体并未穷尽实际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形,并进而决定修改相关规范来杜绝类似情况的发生呢?
北宋著名疑孟派李觏的《礼论第六》曾说:
孟子据所闻为礼,以己意为权,而不谓先王之礼,固有其权也。自今言之,则必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亦礼也。⑤李觏著,王国轩校点:《李觏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8页。
救不救嫂子,先王之礼显然没有作出过明确的指令,相反,有关条文却明显倾向于不救。所以,说孟子“据所闻为礼”不对,说他“以己意为权”极有道理。孟子“以己意为权”,就是虚拟了小叔子救不救嫂子的突发事件,让小叔子以权抗礼,伸手救了嫂子。李觏肯定“嫂溺援之以手,亦礼也”,表明孟子经由小叔子救嫂子的思想实验,不仅成功地修正了既有礼乐规范的一大缺失,而且现实地产生了维系礼乐文明的政治—伦理统制功能。
《朱子语类》卷37就认为:“可与立”,是如“嫂叔不通问”;“可与权”,是如“嫂溺援之以手”①参见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3册,第987页。。二程尤其指出:
行礼不可全泥古,须当视时之风气自不同,故所处不得不与古异。如今人面貌,自与古人不同。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称。虽圣人作,须有损益。(《河南程氏遗书》卷2上《二先生语二上》)②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1册,第22,327页。
礼之本,出于民之情,圣人因而道之耳。礼之器,出于民之俗,圣人因而节文之耳。圣人复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为之节文。其所谓贵本而亲用者,亦在时王斟酌损益之耳。(《河南程氏遗书》卷25《伊川先生语十一》)③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1册,22327页。
小叔子救嫂子,把“嫂溺援之以手”变成了礼,但并未取消“男女授受不亲”作为礼的固有性质,它自始至终是中国古代社会必须遵守的国法家规,所以李觏说“则必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也”。“海瑞杀女”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见三处记载:
海忠介有五岁女,方啖饵。忠介问饵从谁与。女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此女即涕泣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余谓非忠介不生(此女)。(姚士麟:《见只编》卷上)④姚士麟:《见只编》,《丛书集成新编》第11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版(未署出版年月),第646—647页。按,姚士麟,通称姚士粦,又称姚叔祥,生活于明清之际。
相传海忠介有五岁女,方啖饵。忠介问饵从谁与。女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女即涕泣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异哉,非忠介不生此女!(周亮工:《书影》卷9)⑤周亮工:《书影》,《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3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408页。
国朝周亮工《书影》云:“相传海忠介有五岁女,方啖饵。忠介问饵谁与。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女即涕泣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按,此即忠介杀女之说所自来也。(俞樾:《茶香室续钞》卷4“海忠介被纠”条)⑥俞樾:《茶香室续钞》,《续修四库全书》第119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第420页。
《礼记·内则》说过:“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女子十年不出。”⑦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471页。假如杀女真有其事,海瑞无疑机械地理解了“男女授受不亲”之礼。这个故事不见于正史,只能算作传闻⑧参见杨海文:《“海瑞杀女”与“百度百科”》,《人民政协报》2011年1月31日,第10版。该文考证了“海瑞杀女”的来历问题。。李锦全指出:“由于海瑞为人迂憨与拘执,要说他是个死守封建道德纲常的卫道士,这样评价还是恰当的。”⑨李锦全:《海瑞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5页。
“男女授受不亲”面前,女性属于弱势群体:小叔子不救,嫂子就会溺死;小女孩吃了男孩子给的点心,就得活活饿死。跟“男女授受不亲”相搭配的具体生活情景,变化万端,层出不穷,哪里只有嫂子落水、女孩食饵两种情形呢?孟子与淳于髡那场著名的对话共三节,最后一节是: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7·17)
《四书评·孟子卷之四》写道:“老孟日日以道援天下,而淳于不知,是必手援天下而后知也。故曰:‘子欲手援天下乎?’”⑩李贽:《四书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20页。嫂子落水,小叔子一只手救得了;天下落水,就得仰仗强大的道!《淮南子·氾论训》指出:“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末世之事,善则著之。是故礼乐未始有常也。故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高诱注云:“圣人能作礼乐,不为礼乐所制。”①高诱:《淮南子注》,第213,212页。所以,小叔子救嫂子,既是孟子经权之思的标志性案例,又是孟子经权观与道德理想主义的完美结合。
二、“背反于经”的激进权智
小叔子救不救嫂子,尚属激进权智方面比较简单的例子。张载《正蒙·作者篇》有云:
舜之孝,汤、武之武,虽顺逆不同,其为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伦,然后能精义致用,性其仁而行。汤放桀,有惭德而不敢赦,执中之难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己不见其有间也,“立贤无方”也如是。②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4—195,192页。
包括《作者篇》在内,《正蒙》“此下四篇,皆释《论语》、《孟子》之义”③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4—2页。。孟子说过:“汤执中,立贤无方。”(8·20)执中何以如此之难?立贤为何必须无方?“舜之孝”、“汤放桀”云云,表明行权者的社会地位不同、礼与权的冲突层次不同,以权抗礼的历史意义也会有所不同。这里,我们把行权者的社会地位、礼与权的冲突层次、以权抗礼的历史意义视为三项标准,再看《孟子》书中背反于经的其他事例,又是如何经由以权抗礼,使得礼与权从冲突走向圆融、从相反走向相成的。
(一)舜不告而娶
《淮南子·氾论训》云:“舜不告而娶,非礼也。”④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4—2页。它也是孟子经权之辨的著名案例:
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若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
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
万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则吾既得闻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
曰:“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9·2)
舜是“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8·19)的圣人。作为行权者,其社会地位岂是小叔子所能望其项背!不告而娶,其间礼与权的冲突层次也更为曲折。
先看看那个时候的礼:
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9·2)
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6·3)
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9·2)
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踰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6·3)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7·26)
中国古人必须老老实实遵守的“婚姻法”,包括三个方面:“男女居室,人之大伦”是其婚姻的本质,婚配是人们在伦理生活中必须履行的天然义务,是人的社会化的必然要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其婚姻的程序,婚事必须听从父母的安排,经由媒人的介绍,绝对不能偷鸡摸狗,更不允许自由恋爱;“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其婚姻的目的,传宗接代是结婚最神圣的使命,否则就是对父母、对家族最大的不孝。其中,婚姻的本质、目的属于“实质正义”范畴,婚姻的程序属于“程序正义”范畴。
舜不告而娶,凸显了“必告父母”与“无后为大”之间的冲突,展示了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博弈。舜的父母为什么不同意舜的婚事?舜的家庭主要成员有:父亲瞽瞍⑤瞽瞍,亦有典籍写作“瞽叟”。除引文外,本文一律从《孟子》,写作“瞽瞍”。,继母,同父异母之弟象。《尚书·尧典》说他们三人为“父顽,母嚚,象傲”⑥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23页。。《汉书·古今人表》把瞽瞍(鼓叜)、象列入下中等⑦参见班固:《汉书》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878页。,评价极低。《四书评·孟子卷之五》点评“娶妻如之何”章:“形容后母之毒,无如此处为详矣。”①李贽:《四书评》,第239页。《史记·五帝本纪》云: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②司马迁:《史记》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2,33—34页。
《史记》书中,《游侠列传》有句“虞舜窘于井廪”③参见司马迁:《史记》第10册,第3182页。,《五帝本纪》又说:
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舜居妫汭,内行弥谨。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尧九男皆益笃。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尧乃赐舜絺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瞽叟尚复欲杀之,使舜上涂廪,瞽叟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为已死。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鄂不怿,曰:“我思舜正郁陶!”舜曰:“然,尔其庶矣!”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④司马迁:《史记》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233—34页。
司马迁写舜,大多本于《孟子》:
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揜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9·2)⑤《河南程氏遗书》卷4:“孟子言舜完廪浚井之说,恐未必有此事,论其理而已。尧在上而使百官事舜于畎亩之中,岂容象得以杀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学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1册,第71页)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卷上云:尧“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锡虞舜命”,“七十一年,帝命二女嫔于舜”⑥参见王国维撰,黄永年校点:《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44、45 页。。对照《史记·五帝本纪》,可知舜31岁结婚,符合“男子……三十而娶”(《春秋穀梁传·文公十二年》)⑦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408页。按,《淮南子·氾论训》云:“礼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高诱:《淮南子注》,第212页)的规定。《孟子》《史记》记载的“焚廪”、“揜井”,虽然都发生在舜结婚以后,但足以证明瞽瞍、继母、象对舜一直不好。所以,即使舜禀告自己的婚姻请求,他们也断然不会同意;即使尧以帝位之尊从中斡旋,他们同样不会点头。
不言而喻,舜已经陷入礼与权的冲突之中:如果舜遵守禀告父母之礼,他就结不成婚,最终不能传宗接代;如果舜认为传宗接代是孝子不可推卸的伦理责任,他就必须跟尧的两个女儿结婚,但却背反了禀告父母之礼。遵循一礼,就得违反另一礼,舜该如何抉择?孟子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7·26)两相比较,传宗接代重过禀告父母,实质正义大于程序正义,人们把舜不告而娶等同于事先征得了父母的同意。“君子以为犹告也”,正写照了人们对舜以权抗礼的高度肯定。
(二)汤放桀、武王伐纣、伊尹放太甲
汤、武、伊尹都是孟子眼里的圣人。《汉书·古今人表》把汤、武列为上上等圣人,把伊尹列为上中等仁人①参见班固:《汉书》第3册,第884、892、884 页。。汤、武、伊尹“以权抗礼”的激进权智同样发人深省: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也,未闻弑君也。”(2·8)
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9·6)
公孙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顺,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13·31)
首先从《孟子》书中看看那个时代的君臣伦理观:
《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9·4)
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4·2)
无父无君,是禽兽也。(6·9)
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7·2)
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7·2)
拿这些君臣伦理观来考量,汤放桀、武王伐纣、伊尹放太甲无一不属于罪大恶极、罪不可赦的违礼行为。且看下面的说法:
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陵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庄子·盗跖》)②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78,791页。
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庄子·盗跖》)③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下册,第778—779页。按,“文王拘羑里”一句,陈书无,据郭象本《庄子》增补(《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9页)。
尧杀长子,舜流母弟,疏戚有伦乎?汤放桀,武王杀纣,贵贱有义乎?王季为適,周公杀兄,长幼有序乎?儒者伪辞,墨者兼爱,五纪六位将有别乎?(《庄子·盗跖》)④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77页。
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子·说疑》)⑤《二十二子》,第1178,1187页。
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韩非子·忠孝》)⑥《二十二子》,第1178,1187页。
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古本竹书纪年》)⑦朱右曾辑录,王国维校补,黄永年校点:《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第7页。
孟子为何如此赞许这些违礼行为呢?王道政治学是孟子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4·14)乃其核心价值理念,《孟子微·总论》指出:“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⑧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孟子微 礼运注 中庸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0页。“得其民,斯得天下矣”(7·9)蕴涵了“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14·4)的理想展望,但孟子同时清醒地意识到了“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6·9)。国君仁还是不仁,正是治乱循环的根本原因:“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7·3)“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7·20)可大臣们又该怎样直面国君的不仁、不义、不正呢?
齐宣王问卿,孟子答曰:若是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若是异姓之卿,“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10·9)。大臣劝谏国君,国君我行我素,异姓之卿可以一走了之,贵戚之卿可以取而代之。孟子还说过:“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7·3)一走了之、取而代之说的是“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天子不仁,不保四海”又将如何?那就会汤放桀、武王伐纣、伊尹放太甲。
《尚书·仲虺之诰》言:“成汤放桀于南巢。”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61,182,60,163页。《史记·夏本纪》云:
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廼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桀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汤封夏之后,至周封于杞也。②司马迁:《史记》第1册,第88,121—122,98—99页。
《尚书·泰誓》三篇对武王伐纣有详细记载,《史记·周本纪》也说: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犇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曰:“孳孳无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逿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③司马迁:《史记》第1册,第88,121—122,98—99页。
《汉书·古今人表》把桀(癸)列入下中等,纣(辛)列入下下等④参见班固:《汉书》第3册,第883、889页。。桀的人品比纣好那么一点点,但桀、纣之失天下的缘由却是相同的,都失去了民心的支持。孟子指出: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7·9)
孟子论汤放桀、武王伐纣,明显受到过思想史传统的影响。其言“一夫纣”(2·8),《尚书·泰誓下》就有“独夫受”一语:“古人有言曰:‘抚我则后,虐我则雠。’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雠。树德务滋,除恶务本。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雠。尔众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⑤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61182603页。《周易·革卦·彖传》更是强调:“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⑥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61,182,60,163页。
伊尹放太甲,历史记载多有不同。《尚书·太甲上》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⑦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61,182,60,163页。《史记·殷本纪》云:
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廼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廼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汤適长孙也,是为帝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作《肆命》,作《徂后》。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
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廼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廼作《太甲训》三篇,襃帝太甲,称太宗。
太宗崩,子沃丁立。帝沃丁之时,伊尹卒。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⑧司马迁:《史记》第1册,第88,121—122,98—99页。
《古本竹书纪年》则曰:“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⑨朱右曾辑录,王国维校补,黄永年校点:《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第7页。李善注陆机《豪士赋序》“伊生抱明允以婴戮”一句,亦云:“《纪年》曰:‘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①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046页。
《尚书》《孟子》《史记》均肯定伊尹放太甲:太甲不仁,伊尹放之,可谓之权;太甲悔过自新,伊尹归还政权,可谓之经。《古本竹书纪年》却认为:伊尹放逐太甲之后自立,太甲后来从桐宫逃回王都,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还宽宏大量地对待伊尹的两个儿子,让他们分了伊尹的田宅。《汉书·古今人表》把伊尹、太甲都列为上中等仁人②参见班固:《汉书》第3册,第884、885页。。
大臣杀戮或者放逐天子,毫无疑问违反了一般意义上的君臣伦理观。在孟子看来,汤放桀、武王伐纣、伊尹放太甲这些违礼之举,却鲜明地体现了汤、武、伊尹“救民于水火之中”(6·5)、“格君心之非”(7·20)的激进权智。伊尹放太甲于桐,目的是让太甲处仁迁义,太甲也洗心革面了,所以,伊尹放太甲属于稳定社稷的守成性治乱类型。汤也曾经放桀于南巢,但桀、纣作恶多端,完全失去了民心,“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7·9),所以,汤放桀、武王伐纣属于改朝换代的革命性治乱类型。孟子又引孔子说的“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9·6),以进步的治乱史观消解了保守性的君臣伦理观,认为汤、武、伊尹背反于经、以权抗礼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孟子集注》卷9引尹氏曰:“知前圣之心者,无如孔子,继孔子者,孟子而已矣。”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9页。
(三)舜窃负而逃
舜窃负而逃,是孟子设计的思想假说,也是孟子论激进权智的经典案例: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
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然则舜不禁与?”
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
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13·35)舜为天子,皋陶做法官,假如瞽瞍杀了人,舜该怎么办?孟子告诉桃应:皋陶必须依法逮捕瞽瞍,舜不得干涉;其后,舜会像扔掉破鞋子那样,舍弃天子之位,偷偷地从牢里救出父亲,逃到海滨住下来,从此幸福地生活着,把做过天子那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思想史上,有人认为舜放父杀弟,人品并不高尚;也有人认为舜根本不可能窃负而逃,它纯属委巷之言。且看下面两段记载:
瞽瞍为舜父,而舜放之。象为舜弟,而(舜)杀之。放父杀弟,不可谓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谓义。仁义无有,不可谓明。《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信若《诗》之言也,是舜出则君其臣,入则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韩非子·忠孝》)④《二十二子》,第1187页。
《虞书》称舜之德曰:“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所贵于舜者,为其能以孝和谐其亲,使其进退,以善自治,而不至于恶也。如是,则舜为子,瞽叟必不杀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于杀人,执于有司,乃弃天下,窃之以逃,狂夫且犹不为,而谓舜为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叟既执于皋陶矣,舜恶得而窃之?虽负而逃于海滨,皋陶犹可执也。若曰皋陶外虽执之以正其法,而内实纵之以予舜,是君臣相与为伪,以欺天下也,恶得为舜与皋陶哉!又舜既为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虽欲遵海滨而处,民岂听之哉?是皋陶之执瞽叟,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也。(司马光:《传家集》卷73《疑孟》)⑤司马光:《传家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第666—667页。
舜窃负而逃,包含了“有罪必罚”、“孝高于法”两个法观念,前者要求严格维护法律的权威,后者则不惜违背、破坏法律,两者看起来非常矛盾,但孟子认为它们是统一的。有论者指出:
作为天子(包括一切官吏和国民),必须严格执法和守法,忠于职守,不能以权徇私;作为人子,必须克尽孝道,必要时不惜代价,包括个人的尊荣,亦可以不顾国家法律和利益。照后来的说法,这是忠和孝的矛盾,所谓“忠孝不能双全”。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总是想调和这对矛盾,所以有“亲亲相隐”、“复仇”、“存留养亲”等等问题的讨论和有关规定,但终中国封建社会之世,也没有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然而,中华法系及其法文化的许多特征,却围绕这个问题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孟子本人触及到了这个问题,但并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他设想的“舜窃负而逃”,只是舜个人采取的一种法律行为,至于如何在法律制度上保证舜既能继续当天子,又能尽到孝道,孟子连想也没有去想。但孟子却为后人留下了这样一种法律思考课题:立法应取家族本位主义,并使天下利益和家族利益尽可能地结合起来。①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88页。
舜窃负而逃,虽然破坏了法律,但并未违背伦理,相反却是对“亲亲相隐”的真实践履。先秦时期,“亲亲相隐”是一股强大的思想史力量: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13·18)②此种序号注释,以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为据。下同。
仁,内也。义,外也。礼乐,共也。内立父、子、夫也,外立君、臣、妇也。疏斩布实丈,为父也,为君亦然。疏衰齐戊□(麻)实,为□(昆)弟也,为妻亦然。袒字为宗族也,为朋友亦然。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为□(昆)弟绝妻,不为妻绝□(昆)弟。为宗族□(疾)朋友,不为朋友□(疾)宗族。人有六德,三亲不□(断)。门内之糹司纫弇义,门外之糹司义斩纫。(郭店简《六德》)③荆州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第188页。
门内之治恩揜义,门外之治义断恩。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礼记·丧服四制》)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695页。
后来,“亲亲相隐”的伦理原则不断落实为具体的法律规范。终中国传统社会之世,皆是如此。这里仅引两条较有代表性的文献:
(地节四年)夏五月,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书·宣帝纪》)⑤班固:《汉书》第1册,第251页。
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唐律疏义》卷6“同居相为隐”条)⑥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第99页。
有论者把舜窃负而逃当作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的腐败问题看待⑦参见刘清平:《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哲学研究》2002年第2期。按,以刘文为导火索,国内学术界就“亲亲相隐”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代表性作品有:郭齐勇主编《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陈壁生《经学、制度与生活——〈论语〉“父子相隐”章疏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邓晓芒《儒家伦理新批判》,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邓书的封面甚至印有“五十年来国内最有深度的中国伦理争鸣”一语。又,笔者亦是这场争鸣的参与者。参见杨海文:《文献学功底、解释学技巧和人文学关怀——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般问题意识”》,《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刘清平:《也谈“善意解读”与“人文学关怀”——与杨海文先生商榷》,《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以上两文均收入郭书。,这种观点实则未能洞察到激进权智与理想人格的紧密关联。中国古代社会不是法治社会,而是人治社会。人治社会中的法律与道德,既是道德的法律化,也是法律的道德化,道德又高于法律,德主刑辅,法律的制订及实施必须以天理、人情作为最高、最终的依据①西方文化传统亦有类似看法。如,亚里士多德说:“法治应当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99页)孟德斯鸠说:“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行为……为了保存风纪,反而破坏人性,而人性却是风纪的泉源。”(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76页)。正如下面几段话所说:
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盐铁论·刑德》)②桓宽:《盐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15页。
孔子曰:“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正其忠爱,以尽之。”(《孔子家语》卷7《刑政》)③陈士珂辑:《孔子家语疏证》,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188页。
刑者,圣人所以爱民之具也。其禁暴止杀之意,一本乎至仁。然而执挺刃刑人而不疑者,审得其当也。故法家之说,务原人情,极其真伪,必使有司不得铢寸轻重出入,其为书不得不备。历世之治,因时制法,缘民之情,损益不常。(《欧阳文粹》卷16《崇文总目叙释》)④欧阳修著,陈亮编:《欧阳文粹》,《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第772页。
说到底,舜窃负而逃,既是以礼抗法,更是以权抗礼。舜更看重伦理亲情,所以,礼法冲突之际,他从“门内之治恩揜义,门外之治义断恩”的原则出发,宁愿“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法又从属于礼,因而,舜窃负而逃,实则背反于经的激进权智使然。礼法冲突是个永恒的问题,理想人格是种永恒的追求,孟子让舜以九五之尊窃负而逃,进一步为理想人格的最终全面实现夯实了激进权智的路径依赖,凸显了礼法冲突之际法让位于礼、礼高于法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这一做法亦是对孔子“无讼”理想的坚守与实践:“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12·13)蔡仁厚说得好:“如果你认为这样还不算真正解决问题,那是因为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无憾地解决,即使上帝也做不到。孟子的回答,已经是最好的了。”⑤蔡仁厚:《在解构中重建,在诠释中开展——记一段会议论文的讲评》,《鹅湖月刊》1997年9月号,第51页。
以上分析了激进权智的三组案例:一组是舜不告而娶,一组是汤放桀、武王伐纣、伊尹放太甲,一组是舜窃负而逃。这些行权者都是圣贤,社会地位极高,礼与权的冲突层次较为复杂,他们以权抗礼,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历史影响。加上小叔子救嫂子,《孟子》论激进权智的几个故事,均情节生动,发人深思。人们从中意识到了权变与经文并非总是协调的,并试图去消解这种不和谐。《朱子语类》卷37就说:“经自经,权自权。但经有不可行处,而至于用权,此权所以合经也,如汤、武事,伊、周事,嫂溺则援事。常如风和日暖,固好;变如迅雷烈风。若无迅雷烈风,则都旱了,不可以为常。”⑥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3册,第987页。
舜、汤、武、伊尹被孟子奉为圣人,人们同样认为救嫂子的行权者其实不是这个或那个小叔子,而是孟子本人。我们的思想史传统普遍认为惟有圣人才能行权:
故孔子曰:“可以共学矣,而未可以适道也;可与适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与权。”权者,圣人之所独见也。故忤而后合者,谓之知权;合而后舛者,谓之不知权;不知权者,善反丑矣。(《淮南子·氾论训》)⑦高诱:《淮南子注》,第223页。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权用也。惟圣人为能知权。言而必信,期而必当,天下之高行,直而证父,信而死女,孰能贵之?故圣人论事之曲直,与之屈伸,无常仪表,祝则名君,溺则捽父,势使然也。夫权者,圣人所以独见。夫先迕而后合者,之谓权;先合而后迕者,不知权。不知权者,善反丑矣。(《文子·道德》)①《二十二子》,第843页。
大抵汉儒说权,是离了个经说;伊川说权,便道权只在经里面。且如周公诛管、蔡,与唐太宗杀建成、元吉,其推刃于同气者虽同,而所以杀之者则异。盖管、蔡与商之遗民谋危王室,此是得罪于天下,得罪于宗庙,盖不得不诛之也。若太宗,则分明是争天下。故周公可以谓之权,而太宗不可谓之权。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故在伊尹可以谓之权,而在他人则不可也。权是最难用底物事,故圣人亦罕言之。自非大贤以上,自见得这道理合是恁地,了不得也。(《朱子语类》卷37)②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3册,第991页。
夫权也者,圆而通者也。是圣人之事,而学之仪的也。圣人圆,而学圣人者以方,始而方可也。终而愈方焉,则遂失其圆也。圣人通,而学圣人者以一隅,始而一隅可也,终而止一隅焉,则遂失其通也。夫学不至于圣人,非成也;不能权,非圣人也;非圆非通,不可以与权也。而不知所以求,不求所以至,非学也。(高拱:《问辨录·论语》)③高拱著,流水点校:《高拱论著四种》,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62页。
圣人既是单数的,又是复数的。单数言其实际之少:《孟子》末章只列举了5位圣人(14·38),《汉书·古今人表》只遴选了14位圣人④参见班固:《汉书》第3册,第861—954页。。复数言其可能之多:“圣人,与我同类者”(11·7),“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11·7),“人皆可以为尧舜”(12·2)。惟有圣人才能行权,说的是单数。他们一旦行权成功,则为千千万万人成就理想人格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说的是复数。少数的圣人以权抗礼,修正了既有礼乐规范的不足之处,权变与经文由不和谐变成了和谐,无数人以此指导自身的伦理生活,不断地逼近理想人格。这个过程既敞开了背反于经的激进权智,又召唤着返归于经的温和权慧。孟子的经权之辨如何从以权抗礼走向以权行礼呢?
三、“返归于经”的温和权慧
《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曰:“古人之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何休注:“古人谓伊尹也。汤孙大甲骄蹇乱德,诸侯有叛志,伊尹放之桐宫,令自思过,三年而复成汤之道。前虽有逐君之负,后有安天下之功,犹祭仲逐君存郑之权是也。”⑤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220页。这里用伊尹放太甲、祭仲逐君存郑来解说“权者反于经”,权难道只是“背反于经”、“忤而后合”吗?人们的日常生活难道就不需要权变智慧吗?
《韩诗外传》卷2记孟子论卫女曰:
高子问于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亲也,卫女何以编于《诗》也?”孟子曰:“有卫女之志则可,无卫女之志则怠。若伊尹于太甲,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夫道二,常之谓经,变之谓权。怀其常道而挟其变权,乃得为贤。夫卫女行中孝,虑中圣,权如之何?”《诗》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⑥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4页。按,孟子论卫女,又见《孟子外书·为正》(参见刘培桂:《孟子大略》,济南:泰山出版社,2007年,第164页)。两者文字稍异。
卫女故事,见《列女传·仁智传》“许穆夫人”条:
许穆夫人者,卫懿公之女,许穆公之夫人也。初,许求之,齐亦求之,懿公将与许。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系援于大国也。言今者许小而远,齐大而近,若今之世,强者为雄,如使边境有寇戎之事,维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国,妾在,不犹愈乎?今舍近而就远,离大而附小,一旦有车驰之难,孰可与虑社稷?”卫侯不听,而嫁之于许。其后翟人攻卫,大破之,而许不能救,卫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齐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卫侯于是悔不用其言。当败之时,许夫人驰驱而吊唁卫侯,因疾之而作诗云:“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君子善其慈惠而远识也。①张涛:《列女传译注》,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94页。
许是小国,又远,齐是大国,又近。卫女想嫁到齐国而不是许国,因为万一娘家有事,大国比小国更能照应,近处比远处更好关照。后来翟人攻卫,证明卫女的想法是对的。卫女以《载驰》明志,但她并未以权抗礼,而是实实在在地践履了“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6·3)、“大孝终身慕父母”(9·1)的礼乐规范。难道这不是权吗?孟子说“卫女行中孝,虑中圣,权如之何”,表明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样离不开权变智慧。它不是背反于经的激进权智,而是“怀其常道而挟其变权,乃得为贤”,是返归于经的温和权慧。刘向把卫女(许穆夫人)列入《仁智传》,足见这种温和权慧有助于人们成就“仁且智”的理想人格。
圣人紧扣人之常情制作的礼乐规范,理论上不会穷尽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形,实际上则是道德实践主体的日常行为准则。经文绝大多数时候是对的,偶尔才会有错。经文不对,才需要圣人以权抗礼;经文对,只需人们以权行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常运用的其实不是背反于经的激进权智,而是返归于经的温和权慧。更何况,经文本身是静止不动的,它必须经由人们的理解与实行才会被敞开,否则它就永远无关乎人们的实际生活。所以,温和权慧就是不断地激活静态不动的经文,让自身的行为举止真正地符合礼乐规范,以返归于经也。
孔孟时代,礼坏乐崩,人们以温和权慧践履礼乐规范,谈何容易?孔子说过:“乡愿,德之贼也。”(《论语》17·13)孟子进一步指出:
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14·37)
乡愿,《孟子》作“乡原”。乡愿就是八面玲珑、是非不分的好好先生,他们足以败坏道德,是为“德之贼”。人们如何拒斥乡愿?孟子指出:“君子反经而已矣。”反即返,反经即返归于经。《孟子集注》卷14云:“世衰道微,大经不正,故人人得为异说以济其私,而邪慝并起,不可胜正,君子于此,亦复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复,则民兴于善,而是非明白,无所回互,虽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76页。归于礼法叫复礼,归于经常叫返经。
道德实践主体返归于经,为的是践履中道,可乡愿横行于世,《四书评·孟子卷之七》就说:“乡原故是贼,一乡也是个窝家。”③李贽:《四书评》,第298页。返归于经虽为温和权慧,实则离不开狂狷:“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14·37)《梁启超论孟子遗稿》指出:“凡《孟子》书中教人以发扬志气坚信自力者,皆狂者之言也;凡《孟子》书中教人以砥厉廉隅峻守名节者,皆狷者之言也。故学孟子之学,从狂狷入焉可耳。”④王兴业编:《孟子研究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508页。狂就是进取、意气风发,狷就是有所不为、砥砺名节,狂狷实质上就是返归于经的温和权慧。
(一)如何应付违礼行为?
《孟子》记有孟子不与右师言的故事:
公行子有子之丧,右师往吊。入门,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孟子不与右师言,右师不悦曰,“诸君子皆与驩言,孟子独不与驩言,是简驩也。”
孟子闻之,曰:“礼,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我欲行礼,子敖以我为简,不亦异乎?”(8·27)
右师就是王驩,又名王子敖。公行子举办儿子的丧礼,王驩一进门,就有人上前搭讪;他坐定了,凑过去嘘寒问暖的更多。人们为何如此?因为王驩有权有势。人们这样做,是否顾及到了必要的礼节呢?孟子没有去跟王驩说话,他极不高兴,认为孟子看不起他。孟子说道:“礼经规定人们:朝廷中,不跨过位次交谈,不越过石阶作揖。我不过依礼而行,王子敖却以为我简慢了他,这真是可怪呀!”
《孟子事实录》卷上云:“王驩,齐王之宠臣,恃宠而骄,常也;然乃朝暮见焉,虽不与言行事而不改,是何其敬孟子乃尔?”①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19页。王驩尊重孟子,也想孟子尊重他,皆在情理之中。《四书评·孟子卷之四》曰:“许多人与他言,未尝悦,孟子一人不与之言,便不悦。的是妙人,与言众人,岂不自愧。”②李贽:《四书评》,第231—232页。王驩要孟子用周围人的方式尊重他,可那些人只是巴结王驩而已,孟子怎么可能会做?!
“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这些礼节并不复杂、深奥,王驩难道不知道吗?他为何接受人们无视礼节来逢迎他呢?其他人难道不知道吗?他们为何无视礼节而去讨好王驩呢?礼节,仅仅知其条文还不行,更得行其实质。行礼又不是单一的行为,它涉及到具体情景,并且要在礼节与权势等等之间进行抉择。选择权势,就有可能违礼。乡愿趋炎附势,权贵乐于被趋炎附势,既是礼坏乐崩之果,亦是礼坏乐崩之因。孟子选择了礼节,身体力行地拒斥乡愿,体现的却是看似平淡、实则难能可贵的温和权慧。
特殊情形下,径庭历级则体现出以权抗礼的激进权智。季平子生前专权,把鲁昭公赶到了国外,季桓子却用鲁昭公的佩玉——玙璠给季平子入殓,孔子就不顾礼节,径庭而趋,历级而上,严词指斥:
鲁季孙有丧,孔子往吊之。入门而左,从客也。主人以玙璠收,孔子径庭而趋,历级而上,曰:“以宝玉收,譬之犹暴骸中原也。”径庭历级,非礼也;虽然,以救过也。(《吕氏春秋·安死》)③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上册,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537页。按,陈书引高注:“孔子‘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言不欲违礼,亦不欲人之失礼,故历阶也。”(同上书,第550页)
季平子卒,将以君之玙璠敛,赠以珠玉。孔子初为中都宰,闻之,历级而救焉,曰:“送而以宝玉,是犹曝尸于中原也。其示民以奸利之端,而有害于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顺情以危亲,忠臣不兆奸以陷君。”乃止。(《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④陈士珂辑:《孔子家语疏证》,第281页。
鲁人将以玙璠敛,孔子闻之,径庭丽级而谏。夫径庭丽级,非礼也,孔子为救患也。患之所由,常由有所贪。玙璠,宝物也,鲁人用敛,奸人僴之,欲心生矣。奸人欲生,不畏罪法,不畏罪法,则丘墓(抽)[抇]矣。孔子睹微见著,故径庭丽级,以救患直谏。夫不明死人无知之义,而著丘墓必(抽)[抇]之谏,虽尽比干之执,人人必不听。何则?诸侯财多不忧贫,威强不惧(抽)[抇]。死人之议,狐疑未定,孝子之计,从其重者。如明死人无知,厚葬无益,论定议立,较著可闻,则玙璠之礼不行,径庭之谏不发矣。今不明其说而强其谏,此盖孔子所以不能立其教。(《论衡·薄葬》)⑤王充:《论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53页。
《孟子》还记有虞人非其招不往的故事:
孟子曰:“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6·1)
曰:“敢问招虞人何以?”
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岂敢往哉?况乎以不贤人之招招贤人乎?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诗》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10·7)
虞人就是猎场管理员,掌山泽之官,地位卑微。《左传·昭公二十年》亦云:
十二月,齐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进。公使执之。辞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韪之。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093页。
礼仪规定:君主召唤不同级别的臣民,得用不同类型的物什;如果用错了召唤物,被招者不能接受召唤。齐景公田猎,错用了召唤物,虞人死不敢往,气得齐景公要处死他。历史上,人们却很少注意到,《孟子》《左传》各自所述的召唤物竟然大相径庭(如表1所示)。不管《孟子》的记载对,还是《左传》的记载对,都不再重要,因为这种差异本身已然写照了春秋战国时期礼坏乐崩的严峻事实。惟其严峻,人们才经久不息地喟叹于齐虞人非其招不往。《汉书·古今人表》就把齐景公列入下上等,而把齐虞人列入中下等②参见班固:《汉书》第3册,第926页。。

表1《孟子》《左传》所述召唤物之差异
《孟子》书中,孟子认为孔子肯定齐虞人非其招不往,就是肯定虞人不枉尺而直寻的道义品格。弯曲一尺却能伸长八尺,代价小而收益大,这是经济生活;如果拿利益最大化原则来评判或者指引道德生活,就会破坏道义本身。本职岗位上能够坚守义利之辨,也正是齐虞人最可贵之所在。《左传》笔下,孔子认为:“守道不如守官。”杜预注:“君招当往,道之常也。非物不进,官之制也。”③阮元 校刻:《 十三经 注疏 》下 册,第2093页。有招必应,本是常道;非其招不往,则是官制。齐虞人守的不仅仅是常道,更是官制。做了分上的事却面临杀身之祸,以权行礼却得视死如归,而且是违礼者处罚守礼者,这不是礼坏乐崩,又是什么?!
人们首先在理论上熟练地掌握礼乐规范,随之在实践中真切地践履。熟练地掌握一套礼乐规范并不难,难的是真切地践履它们。面对伦理生活中的违礼行为,返归于经不是张罗待鸟,而是好比荷戈御兽;不具备足够有力的温和权慧,就直面不了强势的违礼者,拒斥不了无处不在的乡愿!孟子不与右师言,虞人非其招不往,敞开的正是实践比理论更重要的温和权慧。
(二)如何应付位移现象?
每个人既是对象性的存在,又是主体性的存在。从对象性存在看,一旦置身于新的伦理位置,人在礼乐规范体系中就会获得新的意义。从主体性存在看,交往网络会因时因地变换人的伦理位置,人必须积极主动地意识到由此而被赋予的新意义。体认自身的主体性存在,不妨从对象性存在入手。先看下面这段对话:
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
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
“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
曰:“敬兄。”
“酌则谁先?”
曰:“先酌乡人。”
“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
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将曰,‘敬叔父。’曰,‘弟为尸,则谁敬?’彼将曰,‘敬弟。’子曰,‘恶在其敬叔父也?’彼将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
季子闻之,曰:“敬叔父则敬,敬弟则敬,果在外,非由内也。”
公都子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然则饮食亦在外也?”(11·5)
伦理生活中有种常见的位移现象:一个是伯兄,另一个是年长伯兄一岁的乡人,我应该心中对谁恭敬呢?如果斟酒,又该先斟给谁呢?假如只有伯兄与我在场,或者只有乡人与我在场,我不会犯难。现在却是伯兄与乡人同时在场,我必须回应。
公都子是孟子的弟子,他认为:伯兄与我同一血缘,我应该心中恭敬伯兄;乡人比伯兄年长,我应该先斟酒给乡人。这一认识很质朴,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孟子则指出:叔父与弟弟两个人在场,恭敬问题很简单,只能恭敬叔父;如果弟弟做了受祭的代理人,情形就不一样了,叔父必须恭敬弟弟。孟子还告诉公都子:弟弟一旦做了受祭代理人,就从主体性存在变成了对象性存在,所以必须受到恭敬;同理,先酌乡人,也是因为他处在应该首先被斟酒的位置上。
“弟为尸”就是弟弟做了受祭代理人,“在位”就是弟弟取得了受祭代理人的新身份。《孟子集注》卷11云:“尸,祭祀所主以象神,虽子弟为之,然敬之当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乡人在宾客之位也。”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27页。《礼记·学记》也说过:“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弗臣也……”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524页。
祭祀、社交之际,变换伦理位置是常有的事。人们必须对自身或他人由此获得的新意义进行体认,才能释放出祭祀、社交等礼乐文明固有的政治—伦理统制功能。其间同样离不开权变智慧,否则,人们就难以从变动不居的角色丛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伦理位置。孟子就说:“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孟子集注》卷11云:“庸,常也。斯须,暂时也。言因时制宜,皆由中出也。”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27页。《日知录》卷7“行吾敬故谓之内也”条曰:“先生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礼、五服、五刑,其出乎身,加乎民者,莫不本之于心,以为之裁制。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故孟子答公都子言义,而举酌乡人、敬尸二事,皆礼之也,而莫非义之所宜。”④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259页。这种权变智慧不是以权抗礼的激进权智,而是以权行礼的温和权慧。
(三)如何应付收礼情形?
《礼记·曲礼上》云:“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⑤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231页。从礼物的角度看,往就是送礼,来就是收礼。送礼与收礼,既是礼节的要求,更是礼义的体现。你送出什么样的礼物,送出的其实是你的某种自我,因为礼物折射了你的本性的一部分;你接受什么样的礼物,也是在接受送礼人的某种自我,因为礼物同样折射了送礼人的本性的一部分。礼尚往来,礼物必须处于流动、活跃的状态。你拒绝接受礼物,或者接受了礼物却不回礼,都将面临来自整个礼乐文明体系的压力。
孟子讨论过送礼问题,如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并解释为:“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6·3)孔子要是三个月没有君主任用他,就非常焦急,离开这个国家,一定带上跟其他君主初次见面的礼物。这是因为:知识分子得从政,就像农夫得耕地一样;农夫出境不会不带上农具,知识分子出境也得带上见面礼物。
相比之下,孟子对收礼问题的讨论,更加发人深省。例如,他曾与弟子万章讨论过三种不同的收礼情形:
万章问曰:“敢问交际何心也?”
孟子曰:“恭也。”
曰:“‘却之却之为不恭’,何哉?”
曰:“尊者赐之,曰,‘其所取之者义乎,不义乎?’而后受之,以是为不恭,故弗却也。”
曰:“请无以辞却之,以心却之,曰,‘其取诸民之不义也’,而以他辞无受,不可乎?”
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
万章曰:“今有御人于国门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馈也以礼,斯可受御与?”
曰:“不可;《康诰》曰:‘杀越人于货,闵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诛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辞也;于今为烈,如之何其受之?”
曰:“今之诸侯取之于民也,犹御也。苟善其礼际矣,斯君子受之,敢问何说也?”
曰:“子以为有王者作,将比今之诸侯而诛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也。孔子之仕于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猎较犹可,而况受其赐乎?”(10·4)
以上这段话,《四书评·孟子卷之五》评曰:“问处每胜。”①李贽:《四书评》,第249页。万章问得好,孟子回答好了所有问题吗?《孟子集注》卷10引尹氏:“不闻孟子之义,则自好者为于陵仲子而已。圣贤辞受进退,惟义所在。”又自按:“此章文义多不可晓,不必强为之说。”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20,319—320页。
三种收礼情形之中,前两种是尊者赐予礼物、强盗馈赠礼物。孟子认为:尊者赐予礼物,只要合乎礼仪,就应该接受,否则就是不恭;强盗馈赠礼物,即使合乎礼仪,也不能接受,因为夏商周的法律都把强盗看成不待教而诛者,何况打打杀杀如今更为厉害呢?这里,接受尊者赐予的礼物,亦即接受了尊者本性中的一部分;拒绝强盗馈赠的礼物,亦即拒绝了强盗本性中的一部分。
第三种情形较为复杂。万章以为:诸侯从民间获取财物,跟强盗打家劫舍没有差别;如果诸侯也按礼仪赐予礼物,人们接不接受就会陷入两难——不接受就是不恭,接受就好似接受了强盗的礼物。万章的提问既从道德理想主义立场针砭了诸侯们的巧取豪夺,又清醒意识到了道德实践主体难以回避政治伦理生活中的某类错置特例。但是,万章也清楚地知道:“苟善其礼际矣,斯君子受之”,现实生活中,人们同样会接受诸侯所赐的礼物。这又是为什么呢?
如何处理第三种收礼情形,可谓这场对话的焦点。孟子认为:不是自己所有的,却要得到它,把这种行为叫做抢劫,不过是提高到原则性高度的话而已;只要合乎礼仪,这类赐予就得接受。理由在于:第一,圣王兴起,也会首先教育诸侯,实在不能改过者才会诛杀;第二,现在圣王尚未兴起,士阶层惟有接受,才有机会去教育诸侯;第三,诸侯“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士阶层却不接受,就是不恭,就失去了教育诸侯的机会。
《孟子集注》卷10亦云:
言今诸侯之取于民,固多不义,然有王者起,必不连合而尽诛之。必教之不改而后诛之,则其与御人之盗,不待教而诛者不同矣。夫御人于国门之外,与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义之类,然必御人,乃为真盗。其谓非有而取为盗者,乃推其类,至于义之至精至密之处而极言之耳,非便以为真盗也。然则今之诸侯,虽曰取非其有,而岂可遽以同于御人之盗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犹或可从,况受其赐,何为不可乎?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20,319—32页。
可是,小盗被杀、大盗得国的“窃钩盗国”观念却是一种悠久的思想史传统:
今有人于此,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墨子·鲁问》)④吴毓江著,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734—735页。
窃钩者诛,窃邦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之所存。(郭店简《语丛四》第9简)⑤荆州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第217页。
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庄子·胠箧》)①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册,第256页。
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庄子·盗跖》)②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下册,第790页。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史记·游侠列传》)③司马迁:《史记》第10册,第3182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万章明显受到了以上思想史传统的影响,孟子却是另外的态度。礼物之为物,首先得是财物。万章质问财物的来源是否合法,把诸侯与强盗相提并论,“今之诸侯取之于民也,犹御也”,充盈着批判精神,俨然狂者;孟子关注礼物的交接是否合礼,认为诸侯不同于强盗,“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也”,内敛着建构思维,仿佛狷者。
孟子这里的狷者姿态,其实并不出人意料。诸侯放恣乃是政治—伦理生态恶化最显著的表现,士阶层的历史担当就是要尽力改变这种状况。诸侯给士阶层送礼,隐含了某种政治期待;士阶层接受诸侯的礼物,同时也就接受了这一政治期待。只要诸侯依据规矩同我交往,按照礼节同我接触,我就没有理由拒绝他们。士阶层接受了赐予,才有可能“格君心之非”(7·20)。“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13·33),是士阶层对自身的要求。士阶层却不能拿自身的标准来要求诸侯,所以,“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也”(10·4),这其实亦是权衡的体现。退一步,即便诸侯的礼物是像强盗那样巧取豪夺而来的,士阶层又接受了这一赐予,但跟听任诸侯放恣的恶性发展相比,其过也要轻微得多。
回到我们的论题,孟子的收礼观何以体现了以权行礼的温和权慧呢?送礼与收礼是礼乐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们一旦进入具体的伦理实践,同样需要身体化对条文化的激活与敞开。条文化的规矩是死的,身体化的践履是活的,送礼与收礼要合乎礼仪地进行,都离不开权变;一般情形下,这种权变不是以权抗礼的激进权智,而是返归于经的温和权慧。即使送礼人都按照礼仪来交往,士阶层不接受强盗的礼物,却接受尊者、诸侯的礼物,这一区别对待也是权变的结果。强盗的礼物折射了强盗本性的一部分,尊者、诸侯的礼物折射了尊者、诸侯本性的一部分,士阶层拒绝前者而接受后者,既符合固有之礼的规定,更是收礼人实现自身政治理想的必由之路。郭店简《语丛四》有言:“邦有巨雄,必先与之以为朋。”④荆州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第217页。孟子也说过:“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7·6)连礼物都不敢接受,士阶层从政,又哪里谈得上仰仗于那些巨雄、巨室呢?
有论者认为,接受诸侯的赐予却不接受强盗的馈赠,也是背反于经⑤参见杨泽波:《孟子经权思想探微》,《学术论坛》1997年第6期,第55页。。孟子引《康诰》,表明不接受强盗的馈赠,乃是固有之礼的要求。接受诸侯的赐予,则是因为孟子认为“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也”;先前论尊者的赐予,孟子又指出:“尊贵的人有所赐予,自己先想了想:‘他获取这些财物是合乎义的,还是不义的呢?’想了以后才接受,这是不恭敬的。所以便不拒绝。”接不接受诸侯的礼物,孟子主要以“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作为标准。士阶层接受诸侯的礼物,其实并没有违反固有之礼;即便接受诸侯像强盗那样得来的东西,也不是背反于经,而是返归于经的温和权慧使然。
下面这段对话也是关于收礼的:
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
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4·3)
于宋,孟子要远行,给远行的人送些盘缠是合乎情理的,所以孟子接受了宋王的七十镒;于薛,孟子听说路上有危险,需要加强戒备,薛君给孟子五十镒来购买兵器,孟子接受了;于齐,齐王送上兼金一百,孟子觉得齐王在用金钱收买他,没有接受的理由,所以拒绝了。这里,孟子收不收礼,也是在接受或者拒绝送礼人本性的一部分。它们并未违背任何固有之礼,反而却是返归于经、以权行礼,从中尤其可见义仕派智识分子“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的独特精神风貌。
以上,我们从如何应付违礼行为、位移现象、收礼情形三个方面,试图证明返归于经的温和权慧同样也是孟子经权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传习录上》有段对话:“问孟子言‘执中无权犹执一’。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随时变易,如何执得?须是因时制宜,难预先定一个规矩在。如后世儒者要将道理一一说得无罅漏,立定个格式,此正是执一。’”①王守仁著,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9页。预先定出所有规矩,仅仅只是良好的愿望,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所以圣人才会背反于经、以权抗礼。但是,“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7·1),固有之礼或者既定的礼乐文明体系就是这个规矩;而且,这个规矩要从条文化的框框走向身体化的践履,就得随时变易、因时制宜,须臾离不开返归于经的温和权慧,否则,执中无权,其犹执一。
假如返归于经的温和权慧不发挥着即时当下、真切有力的作用,猎场管理员以及孟子凭什么抵挡齐景公、王驩等权贵们明目张胆的违礼行为呢?公都子凭什么知道首先要斟酒给年长于伯兄一岁的乡人,要尊敬受祭代理人位置上的弟弟呢?万章凭什么懂得士阶层可以接受诸侯的赐予呢?权是个体的自由性、自主性的实践和显现。人们实践返归于经的温和权慧,就是为了激活并敞开条文化的规矩到身体化的践履这一转变,同时借助这一转变,显现出自己的自由性、自主性,推动着经文与权变和谐地朗现于人们的政治—伦理生活本身。这种显现越是充分,理想人格越是得以逐渐培塑。
四、孟子经权观的独特理论价值
钱锺书的《左传正义》有言:“‘权’乃吾国古伦理学中一要义,今世考论者似未拈出。”②钱锺书:《管锥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06—207页。譬如,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以及方立天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均以问题为中心梳理中国哲学观念,却未对经权问题进行专题研讨。我们不讨论这个论断是否准确,但孟子的经权观迄今为止未能获得真正全面的研讨,则是不争之实。
我们的思想史传统认为:经是原则性,适应于常态,指导着一般情形下的伦理生活,是为本;权是灵活性,适应于变态,指导着特殊情形下的伦理生活,是为末(如表2所示)。赵纪彬的《高拱权说辨证》一文甚至勾勒过经权思想史上的汉宋之争:汉儒主张“反经合道为权”,宋儒主张“常则守经,变则行权”,两者存在着冲突③参见赵纪彬著,李慎仪编:《困知二录》,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84—285页。按,赵纪彬曾计划写作十多万字的《中国权说史略》,最终只完成了三文,即《释权》《〈论语〉“权”字义疏》《高拱权说辨证》。这三篇文章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均收入《困知二录》。。这种冲突激烈吗?且看董仲舒、朱熹两家在基本设定上近乎一致的提法:
《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春秋繁露·竹林》)④苏舆著,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3,327页。是故天以阴为权,以阳为经……经用于盛,权用于末。以此见天之显经隐权,前德而后刑也。(《春秋繁露·阳尊阴卑》)⑤苏舆著,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337页。
经毕竟是常,权毕竟是变。(《朱子语类》卷37)⑥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3册,第989页。
经是万世常行之道,权是不得已而用之,大概不可用时多。(《朱子语类》卷37)⑦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3册,第989页。

表2 传统经权观的一般解读
拿上述看法来解读孟子的经权观,显然无法洞见其丰富而又独特的内涵。换句话说,人们尚未认识到孟子经权观的庐山真面目,亦是这种约定俗成的传统经权观念使然。
众所周知,圣人为了让道德实践主体充分自由地展开伦理生活,制作了代代相传的礼乐规范——经。经文首先驻留于典册之中,其后得到人们反复地学习,但相对于伦理实践而言,它们还是静态的。经文由静态变成动态,就离不开权变。正如明代学者高拱《问辨录·论语》所言:
夫权者何也?称锤也。称之为物,有衡有权。衡也者,为铢、为两、为斤、为钧、为石,其体无弗具也,然不能自为也。权也者,铢则为之铢,两则为之两,斤则为之斤,钧则为之钧,石则为之石,往来取中,至于千亿而不穷。其用无弗周也,然必有衡而后可用也。故谓衡即是权,权即是衡,不可也。然使衡离于权,权离于衡,亦不可也。盖衡以权为用,权非用于衡,无所用之。分之则二物,而合之则一事也。①高拱著,流水点校:《高拱论著四种》,第162页。
以秤喻经,以锤喻权,“盖衡以权为用,权非用于衡,无所用之”,形象地说明了权变乃是经文走向实践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甚至就是经文走向实践这一活动过程本身。人们依据经文规范以展开伦理实践,同时也就是在实施返归于经的温和权慧。加上圣人制作的礼乐规范具有高度的真理性,因此,返归于经的温和权慧可谓人们践履伦理生活的基本方式。《河南程氏遗书》卷4云:“穷经,将以致用也。如‘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今世之号为穷经者,果能达于政事专对之间乎?则其所谓穷经者,章句之末耳,此学者之大患也。”②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1册,第71页。返归于经的温和权慧就是经以致用的内驱机制,否则,人们永远只能停留于章句之末。
圣人制作的礼乐规范事实上不可能穷尽日常生活中的所有情形,既有的礼乐规范有时还可能扼杀置身于伦理新情境之下的道德实践主体自然而然的道德情感。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人们就必须背反于经、以权抗礼。先秦两汉典籍对此有过许多论述:
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③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220页。
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为也,公子目夷是也。(《春秋繁露·玉英》)④苏舆著,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79页。
权者,反经而善也。(《孟子正义》卷15引赵岐注)⑤焦循著,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21页。
这里有必要清理一下汉儒“反经合道为权”之说的来龙去脉。前引《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以及《论语·子罕》是其两个源头,后者又更为重要。《子罕篇》有相连的两章: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9·30)⑥唐代冯用之《权论》引《论语·子罕》第30章为“可与共学,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与今本有异。参见董诰等辑:《钦定全唐文》卷404,《续修四库全书》第164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第562页。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9·31)
王夫之的《四书稗疏·论语上篇》“唐棣”条认为汉儒把“偏其反而”理解为“反经合权”,乃是一种邪说:
《诗传》:“唐棣,思贤也。”既删之后,《诗》尚未逸,唯《毛传》失传耳。既为思贤之诗,则子曰“未之思也”,亦言其好贤之未诚;“夫何远之有”,言思之诚而贤者自至耳。义既大明,则汉人以“偏反”为反经合权之衺说,不攻自破矣。①王夫之著,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编校:《船山全书》第6册,长沙:岳麓书社,1991年,第35页。
清代学者毛奇龄《论语稽求篇》卷4指出:
按“唐棣”二节,旧本与“可与共学”节合作一章。其又加“子曰”者,所以别诗文也。但其义则两下不接,颇费理解。惟何平叔谓偏反喻权,言行权似反而实出于正,说颇近理,然语尚未达。予尝疏之云:夫可立而未可权者,以未能反经也。彼唐棣偏反,有似行权,然而思偏反而不得见者,虑室远也。思行权而终不行者,虑其与道远也,不知无虑也。夫思者当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为远。能思其反,何远之有?盖行权即所以自立,而反经正所以合道。权进于立,非权不可立也……汉儒以反经合道为权,此正本夫子偏反喻权之意。且亦非汉后私说,在前此已有之。《公羊传》曰:“权者何?权者反乎经者也,反乎经然后有善也。”“反经”之语,实始于此。其后,相习成说,著为师传,然皆本夫子是语。②毛奇龄:《论语稽求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1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第170页。
“反经”一语典出《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反经合道”一语则不见于汉代大儒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毛奇龄所说“惟何平叔谓偏反喻权……”,见《论语注疏》卷9;但何晏注《子罕》第31章亦只是认为:“赋此诗者,以言权道反而后至于大顺。思其人而不得见者,其室远也。以言思权而不得见者,其道远也。”“夫思者,当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为远。能思其反,何远之有?言权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③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491页。王充《论衡·本性》倒是说过:“余固以孟轲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若反经合道,则可以为教;尽性之理,则未也。”④王充:《论衡》,第47页。《易传·系辞下》云:“巽以行权。”东晋韩康伯注:“权,反经而合道。必合乎巽,顺而后可以行权也。”⑤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89页。以上两段话可能就是“反经合道”一语较早的语源。
把“反经合道为权”当作汉儒经权观的基本理念,实则宋儒的理论概括。《论语集注》卷5注《子罕》第30章,朱熹引程子:“汉儒以反经合道为权,故有权变权术之论,皆非也。权只是经也。自汉以下,无人识权字。”又自按:“先儒误以此章连下文偏其反而为一章,故有反经合道之说。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义推之,则权与经亦当有辨。”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16页。《朱子语类》卷37论“可与共学”章,着墨极多,线索尤为清晰。
小程论权,有两段话值得重视:
论事须著用权。古今多错用权字,纔说权,便是变诈或权术。不知权只是经所不及者,权量轻重,使之合义,纔合义,便是经也。今人说权不是经,便是经也。权只是称锤,称量轻重。孔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河南程氏遗书》卷18《伊川先生语四》)⑦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1册,第234,294—295页。
唐棣之华乃千叶郁李,本不偏反,喻如兄弟,今乃偏反,则喻兄弟相失也。兄弟相失,岂不尔思,但居处相远耳。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盖言权实不相远耳。权之为义,犹称锤也。能用权乃知道,亦不可言权便是道也。自汉以下,更无人识权字。(《河南程氏遗书》卷22上《伊川先生语八上》)⑧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1册,第234,294—295页。
“自汉以下,更无人识权字”,足见小程轻视汉儒的“反经合道为权”之说,而是认为权便是经:它也是有条件的,只有在权量轻重并使其合义的情况下,权才是经。唐代陆贽《论替换李楚琳状》有言:“夫权之为义,取类权衡。衡者,称也;权者,锤也。故权在于悬,则物之多少可准;权施于事,则义之轻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舍轻;其远祸也,必择轻而避重。苟非明哲,难尽精微,故圣人贵之,乃曰:‘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言知机之难也。今者甫平大乱,将复天衢,辇路所经,首行胁夺,易一帅而亏万乘之义,得一方而结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轻,而轻其所重,谓之权也,不亦反乎?以反道为权,以任数为智,君上行之必失众,臣下用之必陷身,历代之所以多丧乱而长奸邪,由此误也。”①董诰等辑:《钦定全唐文》卷471,《续修四库全书》第164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第635—636页。按,陆贽之前,《刘子·明权》亦云:“循理守常曰道,临危制变曰权。权之为称,譬犹权衡也。衡者测邪正之物,权者揆轻重之势。”(旧题北齐刘书撰,唐袁孝标注:《刘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第923页)《论语稽求篇》卷4曾节引这段话,并云:“此不过一时一人有为之言,而宋人一闻其说,便群遵之,遂谓权即是经,反经即非权。”②毛奇龄:《论语稽求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10册,第171页。毛奇龄的一引一评,可知伊川之说受到过以锤喻权思想的影响。《论语集注》卷5引程子:“权,称锤也,所以称物而知轻重者也。可与权,谓能权轻重,使合义也。”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16页。但是,“反经合道”一语并不见于《河南程氏遗书》,“权只是经也”一语亦不见于二程著述④这一判断亦得到二程研究专家、四川师范大学首席教授蔡方鹿先生的确认,特此致谢。。后者很可能是朱熹总结出来的,或者说经由朱熹才得到了推广。
“权只是经”也仅仅只是经权思想史从“反经合道为权”过渡到“常则守经,变则行权”的中间环节,因为朱熹并不十分赞成这一说法。《朱子语类》卷37指出:
吴伯英问:“伊川言‘权即是经’,何也?”曰:“某常谓不必如此说。孟子分明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权与经岂容无辨!但是伊川见汉儒只管言反经是权,恐后世无忌惮者皆得借权以自饰,因有此论耳。然经毕竟是常,权毕竟是变。”又问:“某欲以‘义’字言权,如何?”曰:“义者,宜也。权固是宜,经独不宜乎?”⑤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3册,第989,993页。
问:“伊川谓‘权只是经’,如何?”曰:“程子说得却不活络。如汉儒之说权,却自晓然。晓得程子说底,得知权也是常理;晓不得他说底,经权却鹘突了。某之说,非是异程子之说,只是须与他分别,经是经,权是权。且如‘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此是经也。有时天之气变,则冬日须着饮水,夏日须着饮汤,此是权也。权是碍着经行不得处,方使用得,然却依前是常理,只是不可数数用。如‘舜不告而娶’,岂不是怪差事?以孟子观之,那时合如此处。然使人人不告而娶,岂不乱大伦?所以不可常用。”⑥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3册,第98999页。
经权思想史上的汉宋之争充斥着针锋相对的争辩,譬如以下两段话:
或者不知权之所以为中,乃指为反经合道。夫经者,道之所以为常也;权者,所以权其变而求合夫经也。既反经矣,尚何道之合乎?以至于尧舜之禅、汤武之伐、周公之诛,盖亦如夫夏葛冬裘、饥食渴饮,当其可而已。非理明义精,畴足以识之哉?([南宋]张栻:《癸巳论语解》卷5)⑦张栻:《癸巳论语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第249页。
南轩以为:“既曰反经,恶能合道?”盖不知非常之事,固有必须反经然后可以合道者。如汤征桀、武王伐纣、伊尹放太甲、周公诛管叔,皆非君臣兄弟之常理,圣人于此,不得已而为之,然后家国治而天下平,未闻不能合道也。只如嫂溺援之之事,视其所以,乃是以手援嫂,诚为反其授受不亲之经;察其所安,乃是以仁存心,期在救其逡巡溺者之死,斯岂不能合道哉?([元]陈天祥:《四书辨疑》卷5)⑧陈天祥:《四书辨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第407页。
实际上,朱熹对汉儒的“反经合道为权”之说并未一棍子打死,而是承认它也有合理的成分。《朱子语类》卷37就说:
盖经者只是存得个大法,正当底道理而已。盖精微曲折处,固非经之所能尽也。所谓权者,于精微曲折处曲尽其宜,以济经之所不及耳。所以说“中之为贵者权”,权者即是经之要妙处也。如汉儒说“反经合道”,此语亦未甚病。盖事也有那反经底时节,只是不可说事事要反经,又不可说全不反经。如君令臣从,父慈子孝,此经也。若君臣父子皆如此,固好。然事有必不得已处,经所行不得处,也只得反经,依旧不离乎经耳,所以贵乎权也。①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3册,第992页。
董仲舒同样也认可“常则守经,变则行权”,《春秋繁露·玉英》指出:
《春秋》有经礼,有变礼。为如安性平心者,经礼也。至有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不平,于道,无以易之,此变礼也。是故昏礼不称主人,经礼也。辞穷无称,称主人,变礼也。天子三年然后称王,经礼也。有故则未三年而称王,变礼也。妇人无出境之事,经礼也。母为子娶妇,奔丧父母,变礼也。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可与适权矣。难者曰:《春秋》事同者辞同。此四者俱为变礼,而或达于经,或不达于经,何也?曰:《春秋》理百物,辨品类,别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坠谓之陨,螽附谓之雨,其所发之处不同,或降于天,或发于地,其辞不可同也。今四者俱为变礼也同,而其所发亦不同。或发于男,或发于女,其辞不可同也。是或达于常,或达于变也。②苏舆著,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74—76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仔细考量经权思想史上的汉宋之争,双方都有夸大其词的嫌疑。一旦夸大其词,汉儒的“反经合道为权”就成了经权互悖之论,宋儒的“常则守经,变则行权”就成了经权互隔之说。既然朱熹并未一棍子打死“反经合道为权”之说,董仲舒也认可“常则守经,变则行权”的合理性,双方的冲突就有可能得到调和。在笔者看来,汉儒的“反经合道为权”实则宋儒说的“变则行权”,宋儒的经权观已经包含了汉儒的观点,宋儒只是不同意汉儒一味地强调“反经合道为权”而已。进一步看,汉、宋两家积淀并构筑了传统经权观,其实质则是经权互隔之说:经是经,权是权;一般情形下只需坚守经的原则性,特殊情形下才需要调动权的灵活性;常人只有守经的本分,行权则是圣贤的专利。一般情形下是否需要权变智慧,常人是否也可以行权,因而成为传统的经权互隔之说与孟子的经权互动之说两者最根本的差异。
传统经权观认为:经、原则性、常态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权、灵活性、变态也是一一对应关系,前者为本,后者为末。它用互隔的眼光看经权,经在特殊情形下不起作用,权在一般情形下不起作用,经、权成了两个东西。孟子承认经是原则性、权是灵活性,但割断了经与常态、权与变态的一一对应关系,并以互动的思维看经权,无论特殊情形还是一般情形之下,经、权都紧密联系在一起,各自起着不同的作用(如表3所示)。

表3 孟子经权观的基本内涵
孟子的经权互动观,尤其从权的角度,激活并敞开了返归于经的温和权慧与背反于经的激进权智之间的互动。特殊情形下,道德实践主体的权变智慧表现为以权抗礼、背反于经的激进权智。这种权变智慧仅仅只是针对于礼乐规范体系中的某个或几个子项,而不是针对于整个礼乐规范体系。小叔子救嫂子、舜不告而娶,其权是对礼经的否定,目的却是更能合乎人道。一般情形下,道德实践主体的权变智慧表现为以权行礼、返归于经的温和权慧。这种权变智慧追求中道,旨在让各种礼乐规矩巧妙地契入人生实践之中。虞人非其招不往、孟子不与右师言,其权则是在他人违背礼经的情形下,自己却坚守礼经。归结起来,对礼经行使否定性的做法,这种权变可谓激进的;对礼经行使肯定性的做法,这种权变可谓温和的。
孟子经权观的解读史上有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以权抗礼、背反于经的激进权智因其曲折激荡,人们往往难以忘怀;以权行礼、返归于经的温和权慧因其平淡无奇,人们通常熟视无睹。其实,从哲学味、故事性看,人们有理由钟情于激进权智;从时代感、社会化看,人们有责任服膺于温和权慧。原因在于:小叔子救嫂子,舜不告而娶,激进权智支付的成本倒是温和的;虞人非其招不往,孟子不与右师言,温和权慧付出的代价却是激进的。如果回到孔孟那个礼乐文明越来越分崩离析的时代,又只能作出惟一抉择,人们就应当选择温和权慧,而不是激进权智!
“反经”一词,《孟子》书中仅仅出现过一次。《河南程氏遗书》卷15《伊川先生语一》云:“中者,只是不偏,偏则不是中。庸只是常。犹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经也。孟子只言反经,中在其间。”①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1册,第160页。我们需要重温这个词的出场语境:礼坏乐崩,政治—伦理生态恶劣,不依礼而行的乡愿之流难辞其咎,孟子为此提出“君子反经而已矣”(14·37)。其意则跟汉儒说的“反经合道为权”截然不同,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小程意义上的“权即是经”;它不是指以权抗礼的背反于经,而是指以权行礼的返归于经。
返归于经既是为了恶乡愿,更是为了人自身。孟子曾说:“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7·2)“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14·5)圣人制作的礼乐规范,为道德实践主体展开伦理生活设定了最基本的规矩。要让规矩真正自由地落实在一己的伦理生活之中,则离不开巧:“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10·1)智好比技巧,圣好比气力。百步之外射箭,射到了,那是气力的结果;射中了,那是技巧的结果。仁、义、礼、知(智)四者,《礼记·丧服四制》认为“权者知也”②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694页。。《中论》卷上《智行》云:“仲尼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孟轲曰:‘子莫执中,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仲尼、孟轲,可谓达于权智之实者也。”③徐幹:《中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第482页。赵纪彬的《〈论语〉“权”字义疏》指出:“‘权’是把原理原则应用于实际,使之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用以观察问题,解决矛盾的方法。这是认识发展的最高阶段。”④赵纪彬著,李慎仪编:《困知二录》,第270页。要返归于经,就得以权行礼,化理论为方法,并见之于行为。一旦以权行礼,“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8·6),人就能栖居于礼乐文明的德性愿景,乡愿之流就不可能再横行于世。
行权,不是圣贤们的专利,而是每一个道德实践主体不可让渡的权利。从权智一体看,“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3·6)。惟其人人可以行权而且必须行权,人们才有可能像尧舜那样成就自身的理想人格,礼乐文明的政治—伦理统制功能才会得到自由地呈现。激进权智的使用范围极其有限,温和权慧的作用空间无边无际;激进权智只是醒目的标志,温和权慧却是普遍的风格。所以,既是以权抗礼更是以权行礼,既是激进权智更是温和权慧,既是背反于经更是返归于经,才写照了孟子“经而权”的伦理智慧,揭示了孟子经权观不同于而且高于传统经权观的所在,彰显了孟子的经权观在传统经权思想史上的独特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