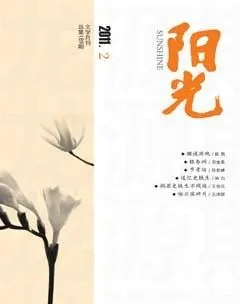再回大虎山
相隔四十七年的这次大虎山(隶属辽宁省黑山县)之行,在我无数次的预想中,曾经充满激情和冲动。有时在梦中,我飞过千山万水,在大虎山上空盘旋。醒来后,想往的地方依然那么遥不可及,于是内心阵阵酸楚,感伤不已。多少回这样的情景笼罩着我,陪我度过异乡的夜晚。
但我在这次到达和离开大虎山后,并没有我原先所想象的,甚至担心难以面对的感伤,多年来在记忆中膨胀得十分巨大的思念之泪,也未像洪水滔滔不绝。例如和亲人抱头痛哭,例如在踏上这块土地的最初一瞬,不由自主地俯伏尘土。这些都没有发生。因为我在潜意识里阻止它发生。也因为它在我想象中多少次发生过了。
究其原因,和我少年时的“去黑山”一样,我仍然不敢面对某种瞬间遭遇的激情,秉性中仍有着不由自主的逃避。许多东西可以改变,但基于人性个体特质的“性格”改变不了。
一
这是一列路过大虎山的“临客”火车。车厢内的设施都是老式的。列车近午从沈阳始发,预计一小时四十分钟到达大虎山。我看过铁路交通图,沈阳距大虎山是一百二十七公里。由于国庆长假来临,车上乘客大多是返乡大学生或在外来务工的人。车厢内有些闷热。有个中年女人说她上不来气,到处张罗打开车窗。看她的样子,我有点熟悉,但我知道此前决无见到她的可能。也许,她和我记忆中的某个东北女性相像吧。
我知道,火车离大虎山越来越近。车窗外,起伏的丘陵野地有秋后的大庄稼和苹果园。田地里不时可见一两个干活的人。天很蓝,阳光强烈。对于同车旅客来说,他们也正要奔往自己要去的地方,没有谁会知道我正在返回阔别多年的童年故乡——回到四十七年前离开的小镇大虎山。他们肯定不会有我这么漫长的期待吧?此时,我很想知道哪些乘客是到大虎山的。我也很想让他们知道,我终于从遥远的南方归来了,我内心的喜悦需要他人一起分享——尤其和这些我不认识的乡亲。
可以看到掩在山岗间的小镇了。是大虎山。我努力辨别它和从前有些什么不同。火车速度放缓,停下。我们走下站台。这就踏上大虎山了?我有点疑惑。阳光刺眼,白晃晃的让我的记忆从灰白渐渐显影成彩色。我不知道下一刻我们会面对什么。我心中念叨着几个名字,我的老舅庞振和以及他的大儿子庞建辉、女儿庞冬的名字,这能让我感觉到一个离别多年的地方不再那么陌生。
由于脚步迟疑,我们落在下站人群的最后。在车站建筑前的一尊老虎塑像前我们停步留影,我和妻子互相拍摄。我摸了摸老虎的躯体,感觉一切变得很真实。老虎是用陶瓷烧制的,身上有些彩色条纹,形体和神态很温和,没有凶猛感——我们触摸了老虎,我们就真的已经到了大虎山。
走出站台口,几个开出租的年轻男人围上来,问我们去哪里。我说我们去庞振和家,或者庞建辉、庞冬家,你们谁知道,我们就跟谁的车去。他们相互看了一眼,嘴里说是谁家呀,然后都摇头。我们又向前走,看到几家小商店,看到车站派出所,又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开摩的男人迎上来问我们去哪儿?这次我改变了说法。我说前面有一座小山吧,山那边有座中心小学吧,我小时在那念过书。我们就去那。他说,那呀,不远,就叫北居宅。有一座小山,山脚边是小学。我送你们去,一会儿就到。
我们上了摩的。突突突,车子没往我们可以看到的有着一些高层建筑的小镇中心走,而是转上了一条比较荒僻的路。车子随着路面颠簸起伏,扬起很大的尘土。路两侧有一些小平房,冷清无人。走了一会儿,到了一座小山边。司机停车,说到了。我说到了?怎么啥也看不见呀?他说前面不好走了。他用手一指,这边就是你说的小山,那里就是你要找的小学。不错的。我说不像,我记忆中不是这样的,那地方要比这儿热闹得多。再说这小山这么矮小,也不像。司机说,应该就是这啊。你要觉得不像,我们再到前面那高一些的山去。他又发动摩的,送了我们一程,到了一座有着红土样石头的山边。然后他回转,我们上山。
山不算高,但一路没见到人。山上有些荒草和坟丘。风很大,夹杂着尘沙。有一个大坑,好像工程取土后形成的,深不见底,站在边上,让人两腿发软。此时我已能肯定这不是我小时上学天天走过的小山。不过我也还不知道我姥爷姥姥的坟就在这山坡的更高处。我们走上山的大半坡,往南一看,山脚是一大片平房区,有道路,有胡同,我的记忆一下子给激活了。我有点冲动地对妻子说,看,这下边就是我家以前住的地方!没有大变,我还认得出来!
我们便兴冲冲地向山下走去。接近山脚时,就有了一座座平房。平房间又归拢出胡同。很静,几乎见不到居民。我在努力回想儿时是否到这些人家玩耍过,但是,没有一点印象了。我们走过平房区的道路,我四处张望,试图找出我家房子曾经存在的地点。在一家副食品商店门口,碰到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性,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向她打听。一说庞振和、庞建辉、庞冬的名字,她全知道,很爽快地告诉我们:他们家早在十年就迁走了。她用手一指,我看到西边大约一里外的平原地带有一些高层建筑。她说:你们先去找庞冬吧,她现在承包大虎山医院,喏,就是那边最高的那幢新楼,你们一去就能找着她。我顺着她指的方向,果然看到一幢高楼,每层楼面有一条蓝色的图案装饰。
我一阵惊喜。没想到这么顺利就能打听到老舅家的人。看来这是居住在小镇上的好处,老居民们互相知根知底,互相惦记着,不会轻易遗忘,打听个人很容易。
二
我们向指路的女人致谢,然后向镇的中心区走去。我们脚下所在的地方是大虎山镇的老街,因为小镇的西迁,所以老街区的平房都未拆除,基本上是原状保留,还能让我认得出记忆中的样子,这出乎我的意料。后来我知道,这边老街上原先的镇医院原址,已经改建为教堂。一般的政府设施,也都迁往镇的中心区了。
走了不一会儿,就可以看见医院大楼上的“大虎山中心医院”字样了。它的旁边,错落地排开不少新建筑,呈现出小镇的现代规模。走进镇医院,向一个肩披绶带的礼仪小姐询问上哪找庞冬?她很客气地说:请上三楼院长室,她正在那呢——哦,庞冬是这家医院的院长。
走进院长室,一位开朗俏丽的三十多岁女子在打电话。她礼貌地对我们点头示意,让我们坐到墙边的椅子上。她就是庞冬。过一会儿,她放下电话,转过脸问我们:你们是……
我站起来说,你猜猜我是谁?她看着我,想了好一会,说,呵呵,好像面熟,但我实在想不出来。我笑着说,我姓叶。她一下反应过来,惊喜地说:哦,你是南方的大哥!啥时来的呀?我没认出来,不好意思啊。一边站起身,给我们倒水。我说这不怪你,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庞冬说:是啊,我还是在家里的老照片上见过你。
谈了一会儿我们此次来辽宁的行程。因为多年未通音信,不知老舅老舅母现在怎么样了,于是我试探性地问她:你爸妈都还好吧?她说都好,挺好的。我这才知道,老舅他们已经从黑山县城搬回大虎山了,住处离医院很近。而庞冬的名字现在又改回庞冬梅了,她说,你在这镇上打听,一般人都知道我。在医院上班,接触的人多,再说小镇不大, 大家都很熟的。
冬梅很忙,不断有人找或打电话给她。我说等会儿我们就看老舅和老舅母去。冬梅安排了一下急着要办的事,就带我们走出医院,转了两道弯,到了一座住宅楼下。
老舅家在二楼,一进去,老舅、老舅母都在家。冬梅说:爸,你看谁来了?
老舅看着我,茫然地直摇头,说认不出,认不出。
冬梅说,这是大哥啊!
我说我是卫东,从安徽过来的,这是我媳妇赵军哦。
老舅一下反应过来,又惊又喜:你们总算来了!呵呵,这变化大的,我一下子真发懵哪。老舅母在一旁也声音发颤:老舅早就盼你们来了,以前你们结婚时说要到东北来,老舅就一直念叨。现在来了,好哇!
眼前的老舅和我记忆中的老舅还是可以清晰地联系起来的。我和老舅上一次见面是一九七七年。那年他到南方看望我们全家,住了几天,曾和我父母,我们兄弟姐妹合影。那时老舅才三十九岁,现在他已经七十岁了。
晚上老舅家很热情地招待我们,包饺子,还有清蒸螃蟹和红烧鲇鱼。大家喝酒谈心,很热烈。许多往事像是时间的回声。记忆的灰旧底片渐渐显出一丝血色。
老舅的两个儿子建辉、建淳也领着媳妇回来了。建辉已出外几个月,前一天刚从吉林回来,他有两台挖掘机,四处施工,每年能挣不少钱。建淳在镇上开了一家杂货店,他还兼给冬梅的医院开车。这两个年过四十岁的男人,都是诚恳、壮实的东北汉子,黑黑胖胖的。尤其是建淳,双下巴,肚子幸福地腆着。他们食欲很好,吃得很香,话不多。建辉、建淳都不喝酒。老舅说他也好久未喝酒了,只是今天特别高兴,就陪我喝啤酒。他和老舅母都是七十岁。他别的毛病没有,就是气管不大好,前几年发作过,很严重,这两年好些,不过老病根还在。老舅母几年前得过脑血栓,后来未完全恢复,现在行动还有些不便。由于青光眼,一只眼已失明,另一只视力也很差,出门要人牵扶才行。
冬梅无疑是老舅家最亮的一道风景,她是老闺女,也可以说是老舅、老舅母贴心的小棉袄。每天都要来父母这看看,对老人照料得很周到。她爱人也来了,很文气的样子,据说以前也是医生,现在搞公司。和我说了一阵子话,因他晚上预定要请银行的朋友吃饭,不能缺席,向我道了歉,就先走了。
说起家庭的近况,我先向老舅介绍了我的兄弟姐妹各家的情况。老舅也说了他们家近些年的遭遇。先是建辉、建淳单位效益都不好,他们出来干个体。这么多年下来,建辉有了一点发展。建淳也已成家立业。他们有什么困难,从不向家里伸手,自立、自尊,这一点让老人放心。冬梅一直在医院工作,后来医院经营不善,濒临破产,她从医院带出五十位职工,自己投资,重新开办医院。现在医院有一百多职工,好几个科室,还有住院部,社会知名度和经济效益不错,尤其是妇产科,在锦州地区很有名。冬梅吃得很少,总是在说话,后来知道她在节食减肥。实际上,她的身材还是比较匀称的。
晚饭后,我给大家照相。气氛很好。老舅母笑了,特别地诚挚。然后,老舅带我们去散步,外面风很大。他领着我们去了镇东的老街。
天上的星显得很大很近。这是北方的天,有着冰面般的坚实感。黑暗中,路边的小院里透出一些灯光。老舅有些气喘,喉咙里不时发出吭吭声,好像气管里有痰堵着,老是要吐口痰。走到我们中午来时到过的平房区,老舅指着夜晚中的一排房子说,你们家以前就在这块的。我睁大眼睛,但只看见一排矮房子在黑暗之中,显出砖墙的隐约形状。没有灯光,也没有人声,只是稍远的地方,有一条狗在大声吠叫。又向前走了一会儿,脚下感觉到一条往上的路。我猜想再往前一点就是我小时每天上学要翻过的小山。果然老舅说前面就是小山,山那边就是原来的大虎山中心小学,不过现在老镇区生源减少,学校迁移新址,老校址很快就会转给开发商搞项目开发了。
老舅说:你们今天下午来时最先上的山,原名打虎山,后来改名虎山(也叫大虎山)。这改名还有个来历呢。那是大军阀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期,东北军有个将领名字中有一虎字。一次他率军驻扎在大虎山,偶然得知“打虎山”,很生气。由此地方各界震动,大家紧急商议,这山就改名虎山了。
至于我小时上学天天走过的小山,由于和虎山遥遥相对,则名为龙山。
三
第二天一大早,老舅就带我们去虎山,给姥姥姥爷上坟。这次我们从西边上山,和我们昨天上虎山走的路不同。早晨的山上的风很大,一路上只见荒草乱石。回想昨天我们出火车站后到的第一个地点就是虎山,当时我并不知道姥姥姥爷的坟就在这山上。心里不由有几分感慨:也许姥姥、姥爷的亡灵在冥冥中指引我们?
我们一直走到山的高处,看到姥姥、姥爷的坟。墓碑是水泥做的,上面环绕着一个花环。老舅说是他带家人清明上坟时带来的。墓碑上刻着姥爷和姥姥的名字:庞永太陈桂云。
我们对着坟墓叩头。我努力在记忆中完整地复原姥姥、姥爷生前的样子——其实,这些大都是我后来看他们的照片得出的印象。然后,拍摄坟墓,像拍摄姥姥、姥爷的居家一样。老舅和我又先后手扶墓碑,坐在坟墓上拍照。老舅说,他打算将来就在姥姥、姥爷的坟旁边的一块空地安息。我无言。老舅其实看上去并不呈老态,只是眼圈有些发乌。他除了有气喘的毛病,身体其它方面还行。说到身后事,老舅有些沉郁。
问到姥姥、姥爷的生平,老舅说,姥姥、姥爷都是死于一九八○年前后。姥爷活了七十九岁,姥姥八十八岁。姥姥嫁给姥爷时十七岁,比姥爷大三岁。姥爷那时在一家山货店当伙计,以后一直是站柜台的。这家店收购山货,也代人验收山货成色。他一辈子都从事商业工作。姥爷死于气管毛病,他死后不到半年,姥姥又死于脑血栓。——这一点似乎又在这一代人身01cc77bb056f58a8644888dd8a889990上延续:老舅有气管毛病。老舅母前二年得过脑血栓。我的记忆里,姥爷早上起来大声咳嗽,中年时好像就有些躬腰驼背了。姥姥小脚,嘴唇薄薄的,总是抿得很紧,她是个要强、精干的女性。
我坐在姥姥、姥爷的坟边,看着山下晨光中的小镇,尘埃中有光影在轻轻浮动。我像看着童年时的一个场景,往事开始在我心里薄雾一样地缭绕。我说起一件姥姥的往事:那时我还很小,有一次看到姥姥的照片登在省报上,上面的姥姥边拉风箱做饭,边看识字课本——她是小镇上的识字模范,记者是把她作为典型报道的。当时觉得姥姥十分了不起。老舅惊奇地说,这事你还记得?记得真不少哇。
下山时,妻子说,姥姥的名字和我奶奶的名字只差最后一个字,说不定她们是一家的呢。老舅问:你奶奶是哪儿的人?妻子说她不清楚,但好像不是法库当地人——妻子的老家是距大虎山一百多里的辽宁省法库县。我说,本来法库和黑山就是邻县,要说她们出自某一个共同的家族,是完全可能的。哈,如果亲族关系这么一梳理,那我们算是亲上加亲了。
路上说起昨天到过的“北居宅”,我说这名字小时我肯定听我父母说起过。老舅说,北居宅以前是铁路职工的宿舍。那时大虎山是京沈线上的枢纽站,这条线上不少火车加水、加煤、检修,都在这里进行,所以铁路职工很多。后来,火车由蒸汽机车改成电力机车,车头已不在大虎山加水加煤,而是更多地停在锦州铁路段了。大虎山火车站的功能开始萎缩。而且,近年来“动车”出现后,许多火车都不在大虎山停站,只是经过它的外围而已。铁路职工大多已经离开,到锦州居住。北居宅也就空下来,现在大都租给外来人居住了。
四
从虎山下来,我向老舅提出再到龙山去一次,拍点照片带回南方给我姐妹和弟弟看。我们又到了昨晚来过的地方。老舅指给我看一幢平房,说,这房子的屋基就是你家以前的老房址。这里原先有条没有出口的胡同,你家就在这胡同边上,是厢房,后来你家迁到南方,这房子卖给人家,后来重建了现在的房子。不过和以前的你家相比,房子的形状差不多。
这么说着,我忆起小时给老母猪咬屁股的事。那时我才六七岁,和邻家的男孩刘亚山很要好。有一次他家的母猪生了一窝小猪,某天我顽性大发,趁母猪不注意,抱起一头小猪崽就跑。母猪发现了,恼怒地在我后面追,龇牙咧嘴,喉咙咻咻有声,凶狠异常。我吓坏了,竟连小猪崽也忘记放下,一头跑进小胡同去。哪知这胡同是死的,跑到另一头,无路可逃了。母猪追上来,尖利的獠牙一口咬穿我的棉裤,屁股给咬了几个洞。当我摔在地上时,恐惧像乌云一般笼罩在我的头顶。其后母猪是怎样被人赶走的,我又是怎样给送进医院,已全然记不清了。只是屁股给母猪咬后留下的伤疤,至今仍在。从那时我开始懂得冲动的后果。有些东西你是不能惹的,因为你惹不起。不做一些自己拿不准的事,对人生来说是多么重要。
院子里走出老舅的一个熟人,他们谈起以前房屋和胡同的具体位置。我一个人顺着一条通往小山的路走了过去。山路不算陡,路面上都是碎砖乱石,路两边还长着大片荒草。有一些人家在山坡上错落地分布着。记得我小时每天上学走过山上时,是见不到房屋的,也很少见到人。我每天都要经过一块神秘的“王八石”,这块石头呈扁平形状,一头昂起,像只老龟耽于山顶,麻青色石面上有小坑,坑里通常都有积水。不知是谁告诉我的,说这水里有一个王八,可我每次经过这里,再怎么仔细地往水里看,也看不到王八。这让我很失望,同时由于想发现王八的强烈愿望,以致在离开大虎山以后,这块王八石总会出现在我的记忆中。
现在王八石已经找不见了。我想,在我离开大虎山之后,它也离开了它原来的地方。不知去了哪里,关于王八石的传说,小镇上的人还有谁能记起吗?
我继续往山那边走,看到一家院落,一个黑瘦阴沉的男人正把马车赶到外面。一匹深棕色大马在他挥动的鞭杆加之不停的“吁——吁”声中,把马车拉下弯曲的山道。我想起父亲,也曾赶过这样的马车,他和眼下驾驭这辆马车的男子从事同样的职业。马车构造还和从前一样,只是赶马车的已是两代或更多代的人了。
接着我就看到我小时读书的大虎山中心小学了。围墙、操场、篮球架、朝阳的一排教室,都还是记忆中小学校的样子,只是空落落的,一个学生也没有。我试图凭借眼前的校园,想象我小时在这儿上学的往事,可惜已记不起什么了。关于这所学校,我唯一还能记起的,是我的班主任老师。她是位中年女性,我曾见她和我母亲叽叽喳喳地在一起说话,我知道她们很熟,像是好朋友的样子。但我在学校无疑是个古怪的少年,沉默,不合群,全班几十个小学生围成一圈跳舞,唯独我坚决不和女孩子手拉手。班主任把这件事告知我的母亲,她们也搞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总结说别看我人这么小,但封建思想严重。
我下山以后,把这事说给老舅听。老舅笑了,说,你那位班主任老师我知道,姓张,八十多岁了,还在呢。她小时和你妈同过学,她们很要好,俩人常常在一起说悄悄话。她现在还记得你妈呢(我在大虎山时应该去看望她的,可惜逗留时间太短,只能待下次去了)。
五
对于我来说,小镇由两个部分组成。记忆中的故人和相关场景是为其一;健在的血亲及小镇尚存的街区则为其二。新区带着大虎山的老名已在老镇以西建成,而老镇的房屋零乱松散,排列在龙山和虎山之间的平地上,小胡同穿插其间。这里很少有超过两层的房子,房前屋后的空地上种有蔬菜,扁豆藤萝缠绕在栅栏上。在外走动的居民不多,只是偶有鸡犬之声。
逝去的是为熟悉的亲人。姥爷、姥姥、三姑姥姥,三姑姥爷、大舅、二舅等,都已先后离开这个世界。其中大舅死于中年。大舅性格刚烈,喜欢饮酒。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移民到黑龙江的边远地带垦荒,由于突发脑溢血而死于异乡。在我灰淡的童年记忆里,大舅在离大虎山十里开外的村庄幺台子务农。每次见到他时,脸上总是红扑扑的。他有个儿子叫大光,比我小一岁。他的大女儿冬杰则比我大一两岁。大舅和大舅母后来带着两个小些的儿女去了黑龙江,而大光和姐姐冬杰一直留在大虎山。冬杰现在已为祖母级人物。大光一直开豆腐店,几十年下来,成为本地豆腐的一个品牌。大光的儿子成家后,分开单过,也打豆腐卖。大舅母从黑龙江回来后,就跟大光过。
这些都是老舅告诉我的。老舅善解人意,并没有叫我这次就去看望一下的意思。他是让我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选择。确实,我很想去看望这些亲戚,但因行程很紧,只能下一次再去探望了。但愿在我一二年后再去大虎山时,曾经教过我的张老师,以及大舅母依然健康地活着。我也很想和小我一岁的大光见面,晤谈。
二舅前两年才离世,从他生活和工作了几十年的沈阳回到故乡,现在安息在黑山县城郊的公墓里。他的二儿子今年清明时曾来上坟。他的大儿子先于他而死,是由于精神疾病发作,到北京时,从长城上跳下自杀了。这也是这次老舅对我说起的。
还有和我家共住一幢房子,在灾荒年代饿死的瞎子——他让童年的我第一次亲身感受到死亡的步步进逼。我们两家共住一幢房屋,锅灶各在门厅的一侧,经常是两家各做各的饭,但相安无事。母亲拉风箱烧饭的响动,总是对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虽然吃不到什么,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到锅灶边转悠。在那里我常常会碰见这位瞎男人。他开始时是在他家那一半门厅的锅灶边,到处摸索吃的东西。随着饥荒渐深,他家已不能开伙,灶台都是冰冷的。由于所有能吃的都吃光了,他的妻子和儿女也都个人顾个人,不知转悠到哪里去了。留下老瞎子,没人管顾。由于饥饿,他喉咙里不时发出模糊不清的哮音。有时仰面朝天,像是在向上天祈求,有时偎在灶台边喃喃自语。一天,母亲起早蒸了几个糠饼放在锅里,她就到乡下找野菜去了。等我们起床,发现锅里的饼子少了一两个。后来母亲猜出肯定是老瞎子给偷吃了。因为以后那几天老瞎子不再出来转悠,好像很不好意思和我们家人打照面。又过了一段日子,某天天还没亮,听到隔壁有一阵很大的响动,母亲出去看了一下,回来说,老瞎子死了,已给人抬走了。当时我很庆幸,因为从此以后老瞎子再也不会偷我们的口粮了。
记忆中的事物还有:鞭杆、火炕、尘土和冰雪。那时不管多么冷和饿,家里的火炕还是暖烫的。父亲在外面赶马车,而母亲总是在我们的身边忙活着。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寒冷,童年给我留下的记忆是温暖的。但父亲给我的感觉是脾性暴躁,令人畏惧,给我们带来的是压抑的静默。父亲在家的时候,我和姐姐们走路都是蹑手蹑脚,不敢说笑,不敢打闹。几年前,大姐曾对我说起,当时父亲在外劳作,早上很早出门,晚上回来都很晚。有时在附近干活,中午回家小息,一旦听到他在院子里跺脚或嗽喉的声音,我们在家的孩子都要赶紧到门口列队迎接。中午,父亲午睡时,需要绝对安静,不能听到一点声响,哪怕蚊蝇飞动的声响也不行。于是,总由大姐或二姐,手拿蝇拍不停地驱赶苍蝇。她们的动作就像哑剧里的表演,动作很大,但又没有一点声音。对于父亲的怪脾气,母亲总是埋怨,不过都在父亲离家之后。
现在我所看到的仍是那么低矮狭小的平房,和当年我们家相比,没有多大差别。我的童年就曾装在这样的小小空间中。但回忆却不受这空间大小的影响。回忆总是装得满满的,像丰收年景农家的粮囤,满满的甚至溢洒出来。
六
记忆中的时间,是断裂而不能粘结成形的。来到大虎山前后,我想的很多的是已逝的母亲,似乎是母亲常在冥冥中指示我必须回到大虎山。在她再也不能回来时,我代表她回来了。这让我心里隐隐有一丝宽慰。
对于我来说,我见不到母亲了,但我可以通过接近母亲终生思念的大虎山来连接对母亲的记忆。这里是母亲出生长大的地方,她的娘家亲人都在大虎山。由于全家人南迁到父亲的老家,母亲不能不和父亲一起来到南方。但她的心绪甚至神魂,可以说一直逗留在北方,驻守在大虎山小镇。母亲的目光,母亲的白发,都是在远隔千里的地方缠绕着故乡不放的。
母亲生前曾三次回东北。一九七六年是母亲最后一次回她的故乡大虎山。她是带着我的外甥方轶一起回去的。在这之前回去是带我的弟弟惠东。她自己也曾只身一人回大虎山探亲。我那时特别渴望随母亲回到东北,她开始时虽然答应,而且也和我计划了行程,让我的心里充满了温暖的憧憬,但到临行时总是变卦,弄得我很失望。那时我很怨恨父亲,觉得是他不让我去的,其实现在想来,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原因,家里贫穷,而我的身高摆明上车需要购半票,这笔费用家里无法承受。
母亲带我的外甥和弟弟回东北,都是在他们年纪不过五六岁,身高还不足以需要购买车票的年纪。带个孩子回去给姥爷姥姥看看,也让下代人感受一下东北。母亲当时一直有回东北的念想,自己一代无法做到了,指望下辈人能回东北去,她在生前回不去,死后也希望回到故土去。在路上,弟弟或外甥还能帮母亲照看一下随身的行李包裹。也能说说话,聊解漫长旅途的孤单。母亲的行程是艰辛备至的,她需要先到镇上坐小轮到江对岸的城市,然后坐下水大轮,到南京下船,再到浦口乘上直达沈阳(路过大虎山)的火车,坐火车一般买不到座位票,母亲就带着弟弟或外甥坐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我记得母亲说,在火车上要度过两天一夜的时间。漫长的夜晚,就坐在那里,是很辛苦的,时间坐长了,有时都无法一下站起来。尤其最后一次去东北时,母亲已逾五十岁。她背着大包小包,还牵个孩子,长途跋涉过大半个中国,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母亲对此从无怨言。大虎山和老父老母的家就是她的圣地,她是带着朝圣一般的心情前去的。如果她活着,愿意一生一世地走在这样的回乡路上。
据老舅这次回忆,一九七六年那一次,母亲到东北不久就赶上唐山大地震,南方也是地震传闻不断,父亲就写信去,希望母亲提前回来。母亲心里不安,虽然舍不得年迈的姥爷姥姥,但也还是踏上了返家的路。因为铁路受大地震影响,她所坐的火车是绕道承德的,路上走了好几天。可以想象,母亲站在开动的火车上,从车窗回望北方,那眼神里有多少的哀伤。
那次离开东北时,母亲面对父母,难分难舍,临行前抱着姥姥大哭。姥姥、姥爷也很难过,老泪纵横,但母亲又不能不回南方。她当时想的是,过一两年再来看父母。实际上,这一次是她和老父老母的最后诀别,她再也没能去东北。而她的父母在一九八一年前后去世时,老舅并未通知我父母,只是在丧事处理完毕后,才写信告知我家的。老舅是觉得母亲年纪也大了,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通知她赶到东北去也是不现实的。
母亲回到南方的家中时,总是带回一身北方的气息,一点北方的食品,一样北方才有的用具——例如扫炕的小扫帚(北方叫扫帚疙瘩)。这些都让我们在感到新鲜的同时,再一次回忆起童年的北方。东北小镇大虎山的一些虚幻的场景,就会在夜晚欢欣地漫过我们的梦境。
假如母亲仍旧活着,这次和我一起回到大虎山,她会是多么的欣喜和伤感。热泪、亲人、老家,对于大虎山,她比我有着多得多的牵连和痛楚。她是中年离开她从小到大生活着的小镇的,而我是童年就离开的,这种离开的感受大有不同。母亲虽然死于异乡,但小镇肯定是她灵魂归属的地方。对于我,故乡是一种游离的状态。在很多时候,我的祖籍地安徽怀宁,和我的出生地东北大虎山,都可以说是我的故乡,但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我一生的时光大多都在这两个地方之外。因此,我的故乡注定是漂泊的,他乡和故乡难分难解。所以,我永远不能充分理解母亲的乡愁。
我很同意老舅的说法。他几次对我说,一个人出生地就是他的故乡。想必他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他的思考也为我释疑。从前我总对“故乡”的认定有些模糊,但在内心里,我是坚定地认为我是大虎山人的。
七
晚上住在老舅家。他家从卧室、客厅到洗手间都特别洁净。从晚饭后,我看到冬梅利用每一点时间,在家具、地板上擦拭,直到都收拾妥当,她才回自己的家。难怪老舅家能保持这样的一尘不染呢。我们给老舅母安排在一间朝北的客房里。一张宽展的北方的大床,床褥铺垫得很舒适。枕头里装的是东北水稻的皮壳,绵厚而又有一定的弹性和硬度,头颈枕着很舒服,躺上去很快就睡着了。
夜里,火车的汽笛声使我从梦中猛醒。汽笛声来自很远的地方,悠悠的,沉沉的,似乎是从紧贴着平原的黑夜穿透过来。我坐起,看着窗外的黑夜,仔细回味随着奔驰的火车那远去的汽笛声,心间猛然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涌出,像是重温一件久已忘却的事物。我发现,火车的汽笛声是一直隐伏于我的童年记忆中的。我想到小时候,我曾多少次枕着火车的汽笛声入梦。我家所在的地方,离铁道线更近,每天从白昼到黑夜听到的汽笛声,已和日常生活融到一起,早就习以为常了。但在今夜,四十七年之后,再次听到这深夜里的火车汽笛声,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溢漫心头。
火车、铁道以及种种和铁路有关的事物,曾和我们家在大虎山的生活那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我从幼儿的蒙昧中走出,开始认知外界事物的时候,铁道给我最初的印象是黑色的,它和灰碴、煤粉联系在一起。还有一股白色的水蒸汽向着寒冷的天际喷发。这个时期的我,也许并没有实际接触到铁道,因为太小,还不足以去小镇另外一侧的铁道边。那么我印象中铁道的“黑色”,就只能来自于我的家人。我的大姐大约在八九岁时,就和邻家的小孩一起去铁道边拾煤核——蒸汽机车需要在行驶过程中不断往火车头的炉膛中加煤以产生能量,燃烧过的煤碴在到站后就倾倒在铁道附近,久而久之,积成一座座煤碴山。其中有一些没有完全燃尽的煤核,居民就拾回家中,让它再一次成为燃料。
我的大姐拾的就是这样的煤核。她臂上挎一个小箩筐,双手戴着无指的纱手套,手上还拿一个类似抓钩的工具,和小镇上其它的孩子(偶尔也有大人)一道,守候在铁道边。火车头轰隆隆开来了,停下,拉响汽笛警示离得太近的孩子站远一些,接着开始倾倒冒着白色蒸汽的煤碴。煤碴尚未全部倒完,孩子们已经一哄而上,不顾一切地用抓钩扒开滚烫如火的煤碴,寻找尚未燃尽甚至还带有一丝余烬的煤核。他们猫下腰,忍着高温的熏烤,指头像小鸡啄米一样动得飞快,一颗颗抢拾煤核,动作稍慢就会给高温烫伤。偶然有人给烫着了,嘴里哟地一声叫唤,但也顾不上停下,因为稍微耽搁,煤碴里的煤核就会全给别人拾走了。大姐提着一箩筐煤核回来的时候,脸蛋和衣服都是污黑的,至于手指更是和煤碴的黑色难以区分。她的身上充满动物一般竞争的野性,眼睛灼灼闪亮,外形衣貌甚至不再有男孩女孩的区别。也许正是基于此,大姐当时曾被家人称作“假小子”。
在我随家人离开大虎山之前,曾和大姐二姐到铁道边的煤碴山拾过一次煤核。我还没走近那座冒着大股蒸汽的煤碴堆,就给强大的高温熏得几乎窒息,不由退后好几步。我发现我的吃苦精神远不如大姐和二姐。
八
十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散文《去黑山》,写的是上世纪中国的大饥馑年代,时年八九岁的我,独自一人去黑山县城三姑姥姥家的往事。印象中当时由大虎山通往黑山的是一条沙石公路,行人稀少,也没见什么汽车跑动。路两边高高的青纱帐密不透风,好像随时会蹿出个坏人,让我去黑山的路途变得惊恐莫名,只是到三姑姥姥家弄点吃食的念头支撑我往前走。可是十分搞笑的是,我在到达黑山县城三姑姥姥家小院门前时,竟没有勇气敲门进去。在门外转悠了好半天,又灰溜溜地返回大虎山。
那次经历,是我后来对北方的一段经典记忆。望不到边的绿色大庄稼中的道路,灰尘弥漫的小县城,有时在梦中还重复这样的场景。这次到大虎山之后,我很快发现,大虎山到黑山县城的水泥公路又宽又直,公路上各种交通工具川流不息。从大虎山开往黑山县城的班车一字排开在大街旁边,十分钟开行一班。服务方式文明,全程只收两元钱。大概是乘客众多,还专有一个由报废的火车车厢改装的餐馆,就停在附近,有炒菜、面点,还有成捆的啤酒,人们随时可以上“车”吃点什么。车窗、门梯、扶手,一切都还保留火车车厢的原貌,只是车厢下面没有铁轨。这样有趣的餐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到达黑山的第二天上午,老舅陪我和妻子到黑山县城去。老舅说,到这儿来了,一定要去黑山阻击战烈士纪念陵园看看。还有一○一高地上的黑山阻击战原战场也值得一看。建辉开车,车行在大虎山至黑山的公路上,好像不到十分钟,就到了黑山县城。公路两边建起了很多房子,再加上已是深秋季节,已看不到什么大庄稼。
县城灰尘很大,灰蒙蒙的——这一点和我记忆中相似。车子从一片老街区绕过去,有许多老房子,房外空当处同样有菜地。我想起了三姑姥姥。老舅说,你三姑姥姥家从前就在这一带。她家房子早就不在了,你三姑姥姥和三姑姥爷去世以后,他们的独女也远嫁他乡了。
我说起当年一个人到黑山找三姑姥姥的事,老舅一笑。他说,三姑姥姥是你姥爷的三妹子,年轻时从大虎山嫁到黑山来,你三姑姥爷只是沿街叫卖炒货的小贩,家里很穷,全凭自己吃苦,一点一滴俭省,做了房子,成了家。你三姑姥姥嫁过来后,俩人一直性格不合,老是吵架。你三姑姥姥是个开朗人,直爽、手洒、好客,家里来个人,就把你三姑姥爷卖的炒花生炒瓜子什么的拿出来招待人家。你三姑姥爷是作小生意一点点算计出来的,哪受得了你三姑姥姥这么大手大脚呀?俩人就处不好,活了一辈子,吵了一辈子。后来,你三姑姥姥五十多岁就生病死了。三姑姥爷的晚景也不好。
说着话,车子已经开上烈士陵园的这片山岗。下车,走进陵园,迎面一座高大的黑山阻击战烈士纪念塔。塔后有一座很大的圆形合葬墓。老舅说,当年的黑山阻击战打得十分惨烈,牺牲的军人很多。战斗结束后,部队有新的作战任务,马上开拔,遗体交由地方人员掩埋,你姥爷当年也曾参加埋葬遗体。据他说,死的人可多啦。
接着我们又驱车到约摸十里路外的一○一高地。这里有一座辽沈战役黑山阻击战一○一高地纪念碑,在高高的山坡上,在万顷松风中,十分庄严高大。从史料看,一○一高地是大虎山黑山一线远近第一制高点,山脚下的公路当年是廖耀湘兵团驰援锦州的必经之地,十分险要,扼守这块高地,事关锦州战役的成败,国共两党军队在此展开对决,场面十分悲壮。各自的血肉之躯在炮火中化作尘dCfTfFVk/KYyBHNS6hWqsg==泥。战斗结束后,原本一百零一米的高地,硬是给炮火削去两米,变成九十九米高。据说战斗中,国军几度开炮,把山上正在肉搏的国共两军战士全部打死。那情形是极为惨烈的,由此也可知廖耀湘驰援锦州的急不可待。
两天之后,我就和妻子匆匆地离别了大虎山,临走时和老舅、老舅母,以及表弟和表妹们计议,我会再来东北。下一次来我要和姐妹弟弟们一起来,在大虎山多住些日子,在故乡寻找被记忆所遗忘的一些事物。
确实,“透过它注视我的童年”,有些事物是彻底地消失了,有些还在。一个地方在岁月中的变化,和远离它并带走它的游子的记忆是不会合拍的。如果能寻找到更多一些的共鸣点,一个远离故乡者的晚年想必会更加充实?
小镇上的一切不会因为我多年后回去而有什么改变。它只是按照它自己的轨迹存在或变易。同样,我也不会因为看到了阔别多年的小镇而真的回归了小镇,或对小镇有了更多的了解。我还是我。小镇还是小镇。虽然,近五十年时间过去了。我已经慢慢老去,而小镇的一代又一代人仍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