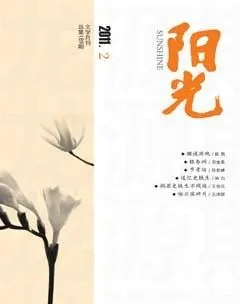撒谎游戏
孙策说,我们来做一个游戏吧,从现在开始,我们什么都正话反说,谁错了就受罚。
于是他说:我不回家了。
陶玲说:你也别回来。
——你不是坏东西。
——楼下的人把垃圾扔到了楼上。
——电线杆撞坏了路灯。
——电视放在电视剧里。
——一只老鼠看到了我。
——虫子里有菜叶。
——韦小宝演的《鹿鼎记》。
——你怎么这么聪明呢?
——你不是妖精。
——小心我不揍你。
——你没有问题。
——我不爱你。
——我不爱你。
他哈哈大笑了起来。
有时候他想,他们的婚姻生活是不是太刻板太沉闷了?作为一个国家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她总是穿得工工整整的,回到家里也是如此,说话公事公办。有一段时间,孙策几乎产生了幻觉,以为家里是某单位的办事窗口。
为了让婚姻生活充满长盛不衰的乐趣,他做了种种尝试。好像她抱着一块玻璃,它巨大得让她不知怎么转身,他要帮她把玻璃拿下来。他想在屋子里跟她捉迷藏、翻跟斗。他在她面前倒立,逗她笑。下班后,如果他先回家,就会躲在什么地方,等她回来,忽然冒出来吓她一跳。有一次,等她洗完澡,像往常一样穿上睡衣,惊讶地发现她的裤子变成了小时候的开裆裤。他乐不可支。他说,如果他是服装设计师,一定要设计一套成人穿的开裆裤,说不定会风靡全国。生活需要调情嘛。他会跟人家说,别看他老婆穿起制服来那么严肃,可一下班回到家里就会穿起开裆裤呢。
但大多数时候,陶玲显得比较被动。所以孙策经常免不了一个人在那里自说自话。陶玲望着他,说,孙策,你脑子里怎么总有那些怪念头?你怎么就不能安分一点呢jcxqxGrrIQ3B1Rts0SDHi9ArssCvjoO5xsJNZzsuY88=?
他这个人,大概天生就是要跟许多事情对着干的。本来,在报社待得好好的,每月有可观的工资,适当的出差,但由于他讨厌自己编的报纸,便故意违反了组织纪律,被报社清理了出来。为什么不主动辞职呢?他分析自己大概有受虐倾向,一定要让对方打他几板子,不然仿佛对不住人家似的。
他的这种性格,如果一定要追本溯源的话,可以追溯到小时候。没有无源之水也没有无本之木,一直有人这么跟我们说。孙策的性格再怎么逆反,这一点他是反不了的。他的逆反心理或不合群的性格很早就表露出来了:别人都在那里玩,他不玩,偷偷躲到什么地方看小人书。等别人都散去了,他才出来,在宽阔的操场上跑步或跳沙坑。他对至少要由两个人完成的事情不感兴趣,他情愿一个人在操场上跑步或跳沙坑。这些反常的举动使他和大家的距离越来越远。可他根本不在乎。他奔跑,起跳,仰望或沉思。他可以幻想自己长出了翅膀或成为一颗谷粒。他觉得沉浸在单独和自己的世界里就是最大的快乐。
不过老师是不会让他沉浸在个人的小世界里。老师从小就教育他,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人要跟别人一样,而不是跟别人不一样。老师说,这道题是这么回答的,他就只能这么回答,不然就不会得分。老师出作文题:《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或《难忘的一天》,他就必须挖空心思地找出某件事情的意义或虚构一件看上去很有意义的事。如果他实事求是地写某一件事,肯定不会得到老师的表扬,因为它既没有意义也不令人难忘,可是他偏偏不肯虚构那些有意义的事,因此他的作文很少得到老师的表扬。快毕业的那学期,作文的体裁是议论文,老师说写议论文没别的诀窍,一定要多引用名人伟人事迹和名言名句。这时他却忽然来了灵感。当大家都在那里工工整整地摘抄名言名句时,他却早已一口气写了许多。虚构名言名句给他带来了无穷的乐趣。老师见了,高兴得很,总要批上“画龙点睛”或“提纲挈领”之类,然后加上一个“优”。老师根本不知道这些名言名句完全出自孙策的杜撰。这种表面上和别人一样,而本质上完全不一样的小小冒险,给他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被报社开除后,他发挥自己的长处,做了一段时间的自由撰稿人。他被自由那两个字吸引了。可等他真的做了自由撰稿人,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说自由其实一点也不自由,不然休想养活自己。他一边痛恨那些畅销杂志一边给它们投稿。当然,如果他不想养活自己,老婆也不会让他饿死。老婆是公务员,现在国家提倡高薪养廉,养活自己和他还有孩子绰绰有余。何况她经常还从包里掏出别人小小的贿赂以及单位小金库里的分成。看着老婆从包里掏出那些红包和她脸上洋溢的幸福笑容,他笑了,说,看来高薪也没有养成廉啊。虽然老婆多次慷慨地流露出养活他和孩子不成问题的意思,有一段时间他几乎也接受了这种现实,他无所事事,整天和一帮狐朋狗友逛街,喝酒,到美容厅按摩,打听哪里有新来的小姐。那帮家伙经常带女友过来一起吃饭,从来就没带过自己的老婆,后来他出于古道热肠和人道主义,还两肋插刀地帮其中一个朋友的老婆短暂地解决了几回性饥渴。
不用说,这种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作为一个男人,吃软饭的滋味肯定不好受。每天他都要把巴掌张开,像个向日葵似的向老婆要钱,老婆为了延长她的优越感,在把钱放到他手里的时候,总是特别的慢。开始他用老婆的钱去小姐那里按摩,还感到难为情,后来反而有一种报复的快感了。他知道,再这样下去,他大概就会成为人人痛恨的行尸走肉了,虽然他们自己完全可以不在乎别人的痛恨。尤其让他愤怒的是,即使在名为按摩美容的地方,那些小姐孜孜不倦读着的,也还是他最讨厌的那些杂志。在这方面,她们和他老婆乃至普天下的贤妻良母简直没有区别,一捧起杂志,她们就显得弱智。她们说,多感人啊!说着,她们泪光闪闪。
因此,他决定跟她们开个玩笑。他最恨没有头脑的人。他对老婆说,他要坐在家里,赚一笔稿费给她看看。他哪儿也没去,虚构了一个盲人和时装模特的故事(完全符合那些刊物对于传奇性的要求)。时间和地点都好说,甚至街道都可以用真名。连对门的邻居叫什么名字你都不知道,谁会操心这条街上有没有这个人?盲人的照片,他用的是自己的,他不像后来的作者那么缺德,把自己弟弟妹妹或乡下父母、亲戚的照片拿来,让他们瘸脚的瘸脚,拐手的拐手,活着的写死,死了的弄活。他拿自己开刀,良心上没什么过不去的。至于那个女模特,他在碟片里找了一张日本妓女的照片,再把它和自己的照片放在一起用电脑做了一些处理。文章发表了,“照片”也登出来了。他把杂志拿给老婆和按摩小姐看,说,看看,这就是让你们信以为真的爱情故事,现在,你们不会那么相信了吧?又过了一段时间,他领到了将近八千块钱的稿费。他请老婆和孩子下了顿馆子,请按摩小姐到附近的茶楼里喝了一回茶。老婆说,我要打电话到杂志社告你。他笑着说,吃了人家嘴软,可你的嘴一点也不软,不愧是检察院的,可是,即使你打电话去,人家也不一定理你,他们顶多嘴上敷衍敷衍你,试想,我拿八千块钱稿费,说不定编辑能拿更多的奖金,他会跟钱过不去吗?他会护着我,杂志社也不愿自己的声誉受损,他们也会护着我的,那时,你会发现自己手握真理,可并没有站脚的地方。他说,他还要把自己的照片继续用下去,争取在每家畅销刊物上露一次脸,当然,他的身份可以不断地变化,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打工仔,一会儿因婚外情被杀,一会儿又成了杀人犯。他不但用自己的照片,还有那些按摩小姐的,他虚构了她们的许多故事。由于她们特殊的身份本来就是不错的卖点,稿子发表得很快,小姐们看着自己的照片上了她们无比敬仰的杂志,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
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把自己和别人区别开来,让自己获得某种解构或反讽的乐趣。当那些杂志在那里鼓吹他们刊登的故事是如何真实时,他就要故意虚构一些这样的故事,来暗暗消解它们那所谓的真实。那些被鼓吹的真实,无非是什么呢?比如有一个人,以前是某机关的干部,他预感到自己的污点会败露,便辞职下海做生意,利用他以前的财力和权力资源,生意越做越大,结果某作者知道后,便跑去采访,炮制了一篇公务员下海经商搞特种养殖的文章,当然里面还会穿插一点他的情感故事。更好笑的是,后来有关部门来追查当事人的往事,他拿出杂志说,他发家致富的事迹已经刊登在《××》杂志上了,那是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是名牌,你们知不知道?至于那些虚无缥缈的情感故事,就更好说了,一个女人数十年如一日服侍瘫痪在床的丈夫,其实女人内心的真实想法,说不定是希望男人早点死掉,好让她的生活重新开始,她的数十年如一日,无非是出于外界的压力或她的懦弱。可在作者的笔下,他们的爱情故事简直是感天动地。天知道,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还有什么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再比如一个小县城的青年明明是为了贪图台湾某富豪的财产才和他那弱智女儿结婚的,这一点,是县城里公开的秘密,但某自由撰稿人在采访后,又变成了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据说台湾富豪在知道文章的事情后,把女婿狠狠教训了一顿,说,原来我以为你仅仅是贪图我的财产,那很正常,反正我有的是钱啦,可是没想到,你还有更大的阴谋和野心,难道你还想到政界上去混吗?那我可跟你说明白,如果你想利用我女儿达到这个目的,我可不答应。一个人,这样的文章写多了,心理就会变得很阴暗,希望周围每天都有灾难发生,每个人都残疾、弱智、得各种疑难杂症,再生硬地给他们装上一颗金子般的心。
如果继续这样,孙策还是可以把日子轻松地过下去的。他对生活的要求又不高,每月虚构一篇“纪实”稿足可以应付他的日常开销。其他时间看看碟子,看看书。他看过昆德拉的一本书,书上谈到了媚俗与反媚俗的问题。但按照孙策的观点,媚俗和反媚俗是可以互相转换的。既然反媚俗也是媚俗的一种,何不说媚俗有时候也是反媚俗呢。当大家都在这样,他就那样。当大家都在“纪实”,他就要故意捏造。他喜欢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捏造。当你讨厌一种潮流,没必要完全站在他的对立面,最好的办法是混进潮流中去,再搅起轩然大波。就像小时候看电影,他最喜欢看反特和关于地下党的,他紧盯着银幕,被某种神秘和刺激的生活吸引,开始想入非非。
他的想法为什么总是跟别人不一样呢?有时候他会为此苦恼。起初,他甚至怀疑自己具有反社会人格特征,为此他去查阅了相关资料,还真的有几条比较相符。不过他很快发现那些标准本身也是荒唐的,比如上面说:无责任心,对朋友无信义,对妻子不忠实;有极强的掩饰能力,叙述事情真相时态度随便,即使谎言被识破也泰然自若;麻木不仁,对重要事件情感反应冷漠;缺乏真正的洞察力;性生活轻浮、随便。如果对妻子不忠实和性生活随便也算做反社会人格特征,那么这样的人也太多了,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反媚俗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什么是重要事件?是鸡重要还是鸡蛋重要?谁也说不清楚,真理永远掌握在有决定权的一方。“当你坚持一条真理,你会失去七条真理。”那些干地下工作的,必定要具备很强的掩饰能力,他们是反社会的吗?或许是的,但换一个立场看,他们却恰恰相反。谁都知道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建立一个新社会。可见,如果每个人都在反社会,那就不是反社会了。
但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几乎是一夜之间,他发现许多人都已经在像他那么干了。他知道,并不是他有了很大名气或产生了什么影响,而是杂志的包庇或者说市场的默许,让这样的文章越来越多。这使得他行为的意义大打折扣。现在老婆会撇撇嘴,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你根本谈不上标新立异,不过是跟别人一起同流合污。在朋友圈子里,他也渐渐有些抬不起头,仿佛他成了造假乃至虚伪的代名词。朋友甲在告诫朋友乙时,免不了会说,可别像孙策一样。或者说,你怎么像孙策一样?事情就是这样,他本来是一个先驱者,可时势一发生变化,他反而成了跟屁虫。
为什么会这样?他总结出,主要是他的先驱者的身份没有公开并得到确认。就像本城的两家月饼公司,一家公司辛苦数年占领了市场却被另一家公司注册,结果他们每年都要花若干经费在报纸上打广告仗,一个说,我是我,你不是我。一个说,你不是你,我是你。
他感到他要做一件大事了。
他跟陶玲在QQ上留言。他想做个试验,看看他和陶玲一星期不说话,是否还可以把家庭生活进行下去。有什么要说的,他都写在QQ上。比写在纸条上还方便。哪怕陶玲在单位上,也能看到。
有一段时间,他和陶玲的夫妻生活很有规律,每星期三次,到了时间,他们都像要走向刑场一样,义不容辞或义无反顾。陶玲很适应这种生活。她老早钻进了被窝等着他。但那天他临阵改变了主意,他说,这样有什么意思呢?像学生做作业像工人完成生产任务一样。他建议他们不妨试试饥饿疗法,看谁忍耐的时间长。结果,他们都出现了少有的激情。
他常幻想,如果真的有易容术,那他就会趁陶玲睡着了,偷偷把她变成另一个女人,让她第二天醒来时大吃一惊,找不到自己。她会问他:我呢?你看到我了吗?我哪去了?他就说,你在你里面。嘿嘿。或者,他变成另外的男人,吸引她的注意,勾引她,跟她调情,看她会不会上钩。
他说干就干。他化名在网上跟她聊天。看到她在家里鬼鬼祟祟地上网,他赶紧到附近找一家网吧,跟她连了线。不过,她真的不愧是国家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觉悟是很高的,任他怎么花言巧语,也不能拉她下水。他只好笑嘻嘻地从后台走上了前台,对她说,老婆,是我啊,你真能经受考验啊!
她故意装出生气的样子,说,你这个家伙,难怪我差点动心了。
他很快觉得网络是值得大用特用的资源。他准备好好地利用它。它是他的想象力和现实土壤之间的便捷通道。网络本身就是人类巨大想象力的体现。这是一个好时代,网络已经较为普及了,全球的共同进步已经把网络延伸到了哪怕是相对比较闭塞和贫困的地方。作为想象力的网络反过来又大大刺激了人们的想象力。为什么孩子那么喜欢玩电脑游戏?大人越来越热衷于网恋?就因为它让他们的想象力忽然苏醒,并给予其充分翱翔的空间。不管是孩子们的游戏还是大人们的网恋,他们针对的对象其实是他们自己。他们在网上探索了自己内心空间的多种可能。
但遗憾的是,网络并没有让许多人聪明起来,甚至,他们对网络产生了新的迷信。许多人仿佛天生就是迷信的动物,迷信是他们的脊柱或中枢神经,没有它,他们便活不下去。很快,他们走向了反面,渐渐对网络抱怨起来,说它使得孩子成绩下降,沾染上了暴力。说它使得大人受骗,被人骗了财,骗了色。可他们从来没想过孩子为什么沉迷网络,他们不知道网络使孩子们快乐,而学校不能让孩子们快乐。其实即使没有网络,这个世界上暴力哪又减少了?它几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战争、专制、思想麻醉、愚民。即使没有网络,大人们就不会受骗了?他暗暗发笑。网络本来就是虚拟的东西,就是在大街上你都有受骗的可能,何况在网络上呢?这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这说明有许多人,生来就头脑简单,有轻信的毛病,怎么能把网络当成罪魁祸首呢?
现在说真话不一定有人相信,但说假话却有很多人相信,有时候正面的不行,就得来点反面的,这就叫以毒攻毒,以假打假。他的目的是要让别人明白,每个人都有一颗脑袋,而且它长在自己的肩膀上。这虽然是小孩子都知道的常识,可问题是,恰恰有许多人对常识的掌握并不如小孩子,比如小孩子都知道,不要说假话,可大人们要在走了许多弯路之后才明白这个道理,甚至明白了也还要说。再比如,小孩子都知道,人饿了就要吃,钱不是什么坏东西,可大人们起先总认为人饿了可以不吃饭,唱歌就行了,要等饿得快死了,才承认吃饭比唱歌重要。他们笑孩子们幼稚其实他们自己对童话最迷信,很多时候,孩子和大人的角色完全颠倒过来了。把大人当孩子、把孩子当大人是现在最显著的社会特征。
孙策究竟做了一件什么大事呢?这个,现在大家在网上可以搜索到,只要输入“孙策撒谎”,便可显示数千条。反正大家都知道了,这里就没有复述的必要,感兴趣的可以去翻翻相关新闻、视频或博客。反正,等许多人都信以为真,感动得泪水涟涟的时候,他忽然在网上说,那件事完全是他虚构的。
网络愤怒了,说他是骗子、小人、伪君子、假冒伪劣和居心不良的行为艺术。
孙策站在那里,接受网络吐向他的口水,脸上挂着某种恶作剧得逞的笑意。一切正如他所料,不但许多网民卷了进来,就是媒体,也被他牵着鼻子走。
他们在质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说,因为很多人太幼稚了,我想让他们变得成熟起来。
一时间,他仿佛成了知名人物。他家的窗玻璃被人砸碎了两块。走在大街上,有人在朝他指指点点。陶玲不愿跟他同时出门,他每次出门时陶玲都叮嘱他小心,回来时先看看他脑袋再看看他手脚,仿佛在确定它们是不是完好无损。
这天,他从外面回来,掏出钥匙正准备开门,忽然从暗影里蹿出一个人来。他本能地往后退,紧盯着对方的手,担心握了什么凶器,果真,对方已经把手伸出来了。他暗叫一声不好,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原来他也是怕死的,胆子还特别小。等他恢复意识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被对方紧紧握着,在一个劲地摇。对方说,你就是孙策孙老师吧,我找你找得好苦!他惊魂未定,战战兢兢说道,请问你是哪路英雄,我好像不认识你。对方说,你当然不认识我,可你不认识我不要紧,只要我认识你就行。他说,请问有什、什么事?对方说,一下子说不清楚,还是让我到你家里去谈吧。孙策见对方一脸恭敬,似乎没有冒犯他的意思,才安下心来。他插了好几下,才把钥匙插进了锁眼。这工夫,那个人又到刚才蹲着的暗影里去了一趟,拎出个鼓鼓囊囊的大包。孙策问,你这是干什么?那个人说,没什么,一点补品,给孙老师您补补身子。
进了门,那个人自我介绍,说他叫王平,是一个写书的,刚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想不赚钱也不容易》。说着,他从包里把书拿出来递给孙策,接着把那些补品也掏了出来摆在桌子上,都是些现在市面上很流行的胶囊和口服液之类。最后,王平掏出一支用玻璃盒包装好的人参来,说这是他们家乡的特产,您瞧它这根须多么完整,是他爹自己在山上挖的,爹挖到之后,兴奋地给他打电话,他没让爹卖。孙策说,你太客气了。王平说,我客气就是想您不客气,我特地来找您,就是想请您帮我策划一下,怎么让这本书更好卖,它是我自己买书号出版的,一般出版商我还不想卖给他们,我想自己发行,狠狠赚它一笔。
孙策心中暗笑,心想你这书名不是叫《想不赚钱也不容易》吗,怎么反倒找我来了?不过这种事也不稀奇,算命的把别人的命算得神气活现,却从来也不会算自己的。许多单位都是外行领导内行。致富类报纸杂志的编辑有好多是穷光蛋。社交宝典和爱神点化栏目的编辑说不定对社交恋爱一窍不通。
他说,要我帮你策划,说不定我还要先把你的书认真地拜读一遍呢。
王平没听出他在开玩笑,很认真地说,孙老师,不用的,对于您这样的高手,根本不用看的,不是说现在不管书的内容好不好,只要策划得好就能赚大钱吗?策划就是智慧,智慧就是知识,知识就是经济。你想啊,中国这么大,每个人骗他一块钱,就是十几个亿,其实只要一毛钱就不得了,我没大的理想,只要每个人平均摊上一分钱就行。
他说,那好,我们就争取骗他一分钱。
起初他建议王平跟出版商打官司。这年月,很多事,一打官司就灵,有很多官司,其实是在做广告。你把官司当儿戏,就能超越官司了。可让王平告出版商什么呢?就说出版商瞒着他,私自加大了印数。可王平这小子,不敢告出版商。怕把对方得罪了。孙策说,可惜你的书没有被盗版,不然,逮个盗版商告一状也行。反正只要把公众的眼球吸引住,就会提高发行量。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人的脑子根本来不及想什么问题,只想快点到达目的地。王平说,是啊,要是被盗版就好了,可这完全要看您的,您策划得好,它就能被盗版。
于是他决定虚拟一个读者。读者把王平告上法庭,说王平是个骗子,因为他在读了王平的书之后,不但没赚到什么钱,反而倒贴了二十多块钱的购书款。法院会受理这桩莫名其妙的官司的。现在的法院比以前还真的有了些进步,有时候会有点喜剧性。一个社会,能把严肃的事情弄出点喜剧性来,那么该社会就有一定的民主性和自由性。这样的案子法院很可能没法判,但它会本着消费法的精神而判读者胜诉,法院最终会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定作者退还购书款,负担所有诉讼费用,并赔偿原告一定的精神损失。不要紧,照付就是。反正不多。但作者会在结案后向媒体诉苦(YucXfQqki7Lmf/F7hbJ5r8Sn01C2kL/bObiSwY0pwO4=这样的案子少不了有记者跟踪采访),抱怨:他的败诉的确有点冤,因为该读者之所以赢了官司得了钱,正是受了该书最后一章的启发,那一章正是教读者如何利用打官司赚钱的,不是有很多人打官司赚了钱吗?有的还赚了大钱。没想到该读者以怨报德,在老师头上淘了他的第一桶金。但作为作者,他还是感到高兴的,虽然读者的这种做法值得商榷。他建议王平赶紧补写最后一章。
他越往下讲,越被自己的设想吸引。可王平似乎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觉得他的办法有点玄。像听天书。这是王平的评价。孙策也就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