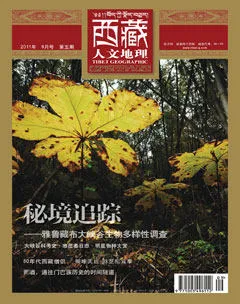南峰寻蛇记
由于前两天在加拉村寻蛇未果,于是6月24日,我和B组做人文的刘源博士一起先出加拉,前往直白村。走的时候看着因为被大蜜蜂蜇伤较严重、昨日才与B组会合的巍巍和老徐依然神清气爽,心里的担忧放下不少,同时也希望直白不要有大蜜蜂,手上和头上的刺伤还隐隐作痛(事实上,后来我们还是在直白村发现了大蜜蜂的蜂巢)。
路上皮卡车开得实在太快,一路的美景在眼前飞一般划过,真担心货兜里的丹增和白马两位兄弟被甩出车外。路过一段很棒的森林,真想让大家给我20分钟下来,看看有没东西可以记录—下……还是赶到村里吧。
“哇……”车上的所有人几乎同时大叫起来,一只淡黄色皮毛、深色尾巴的小动物,一跳—颠的从车前横穿过去。还以为是一只鼬,回过神来才反应是黄喉貂。上次云南梅里雪山IBE生物多样性调查,老郭有该物种精彩的记录,没想到能亲眼所见这小家伙,心想今天一定会有好收获,毕竟加拉村环境虽好,但还是太干,我需要的类群踪迹全无。
小雨—直不停地下,车终于来到直白村。人文刘老师立马在村里开始了采访,我一个人在外面观察这里的地形与环境。好多行李让我不能走远,只能守着,还好有只老板的洋猫
英国短毛猫(没想到藏区还有这玩意儿),—直陪我等雨停。
临近中午,天空开始放晴。从农庄老板的口中了解到,就在下面的湿地里发现有“脆蛇”,我猜想可能是细脆蛇蜥,天晴就在草地上晒太阳。
向导贡嘎终于从派镇赶了过来,把我们安顿在一个“农家乐”里,匆匆喝了两碗浓香的酥油茶后各自分头开始工作,刘老师值接和农家乐老板一家沟通起来,我了解了线路后穿上雨裤,带着白马兄弟下湿地开始调查。
高原的太阳很晒,雨裤一点气不透,闷热难忍,正脱下一半,听到白马在后面不时发出笑声,不知他在想什么美事。这里的环境真是理想,心里一直想着天黑之后必有好的收获。白马穿的是军帆布鞋,只能绕水沟走。突然见他停下了,回身去找什么东西,一直呆立在原地。肯定有什么发现,于是,我跑过去问他。“看到一条白色的蛇。”白马同时用手比划着长度——超过了一米。这是大发现啊!“白色的!”我心里一直这样想。开始了整条沟的搜索,结果一无所获,没有他说的“白蛇”。还是接着看地形……
转了两个大圈,也没有发现晒太阳的“脆蛇”,走到一个水边时天色暗了下来,之前突然放晴的阳光,让水里的豆娘集体开始羽化。较早羽化的开始了飞行练习,起起落落,漂亮的画面,可相机却难以表达,只能拍拍停在水草上休息的那些。
这时白马叫我准备收工回去先吃晚餐,顿时,没有吃午餐的饥饿疲倦感充满全身。收起相机,天色已暗,一个劲地往回走。就在我跨一条水沟的时候,眼睛余光扫到左边沟里有东西快速移动,定睛一看一条灰色的蛇,个头不算小,朝着灌丛深处钻,最后停在一块大岩石下。我赶紧让白马把我的相机背过来,准备拍摄,可惜只有它的尾巴在水面上能够看到,无奈,我在大石头后静静守候,白马被我支到一边。10分钟后,蛇才渐渐缓慢移动,这时,我能清楚看到它头部及背上的花纹,是锦蛇属的。
目标朝着小溪上游—直游走,天色越来越暗,移动中无法用相机进行记录,只能_直跟着它等待机会。最后,它在一块大石头下面停了下来,同时也感觉到我的存在,一动不动地观察着我。我立即装了闪光灯,用200mm的镜头站在水里快速远距离拍了几张。当我还想再靠近它时,它突然钻进了一个石缝中。再次等了20分钟也不见出来,最后只能作罢,和白马赶回农家吃晚饭,希望夜里能再次看到它的身影。
晚餐前在相机上放大照片,一阵惊喜,从头部鳞片的排列,以及背部鳞片带有黑色的边缘来看,果然是1982年在中国境内记录到的南峰锦蛇,就在那年李胜全老师在东久扎曲采到国内唯一的1号雄性标本(东久扎曲位于南迦巴瓦峰北坡,雅鲁藏布江大拐弯顶端与帕隆藏布的交汇处,该地属亚热带植物景观,海拔2100米),之后尚未有科学记录。
快速吃完晚饭,晚上9点天黑下来,我再次沿湿地进行调查,希望能再次看到它的身影和更多物种。刚过一个独木桥,地上一个黑影窜动,电筒随手一扫,—只蛙类,快速进行拍摄——高山倭蛙收入相机。随后陆续发现大小不同的高山倭蛙,这种生活在海拔3000-4500米的西藏广布蛙类需要充分的湿度和相对避风的地方才能良好生存。直白村的地形正好能满足这一需要,照片视频拍足之后,继续向着白天踩好的地形点进发。来到南峰锦蛇钻入石缝的点进行了十几分钟的搜索,观察无果,只能遗感地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