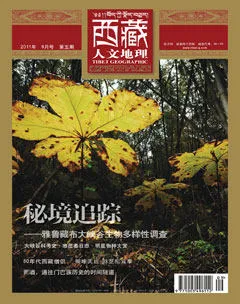曾经的兽类王国气候变暖带来野生动物生存隐忧
2011-01-01 00:00:00李初初
西藏人文地理 2011年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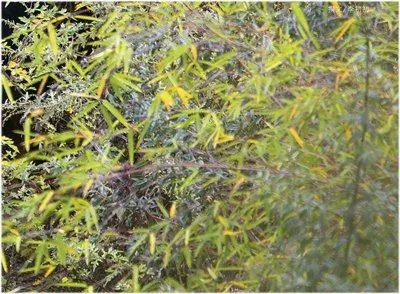

峡谷对岸的赤斑羚
对于赤斑羚的发现及拍摄,郭亮记忆犹新。去年11月,他和徐健、董磊、肖诗白、吴秀山、李磊等IBE队员,在多位大峡谷地区最优秀的向导——其中包括曾经集藏医与猎手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安吉拉的带领下,爬雪坡,翻垭口,拉着绳子淌过冰冷的雪融河,穿行茂密的丛林……最后终于来到了人迹罕至的峡谷深处。对岸,是一面过去曾被猎人们时常光顾的悬崖,经常有兽类出没。
果真守候不久,安吉拉就指着对岸告诉队员们出现了动物,大家纷纷拿起望远镜和相机朝对岸看去,“赤斑羚!”认出了那群动物的队员们忍不住发出惊呼,郭亮也从相机镜头里看到了它们。然而,就在某只赤斑羚的眼神撞入镜头的刹那,整个群体忽然掉头而去,片刻问就消失在绝壁背后的丛林中。
根据匆忙中拍摄下来的照片分析,那个群体应该由三个赤斑羚家庭组成。没有拍摄到理想的影像资料,郭亮和队友们决定就在绝壁的对岸支起帐篷,扎下营来,守候那群赤斑羚再次出现。
守候,是科考队员们在野外拍摄调查时的家常便饭,也是郭亮习以为常的事J隋。然而接下来的几天,对岸的岩壁上始终空荡荡,一点赤斑羚的踪迹也没有,仿佛要让他和同行的队员们失望了。好在第六天傍晚,在峡谷对岸的柔和光线中,一只小赤斑羚终于在大家的翘首等待中现身。它还站在江水边好奇地朝这岸的科考队员们观望。此后几天都是如此,每到傍晚它就出现在峡谷对岸,直到全队完成拍摄,决定离开。
“看来,这是~还从来没有受到人类惊吓的幼畜。”郭亮说。赤斑羚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世界上定名较迟的兽类之一,主要分布于藏东南地区的峡谷丛林问,分布区域极窄。这种珍稀动物曾经被大量猎杀,种群总数一度降到1500只以下。
那次行动,他们还拍到了同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羚牛,还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岩羊和俗称“四不像”的鬣羚。
拍到罕见亚洲野猫
作为一名年轻的野生动物摄影师,IBE队员肖诗白的镜头曾记录过许多动物,但在谈及雅鲁藏布大峡谷的调查,他对2010年秋季的一次拍摄仍意犹未尽,那就是亚洲野猫的发现。
肖诗白的长项是使用红外触发相机,在2010年秋季的调查中,肖诗自在营地周围的河滩上发现了许多新鲜的动物足迹,其中最多的黄鼬,于是他在附近布置了几台红外触发相机用来拍摄它们。几天过后,红外相机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拍摄到了许多黄鼠kyUnevXWzKS2ViN8/JTl5g==狼在镜头前活动的画面。然而意外的是,拍摄到不只有黄鼠狼,还有一只野猫,但是它的特征不同于常见的豹猫。后来经过多位专家鉴定,才确认这是一种亚洲野猫,它不同于喜马拉雅山南坡的印度野猫,也不同于最南分布到甘肃的亚洲野猫,很可能是一个此前还从未被记录过的亚洲野猫新亚种。
IBE队长徐健说:大峡谷腹地的飞禽走兽种类丰富,跟这里随高度差呈垂直分布的林带关系密切。在峡谷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是高原动物的部落,兽类有岩羊、雪豹、鼠兔等;中间海拔2500米到3500米左右的常绿阔叶林和针阔叶混交林中,则以森林动物为主,如斑羚、鬣羚、林麝、黑熊、豹猫等。而到了墨脱周围海拔1500米以下的热带、亚热带季雨林中,兽类更丰富,是各种麂、小型食肉兽和灵长类的天堂。
大峡谷地区是野生动物的天堂,还可从当地很多以兽类命名的有意思的地名中窥见一斑:“档木龙”,意为狗熊出没的山谷;“阿格”,猴子玩耍的坝子;“格当”,野牛的家乡;“京朱”,则是围猎者唾手可得之处。此外,当地的珞巴人还管老虎叫“阿崩”,珞巴人的各部族中,都流行着人与“阿崩”种种亲密无问的故事及传说。在峡谷南端的墨脱县境内,至今还有孟加拉虎的身影,虽然数量已经很少,
与中国许多其他地方的野生动物栖息地一样,大峡谷的野生动物,特别是大型兽类,生存面临严峻挑战。此次带领我们去那拉错的向导扎西就有切身体会,他说以前那拉错一带很容易看到林麝,但现在已经很难碰上了,“除非翻过那拉雪山,到了人迹罕至的山中,幸运的话或许还能看到”,扎西说。
气候变暖带来生境巨变
林芝的原始森林曾遭受肆意砍伐的命运。“林芝有7个县,过去每个县都有4~5个伐木厂,最严重的时候有些山头都被砍成了‘秃子’。”在西藏长大的罗浩非常了解这段情况。林芝由于没有大型矿藏,除了采摘虫草、松茸外卖外,卖木材一度成为人们主要的经济来源。“那时候,村里的壮年劳动力几乎都去山上伐木,虽然政府对每年采伐的木材总量有控制,但人们为了赚钱,采伐的量远远超过规定。”安吉拉称,“木材价格最高的时候,一般性的松木每立方可卖到300元左右,笔直无节子的价格则每立方高达五六百元。
砍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灾难和自然灾难。罗浩记得,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情况有所改观,砍伐森林的行为逐步得到控制,后来过渡到整个大峡谷地区全面禁伐。正式禁伐后,村民们须按规定轮流看护森林,检查有没有偷伐等破坏行为,村民们每个月可以领到80元的护林费。“过去秃了的山,现在又慢慢开始恢复了。”罗浩说。
禁猎则始于1995年。那一年,政府开始没收猎人手中的枪支。当时安吉拉和其他猎人心里还都有些排斥
他觉得,在很长时间内,狩猎并没有使大峡谷内的獐子,狗熊之类的动物数量有明显减少,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一批从四川过来的人开始用铁丝网等工具灭绝性地捕杀野生动物为止。
“以前我们打獐子,只打公獐不打母獐,并且也不会捕杀过度。”10多年之后,这位当年大峡谷地区最优秀的猎手对于禁猎已慢慢想通,虽然“一到打猎的季节,还是会很怀念当年上山时的乐趣”,随着2005年大峡谷正式全面禁猎,安吉拉老人猎人的身份被渐渐淡去,他现在已是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林芝分公司的一名员工。
而对于曾活跃在这里的野生动物来说,全面禁伐禁猎后的另一隐忧来自气候层面。“上世纪70年代,南迦巴瓦一天要发生10多次雪崩,而且声音很响,现在一天听到一两次就不错了。”安吉拉回忆,在他十多岁时,现在的直白大桥附近就是冰川,过河就能在冰川上行走。而如今,桥旁根本见不着任何冰川的影子。“以前多雄拉山3900米以上几乎终年积雪,现在冬天上到3800米也未必有雪了”,安吉拉说。而气候变暖所导致的冰川退化和雪线提升等变化,无疑会连锁式改变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