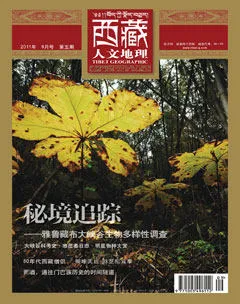自然控的朝圣志愿队员的考察日志
2011-01-01 00:00:00孙淑君李沁阳
西藏人文地理 2011年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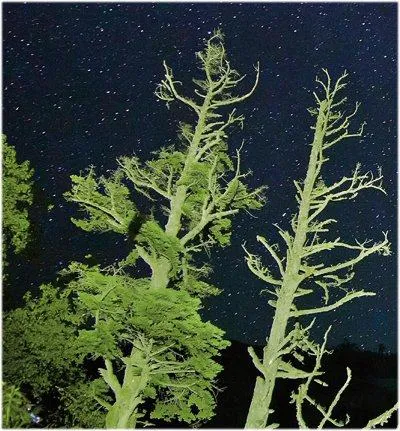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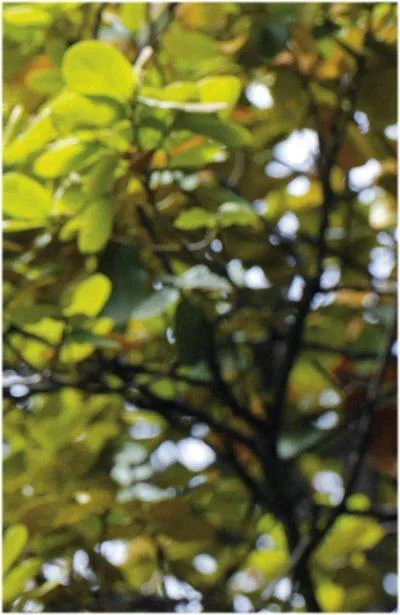

继去年10月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进行科学调查,今年6月21日,IBE再次前往大峡谷展开科考工作。此次项目举办方还特意从5268名志愿者中遴选了两位志愿队员一起参与。他们的科考日志,既是对科考活动客观、平实的记录,也是作为非专业人士直面大峡谷生物多样性时最直接的感受。
A队孙淑君:享受科学盛筵
6120清晨五点半,小雨中的成都还没有醒来,我们就怀揣着奔赴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欣喜出发了。IBE老师们的行囊让人叹为观止,林林总总几十个包。飞机起飞,我的心也跟着一起飞扬起来。
林芝米林机场,高原特有的阳光灿烂通透,远处的雪峰映衬着湛蓝的天空,杉林蓊郁苍翠。罗浩老师亲自到机场迎接我们,给每个人都献了哈达。雅鲁藏布大峡谷,我来了。
6/21很早醒来,莫名兴奋。下雨了,还不算小。所幸还不到严格意义上的雨季,继而转晴。南迦巴瓦深藏在重重云霭背后,不肯显露一点儿真容。今天是科考的第一天,主要做适应性调查和拍摄。队伍被分为两组,我所在的A组奔松林口。
协助王辰老师调查植物,毕竟他是植物学专业出身,分布在林问、草甸抑或湿地上的各种花草,随口就能说出种名来。如果说他大师级的拍摄水准让人叹为观止的话,敬业精神则更让人钦佩不已。
短短两个小时,受益匪浅,结识数十种花草倒是其次,重要的是领略到了IBE队员们的严谨和投入,他们对自然由衷的欣赏,以及对镜头下生灵的呵护和珍爱。
6/22昨晚,遭受大蜜蜂袭击的B组三名队员被连夜送往百余公里外的八一医院医治。科考刚开始就给了我们爪“下马威”,气氛—下凝重起来,早晨A组队员出发去那拉错时,B组队员纷纷前来送行,气氛颇为悲壮。
汽车把我们送到格噶村,雨又下了起来。下车整理好行囊,披上雨衣,队伍开始沿着山道向高山上开拔。尽管是轻装上阵,但一路爬山还是很耗费体力。随着海拔的攀升,心跳声也越发急促。随行一路,真切感受到IBE老师们的辛苦,每个人的摄影包都至少有十多斤重,还要不停地拍照,蹲下、起立,是份重体力活呢。幸好沿途他们不断有惊喜的发现。
越向上行进,植被越呈现典型的垂直谱带分布,各种物种生活在各自适应的环境To高山林线(即郁闭的山地森林与无林的高山灌丛、草甸间的界线),在这一带的向阳坡面上甚至能延伸到海拔4600米左右,这应该是世界最高的林线了。雅江大峡谷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集中了丰富多彩的物种,也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视觉盛宴。
在灌木丛林问穿行时,不小心被荨麻问候了一下又酸又痒。这种形似南瓜叶的阔叶植物边缘带着白刺,能通过毛孔扎入肉里,刺痛肿胀的感觉要持续很长的时间。远远即能看到塔黄,粗壮的茎被黄绿色的苞片覆盖,在灌木丛中鹤立鸡群般醒目,这种多年生的蓼科植物能长到2米多高。
我们的营地依山傍湖。夕阳慷慨地挥洒在加拉白垒的峰顶,我们席地而坐,一边欣赏美丽风景,一边享用大白菜炖罐头的丰盛晚餐。罗浩老师特意叮嘱我们,要把生活垃圾整理好,到时再带回山下。除了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6.23一夜无眠,可能海拔太高的原因所致。早上随彭建生老师爬到雪线上面,有幸看到了雪莲,可l昔花还未开。号称“三江主人”的彭老师(云南香格里拉人,藏族)昨晚给我取了个美丽的藏族名字
冈拉梅朵,即雪莲花的意思。依仗冰雪融水的滋养,雪莲一般要经过5~7年的生长,才能傲然怒放在这高高的雪线附近。
一只高山绢蝶仅给我们惊鸿一瞥,便迅疾飞去。丝绸般的翅膀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这个神奇的物种大多分布在海拔4500~5000米甚至更高的地方,不与寻常的眼蝶、蛱蝶为伍。
雨霁天晴,难得的好天气。高山草甸上,正值杜鹃花的花期,在背后雪山的映衬下,美得令人窒息。远处的加拉白垒似金字塔般巍然矗立,下面的那拉错倒映着群峰的影子。我们必须横切冰川,以观察不同地貌上的植被,这里分布着丰富的垫状植物和高山冰缘植物,如岩白菜、岩须、樱子草等。
下山已是黄昏,饥肠辘辘,远远嗅到营地里罗老师准备好的饭菜清香……
6/24一夜风狂雨骤,几欲把帐篷掀翻。天明,大雨仍在继续,上午的计划只能暂时搁置。大家围着火塘品茶,彭老师带有巴基斯坦红茶,还有各路人马奉上的台湾乌龙、铁观音。因为雪山融水携带的泥沙太重,我们特意把压缩饼干桶放在帐篷下面,收集雨水。
6/25一早,队伍拔营开往山中的一个草坝。穿行丛林的途中,恍如走进了电影《阿凡达》中的潘多拉星球。高大的冷杉被松萝缠绕得密匝厚实,脚下的苔藓和腐殖质足足有几十厘米厚。彭老师连声赞叹,拿着相机全方位不停“扫射”。
这次营地设在林问的开阔地上,四周是笔直高大的冷杉林。草坝上,紫色的报春是主打花,还有白色的银莲、粉色的桃儿七,都开得蓬勃肆意。
背夫们熟稔地搭起帐篷、燃起篝火。我们围站在熊熊大火边烘烤被大雨淋透的衣服。晚饭过后,背夫在我们的力邀下,终于抛弃羞涩,围着火堆唱着歌,跳起了锅庄,让科考队员们大开眼界。
6126从大草坝返回派镇的路上,天气放晴,又都是下坡,王老师拍得兴致盎然。上山时因为下雨没有拍摄的植物还被他一一惦记着,位置丝毫不差,真钦佩他的记忆力。
回到派镇,这一阶段的科考就此结束,同行的媒体记者们告退,我和另一志愿者继续跟进下一期考察。
6/27昨夜睡眠不足三小时,早晨六点半爬起来送别队友,没能再睡个回笼觉,因为前几天在山上采集的植物标本需要压制晾晒,_匕午的时间很陕过去。
下午兵分两路,一队至松林口扎营,科考重点是动物和鸟类。我则依旧随王老师调查拍摄植物。顺着雅江边的沙地前/行,我们又有不少发现,例如可入药的“列当”,还有黄芪和柴胡。
6/28一大早又驱车奔往松林口。多雄拉山口的白雪在阳光下反射出冷艳的光芒。第一天上山看到的那株暗红色的绿绒蒿,已兀自萎谢了,旁边又有一株鹅黄色的正悄然开放。沿着松林口往派镇大约8公里左右的山路,我们边走边拍。琳琅满目的各种植物,不断带给我们惊喜,在王老师眼底更是如此。
天气晴朗,十分难得。在松林口下的湿地,我们终于见到了“龙胆”,一种极罕见的高山植物。龙胆十分矮小,贴地开放,蓝紫色的花朵没有丝毫香味,却美丽异常。
6/29今天,王辰老师因有事结束考察,先行离开。我接下来的任务是协同昆虫专家张巍巍、鸟类专家郭亮、两栖和爬行动物专家范毅三位老师去达林村考察。
达林村宛如世外桃源,村里十分安静,看不到什么村民。我们在村中晃悠了好几个来回,只有藏猪和牛犊在村问林地里优哉游哉地觅食。原来时下多数村民都进山采虫草去了,只剩下老人和小孩留守。由于整个村庄被木板搭成的护栏围着,人们不用担心牲畜乱跑。人省心,猪快活,算是和谐共处吧。只是每次我们出入村庄时,都要各自施展跨栏的绝活儿。
村外的草甸上,蜂蝶乱舞,蝗虫在草问跳跃,显示出了夏日应有的生机。一株不知名的蕨类植株上,聚集了十几只绢粉蝶,每当轻风拂来,它们的身姿就犹如会飞的花朵飘浮在了空中。
6/30早上七点,达林村广播站的大喇叭会准时传来诵经声。我注意到喇叭上印有“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党中央、国务院赠送”的字样。慵懒地躺在藏家人的客厅沙发上,斜望出去便是南迦巴瓦峰。松木在炉膛里哔啵作响,房东阿佳已经在炉火上煮好酥油茶。尽管她不通晓汉语,但微笑和手势仍足以让我们保持良好的沟通。给我们准备好早饭后,她静立一旁,好随时给我们添饭续茶。我们邀请她一块吃饭,但无论如何她都不肯。
今天有幸目睹了传说中的大紫胸鹦鹉,足足有几十只,在杉林问呼啸穿梭。郭亮老师说,嘴巴红色的是雄性,黑色的是雌性,而幼鸟的嘴巴是黄色的,他曾抓拍过大紫胸鹦鹉一家三口的温馨场面。
一丛葳蕤繁茂的灌木,名字极有趣,叫作“锦鸡儿”。“锦鸡儿”被白颈鸫相中,在枝权问搭建了一个窝。幼鸟丝毫不知道怕人,与我们只有一米左右,此前,我还从未体验过与鸟儿近距离交流。
向导加措还在树权问发现了一只伯劳,是一只尚未学会飞翔的幼鸟,其父母在近旁的枝头上喳喳直叫。我们拍完幼鸟后又把它小心翼翼放回了原处,离开时仍听到伯劳父母焦灼的尖叫声。
南迦巴瓦总算展现出了最上面的一点点峰尖,结合以前曾看过的肩、臂、胸膛,也可以聊以自慰地说是朝觐到了神山全貌。放眼四望,正如许巍的歌: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
7/1挂起灯诱用的白幕布以及黑光灯,一度被误认为要放电影。房东的侄孙女好奇地等着观看,她今年12岁,已会主动帮大人洗碗筷。她喜欢唱周杰伦的歌,爱摆各种“POSE”照相,并要我答应以后一定把照片转交给她。
夜半诱来的天蚕蛾、鳃金龟等明星物种,需清晨摆拍后放生,因为当地不杀生,我们尊重这里的习惯。蚊蚋不停干扰,可冷张老师的头上才遭蜂毒,又添虫咬。
中午向导加措把饭给送了过来,在灿烂的阳光下开始享用午餐。烙大饼、牦牛肉、藏鸡蛋,还有辣椒酱,大快朵颐。得知驻扎松林口的队伍已经下山,原计划再在村里盘桓一天的我们决定赶过去会合,以商讨下一步行动。
7/2上午和彭老师到派镇大桥对面的沙丘拍片。先行左拐,在岩壁上看到许多岩蜥。无意中发现一只岩蜥居然还是“摧花辣手”,只见它宽大肥厚的舌头迅速卷住了一枚红色的花瓣,然后叼在嘴里匆匆离去。
可惜没能够遇到沙蜥。沙丘上卧着好几头牛,安详地咀嚼反刍,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忽然飘过一阵不知是杨花还是柳絮的东西,思绪刹那问宛如穿越回了春季的内地。
午后集体到八一镇休整,于是作别“谷客”和派镇。
7,3科考进入第三阶段,驱车奔米瑞乡。据说当年文成公主途经此地时曾亲手植过一棵柳树,人称“公主柳”。现在雅江大峡谷入口段的南岸,长了不少沧桑的老柳,树龄至少百年以上。很好的生境,奇怪的是却没有发现两栖爬行类动物。
午餐后乘坐游艇,经由尼洋河与雅鲁藏布江的分界线。一清一浊,泾渭分明。风从双肩掠过,江岸上的民居显得很格式化,一律有着或红或蓝的彩钢屋顶。
我们到达的佛掌沙丘,因其在江水中的倒影酷似合掌祈祷的佛掌而得名。有几十米高,攀爬上去颇花费力气。在沙丘旁的老柳树上随意掀开一块风干的树皮,数十只蝼蚁慌作一团。步甲的胆子也显得相当小,一有动静,就拼命往树洞里钻。
7/4今天路遇另一沙丘,聚集着成千上万只象甲,这种鞘翅目的昆虫前翅愈合成一体,后翅退化,已丧失飞行能力。为躲避阳光和高温,它们聚集在木块下、牛粪底,每每掀开一处,都是密密匝匝的一团,见到此景,“密集控”或许会喜不自禁。
在江心岛,搞两栖和爬行动物调查的范老师邂逅了一只母蝎子,并意外发现母蝎背上还载有十几只幼蝎,刚孵化出来没多久,白色半透明状。母蝎还不时用前螯切碎食物,举到后面去饲喂幼蝎。
7/5睡得依旧不踏实。木板隔就的房间不隔音,听得到猫叫,还传来远远的狗吠声。
沿着雅江江畔前行,阳光极好。途中遇到一群去转山的藏族妇女,她们好奇地观望着我手中的相机及昆虫网。简单的手势沟通后,给其中的几位照了相。她们看着回放中的自己,仿佛难以置信,抱以羞涩的笑容。
午饭后回转,途径一个小村庄,接上在德木寺做人文调查的刘源博士。德木寺曾经香火旺盛,僧侣达数百之众,可惜毁于1950年的那一场地震。
7/6航班延误,乌泱乌泱的候机人群。雅江大峡谷,让我与你握别……
B队 李沁阳:与牛灵共舞
李沁阳,男,B队志愿队员,本科学习环境科学专业,即将赴瑞典隆德大学攻读保护生物学硕士,热爱自然科学和生态摄影。
6/20早上9:00到达林芝,飞行途中目睹贡嘎主峰和之前从未见过的壮美地貌。林芝风光秀美,天空湛蓝。我们先后经过了尼洋河和雅鲁藏布江的交汇点、江边沙丘及各式藏式传统民居,最终抵达派镇。
分房,午饭,小歇后全体开了个简短会议,介绍了A、B两组的主要行程。由于B组更偏向两爬和昆虫的拍摄,我便加入B组,两根登山杖因此也沦为纯粹的负重。
晚饭后举行看片会,暨去年秋天雅鲁藏布大峡谷IBE的成果展,能在半小时内欣赏到老师们20多天的成果,我深感幸运,也很期待自己即将开始的工作。
6/21今天是适应性拍摄,经过约40分钟的行车,我们到了索松村附近的山脚下,来考察拍摄这里的大蜜蜂。据秋季调查,珍稀鸟种黄腰响蜜裂会偶尔在此现身,所以除了想见识大蜜蜂巢穴,我还期待能把黄腰响蜜裂的影像拿下。
到达目的地后,我们在徐健老师的指引下找到了蜂巢。整体相连,凸起的三块蜂巢上严丝合缝地布满着大蜜蜂“黑压压的三大片”算是贴切的形容。我们队伍一行缓缓爬到蜂巢下方,开始拍摄大蜜蜂和等待那罕见的鸟儿。
没多久,X大蜜蜂便扎在了我左眼眶上,感觉微疼,但并没在意,还略带得意地跟身后的人展示我和小生灵的亲密互动。可马上,范老师急促地催促我们:火速下撤!他的话刚作罢,我头上的蜜蜂便瞬间多过5只,我也意识到情况可能比想象中要严重很多。危机关头,每个^,下山的步伐都变得异常矫健,上来花了10分钟,下去没等30秒。下到公路上,头发里又钻了许多蜜蜂,还有不少拽着耳朵、眉毛以及脖子在疯狂扎刺,其余的则落在黑色的抓绒衣上。此时以为危险已经离我远去,便做了一个十分错误的决定:脱下抓绒衣,企图用它打掉我身上其余的蜜蜂。谁知暴露出来的脖子和手臂给蜂群提供了更好的攻击目标,而真正的蜜蜂大军这才赶到。当头皮、耳背、脖子、手臂以及衣服背后布满蜇人的蜜蜂时,我瞬间有了从未体验过的惊恐,相机和背包也甩在路边无暇顾及。
惊恐中,我小声提醒自己一定要冷静,尽快往远离蜂巢的方向跑,虽然奔跑速度远远不及飞行的野蜂。在海拔2800米的地方一路狂奔,气喘吁吁,只能咬牙坚持,直到见到B组其他成员后,才终于在他们的帮助下摆脱了蜂群。
后来我的手臂,耳背,脖子,头皮里发现了几十根蜂刺,后背衣服上的则更多。
最后统计徐健队长和张巍巍老师受伤最重,其次是随队采访的郁记者。我们一行在索松村一居民家里做了简单处理,两位老师用肥皂洗了头,不少人在伤口上涂了蜂蜜,一个可爱的藏家小男孩也帮我把眼眶附近的蜂刺一一拔出。
回派镇午饭后,三位“重伤员”躺在屋里休息,并有队友用镊子和头灯细心地寻找藏在头皮里的蜂刺。我自认为身体恢复很顺利,便在下午自告奋勇和彭建生老师、李记者及耿记者去蜂巢旁拿回此前匆忙丢弃的摄影装备。早上被蜇的惨痛教训让我们走前做足了防护:冲锋衣配合头巾、手套,确保了身上没有一处直接暴露的皮肤。
在路上,也许是被蜇后的否极泰来,南迦巴瓦峰居然为我们开了一扇“天窗”,中国最美山峰的芳容在那一刻尽收眼底,我几乎说不出话,心中尽是感动与敬畏。还好这一幕并非稍纵即逝,能让我回过神来,用相机记录下来。
回到客栈,听说被蜇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烧,伴随上吐下泻,在一些老师的建议下,伤重的三人一起去八一镇医院接受治疗,目送着上车的三位队友,无比精彩的一天也结束了。先遭遇野蜂惊魂,后透过“天窗”看见了南迦巴瓦,一群才认识不久的朋友,竟在几小时内成了生死之交,不知后面还有什么精彩在等待我们。
6/22一早起来,阴雨蒙蒙,前往加拉村的路上,透过车窗上的细雨珠,看到途径的玉松、格嘎、直白等村落,也目睹对面峡谷颜色从黄到绿,垂直分层直到高人云霄的树林。当经过一个仙境一般的林子后不久,我们便到了加拉——一个只有八户人家的村庄。我们住在布卓大妈家,只有一问房,这问房被她小做改造,成了村里唯一可以接待客人的“小旅馆”。
下午,我在村庄周边寻找小生灵。这里各式各样的蝇类和虻类很多,绿色的长足虻算是双翅目中比较漂亮的,但快门一响就飞走了'好在飞不远,拍摄的难度并不算大。除此之外,一只浑身艳红的象甲,一只捕食小蝇的蜘蛛,一只毛茸茸的金龟和一种翠绿躁动的叶蜂,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昨天把我们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大蜜蜂也单独出现了,此时的它攻击性全无,忘我的在一簇小花上采蜜,浑身沾满花粉。
晚餐后,九指峰(南迦巴瓦下的峰群)和加拉白垒峰相继揭开面纱。我们到了加拉村的神迹之地—工布国王栽柳树的地方,在那里看雪山,只需静静地看,却怎么也看不够。后方,远远的山脚下飘来了一朵矮矮的云,当它和面前的大石头相对时,我按下了快门。我很喜欢这张照片,并不算多美的风光,但很适合诠释这次行程。云的灵动,石的沉稳,截然不同的生活也有交汇的一刻,就像这次在大峡谷与各位老师们一起科考一样。
6/23早上一行人出发徒步至江对岸的阎罗宫,抵达白塔前见识了不少新奇的植被。走过白塔后沿着瀑布支流继续前进,瞬间像进入了空调房一般,无比凉快。路过相传是珠布多吉赤烈的修行洞,不久便到达阎罗宫。
回程时,向导带着我们走近阎罗大瀑布。在浓密的树林中,百米开外就能清晰听见瀑布的怒吼,待穿过密密麻麻的经幡后,终于能近距离体会它的壮美。携大量泥沙的河水狮吼着倾泻而下,而瀑布下方的一道彩虹又恰当增添了一丝柔情。
中午回到加拉村后,之前离队的三人已经赶来和我们会合,气氛热烈起来。
下午的任务是绘制加拉村地图,由于刘源博士一行已经基本把8户人家调查清楚,并梳理出了有趣的八卦关系,规范的俯视图和写意的局部绘画很快完成。接下来,10多部单反相机协同“长枪短炮”轮流给村里的人拍照,摄影师和村民数量相当甚至略有超越,村里也像过节一般,许多人穿着平时不穿的华丽衣服,在镜头前大方地与我们分享喜悦。
6/24分离时细雨纷飞,云很低,人文小分队的四人启程去直白,余下的人则跟着徐健和郭亮老师从村东北走出去,开始沿江拍摄。路上经过一个制高点,我们在此俯瞰加拉村全貌。本来就很“迷你”的村子此时显得更加袖珍,但也能更好衬托出周围山川的壮观。
加拉村这边鞘翅目昆虫很多,有步甲、跳甲、金龟、瓢虫等。细细观察,这些昆虫有许多“萌”点。比如它们用小翅膀拖着笨重身子别扭飞行时,我总能想起《驯龙记》里的那种“短翅肥龙”;它们感到威胁后的装死也特别逗,常戏剧性地六肢一收,十分专业地直接从高处的枝叶中摔下
在雅江沿岸较低海拔的林问,一路的环境几乎和来加拉村所路过的那片仙境般的青冈林一样。这儿的地衣蓬勃生长,我以前见过的都平铺在树皮上,而这里的已如花朵般“绽放”出立体的效果,可见生态环境的原始和纯净。
高潮出现在路程一半,一群猕猴的高亢叫声惊动了所有人。郭老师的“超级大炮”瞬间就位。猴群也发现了我们,飞陕地往山顶行进。幸好它们途径—片开阔区域,6、7只猴群成员便被清晰地记录在了郭老师的高清视频中。第一次看到野生猕猴群,还目睹了猕猴妈妈和怀里的猴宝宝,更有一只好奇的猕猴,还不时从树叶后边探出头来观察我们的动静。
6/25中午到达直白村,这里常有游客光顾,整个村落相比加拉更加现代。当大家全副武装准备出门外拍时,不巧下起了大雨。我们声势浩荡地豪迈走出,半分钟后就垂头丧气地溜回。
雨停后终于可以出门拍摄了,先到一天的鸦鸦老师昨天收获颇丰,不仅拍到了鲜有记录的南峰锦蛇,也目睹了小水塘上豆娘集体羽化的罕见场景。我当然也期待能再次见证这一切,可运气和经验不站在我这一边。几小时下来只收获了一只白颈鸫和伯劳,还有一只蜻蜒。
晚上和鸦鸦、巍巍老师同行。出门找蛙,顺便搜寻沿途的昆虫。两位可爱的老师一路相互吹捧,身在其中乐趣无穷。一路也算高产,搜寻到两只蝎子,一只生活环境另类的衣鱼(土壤里,常见为木头中),三种不同的蛙类和数枚精致的蛙卵。
6/26直白的第二天,天气阴沉并有细雨,寻蛇未果。中午,天空突然放晴。这个珍贵的时间窗口是蛇和其他爬行两栖类活跃的黄金时间,我们六七个人便排成一排,用地毯式的搜索企图能找到它们的蛛丝马迹。可相比起前天鸦鸦老师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们集体踏破铁鞋却全无收获。我们的装备、技术、经验都不差,但还是缺少一点运气。
6/27一大早就送离了一批朋友。这次分离并没下雨,反而不久后艳阳高照。气温升高,江边的岩蜥绝不会放弃这个晒太阳的机会,正如我们绝不会放弃这个拍摄它们的机会,尽管岩蜥的长相实在不敢恭维,又黑又胖,眼神还略带“邪恶”。
到了江边,发现同为石青色但体型各异的岩蜥几乎随处可见,因为数量众多,尽管它们极度敏感怕人,我们仍能从容地拍摄一只又一只。岩蜥晒太阳时的行为十分有趣,除了爱做“俯卧撑”,爱鼓起肚子尽量增大与温暖石头的接触面,它们也爱不时舔食石头表面,八成是为了吸收一些盐分和其他矿物质。舒适的环境总让人愈发懒散,蜥蜴也不例外,一些蝇虻都飞到了眼前,仍见它们懒得动嘴。
下午上松林口,随着海拔的上升,一些让人惊艳的高山植物出现在路边,其中最为醒目的莫过于藿香叶绿绒蒿的那一抹抹幽蓝。
还没为松林口白天的风光感叹完,便发现这里的夜晚更为美丽神秘。在人造光源的烘托下,夜里的绿绒蒿显得更加鬼魅,星空下的松林也庄严和令人敬畏起来。而最壮观的,则是在瀑布和松涛声的交响之下,任凭银河的光芒投射在我们身上。此时正巧在一旁灯诱的巍巍老师等来了一只西藏鹗目天蚕蛾,我们便随着他的构思,拍下了一张银河背景的天蚕蛾照。
6/28清晨透过帐篷听见贾老师的洪亮嗓音,原来将要上多雄拉山口的人马已经到达。今天以松林口为界,他们上,我们下。清早刚要出发就收获惊喜,郭老师先发现了一只鼠兔,随后这个小可爱也跳入我的视野。它很谨慎,但习惯了我们后也便开始旁若无人地嚼起叶子,这揭示了它们的食性。它的短尾巴,戴了美瞳似的好奇双眼和吃东西时才露出来的兔牙真是可爱之极。它离我最近时不到3米远,我那200mm的镜头都几乎照到爆框,让郭老师那等效焦距1500mm的“大炮”瞬间沦为摆设。
鼠兔回窝,我们也开始下山。此时清晨的完美逆光是拍摄绿绒蒿的最佳时刻,我也收获了几张满意的照片。除此之外,酒红色的杜鹃,紫色的法国国花鸢尾,都为我们的下山之路提供了许多亮色。
突然,一阵阵高亢响亮的叫声朝我们逼近,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分不清是鸟还是兽。不一会,一个黑影降落在前方光秃的树干上,原来是X头戴红冠的黑啄木鸟。这种鸟体型堪称巨大,可与红隼等猛禽比肩。它那黄色的眼睛嵌在黑色羽毛中,显得尤其夺目。经验丰富的郭老师很快把黑啄木鸟的清晰特写拿下。
之后,下山的途中还有不少类似与飞鸟邂逅的机会,比如艳丽的红黄相问的太阳鸟,体型袖珍的柳莺以及伯劳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