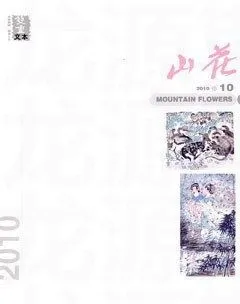“粉本”在美术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一、粉本在美术活动中的地位
粉本是美术活动的基本构成要素。元夏文彦《图绘宝鉴》曰:“古人画稿谓之粉本”。粉本在美术活动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组成与过程,具有无法替代的性质与功能意义。从名家高手到一般画工画匠,每作画都有画样画稿可依,美术活动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粉本是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前的依据。古人运用粉本,其法有二:一是用针按画稿墨线密刺小孔,把粉扑入纸、绢或壁上,然后依粉点作画;二是在画稿反面涂以白垩、土粉之类,用簪钗按正面墨线描传于纸、绢或壁上,然后依粉痕落墨。
古人对粉本是重视的,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每作一画,必先起草,按文挥洒”的绘画过程,说明古人对粉本的重视程度及绘画的基本常识——凡作画必有稿本,且先有画稿然后再按稿作画。画史资料中,画稿有明确记载的比比皆是,如“韩斡,长安人……忽一夕,有人朱衣玄冠扣韩斡门者称:‘我鬼使也。闻君善图良马,欲赐一匹。’斡立画焚之。他日有送百缣来致谢而卒莫知其所从来,是其所谓鬼使者也。建中初有一人牵马访医者,毛色骨相,医所未尝见。忽值斡,斡惊曰:‘真是吾家之所画马!’遂摩挲久之,怪其笔意,冥会如此。俄顷若蹶,因损前足。斡异之,于是归以视所画马本,则脚有一点墨缺,乃悟其画也神矣。”唐段成式《寺塔记》:“南中三门裹壁上。吴道玄白画地狱变。笔力劲怒。变状阴怪。斱之不觉毛戴。吴画中得意处。”。唐韩偓《商山道中》“却忆往年看粉本,始知名画有工夫”,宋苏轼《阎立本职贡图》“粉本遗墨开明窗”,近代缪鸿若《题担当和尚画册》“休嫌粉本无多剩,寸土伤心下笔难”等诗句,形象地说明了粉本在美术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二、粉本在美术活动中的效用
团山民居保持和延续了中原汉族传统合院的构造技术和基本性格,是云南最精美的古民居建筑群的代表,其代表性建筑主要修造于19世纪清光绪至民国年间。2005年6月21日,团山民居被世界纪念性建筑保护基金会(WMF)列为“世界濒临文化遗迹”之一,入选2006年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保护名录。
团山民居建筑构件上装饰的琳琅满目的木雕、砖雕、石雕、绘画等艺术表现形式,具有严谨的整体规划和巧妙的形式布局。同一题材内容,装饰形式相似、但绝不相同的视觉形式美感,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传统装饰艺术进行比较,也呈现出视觉表现形式相似和具体造型个性化的语言特征,这是匠师高超技艺的展示,也说明匠师在进行个性化的艺术创作之前,有一种可资参照或参考的样本——“粉本”存在,“粉本”在美术创作活动中起着一种重要的“格式”参照作用,匠师依据粉本,对同一题材的装饰内容赋予了不同形象的外貌特征。
匠师面对传统建筑复杂的功能结构进行装饰时,唯有依据大量的粉本作为创作参考,才能对画稿进行界定和创作,以区别建筑装饰形式的相似性,分清装饰艺术的功能和目的,性质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以民居木雕为例,第一进院落是木雕的重点,其在雕刻形式的选择和内容的安排上均处于优先地位;庭院中,檐廊又是人们生活起居最频繁的场所,是木雕表现的重点部位。如皇恩府厅房檐枋正中装饰有“八仙”的人物造像,其他地方的装饰则以“暗八仙”为之;木雕的“麒麟吐玉书”与石雕的“麒麟吐玉书”在形式和形象上绝不相同;同一题材的“鹊踏枝”木雕形象绝不相同。具体雕刻中,同一形象的雕饰,匠师稍加调整,或正反运用,表现出来的作品即可产生形式上的差别,取得同中求异的艺术效果。
雕刻中,匠师集诸粉本之长,对雕饰进行整体规划,匠师在具体的雕饰设计上,具有较大的自由性,具体的雕饰,取决于匠师的个性化创作。匠师以“粉本”为“花样”,把设计好的花样复制到刻件上进行放样分位刻凿,使雕饰与建筑风格结合得更紧密、更合理、更符合修造者的欣赏要求。匠师放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放样,一种是靠模放样。直接放样是匠师参照设计粉本,直接在构件和木坯上用线描画,同时做些小范围的调整工作。靠模范样是匠师先制作成一样板,靠在构件上,复描样板上的花样,靠模放样用于相同花样或对称刻件的花板上。
团山代表性民居绘画装饰的题跋中,反复出现逃禅(善书画)、幼江(山水、人物、花鸟皆能)、瀛洲(武士麟,善书画)、敬怡、焕图氏、印山、筱亭、介卿等人的落款,说明团山代表性建筑的绘画装饰是出自同一时期、同一批匠师:题跋中又多有临、摹八大山人、南田老人、石谷子笔意等的题记,说明匠师在进行绘画装饰时,是以前人的绘画作为粉本进行装饰创作的。邹一桂《小山画谱》云:“古人画稿,谓之粉本,前辈多宝蓄之,盖其草草不经意处,有自然之妙也。”。匠师的粉本来源可能有三种途径,其一,是前人留下的粉本,转移默写得到:其二,是同时代的画家所为;其三,是行会艺人们保留的建筑装饰已有的粉本。粉本是经艺人们多方面运思、推敲流传下来的一套诀窍,是可贵的传统技法,在建筑装饰的整个艺术创作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整个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建筑行业里的画工多粗读经史小说,略通文墨,在技法上虽系师徒相承,墨守遗法,然而由于匠师对生活有着较深刻的体验和理解,匠师不以传统的粉本为满足,往往随时代的演变而改变粉本的内容,进行再度的创作和设计。建筑行会里的画师无论技术娴熟与否,对于工程复杂的合院装饰和技术要求,都需要以既往的粉本作为参照,再从中加以富于个性化的变化和改造来完成。匠师手中同一内容的粉本可能存在着多种形式,依照粉本,匠师可以对艺术作品进行反复的修改或增补,使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各有风趣,独具特色,装饰艺术源于粉本不断的创新和发展。
民居代表性合院的木雕、砖雕、石雕艺术,虽没有文字题跋,但从装饰艺术的造型手法、表现风格的相似性,仍可判断出这些装饰艺术是出自同一集体的能工巧匠,这与团山张氏家族的发展史和行会行业的特征相一致。
团山张姓始祖张福原为江西绕州府鄱阳县人,于明洪武年间贸易至临安(今建水),三迁择里,最后看中团山“山川毓秀,风俗醇美,形势耸拔,众山环拱,甲于全境,移而居之”,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大家族,人口的增长与土地的限制,使团山人一直有外出挣钱养家的传统,时光荏苒,到了清末光绪年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兴起,个旧丰富的矿产资源更是被开挖和利用,团山人来到个旧开采锡矿,在开采中,团山人连获富矿,收益颇牛,继而购置厂位,建立炉房,冶炼大锡,扩大矿业开采,成为采、选、冶兼营的大商家。团山人富足一时,达到家族发展史的最辉煌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团山人纷纷把钱寄回家乡修造房屋,营造心中早己向往的诗意居所和精神家园。一时间,团山工匠云集,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三五年间,一座座青砖灰瓦的深宅大院拔地而起,各式各样的家园梦变为现实。有了宅院,见多识广,走南闯北,崇尚文化的团山人怀着对文人士大夫生活方式和精神情趣的向往,在宅院中装饰了各种形式的精美艺术,有了“修身”、“齐家”的各种伦理道德规范。团山的代表性建筑张家花园、秀才府、皇恩府、司马第、将军第等民居就是在这一时期修造的,其装饰艺术做工细腻、造型别致,为我们留下了一座民间艺术的博物馆。
团山民居丰富、有序的装饰艺术,继承和延续了我国自古以来的艺术创作方法,它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粉本在传统美术创作、传承和行会行业规范的实证。
三、粉本的发展与启示
粉本,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远古时期,原始艺术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上绘画的水涡纹、蛙纹、几何纹样等图案,是原始先民对自然和社会在意识形态中一种自由图像的表达,这些自由图像虽不能认为是艺术作品,但它们具有了画稿的性质和特征,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源头。
夏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器身上铸造有内容丰富、情节复杂、造型完整、技术精湛的图像,这些图像足以说明,在当时的青铜铸造业当中,有粉本作为艺术创作的重要媒介,没有粉本,饕餮纹及写实手法表现的车马、乐舞、战斗、狩猎等复杂场景和精美造型无法创作出来,并且完全可以推断,有一批绘画艺术造诣十分高超的匠师,专门从事青铜器具粉本纹样的设计,人们根据粉本的设计再制造成铜范,再由铜范浇筑成青铜器。
秦汉时期,社会进步,粉本开始在生活中广泛流行和应用,考古发掘的大量画像石、砖、瓦当当为有力证据,画像石、砖的绘画题材多以现实生活为表现主题,反映有历史故事、出行、宴饮、狩猎、农作、战斗等情节和场面,内容复杂,情节生动,意味着粉本多样化的发展和不断创新能力的提高。
魏晋佛教寺院壁画的兴起,更是极大的促进了粉本题材画样的创作与发展,从敦煌壁画画风的独特与多变中,我们可以得到深切的体会。
魏晋至唐,有不少名画家参与壁画绘制,其绘画的粉本在民间广为流传。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曹创佛事画,佛有曹(北齐曹仲达)家样、张(梁朝张僧繇)及吴(唐朝吴道子)家样”,“至今刻画之家,列其模范,日曹、日张、日吴、日周,斯万古不易矣。”。
粉本在唐宋广泛流传于画家师徒之间,未见稀罕可贵。后来,由于历史演变,战火兵灾,加上元以后文人水墨画逐渐成为绘画的上乘追求,粉本逐渐成为画工塑匠们赖以谋生的“秘宝”世代相传,很少流传到外,即使是同行之间,也因门户之见,互不相泄,粉本世人难得一见。过去的画家和鉴赏家又因建筑行业里的画师或艺人多出身劳动人民而轻视民间艺人的创作草稿,更不会去关心用于建筑装饰的被视为“工匠末技”的粉本的存在;封建社会中,同一行业的手工业者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不受外人侵犯或为了阻止外来手工业者的竞争和限制本地同行业手工业者之间的竞争,往往由同一行业的工人组成、建立起自己的组织——“行会”,行会定有行规,用以调节会内纠纷和对外进行交涉。行会有各自比较固定的行业区域,为了谋生的需要,行会匠人们也会到经济比较繁荣的地方从工,流动行业的机会,促使匠师与匠师之间有技艺的交流,匠师在生活的历练中见多识广,积累了丰富的艺术创作经验,粉本也在匠师的技艺交流中得到不断的完善和发展。民间艺术作品中许多变化的手法,各种题材内容和不同风格的造型装饰,是匠师高超技艺的展示,也是粉本发展过程的记录。
粉本是传统绘画的底本和基础,是步入艺术殿堂的桥梁。古人以粉本为“转移摹写”的对象,传统“子得之父,第得之师”的艺术教育模式,培养、诞生了历代的画家名师。传统最常用的习画方法是:教师首先选择或自绘好专为其弟子习画临摹的“粉本”,让其临摹,弟子从临摹中学习绘画的语言形式和前人的技法技巧。明清以来最为著名的课徒画稿是《芥子园画传》,它以“白画”的形式,总结了绘画的程式和规律,为后世的习画者提供了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历代流传的美术作品及民间遗存的众多装饰艺术俨然是我们学习的优秀粉本,学习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师其意而不师其迹,乃真临摹也”的古训。
当代文化语境的多元性和艺术教育模式,我们如何继承、发展传统绘画,粉本在其中起到的重要媒介作用,不容我们忽视。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项目批号:07Y20142)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岳仁译注,宣和画谱[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
[2]昆明日报,云南省建水团山“中遗”成功[EB/OL],新华网,2005-10-24。
[3]潘运告主编,云告译注,清代画论[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陈军(1972- ),女,汉族,云南个旧人,副教授,工
作单位:红河学院美术学院。研究方向:中国画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