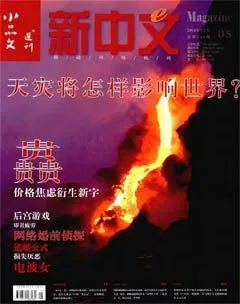被笑恐惧症
被笑恐惧症患者一旦感到自己被嘲笑,就如临大敌,像遇到危险而不能逃跑的动物,恐惧的肌肉紧张、全身木僵,仿佛立刻变成了木偶。
被笑恐惧症(geloto phobia)是一个心理学名词,最早由德国的MichaeI—fze发现并命名,其中词根geloto在希腊语中代表“笑”,而phobIa代表“害怕”,放在一起这个词就代表“对被笑感到恐惧”。MlchaeI Titze在自己的临床实践中发现一些病人很担心被取笑,他们会去观察周边的环境,寻找被嘲笑或被奚落的任何可能迹象。有时并没有明显的原因或证据,他们就会把环境中听到的笑声归结于在嘲笑自己,然后感到很不舒服。
匹诺曹综合征患者一旦感到自己被嘲笑,就如临大敌,像遇到危险而不能逃跑的动物,恐惧得肌肉紧张、全身木僵,仿佛立刻变成了木偶。下一次再进入社交活动之前,被笑恐惧者会感到惴惴不安,对预期可能出现的嘲笑感到担忧害怕。很多时候。由于这种恐惧、尴尬的预期过于强烈而难以承受,他们干脆自己“宅”在一个地方,宁可孤独无聊,缺乏人际交流,也不愿冒这种可能变成可笑的“木偶”的危险。
综合征临床研究
有些科学研究者试图以被笑恐惧者的早年成长经历进行解释。他们推测,这些被笑恐惧者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确实经常受到来自他人尤其是家人的奚落、嘲笑,这些家人通过嘲笑引发孩子内心羞耻恐惧的反应,从而达到控制他们行为的目的。
笑在他们的心中留下了阴影和创伤,对于这些人来说,笑并不代表愉快,而代表嘲笑和贬低。早前已经有研究证实,在青少年时期有过被同伴欺负和嘲笑经历的被试,更可能对模糊情境或者善意玩笑情境产生恐惧、愤怒的反应。
匹诺曹综合征的临床描述可谓十分生动,但针对被笑恐惧症更深入的研究在2008年左右才刚刚起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幽默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幽默研究杂志》在2009年出版了一期专刊,专门报道了对于“匹诺曹综合征”的各类研究。这其中有MichaeITltze关于临床症状的描述,有对被笑恐惧的测量学探讨,也有一些研究从实证的角度证实了被笑恐惧症的症状特点。
例如,瑞士苏黎世大学willIbald Ruch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发现,对被笑感到恐惧者和不感到恐惧者在解释模糊情境下的笑声含义时明显不同。实验中给这两类被试听一些笑声的录音片段,这些笑声具有不同的情绪含义,让被试者评价这些笑声背后的动机是什么。结果发现和对笑声不恐惧的被试相比,被笑恐惧者会更多地把由衷的愉快笑声评价为不愉快的。也就是说,即使是真正的开怀大笑,也很可能被他们知觉为发出笑声的人内心其实并不开心。
这个研究小组进一步就人际情境进行了区分,将笑的动机分为“善意的打趣”和“故意的嘲笑”两类,并让被笑恐惧者和普通被试者评价这两类人际情境。结果发现,被笑恐惧者很难区分哪些情境是善意的开玩笑,哪些是故意的嘲笑。虽然对于故意的嘲笑,两类被试都会产生羞耻、害怕和愤怒的反应。但对于善意的玩笑,被笑恐惧者相比普通人就显得有些敏感和过激了,普通被试者在这样的情况下会感到愉快和惊奇,而负性情绪的水平很低;而被笑恐惧者在此时却如同受到故意嘲笑一样,产生了羞耻、害怕和愤怒的反应。
综合征的影响
被笑恐惧者对笑“过敏”,因此属于“笑不得”的人,即使是朋友之间愉悦、善意的玩笑,也会被他们严肃紧张地对待,你本来出于友好的笑声也可能使他们“心里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实际上,研究已经发现,被笑恐惧症与人格特点上的内向和神经质有很大关联,提示我们这类人本身的情绪敏感性和波动性较高。这种紧张和提防,会使他们丧失掉许多人际交往方面的愉悦体验。此外,奥地利格拉茨大学的Papousek等人还发现,被笑恐惧者对负性情绪的调节能力较差,和普通被试者相比,他们更容易沉浸在带有恐惧、悲伤或愤怒的影片情绪中,主观放大这些情绪,并且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平复这些强度更高的负性情绪。
其实,被笑恐惧是一种条件化的过程:成长经历和家庭教育促使他们在“笑”与“负性情绪”之间建立了连接。实际上有研究发现,当不涉及可能指向自己的嘲笑时,被笑恐惧者对于玩笑和幽默的理解力与其他人没有差别。
被笑恐惧者并不缺乏幽默细胞和开玩笑打趣的智慧,他们所需要的只是感到人际关系的温暖和接纳,这样他们就会小心翼翼地从自我防卫的“保护壳”里探出触角,逐渐放松,让笑与恐惧、愤怒、羞耻一系列负性情绪之间的联系逐步消退,而在笑与轻松、愉悦之间建立积极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