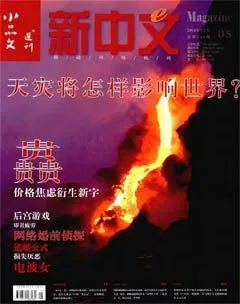精神赡养
“上孝养色”,“色”者,态度和谐恭敬也。以亲切和悦的神色对待父母,常使双亲心情愉快,方为“上孝”。
精神赡养,一般指在家庭生活中,赡养人通常要理解、尊重、关心和体贴老年人的精神生活,给老年人更多的人文关怀,不仅仅是指物质上满足老年人的生活,在精神上更要给予老年人慰藉,使其愉悦、开心。精神赡养背景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老年人的赡养内容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一些老年人在追求物质生活需要的同时,也注重追求精神生活需要。而且《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一条也规定了精神赡养的内容,这说明老年人满足精神需求有了法律的保障,如果老年人在未来的生活中得不到子女的关爱可以利用法律程序来迫使子女“支付”孝心。
中国老年人口约1.3亿,占中国总人口的10%。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6亿,到2050年,将达到4.4亿左右。
精神赡养表现形式
精神赡养的表现形式或方式主要有作为和不作为:为为形式的精神赡养,就是积极满足老人的精神生活需要。包括:为老人提供必要的精神生活的保障,满足老人精神生活的物质需求(即物化的精神赡养)。如购买电视机和其他必要娱乐器具等精神生活物品或者给付相应的费用;对老人进行亲情慰藉(即情感的精神赡养)。这里包括的内容和范围很广,有道德层面的和法律层面的,从道德层面看,非常广泛,要求很高,可以说是没有止境的。但总的要求是:尽量做到对老人无微不至的关怀,使老人常常感到欣慰。从法律层面看,对老人必要的探视或看望等,是不可缺少的。
不作为形式的精神赡养,就是不对老人制造精神痛苦或精神虐待。包括:在行为上不伤害老人(如侮辱行为和动作),更不能殴打老人;在言语上不伤害老人(不讽刺挖苦老人),更不能辱骂老人;不能限制老人生活自由和人身自由。如老人再婚,找伴侣、交朋友,参加文艺体育活动,以及对其他精神生活的追求,都不能进行限制。从其性质看,不作为形式的精神赡养,主要是法律层面的。也就是说,不作为的精神赡养,要求赡养义务人通过不作为的形式来实现精神赡养。如果作为后,往往会触犯法律,情节严重者,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精神赡养诉讼
首先应当肯定,法律对不履行精神赡养的法律责任确实规定得不具体。而且,对精神赡养的判决和执行,确实要比物质赡养的判决和执行复杂得多,麻烦得多。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精神赡养的可诉性。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婚姻法》规定了子孙对父母等长辈有赡养义务?《年人权益保障法》明规定:赡养就是“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的慰寂”等《婚姻法》没有排除精神赡养,《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有精神赡养。
精神赡养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或一种道德义务,也是一种法律义务。对于需要对老人提供精神赡养的作为(即应当作为而不作为),包括提供精神需求上的物质保障和精神慰藉,属于给付之诉的,老人可以提出给付之诉;对于对老人进行精神虐待或限制老人人身自由(包括精神生活自由)的行为(即对于不应当作为而作为),属于侵权的,老人可以提出排除妨害和停止侵害之诉。
虽然有些精神赡养(主要是道德层面的)不可诉或难以判决,但不能因此而否认整个精神赡养的可诉性。精神赡养的范围很广,一切事关老年人的精神愉悦与否的赡养内容和方式,都可能涉及精神赡养问题。因而,至少下列几个方面的精神赡养完全具有可诉性:物化的精神赡养;必要的探望;子女有条件者,老人要求与子女同居;子女“分爹分妈”赡养,当子女有条件时,老人要求夫妻同居者;子女限制老人精神生活或自由,老人要求排除或停止侵权者;子女对老人进行精神虐待,老人要求停止侵权者;等等。
精神赡养中的物质供给需要通过诉讼解决。否则,老年人只能满足物质上温饱生活的需求,精神生活的需求就得不到法律保障。不仅物化形式的精神赡养需要通过诉讼解决,单纯的精神赡养或wadxZ00XAGAkjiuWWm4LSQ==情感慰藉也需要通过诉讼解决。父母要求看望或与子女共同居住,但子女虽然有条件而拒绝,对此,也只能通过诉讼手段解决,否则,老人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保障。
对于子女对老年人进行精神虐待或者限制老年人精神生活自由的行为,不仅具有可诉性,而且有的也只能通过诉讼,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所谓精神虐待,是指使受害者在精神上及心理上倍受困扰的虐待行为,例如打骂老人、当众或私下羞辱老人、隔离或孤立老人,不准老人与家人或朋友来往、控制老人的行动、干扰睡眠,等等。
精神赡养解决方法
精神赡养处理涉及精神赡养诉求的纠纷,应更多地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
从立法层面完善对老年人的权益保护,在《婚姻法》或其他保护老年人权益的相关法律中对精神赡养的具体要求以及不履行精神赡养的法律责任予以明确规定;充分发挥政府、民政、村委会等部门的作用,在诉前有效消解赡养纠纷,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同时,通过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在社会上形成尊老敬老的良好风气;加大调解力度,强化诉调对接。对赡养纠纷,尽量以调解方式结案,从道德义务与法律责任结合的角度,多做被告人的说服教育工作,促使其主动履行义务。发挥民调组织的作用,并积极指导调解员开展调解工作,化解赡养矛盾;即使以判决方式支持精神赡养,应当加大说理的力度,充分阐述精神赡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仅起到教育赡养人的目的,还起到法律宣传的作用。判决后,尽可能对案件进行回访,用人性化执法去说服教育赡养人;加大对拒不履行义务者的处罚力度,可以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提高赡养人履行义务的主动性。
精神赡养执行困难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精神赡养只是作出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对赡养人不履行精神赡养的义务,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并未作出规定。
法律一方面支持了精神赡养的请求,另一方面却遭受着难以执行的尴尬。审判实践中,许多老人是赢了官司,却输了情感,反而可能使双方矛盾更为激化,法院固然判决支持了其诉讼请求,但诉讼的最终目的并未实现。精神赡养,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沟通、慰藉,即便是强制执行,但对于解决纠纷显然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试想,法院判决赡养人每月承担探望、照料、陪护老年人的义务,但法官总不可能每个月强拉着他去探望、照料,陪老人聊家常吧。即使是这样的强制执行,其执行效果可想而知,甚至对老年人造成的伤害更大,还不如不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