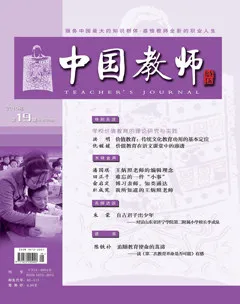书道二十讲(十六).书道之品格
2010-12-29 00:00:00程方平
中国教师 2010年19期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是“道法自然”,但什么是道,什么是自然,却缺少具体的说法和标准,在很大程度上要凭借创作者和欣赏者具体与综合的感受。简而言之,我们于今认识的所谓“道”主要是指反映真理与规律的道理,是经过认识与提炼的思想;而所谓的“自然”则主要是指变化莫测、不可捉摸、不以人们的意志所左右的客观世界。基于此,所谓的“道法自然”,就是明确“自然”是现实、是本体,而“道”是要遵从其基本的变化规律,并加以提炼和概括的道理。在这样一种相对模糊和混沌的文化认知背景中,要论及书道的品格,自然有相当的难度。但作为历代有作为的书道探索者,相关的探索依然有其重要的借鉴价值。
古往今来,所谓的“品”即品格、格调、品质、等第、韵致等的简称,都具有精神的追求和具体的标准。书道之品格主要是依据来自历代学界和书界的共识,它既是行业标准,又是社会欣赏的标准。其思想和做法源于人品、文品等已有和流行的概念,既有时代色彩,也反映了普遍的规律。
在南北朝的齐梁时代,有颍川(今河南长葛)人钟嵘作《诗品》(公元513年),在刘勰《文心雕龙》之后第一个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品评诗歌的优劣得失,为当时及后世诗风的优化作出了突出贡献。据《诗品·序》所言,当时虽然诗风日盛,但是十分混乱,缺少品评的标准,致使诗坛显得混乱无序。为此,钟嵘就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先例写成此书,欲纠正诗坛思想和标准混乱的局面,共涉及两汉至梁诗人122位,包括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钟嵘的《诗品》不仅对后代的诗歌批评有很大影响,对唐司空图,宋严羽、敖陶孙,明胡应麟,清王士祯、袁枚、洪亮吉等在观点上、方法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启发,对书品评判也有极为重要的借鉴与影响。
钟嵘认为:“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由此看来,他十分强调赋和比兴的相济为用,即强调内在的风力与外在的丹采应同等重视,需要整体判断。他不仅反对一味地追求形式、弱化内容;又十分强调诗人独特艺术风格的确立;并注重在史诗源流发展的大背景中评判诗人的贡献,提出了言在、情寄、风骨、雕润、词采、音韵、动心、清便、宛转,以及才、文、气、秀、质、味等相应的角度、标准和概念。《诗品》不仅在诗坛影响巨大,对书道品格的评判也有直接、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与钟嵘几乎同时,仅比其小约20岁的南阳新野人,时任南朝梁度支尚书的著名文学家、书家庾肩吾(487—551)著述了中国书道史上第一部品评书道优劣的专著《书品》。在他之前,虽有南朝宋王献之弟子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记72人),有南梁袁昂奉敕撰的《古今书评》论及古代书家25人,有萧衍的《古今书人优劣评》等,但由于都只作了简要的风格介绍,所以还不能取代庾氏此书的地位。该书仅一卷,载汉至齐梁能书真、草者凡123人(序言128人,当为版本传承之误),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