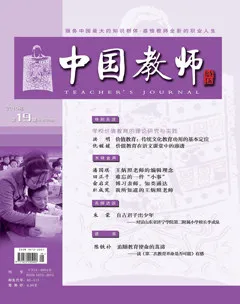价值教育:传统文化教育功用的基本定位
学校价值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逐步走出了“花果飘零”的惨淡期,出现“一阳来复”甚至“三阳开泰”的局面。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形式的传统文化教育也大大方方地出现在世人面前。其原因复杂,既有政府的号召,亦有学者名流的推动,更主要的是家长和民间组织自发的推动。由于动力复杂,从而导致传统文化教育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从名称上看,有诸如“儿童读经教育”“中国古典文化教育”“儿童国学经典导读”等;从形式上看,以学校教育为主,家庭、社会也积极参与其中,甚至还出现过全日制现代私塾;从举办者和参与者的目的来看,也未尽相同。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不同的教育理念所导致的。那么,传统文化教育的追求到底应该是什么,如何给它以准确的功能定位,是每个教育者不得不深入思考的问题。本文试从价值教育的视角,谈谈传统文化教育基本定位问题。
一、传统文化教育功用的核心是价值教育
由于传统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与智慧的结晶,对教育者来说,传统文化有不同的功用,因此也就有不同的功能定位。目前对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功能大致有这样几种认识:一是语言文学方面的知识教育,传统文化首先集中表现在一套文化典籍之中,教育者希望通过经典阅读,使学生更多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掌握祖国优美的语言文化,积淀深厚的文学修养,并通过锤炼语言,运筹气势,提高写作水平。二是心理教育,中国儒释道思想里面蕴涵着丰富的心性修养思想与心理调解方法,学习传统文化,可调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尤其是儒家的积极进取、刚健有为,道家的自然无为、清虚自守,佛家的大彻大悟、普渡众生的思想,为人们提供收放自如的人生价值体系与心理自卫系统,可有效地预防和疗治许多心理障碍的产生。三是习惯与品德教育,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如何做人的规范体系,教育者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学习,塑造儿童良好的行为习惯,变化气质,穷理尽性,培养做人的道理。四是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由于文化经典为中国人历来所倡导、弘扬,因此通过传统文化经典学习,可使学生从小就能够走进我们的历史,体认祖国的传统,亲炙我们的祖先,认同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形成固有的民族精神。[1]
这些观点确有道理,有利于丰富我们对传统文化整体教育功能的认识。但站在价值教育的立场,笔者认为,尽管传统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决定其功能的多样性,但从“体”与“用”的关系来看,其核心功能一定是价值功能,传统文化教育一定是价值教育,其理由起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传统文化核心就是一套价值系统。对于传统,可谓众说纷纭,但总抱有情感与思想上的倾向性,与“革命”时期不同,和平建设时期对于传统总是带有“善”的愿望,这就是钱穆先生所谓的“温情”与“敬意”。由此可见,尽管传统中有“精华”与“糟粕”并存的东西,但前者才是我们当下真正所指,这个东西就是民族的基本精神。中华民族精神内涵丰富,但无疑注重“人”字,中国人的学问是做人的学问,中国人的精神在于如何做人方面,理想是内圣外王,核心是仁爱,路径是修齐治平:从立己始,然后推己及人。这样便形成了一整套为人处世的价值系统。比如,有人把中国人的文化核心定位于“和合”,包括合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方面内容,它包含了人类不同文明主体在解决人与自然、社会、自身所应该坚守的基本价值准则。另一方面,现代价值教育需要传统文化的滋养。石中英教授认为,“价值教育”是有关人们如何行为才是“正当的”“对的”“好的”或“高尚的”教育,是有关人们行为正当性原则的教育。它包含人类基本价值、民族优秀传统价值、社会主流价值三大方面,缺乏这种优秀传统价值的教育,我们的教育就没有中国特色、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就不能培养出真正的“中国人”。[2]
明确传统文化教育核心功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可以端正传统文化教育中一些偏离“中心”的现象,也能够丰富现代价值教育的内涵,提高价值教育的实效性。
二、传统文化为价值教育提供一套价值准则
中国传统文化从纵的方面讲有五千多年不间断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从横的方面讲主要有儒释道等多家并存,可谓内涵丰富。但作为教育者来说必须要把握其中的精髓,也就是其中的基本精神。2006年,胡锦涛在耶鲁大学演讲时把中国文化概括为四个“注重”:第一是“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第二是“注重自强不息,不断革故鼎新”;第三是“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第四是“注重亲仁善邻,讲求和睦相处”。[3]这些内容集中概括了中华民族在处理内外事务中所奉行的基本价值取向和价值立场,强调了文明的多样性。李宗桂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包含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贵和尚中、刚健有为等基本精神,重在以哲学的视角来概括中国人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思维习惯和精神品质。这些概括可以帮助我们从宏观层面理解中国文化的价值追求。[4]
从中观层面看,顾明远先生把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进一步提炼为天人协调、自强不息、贵和尚中、矢志爱国、敬老爱幼、诚信待人、勤劳节俭、慎独自爱等八个方面。[5]这种概括更加关照到教育需求,有利于教育者准确把握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主要内容,防止挂一漏十、以偏概全。
从微观层面看,民族精神所孕育的价值内容不能停留在抽象层面,务必要落实到个人层面和实践环节,要有典型而生动的例子做支撑,因此,应当对中观领域的民族精神进行进一步的分解。对于中小学来说,我们需要传承的民族精神诸如:公正无私、嫉恶如仇、诚实笃信、不尚空谈、戒奢节俭、防微杜渐、三省吾身、先人后己、豁达大度、温良恭俭让等修身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敬业乐群、公而忘私、见利思义的奉献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情操等。这些精神品质凝结在民族的记忆中,孕育着丰富生动的价值品质和价值观念,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价值教育资源。
当然,在具体的教育场景中,由于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体现在许多方面,教育者可有针对性地进行挖掘和整理。如有所小学结合自身实际,从众多的中华传统文化资源中选择了自认为最具代表性、最有针对性、最为根本的三个方面——“爱国、勤俭、礼仪”,挖掘其中的价值资源;也有的学校把传统文化精神提炼为“孝”“仁”“勤”“忠”四个字,以此为教育的重点,逐步延展。具体做法这里不做评论,但从总体思路上说,学校在挖掘传统文化价值时,不可能完全一致,允许有自己的认识和侧重;也不可面面俱到,但一定要把握其精髓。
三、价值教育视野下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要求
价值教育视野下的传统文化教育与以往的类似于“儿童读经教育”有着一定的共性,都必须要了解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宝贵的精神财富,记住古圣先贤为人处世中所坚守的高尚的价值准则。但价值教育的要求不止于此,它的目的不仅在于记诵经典知识,更在于培养优良的价值品质,形成具备一定价值观念、价值态度与情感、价值理性、价值信念及价值行动能力的价值主体。[6]综合起来考量,笔者认为,在价值教育理念指导下,学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应遵循如下几点原则。
第一,确立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和方法。传统文化产生于古代,所凝缩的价值原则总体上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但经典总具有跨越时空的永恒性。这就要求广大教育者既不能过于保守、以古非今,也不能苛求古人、以今非古,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就是前文所述的保持内心“温情”与“敬意”。这种态度的真意不是说传统不能批判,而是指认识评价传统文化要在基本尊重的基础上开展,保持必要的文化自信心,以实现文化复兴为目的取向。在保持“温情”与“敬意”的基础上,认识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即采取冯友兰先生所倡导的“抽象继承法”。意即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时,要分清其中的“抽象(一般)意义”和“具体(特殊)意义”,继承其抽象(一般)意义,充实其时代内涵,赋予其新的涵义。
第二,开展经典教育一定要注意方法的多样性,将传统优秀教育方法与现代科学教育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倡导儿童读经运动的王财贵认为,读经有这几个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越早越好,越多越好,越简越好(主要就是读),快乐原则。这样一来,学习经典就简单地变成了跟读与背诵。的确,由于古代教学条件、设施、环境所限,不可能有更多的方法,但今天时代不同了,用一种单调的方法无法给儿童带来快乐,甚至会导致对经典的厌倦。因此有人认为,除了跟读之外,还有一种重要方法——吟诵,根据文字本身的节奏与音律读出趣味。同时,还有六种辅助方法:书空、影写、描红、摹写、默写和书法。另外,读经不能不讲解,小学阶段的讲解主要有两个重点——以字意与故事为主。以字意为主是指结合六书与训诂,给儿童讲解所学文章中文字的含义;以故事为主是指结合人伦与道德的基本规范,通过图文并茂的故事,使儿童初步把握做人的基本道理。[7]有的学校在传统文化教育中特别注意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组织诵读比赛,参观名人故居,做到形式多样化。在教学手段上,通过播放音乐、动画故事、自制课件等多种辅助方式,力求形象生动。通过情境化、故事化、生活化的教学方法,拉近传统和现代的距离,收到较好的效果。
第三,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以培养具备一定价值品质的价值主体为最终目标。循序渐进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不容易。一个人价值品质的形成大致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先学会家庭、亲人间的规范、礼仪,然后再逐步推延到朋友、社会;先做人做事,然后学文;先启蒙养正、形成行为习惯,然后再逐步上升为价值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