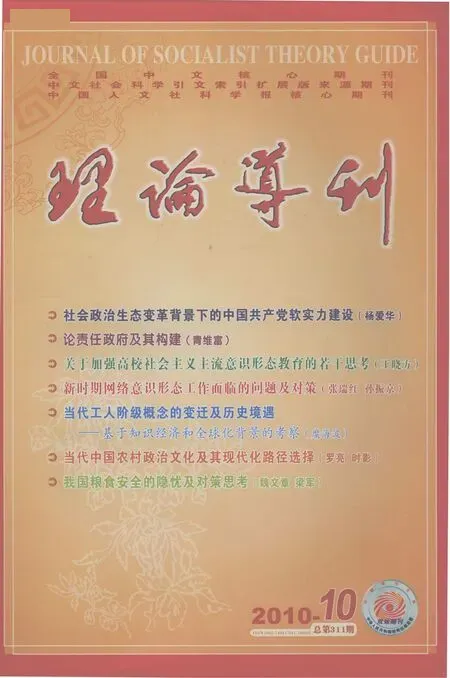现代解诗学视野中的穆旦诗歌
文广会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西安710068)
现代解诗学视野中的穆旦诗歌
文广会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西安710068)
从现代解诗学的角度,考察穆旦诗歌在中国现代诗学的重要地位与其实际的诗学成就形成矛盾的深刻原因。通过对诗人穆旦的个案分析,在理论与实践的错位中重新认识现代解诗学内涵的不足并进行相应的理论完善与补充。
穆旦;诗学地位;现代解诗学;新诗
(一)
中国新诗从1918年《新青年》发表胡适、刘半农等写作的第一批白话新诗到现在,已走过了九十多年的历史。就体裁而言,诗歌变革的步伐最为彻底,从文言到白话,从格律谨严到形式自由,新诗走过了一条曲折而辉煌的道路。
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在对新诗历史的清理中我们发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大新诗主潮相互融合又颉颃互竞。在对现代性追求的矛盾与演进过程中,以往处于诗歌边缘的现代主义诗潮得到更多的重视和青睐,其发生、发展、变构的演进线索清晰可辨。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潮渊源、发展趋势的研究则相对模糊、沉寂得多。这或许是现代性视域下的研究视角造成的遮蔽。
现代主义诗潮以20世纪20年代李金发领军的象征诗派为肇始,历经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诗派、戴望舒为主帅的现代诗派、穆旦为旗帜的中国新诗派、再到新时期文学先声的朦胧诗、80年代众声喧哗的第三代诗等多个诗歌流派的争奇斗艳、各领风骚,共同构成了流光溢彩、芬芳怡人的诗歌百花园。而以穆旦为首的中国新诗派则在其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就像中国新诗派的诗歌理论家袁可嘉认为的那样,这群诗人们将时代风云、民族忧患和个人生命体验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人生与诗意交互叠合的“综合”效果。这种综合即“象征、现实和玄学”的综合:“现实表现于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象征表现于暗示、含蓄,玄学则表现于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及机智的不时流露。”[1]这其中,穆旦便是最能代表中国新诗派艺术特质和思想开掘的一位诗人。
穆旦在上世纪40年代就是很受欢迎的青年诗人。穆旦诗作的艺术风格、思想特质、诗学价值等,在当时就得到了他的同学、师长和诗友们充分的赞赏和肯定。王佐良的《一个中国诗人》、周珏良的《读穆旦的诗》、唐浞的《搏求者穆旦》等一批文章为穆旦诗歌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由于特定历史的原因,诗人在1949年新中国建国后不久,便很快停止了纯真的诗的歌唱。那正是诗人黄金般的年华,却不得不转而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对外国优秀诗人的诗歌翻译当中。后来仅留下由于对缪斯割舍不下的深情而散存的少许诗作。一个伟大的诗人黯然跌落于历史的风尘。
在1978年后的新时期文学进程中,以前受到压抑和挤压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重新得到了重视和清理。穆旦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其卓异、鲜明的诗学特质获得了几乎一致性的高度评价。1986年《穆旦诗选》出版,1987年纪念文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面世,1996年李方编的《穆旦诗全集》推出,1997年再次结集纪念文集《丰富和丰富的痛苦》,2006年12月收集最为详尽的《穆旦诗文集》[2]与广大读者见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对穆旦的怀念和对穆旦诗歌的研究是不断向前推进的,其开掘的深度、铺演的广度让我们切实了解了一个真实、完整的诗人穆旦。
与之相随的,是对以前屡遭压抑的现代主义思潮历史的清理与挖掘逐渐占据了新诗研究的中心,象征诗派、新月诗派、现代诗派、中国新诗派等都得到新诗现代性追求的体认,获得高度的评价。穆旦的诗歌恰处在现代主义诗歌发展的顶峰上,承上启下,甚至在二十世纪中国诗歌大师排行榜上高居榜首。他对新诗意蕴、语言、形式的革新精神为朦胧诗以来标榜现代主义的诗人们所继承。他们奉穆旦的诗为圭臬,在诗艺革新的路途上高歌猛进。穆旦现象成为诗歌史上颇有意味的诗歌事件,对穆旦诗歌的重新审视和细读就变得十分必要。
穆旦生前只出版过三部诗集:《探险队》、《穆旦诗集(1939——1945)》、《旗》,他的全部诗作还应包括晚年创作的《冬》、《停电以后》等和1949年前未收入诗集但散见于报刊的数十首诗。建国初期创作的如《去学习会》、《三门峡水利工程有感》等则艺术性不是很高。但是穆旦的一部分诗作如《五月》、《还原作用》、《智慧的来临》、《赞美》等至今仍能给人不小的震撼。《五月》中仿古典的七言与自由体的诗句交错并行,所产生的诗的张力让我们惊叹其诗体形式探求的魅力。穆旦的诗歌自成一个丰富而独特的世界,其主题内涵既有对民族命运苦难承担的体认,又有对个人自我意识的深切呼唤,也有对现实、时代、真理的严肃拷问,其诗作主题呈现出繁复多变的意蕴美,并与诗人卓异的诗艺技巧结合在一起。戏剧性张力的刻意营造,并置结构所凸显的形式感,诗歌意象的着意选取对诗人想象力的承载与跃升,这一切既使穆旦有别于时代浪尖上强调战斗和力的主流诗人们,又使其迥异于中国新诗派的其它诗人们。此外,穆旦诗歌的又一特色是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资源承续的广泛与深入,如对艾略特、奥登、叶芝等诗人的借鉴。王佐良站在肯定的立场上说:“穆旦的胜利却在于他对古代经典的澈底的无知”,诗人“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3]诗人取法异域和对新诗现代性的追求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作品与读者之间巨大的审美距离。为此需要搭建一条引领读者到达诗人深邃诗歌美学领域的桥梁,填补诗人审美追求与读者审美心理距离之间的鸿沟,以使诗作的魅力得到展现和赓续。
(二)
1925年,李金发《微雨》的出版应该是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集中的《弃妇》、《夜之歌》、《故乡》等诗作与当时诗坛流行的直白、质朴的充满感伤情调的诗风是那样的不同。其设喻的晦涩、意向的怪诞、语言的半文半白给评论家和读者都造成了极大的阅读障碍。如何理解和阐释这样一批象征诗歌作品呢?随后,现代派诗歌的崛起,特别是卞之琳的《尺八》、《圆宝盒》等一批内蕴丰富的诗作引起的批评家们的极大兴趣。朱自清、李健吾都对卞之琳的《鱼目集》中的一些有一定阅读难度的诗如《圆宝盒》、《距离的组织》等做了自己精到的分析,有意思的是作者本人对自己诗作的说明与批评家的阐释在美学上保持了一定的歧异。于是,在你来我往的文章往还讨论中,以诗歌文本的解释为中心,以清除诗人和读者之间的心理审美距离为目的的现代解诗学也就应运而生了。朱自清的《新诗杂话》便是诗人追踪诗歌发展时对出现的新的诗艺特征的诗作思考所得,奠定了中国现代解诗学的基石。随后,又有闻一多、朱光潜、废名、唐浞、袁可嘉等人的理论概括和解诗实践,共同为新诗艺术魅力的铺展和呈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丰富了现代解诗学这种新的诗学主张。
现代解诗学在当代的大力提倡者和推行者孙玉石先生特地提出了解诗的三个基本原则。首先要“正确理解作品的复义性,应以本文内容的客观包容性为前提。”其次,“理解作品的内涵必须正确把握作者传达语言的逻辑性。”再次,“理解或批评者主体的创造性不能完全脱离作者意图的制约性。”[4]这三条原则对解诗的对象、解诗的可能性及其限度都做了必要的理论规定。现代解诗学在孙玉石的理论倡导和文本实践中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最初的成果展示是1990年出版的《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其后有2002年出版的《在北大课堂读诗》,2007年11月的《中国现代诗导读(1937-1949)》、《中国现代诗导读(穆旦卷)》等,紧跟着再版了《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7)》(再版时更为现名),最为重要的是孙玉石解诗学理论专著《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的问世。现代解诗学至此成为中国现代诗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中,穆旦诗作的解释专成一卷,可见对穆旦的重视。解诗的过程就是从大量的优秀诗作中拣取意蕴层次丰富、诗艺技巧繁复多变造成读者甚至诗评家理解困难的那一部分按照现代解诗学的原则进行细读、赏析的工作。那么,在解诗实践中对穆旦诗歌的解释是否如理论阐述的那样有效而自足呢?
在《中国现代诗导读(穆旦卷)》中,解诗者对穆旦的45首诗歌进行了细致、详实的分析。在这些文章中,虽然有效地贯穿了孙玉石所提山的三个解诗原则,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忽略了诗歌自身的核心艺术价值即诗歌的独创性问题。在解诗者眼里,这些诗都是高标独举的,文学性毋庸置疑成了默认的前提。只需在诗的审美意义上做出有力恰当的说明就是了,很少去追究诗歌的诗学资源问题。如果一首诗模仿大于创造,不管它是否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有无重要的文本意义,那么对这首诗的美学价值重新进行考量就是必要的了。
江弱水在中西诗歌比较视野中就认为需要检视穆旦诗歌“非中国性”的负面意义并对穆旦诗歌进行“重估”。他认为穆旦的诗表面显得“精警、挺拔、富于穿透力”,[5]语言之间极具张力,一般读者会默认他为首创,以为是攀登上了中国新诗的新的顶峰。但从诗歌资源发生的角度对穆旦诗的艺术成就重新作一梳理、考辨、定位,便会看到穆旦的诗作多有对西方现代诗人如奥登、叶芝、艾略特的诗作成句的化用,又刻意疏离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致使其缺乏包容、广阔的诗歌视野,没有了中西诗学的会通,虽心仪于西方现代诗的艺术风华,却又走不出艾略特等人的阴影,这都对穆旦诗歌已经获得的高度肯定打上了大大的问号。其实对穆旦诗歌评价的分歧就在这里。穆旦对西方现代诗学的借鉴是否超越了“模仿”而注入了自己的诗歌力量。王家新从穆旦诗歌“对现实发言的能力”和诗作中“敏锐的思辨能力”、“内省性质”及在语言、文体上“使汉语诗歌呈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等方面为穆旦诗学的价值做了有力的辩护。[6]但是,穆旦的诗学问题并非一两篇文章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
客观地说,穆旦诗歌在当时世界性的现代诗歌潮流中,紧跟时代步伐,唱出了时代的强音,同时也丰富了中国现代诗学的艺术宝库。相比于中国同时代的诗人们,穆旦无疑是他们中最优秀的诗艺者之一。穆旦诗歌最大的贡献是在其对中国新诗语言的深度开掘上。他习惯于将几组互不关联的词语强行扭结,造成一种奇异但不生硬的句式,词语的着力点既非能指,又非所指,而是词语与词语之间构成一种互文性情境,从而完成对主题恰切的表达。以《反攻基地》中的四句为例:
过去的还想在这里停留,
“现在”却袭击如一场传染病,
各样的饥渴全都要满足,
商人和毛虫欢快如美军
“过去”、“现在”就其能指而言,无特别之处。但一二句联系起来看,两词的意义均得以拓展,“过去”不仅仅指过去的时间,事物的历史,而是有具体所指,指抗战前的中国民众对土地的挚情。战争的烽火让“现在”的人被迫丢弃家园,各种的贪欲没有尽头,这是一切苦难的根源,“商人”与“毛虫”并置的结构产生了戏剧化的效果。以此同时来形容美军别有深意。商人为利益而生,毛虫为温饱而活,他们对己身之外的事情漠不关心。美国开始在战争中的态度既是如商人和毛虫般短视,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其中隐含着诗人强烈的不满和愤慨。穆旦大量的诗作对语词的运用非常讲究,诗人很少直抒胸臆,而是通过语词外延的扩展、深化来表述诗人的深层情感。
无疑穆旦在中国新诗史上是有其独异的贡献的,从上面的诗句中我们看到:对语词的表现,对诗的并置结构的运用,对诗歌主题的表现与开掘等都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典范例。他对诗歌形式的探求与对诗歌内容的表达有效地结合起来,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穆旦在与世界现代诗潮的同声合唱中,有自己的声音但没有形成创造性的艺术成就。止步于西方诗人的借鉴而不是创造,拒斥中国古典诗学的有益养分而不是转化,这些都造成了穆旦诗艺水平一定程度上的单薄。从国内穆旦诗歌的研究状况看,很多论者过多地执着于对穆旦诗歌形式本身的关注,结合其在中国新诗谱系中的位置不断加以阐释,没有正本清源,从而造成了其诗歌艺术成就与他在中国新诗中的崇高地位的严重脱节。实则考察一个诗人的历史地位,应该兼顾中国和西方两个诗学坐标系,又有历时和共时的综合比照,方能全面地认识一个真正的诗人。
中国现代解诗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穆旦带来的诗学财富的一个契机,对一个诗人的最好纪念,不是把他放在神圣的位置供人瞻仰,而是从心灵深处理解诗人的精神品质,在历史真实的层面感受他的苦痛与挣扎,欢笑和泪水,因为诗人更愿意真实地活在我们中间。
[1]陈林.穆旦研究综述[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1,(2).
[2]李方.穆旦诗文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曹元勇.蛇的诱惑[C].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7).
[4]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2.
[5]江若水.中西同步与位移[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128.
[6]王家新.为凤凰找寻栖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08、209.
[责任编辑:黎峰]
I 207.2
A
1002-7408(2010)10-0106-03
文广会(1963-),男,西安人,陕西青年职业学院人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高职教育教学和文学研究工作,研究方向:美学、文学理论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