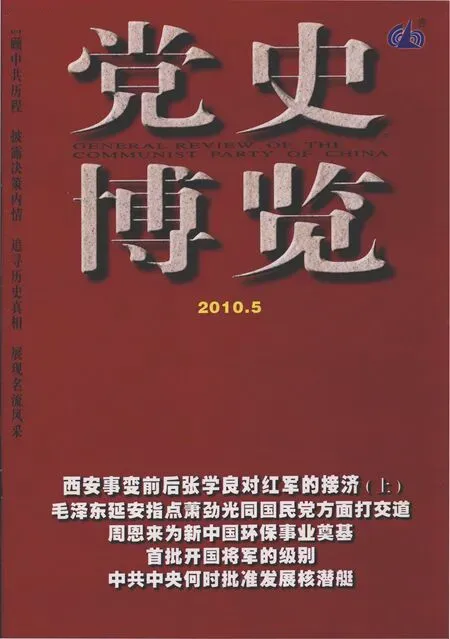毛泽东的秘书柴沫之死
○散木
毛泽东关于柴沫自杀的批示
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书记载,毛泽东于1972年11月4日、12月5日曾分别在反映柴沫情况的两份来信摘报上批示说:“纪、汪酌处。”“纪、汪处理。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这里的“纪”是指纪登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汪”则是指汪东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至于来信中所提到的柴沫,早在延安时期曾任职于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并且是毛泽东的秘书。自杀之前,柴沫曾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长、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秘书长和党委副书记。
1962年,柴沫参加了田家英率领的赴湖南的农村调查组。调查组根据实际情况,向中央反映了农村的现状,主张实行“包产到户”,田家英和柴沫等因此受到毛泽东的冷落。1966年“文革”发动后,陈伯达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组织了对柴沫的批判,并指责他是 “田家英的人”、搞所谓“秘书长专政”等。 此后,随着“文革”的升级,对柴沫的批判也愈演愈烈。1966年9月4日,柴沫在被隔离审查之后,绝望自杀。此后,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亦告解散。
上述反映柴沫情况的两份来信摘报及毛泽东的批复,一份见于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972年11月3日编印的《要信摘报》第270号,摘报说:原马列主义研究院学习班郭冲等八人及该院原秘书长柴沫的妻子王若林写信给毛主席,信中说,1966年5月,陈伯达曾三次来院讲话,说柴沫不听他的话,不走他的门子;陈伯达还勾结关锋、戚本禹等,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柴沫打倒,从此大会批斗、小会追逼,白天监督劳动、黑夜轮番审讯,使柴沫的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很大的折磨,乃至被迫自杀。后来经过对柴沫的历史和他生前全部工作的反复调查,证明他是党的一个好干部。现在陈伯达已揪出两年多,该院学习班也办了一年零七个月了,可是对陈伯达迫害柴沫的罪行还没有得到清算,对柴沫本人也未作出正确的结论。为此,写信人恳请毛主席责成有关部门为柴沫平反,恢复名誉,并作出正确的政治结论。第二份来信摘报,见于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972年12月2日编印的《来信摘要》第858号,摘要说:王若林11月30日来信,她对毛主席的批示表示无比感激,军代表也已向她传达了关于柴沫问题的结论,肯定柴沫是受陈伯达等的迫害,同时又指出柴沫因系自杀,不够党员的条件,应受到党内除名的处分,而王若林认为柴沫是在陈伯达等的逼迫下被迫自杀的,并非是他畏罪于党,故不应给予党内除名的处分。显然毛泽东是同意王若林的意见的,他还愤愤地发问:“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
按理说,有了毛泽东的明确批示,柴沫问题的处理似乎应该不成问题了,然而一直到了“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才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柴沫的骨灰安放仪式。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主持仪式,原研究院副院长胡绳则在悼词中揭批了陈伯达的罪行,正式为柴沫申冤昭雪,恢复名誉。
柴沫其人
柴沫,原名厉全起,1917年9月出生于浙江慈溪县厉家村 (今属慈溪市掌起镇)的一个农民家庭。
柴沫早年因家境困难,初中只读了一年就随族叔到上海一家烟纸店当学徒。他不甘心失学,经常在劳作之余看书到深夜。长时间在昏暗的灯光下夜读,结果眼睛高度近视。柴沫爱看书,并多方寻找进步书刊,无意中被当时的“左联”作家金灿然(后为中华书局负责人)发现,金灿然让他当了一名为“左联”销售出版物的报童,这样使他随时可以阅读“左联”作家的论著。柴沫当时还喜欢上了世界语,那时有许多青年热爱这门人类实现大同的语言工具。他因敬仰世界语的创导者柴门霍夫,因而改名为柴沫。
柴沫在上海苦读不到一年,后因生活困难,又返回家乡务农,其间还曾在家乡的小学教书。1936年,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宁波各界也成立了救国会,柴沫参加了。抗战爆发后,柴沫又参加了宁波的抗日宣传队,并组织战时流动宣传队,宣传抗日。1937年冬,柴沫来到延安,随即进入陕北公学,开始得以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1938年1月,柴沫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柴沫被分配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工作,开始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抄写文稿、查找资料等。1941年夏,为了克服党内严重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加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由陈伯达主持 (一说毛泽东兼主任),柴沫是成员之一。在大生产运动中,柴沫还曾负责安排中央领导同志的劳动和生活。
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期间,柴沫在很多方面受到了毛泽东的教诲。他认真工作,勤学苦练,在思想水平和写作能力方面都有所提高。
抗战胜利后,柴沫离开延安,奉命随中央大队向东北进发,抵达承德后,任热河省研究室主任。当时,他曾细致地了解了受日军残暴统治达13年之久的当地人民的疾苦,在省委领导下执笔起草了 《热河省发动群众的指示》。毛泽东看到这份文件后,批示“这个指示可以应用于东北”。不久,柴沫调任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秘书处长兼研究室主任。鉴于当时蒙汉共居的塞北林西蒙区因受敌伪残余势力挑拨,不断发生民族纠纷,柴沫经常深入这个地区进行调查,撰写了《内蒙人民解放的道路》一书,用以揭露敌伪残余势力的罪行,阐述蒙古族人民奋斗的方向,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天津解放后,柴沫调任天津市军管会办公厅秘书处长,不久又随大军南下,转任中共湖南省委秘书长。广东解放后,他响应中央关于要部分老干部转入工矿企业、交通运输方面的号召,到广州任广州铁路局副局长。1956年,又调任铁道部科技局局长。其间曾在《中国青年》发表 《试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根本问题》一文,激励广大青年为祖国的科技事业而奋斗,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1959年,柴沫进中央党校学习。因工作需要,在学习尚未期满的1961年,经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推荐,他又调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长。其时正是“大跃进”运动负面效应开始呈现之际,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遇到了沉重的挫折,中苏两党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因此,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政治研究室的任务十分繁重。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主任是陈伯达,但陈伯达不暇及此,实际工作由副主任胡绳和田家英主持。作为秘书长,柴沫肩负研究室的日常事务,恪尽职守,成为田家英的得力助手,减轻了田家英的负担。
柴沫还在中苏论战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他的主持下,研究室同人编写出了《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等资料。他还参与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等的编选工作。
在一次调查中命运发生转折
1962年2月底,即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之后不久,为了了解农村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让田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赴湘潭韶山、湘乡唐家坨和宁乡炭子冲等地开展调查。田家英要柴沫共同带队去。然而,这次调查的结果却没有让毛泽东满意。
据调查组成员马仲扬在 《难忘的调查》、丁伟志在《跟随田家英调查“包产到户”》等回忆中追述:1962年2月底,田家英再率调查组赴湖南,调查《六十条》下达后的农村状况。这次选定的地点——湘潭的韶山冲、湘乡的唐家坨、宁乡的炭子冲,分别是毛泽东的家乡和毛泽东外祖父的家乡,以及刘少奇的家乡。调查组的成员,以农村工作部、政研室的干部为主组成。此外还有红旗杂志社、人民日报社和中央办公厅的个别人,总共17人。他们是:农村工作部的王录、裴润、王涵之、罗贞治、刘显谦;政研室的柴沫、高禹、李洪林、郭冲、丁伟志、张作耀、孙启佑、宋士堂;红旗杂志社的张先畴、张凛;人民日报社的萧风;中办的金石;还有就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田家英和逄先知。调查组到达武汉时,在东湖宾馆的梅花岭别墅,毛泽东、王任重、谢富治曾会见了组员。当时毛泽东拿着名单逐一点名。点到柴沫时,他说:“柴沫,老朋友了!你在延安我的办公室工作过,还管过我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在困难时期做得不错。”不过,在点完了名之后,毛泽东开玩笑似的说:“知识分子成堆么!”
调查组到达韶山后,分三路开展工作,其中的韶山大队以柴沫、裴润为正、副组长,湘乡大坪大队(即唐家坨所在的大队)以高禹、萧风为正、副组长,宁乡炭子冲大队以王录、张凛为正、副组长。田家英则在韶山负责全组的调查工作。
调查中,社员们普遍提出了实行“分田到户”的强烈要求。田家英等在认真考虑农民群众的意见之后,认为《六十条》虽然改善了生产和生活状况,但是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面临的经济困难,不能有力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无法从根本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随即,调查组在报告中反映了这些农民提出的强烈要求,并且认为只要允许农民这样做后,“就会精耕细作,两三年就能恢复生产”,“粮食可以增产,家庭副业也能很快发展,社员吃得饱,征购好完成,政府也买得到东西”。报告还认为它表达的是农民恢复生产的强烈愿望,“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问题”,“不能用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作解释”。
不久,田家英和逄先知赴上海向毛泽东汇报,调查组则暂由柴沫主持。据逄先知后来回忆:在上海,田家英把调查组在韶山、大坪和炭子冲三个点的调查报告送给了毛泽东和陈云,并把炭子冲的报告寄给了在北京的刘少奇。三人对此的反应立即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陈云称赞了报告,认为“观点鲜明”;刘少奇也认为很好;毛泽东则很冷漠。毛泽东在听了田家英的口头报告之后,当即明确表态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然而,田家英等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相反,田家英回到北京后,认为自己关于在农村实行多种所有制以恢复农业生产的设想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支持,准备在湖南调查的基础上,着手起草《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的文件,又布置政研室再组织两个调查组分别赴对“包产到户”持抵制意见的东北和山西 (这两个地区的主要领导人和省委有反对和抵触“包产到户”的呼声)去调研。
柴沫则在政研室认真传达了田家英的意见。他此时以为中央已经原则上同意要在部分地区实行 “包产到户”,只是考虑到波及面的大小,要调查组再去两地做一番调查。最后,高禹带队去了山西,王忍之、张作耀、马仲扬等则随柴沫去了东北(到长春后又增加了王广宇)。据马仲扬回忆:“柴沫督促我们每到一地,每有所闻所见,都立即连夜写出报告,即发北京,报田家英。”岂不料,这又是“罪”上加“罪”。
就在调查组在湖南开展调查期间,田家英还曾请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和研究室主任、中办财经组组长梅行专程到韶山向调查组传达中央当时拟定的 《休养生息二十条》。梅行说中央对当时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困难还未充分暴露”,“现在还没到沟底”,“要有思想准备”,为此中央设想在“重灾区”对于“包产到户”暂时不纠正。随即,柴沫受田家英委托,派人去安徽无为县考察当地“包产到户”的状况。此后,田家英把《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调查》刊登在中央办公厅的《简讯》上。“文革”中,这成了田家英等人的一条罪状,被视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新农村”、“疯狂鼓吹复辟资本主义”的证据。据逄先知回忆:就在调查组在东北开展调查的时候,毛泽东又严厉批评了田家英,认为他回到北京后不修改《六十条》而是去搞“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决定由陈伯达负责为中央起草《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文件。接着,在北戴河会议(即1962年8月6日至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的工作会议)以及稍后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包产到户”的主张,并大讲“阶级斗争”,提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尽管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公开批评刘少奇等一线的中央领导人,但已公开而且严厉地批评了田家英,并且说他“把持政研室”。这也就是说,自此,田家英已经彻底失去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
在此前后,正在东北开展调查的柴沫突然接到了田家英的电话,要他们立即结束调查返回北京。获悉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之后,柴沫等感到事情突然,不明白中央为什么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此后,田家英不再负责政研室的工作,柴沫则做了一次自我检讨。据丁伟志事后回忆:“谁也没料到,四年之后,从田家英到柴沫,连同我们这些他们的追随者,会因此被一齐投入到灭顶的灾难中。”又据王力回忆:1962年北戴河会议批判“三自一包”,“主要是批陈云,附带批田家英”。与此同时,也曾是毛泽东秘书的柴沫,也受到了冷落。
被陈伯达当做替罪羊
1964年春,在中苏论战的高潮中,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意见,原来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扩大改组为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任务是进行马列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的研究,重点是“两史一中心”(党史、共运史、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院长仍为陈伯达,副院长有胡乔木、周扬(兼党委书记)、胡绳,秘书长兼党委副书记是柴沫。这其中,有3人曾是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柴沫。而此时的田家英,已被排除在这一机构的领导班子之外。
研究院建立以后,开展的第一项重大工作是由柴沫率领研究人员到通县高各庄进行“四清”运动,时间是从1964年10月到1965年8月。接下来则是由柴沫组织大批判组,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1965年12月开始准备,到1966年2月,根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的精神,研究院大批判组撰写了两篇文章,并分别在 《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其中有根据胡绳的指示由柴沫和洪廷彦等撰写的《论海瑞》一文。这篇文章在被《红旗》编辑部排印之后,撰写者柴沫等感到“批判的调子较低”,要求退稿,却未能如愿。
在此前后,柴沫凡事都向院长陈伯达汇报和请示。然而就在5月9日,陈伯达来到研究院,当众指责柴沫搞“秘书长专政”,“走田家英的门子”,“听中宣部的话瞎写文章,不听他的话”。
其实,这是了解内情的陈伯达以为“文革”即将发动,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已受到批判,而《二月提纲》则将被撤销,至于研究院大批判组按照《二月提纲》精神发表的批判文章,其责任不能由他这个院长来承担,应该由与田家英关系较好的柴沫来承担,于是陈伯达跑到研究院“点火”。“点火”的目的,一是撇清与自己的干系,一是清理门户。这样,经过陈伯达的煽风点火,研究院批斗柴沫以及“柴沫一小撮”的大会和小会持续不断,致使柴沫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受到严重的摧残。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同时,也将田家英划为了批判的对象。当时,田家英已被停职反省。5月22日下午,负责处理田家英问题的安子文会同王力赴田家英在中南海的住所,随即,“安子文指出田家英犯了错误,要检讨,暂时不工作,即中办副主任、处理来信来访的工作暂时不作,田家英手边有许多毛主席的文件、手稿,要他交给戚本禹”。5月23日,田家英自杀。
据王力回忆说:5月23日上午,就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组织处理决定时,汪东兴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随即十分紧张地跑到主席台报告周总理:田家英自杀了。周恩来迅即派安子文、王力、戚本禹赶到现场。据王力回忆:当时田家英已不治身亡了,“他喝了一瓶茅台酒然后上吊,事先把公务员打发出去,布置了一大堆任务,如烫衣服、取衣服,买这样,买那样,很长时间才能回来,他自己倒锁了门自杀,等公务员回来敲不开门,最后报告中办把门撬开,把田家英放到地上,已经没有希望了”。王力回忆说:“对田家英,我知道毛泽东是说过一些难听的话,但是在我所参加的大的和小的会上,在他同我的多次交谈中,我没有听到他说过田家英一句坏话。他是喜欢田家英的。我断定他是怀念田家英的,对于田家英的死,他心里一定是很难过的。我不相信他对田家英说的那些气话,就是他的定论,就是不可改变的。”
在田家英自杀后三个多月,柴沫也愤然自戕。对于柴沫的死,毛泽东也表示了极大的惋惜,以至于他在事隔多年之后还气愤难平地问:“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