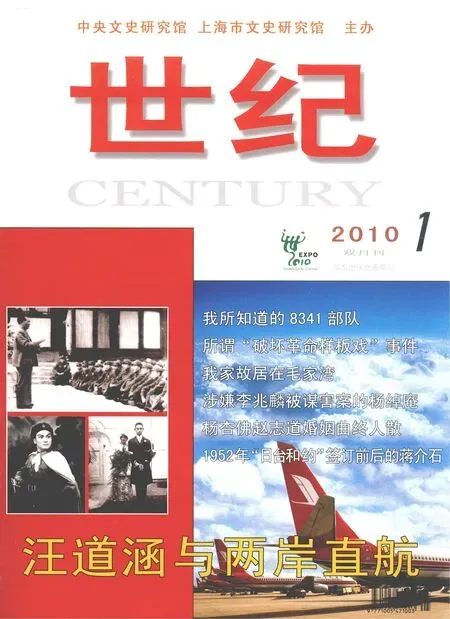抢救我们的汉字
朱铁志
我上小学的时候,尽管处在十年动乱期间,学校和家里对学生依然还有写字的要求。在人们的心目中,能写一手好字,意味着具有良好的教养和学习习惯,通常学习也不会太差。我上的第一所小学,并不是当地特别有名的学校,但老师们的板书个个写得漂亮。受他们影响,我一度对写钢笔字发生浓厚兴趣,简直可以说达到痴迷的程度。一有时间就临摹行书字帖,把黄若舟先生的《怎样快写钢笔字》以及《钢笔行书字帖》第一册和第四册临摹了足足二十多本,摞起来足有一尺多高。
我不敢说自己的字写得怎么好,但我始终对能写一手好字的人充满羡慕和佩服。每当看到前辈学者的手稿,看到那些功底深厚的文字,我就在心中暗自赞叹:这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大学毕业后当了编辑,从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后期电脑普及之前,每天收到的大量来稿还是手写的。多年对写字的爱好,使我产生了一个不无偏执但非常坚定的“原则”:凡是字写得惨不忍睹的来稿,就坚信它的内容也好不到哪里去。我的逻辑是,连字都写不好的家伙,还能写好文章吗?我承认这种看法有很大的片面性,但很难改变它。
工作多年以后,我在单位里承担过一些招录大学生和复转军人的工作。从材料上看,不少同志学历很高,资历很深,水平不错。但一看他们的字,总不免让我心里发凉。显而易见,他们从未受过良好的书写训练。过去把字当门面,是求职时的一块敲门砖,如今似乎不那么为人所看重了。即便是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能够写出一手好字的人,也是凤毛麟角了。中华民族的书法传统,到眼下这波儿孩子身上,似乎就算断了香火了,这不免让人感到痛心。
徜徉在琉璃厂的中国书店,我见过一些写成蝇头小楷的科考试卷。那些娟秀的文字让我久久徘徊,流连忘返。我的手边也有朋友们赠送的复印状元卷。我不仅对饱受贬损的八股文心存一份尊重,更是对赏心悦目的书法喜爱有加。我甚至在心里可笑地想,如果我是考官,单凭这手好字,也要对考生另眼相看。而遥想当年,在那些饱读诗书的考官眼中,“鸡爪扒”恐怕连一丝一毫入围的机会也没有吧。
我不是前清遗老遗少,并没想为一个王朝的背影唱挽歌,或许我还真不配。我不想班门弄斧,讲什么书法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道理,也不敢断言写一手好字对文化的传承和个人教养的养成有多么关键的作用。或许就此让书法艺术从民众的视野和书写中消失,在一些人看来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要比楼市涨价,股票升值次要得多,那我自然无话可说。但绵延几千年的艺术瑰宝从此不被自己的国民看重,生生不息的书法艺术从此在我们这代人手中远去,逐渐成为一个模糊的记忆,总不是我们的光荣吧。我们说了那么多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话,却连老祖宗留下的优美汉字都写不成样子,让我们何以面对列祖列宗,何以复兴中华文明?
《文汇报》报道,偌大的上海,每年只有师大美术学院书法专业招收20名学生,专门培养书法人才,毕业后只有50%能到中小学任教。某小学招聘教师,校长要求最后入围的30名候选人每人在黑板上用汉字书写一到十,结果因板书太差,一个也没有录取。大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可见我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