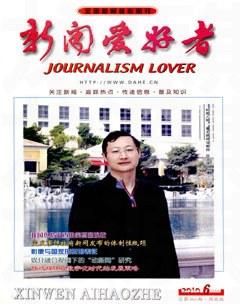电视剧文本符号建构的超现实神话
景 熹 李振委
摘要:本文通过对《蜗居》台词语言符号、场景和大环境等非语言符号以及主要人物“叙事结局”的分析得出结论:在肯定此剧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热点问题和矛盾的同时,我们也不能迷信《蜗居》,其文本符号所反映的只是现实种种镜像的集合体,它并不是现实本身,而是超现实,是人们想象催生的神话。
关键词:《蜗居》超现实神话建构
引言
《蜗居》(以后简称《蜗》)是2009年中国大陆最热门的现实题材电视剧之一,探究其中的原因当然有一些夸大和炒作的成分,但不可否认它的确触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社会现实热点问题。《蜗》的故事围绕着百姓买房难、“小三”、反腐和拆迁等社会热点和矛盾的焦点问题,并且关注到一个都市新兴社会群体“漂一族”的生存状况。故事发生在一个作者虚构的城市——江州,但江州狭窄拥挤的弄堂、世纪明珠塔和博物馆等其实则是上海的表征,而故事是从1998年开始并且一直延续至今。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姐妹,她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通过考大学的方式从一个小地方来到江州,毕业后决定在江州买一套房子从此过上大都市人的生活。姐姐海萍努力、勤奋,为房子心力交瘁,妹妹海藻在看到姐姐的生活后,思想逐渐发生变化,最终成为市长秘书宋思明(后简称为“宋”)的“职业二奶”。
《蜗》的热播引发社会各界的争议,有人认为涉及的话题太敏感,有人认为台词太露骨,也有人认为它反映的并不是现实,甚至此剧曾一度从电视荧屏中消失而被外界猜测遭遇了“禁播”。笔者不想探究《蜗》热播的原因,但是《蜗》究竟是否反映现实,在何种程度上反映现实,这种反映又会对现实造成什么影响却是人们必须认真思考的。
《蜗》文本符号建构的超现实神话
电视剧所呈现、建构和传播的文化,是当代最重要的文化构成之一。首先,电视剧是当代文化借以呈现的主渠道之一。当今中国,电视剧已跃升为中国当代第一叙事艺术,它通过一幕幕悲欢离合表现着中国受众的行为与思维模式,“见证着当代人生活、情感和社会的演化”①。其次,在反映的同时,电视剧也是现代社会文化建构的主渠道之一。它提供价值和意义的象征体系,以叙事的方式进行着民间社会的经验重组、观念交流和话语转换,潜移默化地对当代社会的时代风尚、价值观念、文化潮流产生着复杂和深刻的影响。《蜗》的故事起源于中国房地产元年1998年,这一年国家颁布第23号文件即《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此通知规定自当年起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建立住房分配货币化、住房供给商品化与社会化的住房新体制。②《蜗》的故事发生地是上海的镜像,而上海是我国房价最高的城市之一,《蜗》的编剧通过时间和地点等大环境的典型化,创造出一个电视剧文本符号,而这一符号反过来又对人们关于现实的理解产生作用。笔者认为《蜗》建构了一个超现实的神话乌托邦,它是对现实的拟像与模仿。
超现实神话的界定
超现实是对客观现实的碎片化拟像与模仿,符号学认为在某些社会问题上,符号和意义的缺场会导致符号的片面化。符号的某些部分不被感知而消失,某些部分被感知而凸显。符号在被感知时,片面化到只剩下与意义相关的品质。一事物成为符号,不是它作为物的本体存在,符号载体不是物本身,符号是相关可感知品质的片面化集合,符号的片面化“挑拣”构成文本。在《蜗》文本符号中,“江州”和“1998年”就注定其片面化的趋向,而故事中涉及的核心字眼:百姓买房难、“小三”、反腐等则构筑故事的现实性,因为这些字眼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被高度关注与无限放大。《蜗》成为种种社会现实的镜像集合体,在这之中现实得以实现,成为超现实而非现实本身。
“神话及传说的意义,常常是隐讳的而非彰显的、含蓄的而非直接的,听者无须有意识地明了其所以然,就能充分地接受其存在。电视正具备了这一个特色,它的出现及生存,基于一项先验的假设:接受现状。”③神话可以提供人的理想自我形象的模式,给我们梦想、希望和超越。因此,尽管古代神话消失了,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现代神话即世俗神话。“神话是禁忌与欲望的满足,在神话中寄托着有关可能的统一性和创造出平衡可感的世界的令人欣慰的淡淡希望。”④《蜗》是一种神话叙述,它体现了神话叙述的几个特点:
《蜗》在结构上是封闭的,但在事件和剧情上则是开放的。《蜗》的剧情以姐姐海萍买房为主线,而又以妹妹海藻沦为“小三”为辅线,又加以宋一家的矛盾、反腐机关对宋的暗中调查、老李一家的拆迁、苏淳因泄露商业机密险些坐牢等线索共同建构整个故事,形成一个复调叙事结构。故事最后以贪官宋的死亡、妹妹海藻出国重新生活、姐姐海萍创办自己的中文学校结束,引发受众的联想与希冀。
通过受众不断地参与和介入,《蜗》表现了一种集体想象力。《蜗》构筑的社会与人们生活的社会相对一致,故事中主人公遭遇的问题也似乎是现实中人们会遇到的难题,故事展现的社会是我们现实社会和民众生活的有选择的表征,是一种艺术加工和想象的结果,表现编剧对现实社会某些问题的敏锐感知力和受众丰富的集体想象力。
《蜗》通过口头和受众的创造,在人们的闲聊中再创作和再表现。神话是仪式的语言层面和方式,凭着这种符号方式仪式得以传达。符号既是现实的表征(of),又为现实提供表征(for)。这是硬币的两面,它代表着符号形态的双重性能:作为“……的符号”(symbol of)以表现现实;作为“为……提供现实”(symbol for)则创造了它所表现的现实。⑤《蜗》的故事原型来源于现实,但这一新文本一旦被创造出来则会变为存在,成为超现实反作用于现实。
《蜗》台词对超现实神话的建构
台词作为语言符号是最能表达剧情变化和发展的,也是受众最容易理解的电视剧文本符号。《蜗》的台词是引发此剧争议的核心所在,它以一种幽默诙谐又略带伤感的风格带领受众去关注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与生存状态。
《蜗》中个性鲜明、略带哲理的台词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及抱怨社会种种不满情绪的小花招,台词也成为《蜗》建构超现实的理想工具。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有其能指与所指,它们像硬币的两面,一起构成语言的表意结构,能指是指我们通过自己的感官所把握的符号的物质形式;所指是符号使用者对符号所指涉对象所形成的心理概念。当前大众媒体构成的影像中,出现无能指的所指,也出现同一能指的众多所指以及能指链的滑动和漂流的能指。《蜗》的台词就隐射多种所指,引发受众丰富的联想,也许这就是《蜗》台词之所以引人关注的原因之一。语言符号形态都拥有两种不同的特征:代替性和生产性。代替性能力是当“真正”的刺激物在实物形态上并不在场时产生复杂行为的能力;生产性指每种符号形态都是生产性的,掌控符号的人有能力在有限的符号元素基础上生产无数个表征。《蜗》通过语言符号形态的建构、理解与利用创造了超现实,并使超现实成为一种存在。或者说,现实是由创造这些系统的人创造的——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即台词强调现实的存在并创造社会秩序。现实是一种大量生产的、具有表现力的创造物——是一种由人类生产并维系的产物。无论这世界有着什么样的秩序,它既不是我们基因中本来就有的,也不是完全自然提供给我们的。台词是现实的一个表征,人们的生活可以以不同的语言与言语行为展现。这和宗教仪式并无二致,在某种形态上它代表了人类生活的本质、人类生活的意义,在另一种形态上——宗教仪式也提供了一种形态——它所扮演的特性就是描绘意义。⑥这些台词也存在符号片面性的缺陷,因为意图意义(主观想法)与文本意义(主观的想法落实到文本表现)并非实现的符号意义(文本意义在受众自己解释基础上的“现实”意义)。反过来,这三层意义也在一步步否定前者:文本意义否定了意图意义的存在,如果意图意义并没有在文本中实现,就只是传者的一厢情愿;反过来,如果文本意义体现了意图意义,那么意图本身不再有意义价值而只是意图的变异。符号意义否定了文本意义——得到解释,使文本失去存在必要。不管解释意义是否符合文本意义,它至少暂时地结束一个符号表意过程。因此《蜗》的台词也同剧中其他非语言符号一起共同构筑超现实神话。
《蜗》主要人物的叙事结局对超现实神话的建构
《蜗》中以海萍、海藻两姐妹和宋思明为主要人物,他们在剧中的结局也是很耐人寻味的。宋因贪污死于交通事故,妹妹海藻因成为宋的“小三”意外流产而丧失生育能力最后出国寻求重生,姐姐海藻努力拼搏,创办“海萍中文学校”,事业初成。由此可见,《蜗》的编剧似乎遵循着“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的理念,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表面上剧中的“坏人”得到应有的报应,但笔者认为不应把剧中人物复杂的人生境遇和心理活动简单化。剧中抽取现实生活中众多人生的典型结局并做了冲突话语夸张化的艺术处理,这种结局已经不是现实,而是一种“叙事结局”。“叙事结局”是虚构性艺术叙事矛盾冲突的解决时刻。戏剧冲突的解决和戏剧性的结局有关, 在这个结局中, 妥协或是暂时的解决冲突之道, 都被投射到一种文化和历史的永恒之中。
这些“叙事结局”是通过仪式的固化与象征表现的,具体来说是通过剧中长焦镜头的运用与人物自言自语或旁白来表现的,其中以宋的死亡最具仪式性。宋得知自己的老婆去找海藻便冲出会议室,驾车赶往海藻所在的医院,在途中又接到一通电话,说海藻肚子里的孩子已流产,她的子宫正在摘除中,这个电话让本来就因涉嫌贪污的宋陷入绝望。在宋的车后面紧跟着准备抓捕他的警车,而前面迎面向他驶来一辆大卡车,在一念之间,宋选择了懦弱,他松开方向盘,车子侧翻在马路上,被卡在驾驶室的宋已是奄奄一息。此时,画面切换到海藻动手术的医院,病床上海藻同样是昏迷不醒,最后呈现在受众眼前的是一个由远及近的长镜头,那是搭着白布的宋的尸体。这三个场景的顺序切换完成一个仪式,仪式是一种具体情节的系统,它们是象征性质的, 以明显的隐喻风格来包容和表现某种抽象的信念——宗教的、社会的或个人的。仪式是语言,但比语言更富有静穆的力量,它直接作用于心灵而非理性,并把它所要表达的东西如同纪念碑一般固定下来。在这个仪式中,《蜗》完成了“叙事结局”,并建构了超现实神话。
结语
电视剧《蜗》以现实为原型却又构筑了一个超现实的神话乌托邦,文本表现的现实只是一种“虚拟环境”(“媒介环境”),在这里,意图意义和文本意义发生断裂,而文本意义又与符号意义相去甚远。《蜗》热播后,人们不禁提出疑问:“难道这就是现实吗?”甚至一些网友批评《蜗》,认为其问题恰恰是过度追求现实深度和典型效果,反而失之于虚假。不可否认,电视剧不断地生产着形形色色的社会叙事,这一过程,实际上是表达我们个体经验的过程。也就是说,电视剧提供了一种方式来理解一系列关乎人类生存困境的问题。在消费剧情的过程中,受众不断地以愿望投射的方式使自身的经验获得意义,这种身心投入使得当代电视剧获得了一种几乎是无以伦比的文化建构力量。我们不必迷信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尽管此类电视剧对揭露社会热点和矛盾有重要作用,更不能天使化或妖魔化“社会问题剧”,而必须明白电视剧所呈现的文本仅是社会的种种镜像的集合体,它并不是现实,而是超现实,是人们想象催生的神话。
注释:
①曾庆瑞:《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第2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页。
②http://202.204.208.109/fangguan/policy/disppolicy.asp?id=23,国发[1998]23号。
③费斯克[美]:《解读电视》,台北: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63页。
④伊芙特·皮洛[匈]:《世俗神话》,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年版,第95页。
⑤⑥詹姆斯·凯瑞[美]:《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作者单位:景熹,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传播学院;李振委,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编校:赵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