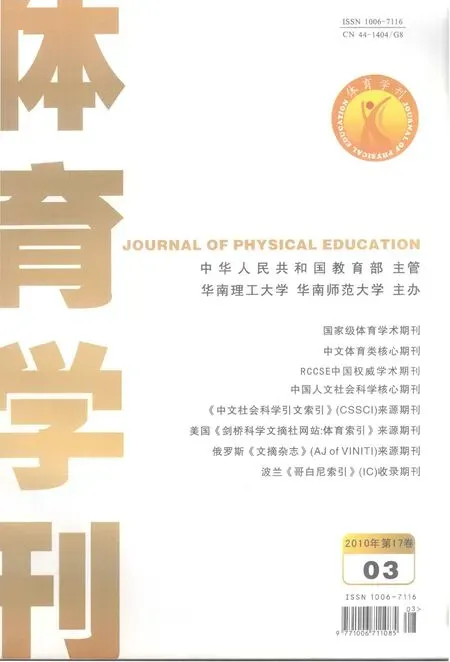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的当代价值——以桂北侗乡抢花炮为例
李志清,覃安,朱小丽38
(1.广西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2.桂林理工大学 体育部,广西 桂林 541004;3.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广西 桂林 541006)
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的当代价值
——以桂北侗乡抢花炮为例
李志清1,覃安2,朱小丽318
(1.广西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2.桂林理工大学 体育部,广西 桂林 541004;3.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广西 桂林 541006)
对桂北侗族聚居区三江县6个花炮节举办地的实地调查,结果发现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价值。从乡土文化方面来看,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成为乡土社会文化传承的良好载体;在人文建设方面,通过建构地方族群的认同与人们的国家认同、调动社区参与、形成健康的竞赛关系以及加强族际之间的理解与沟通,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成为促进民族稳定和谐的重要活动;在乡村治理方面,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以健康的文体活动对不良娱乐方式形成“竞争性抑制”,因而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将成为乡村治理的有效工具。
少数民族体育;仪式;抢花炮;侗乡
以信息的不断重复和传递为特征的仪式是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许多民族文化形式借此获得表达,得以传承。钟敬文[1]指出:“民间的许多节日,是包括着社会的多种活动事项在内的,它是许多文化活动的集合体,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展览会。”节庆仪式是民族文化活动的载体,乡土社会的仪式性体育能形成一种节日开展的活动。一方面,民间仪式性体育活动有社会组织基础及信仰和传统力量的支撑;另一方面,体育活动又是把人们聚集和组织起来的重要手段,体育的竞技性激发集体荣誉感、制造狂欢气氛,因此村落仪式性体育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本文以桂北侗族聚居区三江县6个花炮节举办地的实地调查材料,从乡土文化传承、人文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论述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
1 乡土文化方面的价值
1.1 集中展示民族文化,使民族文化维持活态
影响较大且具有传承性的少数民族体育大都和信仰仪式有关,仪式性体育往往是复合性的活动,同时举办各种民族文化活动。在桂北侗乡,在信仰和老祖宗遗产的认同之下,抢花炮活动代代相传,人们年复一年举办花炮节。每一届的花炮节都包括当地各种民族文艺表演(多耶、侗族大歌、吹芦笙、抬官人等)和民族传统体育娱乐竞技活动(斗牛、钓鱼、斗鸟等)[2]。现在侗乡的许多人平日里基本上不穿民族服装,除过姓氏节、结婚时穿民族服装之外,花炮节是最集中地展示民族服装的时候。花炮节周期性的展演给人们提供了“亮相”的机会,使人们保留着对本民族服饰和文化的情感。为了突出花炮节的民族特色,梅林地区花炮组织者资助各村寨把消失多年的吹芦笙恢复起来,少年儿童都学会了吹芦笙。梅林中学的学生排练和唱响了消失多年的侗族大歌,花炮节的演出使这种濒危文化获得传承的机会。村民在热闹的活动中,获取自我文化的了解和认同,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同时,花炮节带来的旅游人群使村民获得对民族文化经济价值的启蒙,从而更自觉地挖掘和弘扬民族文化,强化抢花炮的民族特色。被需要、被使用的文化艺术才是有生命的,花炮节集中展示这些民族文化,使其由于被需要和被使用而维持活态,保持了这些民族文化的生命力。
1.2 营造传统文化氛围,让青少年感受和热爱本土文化
每个人都受其所在社区的风俗和文化的影响。“在他出生以后,他就受到风俗的熏染。他长大后参加了文化创造活动,那么这种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这种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3]。人们对文化的认同是后天培养然后渐成习惯的,习惯的形成便是文化传承的实现。节庆仪式提供了感受民族艺术的情境和氛围,通过周期性的重复能够培养人们的认同与习惯。“一些民间艺术只有置身于那种情境里,才会感受到它的魅力”[4]。儿童是“民族文化血脉的继承者和文化基因的承载体”[5]。花炮节的时候,林溪、梅林的中小学生都放假参与,家长们为自己的孩子精心打扮,织布、染布、做衣、做绣花布鞋、绣花挎包,从头到脚的打扮都是自制的民族服饰,一套行头要花几个月的时间。穿上节日盛装的孩子们兴奋和自豪的情绪溢于言表,相互的欣赏和夸耀以及游客的赞赏和频频拍照,更增添了他们的自豪感。自从1996年4位侗族姑娘在法国演唱侗族大歌引起极大反响之后,这种天籁之音在国内外获得了极高的地位。梅林中学的女生为准备花炮节的演出自己排练大歌,“老师不懂这种歌,是会唱的同学教,会唱的同学是在家里学的”。花炮节使几乎失传的侗族大歌重新唱响,演出的受欢迎使她们“好高兴”,“很喜欢唱大歌”。花炮节的演出培养了孩子们对自己民族优秀传统艺术的情感,也让她们看到民族艺术能使自己获得向外发展的机会,增强了对自己文化的信心。
1.3 构建活动平台,保留民间体育传承与发展的空间
少数民族文化往往是主流文化背景下的弱势文化。在当代娱乐文化与全球体育文化的冲击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式微甚至消亡是在所难免的。然而,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也是人们获取知识、得到感情及精神满足的一种途径。文化多样性是创造力的源泉。文化的创新根源于传统,文化的繁荣来自于各种文化的接触,文化资产必须加以保存、改进和传递,以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创新。活在社区民众生活之中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才有生命力,因此,应该“让民族文化在社区中传播,在娱乐中发展。”[6]以某一种民族体育面对现代体育与娱乐的冲击,其力量过于单薄和微不足道,因此需要团结的力量。民间节庆具有文化的包容性,以一种活动为龙头,定期地举办综合性的民族体育节庆活动,能保证民族体育在社区的生存空间。民族体育有了展示的机会,人们就能从中获得娱乐和自我实现的满足,就有人去从事这些活动,
该活动就能获得自然的传承。
仪式是联系个人社会和群体的纽带[7]。在乡民的意识里,越是庄严肃穆而带有神秘色彩的仪式,越能激发起民众心里对该活动的“事业”感和服从心理。民间仪式活动往往属于公益性活动,人人都有参加的义务。因此,仪式性的民间体育活动是最具有号召力和能够稳定传承的民族体育形式。桂北侗乡的花炮节除了抢花炮活动,还有斗牛、斗鸟、钓鱼、侗棋等比赛,人们各取所需,满足了多层次的需要。因此,随着抢花炮的传承,侗乡其他形式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传承与发展也得到保障,它们也充实着花炮节的活动,增加花炮节的吸引力。以节庆方式强化民族文化意识,传承民族体育文化是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承的成功模式。而能够形成节庆,并在民族体育传承中起核心作用的民族体育形式就是仪式性的民间体育。
2 人文建设方面的价值
2.1 建构地方族群和人们对国家认同
“民族(族群)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群体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8]。族群认同有利于增强族群共同体的向心力、凝聚力。不同的社会记忆,影响着不同社会群体彼此的认同。仪式的操演形成社会记忆,共同的社会记忆有利于族群社会力量的整合。仪式由于现实意义而流传,也正是由于对现实意义的考虑,仪式的周期性展演并非一成不变的复制,其形式和内容都在随时代进程不断地变化,甚至其民族“身份”也会有所改变而服务于现实的需要。正如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指出的“与其说是文化在控制人、奴役人,倒不如说人在利用文化和顺应文化。”[9]侗乡的抢花炮,经国家认定并贴上“侗族传统体育项目”和“东方橄榄球”的标签之后,侗乡民间的组织者也积极回应,有意识地强化抢花炮的侗民族特点,如古宜和富禄花炮的组委会成员开始在花炮节上穿上侗族服装并且组织大型的民族文艺游行和表演;林溪在花炮起源与五省馆关系上形成“结构性健忘”①;梅林的花炮组委会积极挖掘民族传统节目在花炮节上展示。民间与国家共同推动了抢花炮的民族标签化。国家把抢花炮项目推进民运会,以此作为民族团结的象征符号,民间利用这一符号的建构强化族群认同,同时以民族特征的强化来维持和扩展该活动的生存空间。抢花炮已作为族群认同的象征符号,刺激和唤醒侗乡人的自我认同意识。
抢花炮这项民间仪式性体育活动也在潜移默化中起到国家认同的作用。林溪的游炮有3个庙必须经过,即使现在庙已废也要经过那个地方。这3个庙是飞山庙、神婆庙和盘古庙。他们说,“神婆庙敬的是我们这里的祖先,盘古庙就是敬盘古开天地的盘古了,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②侗乡的民间组织者十分明白侗乡的发展依托着国家的支持,民族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在抢花炮活动和其他活动中,民间组织者总是有意识地宣传和传递着国家认同。例如,2004年葛亮举办花炮节的时候,主办者在天后宫贴的对联是“闽粤湘桂黔一家,汉壮苗瑶侗五族”,林溪花炮节松门的对联为“万炮争鸣振兴林溪经济三大跨越创腾飞,百花争艳迎来侗乡人民两个文明齐并举”。仪式性的抢花炮活动,通过仪式过程不仅建构着地方族群的认同,同时也建构着人们的国家认同。
2.2 调动各村落社区的参与,形成健康的竞赛关系
抢花炮能调动各村落社区的参与,也能调动它们之间形成健康的竞赛关系,显示出全寨同心协力的精神。林溪与程阳抢花炮关乎村寨荣誉,所以“个个都想要那个炮,为寨子争荣誉”。青年们表示参加抢花炮是“为了整个村子的荣誉去比的嘛。我们村子一定要在这里显得很有威风,很有骨气,很团结的样子”。每次抢到花炮,全寨就到鼓楼摆百家宴。林溪抢花炮的时候天气很冷,以前河水很深,但是花炮落在河里人们照样潜入水中去摸、去抢,场面非常热闹。村民说,“我们有人去抢,不怕苦、不怕死,寨子就很有面子。”抢炮中的人数、拼抢能力和游炮中“我的花样比你多”、“我的人数比你多”,“我的芦笙比你响”等等都是村寨力量的显示,也显示一个村寨的凝聚力。抢花炮具有炫耀村寨实力、提高村寨声望的作用。抢花炮队伍、游炮队伍的组织和游炮过程的展示对凝聚人心具有很好的作用。
2.3 加强族际之间的理解与沟通
抢花炮作为一种跨村寨的多民族参与的民间体育活动,既强化了族群认同又加强了族际之间的理解与沟通。钟敬文[10]从西部大开发的角度谈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的意义时说:“西部开发要涉及几十个民族,没有文化的沟通与认同,就会影响整个西部大开发的进程。”“所谓文化认同,就是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理解与沟通,彼此依赖与尊重。”这番话告诉我们族群之间文化的相互理解与沟通的意义。生活在桂北山区的侗族,生活方式的许多方面已经与汉族无异,但却维系并传承着族群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建立在语言、民俗仪式活动等载体之上。随着旅游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逐步发展,当地人通过具有民族历史价值的人文旅游景观的再现和重组来展示自身的文化智慧和创造力,唤起本民族成员的历史记忆,增强族群的凝聚力和自豪感,也使主流文化群体(如前来观光的游客)在民族旅游中获得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识和肯定。通过花炮节的各民族参与、花炮节民族活动展演和花炮节吸引的大量游客,花炮节有效地促进了族际之间的理解与沟通。
3 村治方面的价值
3.1 对不良娱乐方式形成“竞争性抑制”
赌博现象在当今的乡村明显地甚于传统的乡村。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批批乡村青年离农离乡而涌入城市,他们中大多数人在年节的时候返回家乡,一部分人“不会干农活也不想干农活”,打麻将、赌钱现象相当严重。健康娱乐与文化垃圾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堵”和“疏”相结合是制止乡村赌风的最有效的办法。M村曾经因为小孩公开参赌被媒体曝光,2004年花炮会资助村寨恢复芦笙,孩子们着迷地学吹芦笙,这种健康的业余活动配合乡政府的管理措施,使赌博活动得到有效遏止。M村的实践说明健康的农村体育文化活动完全能够对不良娱乐方式形成“竞争性抑制”。
在调查中我们看到,程阳青年在正月初七花炮节之后大量返回广东打工,梅林青年等到二月二花炮节之后才去打工。仪式性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吸引力相当强大。原因包括这种集体性的原始竞技活动使人获得压抑情绪的充分释放、乡民的原始宗教信仰,也有仪式强制性的作用。从桂北侗乡抢花炮的实践来看,以上3方面的原因使仪式性的体育活动有着较强影响力,能够把绝大部分的人长时间吸引到这一活动中。
3.2 具有社会秩序的演示与法规观念的启蒙作用
文化人类学家对仪式在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有过许多论述。涂尔干[11]指出仪式是社会群体定期重新巩固自身的手段。仪式体现了一定的社会秩序与社会关系,并表征了某一时代人们的意识观念、思想情感等[12]。在抢花炮筹办过程中,谁进入筹委会,谁担任主任、副主任和常务理事跟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有关,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扮演的角色也重要些,花炮筹委会实际上体现了村寨的社会结构和秩序规则,在游炮活动背后还蕴涵着浓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和价值。游炮的时候,不仅要让一个有福的老人拿炮,还要有老人队伍陪炮。中青年说,“让老人陪炮,这是上一辈传下来的,我们又要传下去,昭示后人。”抢花炮活动过程凸显了老人的地位和作用,表明了村里人遵从传统,尊敬老人,热心公益事业。侗乡抢花炮的仪式过程有展示社会观念、建构社会权威、整合社会秩序等社会功能。
除了民主选举筹委会常务理事、经费收支张榜公布接受监督之外,在抢花炮过程中也处处看到这项体育活动在培养着村民的民主观念和遵守规则的习惯。抢花炮规则规定了活动的进行方式、奖惩办法以及对违规所采取的措施,在规则约束下的拼抢使得竞争公平化和制度化,使村民意识到尊重规则的意义。侗乡的抢花炮在体育活动中培养着民众通过正常渠道提出意见、民主协商以及遵守裁决的习惯,把民众的反应导入一种有序的状态。侗乡抢花炮的规则正在活动过程中逐步完善,每一届抢花炮人们都会对规则提出意见和建议,每一届都要对规则进行一些修改和补充,这个过程可以说也是培养民主与法规观念的过程。
实现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法治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制度平台。法治实现的十分重要条件是人民对法律普遍的尊重和自觉服从。加强公民法治观念是建设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保障,是法治建设的基础[13]。在侗乡,花炮寓意着吉祥,抢得花炮意味着获得神的眷顾。此外,抢花炮是一项集体的活动,关系到集体的荣誉,得到花炮的寨子会很有“脸面”,来年抢花炮还有机会游炮展示自己,所以大家很重视它。村寨间对名声的竞争、对神灵眷顾的争夺被引导到该项体育活动之中,大家遵守一套约定的规则,承认“抢不过别人就没办法”这种竞技的惯例。村落民间的体育活动可以成为一种寓教于乐的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培养村民制定规则和对规则的遵从意识,把规则看成参加竞赛者必须遵循的准则,把实现规则看成实现公平的条件,这种意识可以迁移到法律意识、法规观念的培养之中。按照现代教育学理念,体验是最好的学习方法之一,经常参与公平竞争的活动可以提高人与人之间公平竞争的道德观念。因此,抢花炮仪式活动是侗族村寨传统道德规范和传统价值的传承场,也具有现代民主与法规的启蒙作用。
3.3 老人协会,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应该重视的力量
在桂北侗乡,抢花炮的民间组织者是村寨老人协会,侗乡的老人协会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老年人娱乐联谊组织,它是一种地方性“草根力量”。传统的侗族社会内部管理自成一统,寨内集体事务的管理,往往“寨老”的话就是法,就是权威,这是一种被韦伯[14]称作“卡里斯玛”的权威。在四清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桂北侗乡与全国各地一样,寨老组织在强大的政治运动和国家力量作用下退出了侗寨民众的生活,但它的根基还在,随着改革开放、土地承包及联产责任制的推行,这种草根力量在侗乡陆续恢复,只不过“寨老”这一名称已改为“老人协会”而已。
“寨老”在当地村寨中,往往是由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担任。当地的寨老和村民说,“有时候,政府号召的事情不如寨老起的作用大。”原因是“行政管理的人,下来只是一两个钟头,或者几天就走了,但寨上的寨老,天天在这地方,你做没做,他很清楚,很晓得你的底细,所以讲话就听些。人是要脸面的,如果你讲一次不听,讲两次又不听,大家就会讲这个人不行,他就没面子。”在本研究调查的桂北侗乡,老人协会与村委的关系比较和谐,上级任命的两委(村长和书记)这种制度性力量和老人协会这种非制度性力量相互配合使得各项地方事业进行得较为顺利。老人协会协助村部管理村寨,负责本村、本屯的社会治安、纠纷,架桥、修路、组织抢花炮等传统仪式以及丧事互助以及平时的喊寨防火等公益事务,是最基层的管理组织。草根力量在桂北侗乡仍然具有许多实际的权威,村部与老人协会形成一定的互相监督。“承认草根力量的合理性并适度宽容之应该有益于中国广大农村特别是那些边陲地带乡土社会各项工作的开展。”[15]老人协会这样的民间组织弥补了当今我国农村基层组织动员能力不足等问题,也让村民真正地有渠道参与村庄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和自我服务。正是这样的民间组织承担着抢花炮活动的筹备和组织,为村民提供了公共空间和文化传承载体。老人协会是农村和谐社会构建应该重视的力量。在革命运动和市场经济的双重冲击造成村庄传统解体,那些“传统型的村庄精英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失去影响力”[16]的情况下,抢花炮活动的组织筹办成为老人协会体现自我存在价值、强化权威的重要方式。草根性的仪式性体育是体现和维系这种乡村自组织根基的一股力量。
村寨老人协会这种模式是一种保证村落社区和谐的管理模式。类似侗乡老人协会的民间力量并不只存在于少数民族乡村。江浙两省村一级大都设有老人协会。浙江温州地区几乎每一个村都有老人协会,且老人协会活动很多,作用颇大。苏南地区大多也有健全的老人协会组织,只是作用没有温州大。温州沿江发达乡镇党委书记和贫困山区乡镇党委书记都用一样的语气说,老人协会在某些时侯的作用比村支部还大,有些事情,特别是涉及民间纠纷的调解,离开了老人协会就是解决不了[17]。2003年贺雪峰[18]等在洪湖渔场倡议成立老年人协会,老年人协会不仅在本村扎下了根,而且为当地社会所认同。这说明,老人协会模式是可以普遍有效的,并且有可能移植到没有这种传统的村落。
桂北侗乡抢花炮的实践表明,具有社会组织基础、信仰和传统力量支撑以及形成狂欢体育节庆的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在当代乡村社会生活中十分有效地发挥着文化传承作用。其传承的文化超越了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本身。在乡村治理、促进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方面,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也体现了特殊的价值。
注释:
① 在《三江侗族自治县县志·民族志》(中央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的第四章“习俗”中“花炮节”归入汉族节日,并记载林溪是祭祀关公,程阳祭祀“飞山”、“关公”。《努志潭——三江村寨传说》也记载林溪花炮的起源与五省馆的成立有关,是五省商人与当地寨老各族头人共同发起,但现在关于抢花炮与汉族的关系已从官方和民间的抢花炮宣传中消失,现在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花炮与五省馆的关系。
② 2003年11-21亮寨百家宴上的访谈。
[1] 萧放. 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实践生活. 钟敬文序[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2] 李志清. 乡土中国的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3] 露丝·本尼迪克特[美]. 文化模式[M]. 何锡章,黄欢,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
[4] 南方民族的节日习俗与文化传承——《电视批判》第28次论坛刘亚虎的访谈[Z].《电视批判》栏目专稿,发布时间:2003-01-15.
[5] 刘铁梁. 谈年味[N]. 光明日报:文化周刊(355期),2002-02-06(B1).
[6] 贾作光. 在“中国少数民族艺术遗产保护与当代艺术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N]. 中国艺术报,2003-12-12.
[7] 保罗·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M]. 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8] 王希恩. 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J]. 民族研究,1995(6):17.
[9] 纳日碧力戈. 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27.
[10] 钟敬文. 没有文化认同,西部打开发如何进行[J].民族团结,2000(4):20-21.
[11] 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 渠东,汲喆,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07.
[12] 吴晓群. 古代希腊仪式文化研究[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13] 张涛. 和谐社会需要法治[N]. 深圳特区报,2005-03-02.
[14] 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上卷[M]. 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41.
[15] 彭兆荣. 边陲地带的草根力量[J]. 读书,2000(5):15-20.
[16] 贺雪峰. 村庄精英的谱系[EB/OL].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2005-02-08.
[17] 贺雪峰. 新乡土中国[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8] 贺雪峰. 老年人协会纪事:之一[N]. 三农中国,2004-08-24.
Modern value of ritual like minority national sport——Taking firecracker-snatching held in villages of Dong nationality in Northern Guangxi for example
LI Zhi-qing1,QIN An2,ZHU Xiao-li3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541004,China;
2.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ilin 541004,China;
3.Guilin Institute of Tourism,Guilin 541006,China)
The authors conducted a field investigation at 6 firecracker festival holding places in Sanjiang county in northern Guangxi, where people of Dong nationality live, and revealed that ritual like minority national sport has important value in modern social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culture, building an activity platform for other folk sport to reserve a space for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so ritual like minority national sport has become a good carrier for the inheritance of rural social cult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tic construction, by building the recognition of local national groups and the national recognition of people, mobiliz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forming a healthy competition relationship, and strengthening the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ople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ritual like minority national spor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ctivity that promotes national stability and harmon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governing, ritual like minority national sport forms“competitive inhibition” on bad entertainment forms with its healthy cultural and sports activities, therefore, ritual like minority national sport will become an effective tool for rural governing.
minority national sports;ritual;firecracker-snatching;villages of Dong nationality
G852.9
A
1006-7116(2010)03-0080-05
2009-09-0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BTY004);广西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FTY002)。
李志清(1961-),女,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民族传统体育、体育人文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