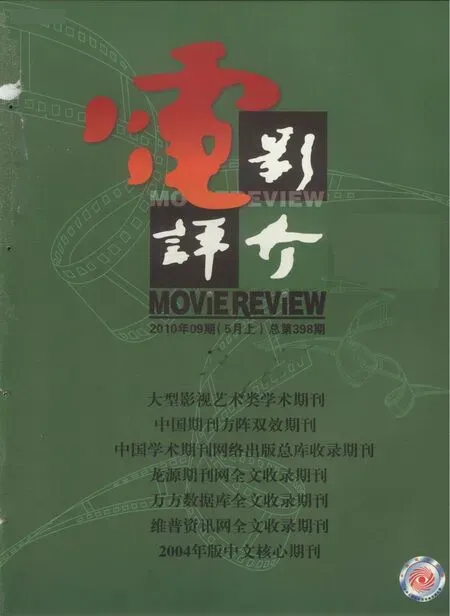从“画框论”、“窗户论”、“镜像论”的演进看电影理论的发展
电影是什么?这是自电影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产生,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的问题。“爱森斯坦说,它是旨在建立含义和效果的画框;巴赞说,它是面向世界的窗户;米特里说,它既是画框,又是窗户。精神分析学则提出一种新的隐喻,说银幕是一面镜子,这样艺术对象便由客体变为主体。”[1]
一、“画框论”、“窗户论”与“镜像论”三种理论的提出
(一)“画框论”——爱森斯坦——蒙太奇
“画框论”就是建立在蒙太奇理论基石之上的银幕观,爱森斯坦把镜头取景形容为“对象与人们观察它的角度和从周围事物中截取它的画框之间的相遇[2]”,强调导演赋予影片的意念和思想。
爱森斯坦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升华”观念和象形字、会意字的启发,提出了蒙太奇“冲突论”,他认为“镜头是蒙太奇的细胞”“蒙太奇是撞击,是通过两个给定物的撞击产生思想的那个点”“镜头内部的冲突是——潜在的蒙太奇,随着力度的加强,它便突破那个四角形的细胞,把自己的冲突扩展为蒙太奇片段之间的蒙太奇撞击”[3]。他强调蒙太奇的理性功能,认为导演可以通过利用蒙太奇来主导影片的主题表达,以达到影响和教育观众的目的。
爱森斯坦对于蒙太奇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发挥的空间,有一阶段甚至走到了一种极端的地步,认为“蒙太奇是无所不能的”。他一度设想把《资本论》拍成电影,并期待这部影片“不受传统的限制,把观念、体系和概念直接表现出来,而不要任何转折和释文。”但是,以这种理论为指导拍摄出来的影片忽略了观众的接受习惯和接受能力,逐渐受到其他理论家的质疑和批判。巴赞的电影纪实理论就是在对蒙太奇理论的批判性吸收中建立起来的。
(二)“窗户论”——巴赞——长镜头
20世纪50年代,以巴赞为代表的纪实主义电影理论家对“蒙太奇至上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若一个事件的主要内容要求两个或多个动作元素同时存在,蒙太奇应被禁用”[4],银幕是观察世界的窗口,而银幕外的世界是无限延伸的。
在影像本体论的基础上,巴赞提出了他的长镜头理论,建立了与蒙太奇截然不同的电影理论体系。长镜头理论包括景深镜头理论、段落——景深镜头理论和场面调度理论,长镜头和景深镜头不仅能保证时空的完整,而且可以呈现由深焦距带来的空间构成的层次感。这样拍摄出的影片可以保持现实的多义性和模糊性、让观众看到空间时间的真实、现实事物的自然流程。他通过撰写一系列的影评,如《电影现实主义和解放时期的意大利流派》、《评<大地在波动>》、《评<偷自行车的人>》等,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进行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评价,并且以此佐证了他的影像本体论的观点,发展了他的纪实美学。
和新现实电影的发展一样,巴赞的美学历程也经历了两个阶段。早期,巴赞主要关注的是人物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真实即外界事物的客观真实;而后期,他的视点渐渐转为对人物内心真实的探索。因而,巴赞的纪实美学往往被称为“总体现实主义”。
(三)“镜像论”——麦茨——电影符号学
麦茨把精神分析学和语言学结合起来研究电影,他在以往电影的“画框论”和“窗户论”理论之上,根据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提出了电影的“镜像论”,将观影主体引入了电影表意过程。他针对克拉考尔关于电影是“物质现实的复原”理论表述,提出了电影是“想象的能指”的理论表述。
麦茨的电影符号学分为第一电影符号学时期和第二电影符号学时期。在第一电影符号学时期,麦次发表了《电影:语言系统还是语言?》一文,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把电影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影像语言,即具有某种约定性的表意符号来处理。[6]但是第一电影符号学忽视了电影符码的生成过程及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存在明显的缺陷。在第二电影符号学阶段,麦茨的研究方向发生了转变,即运用拉康的后弗洛伊德主义来解释电影现象,把电影和观影主体、观影心理联系起来。
“镜像理论是拉康理论的起点,它描述的是婴儿时期自我身份确认之初的心灵状况。拉康认为,对完整的自我形象的渴望和迷恋是人之天性,但这种推动人迈出混沌无知、形成自我意识、看似幸运的第一步也是不幸的起点,因为自我身份的形成必然依赖于对他者的参照,只有以他者形象作为媒介,或者说必须有一个由外界提供的先在模式,主动的自我形象建构才可能完成。”[7]
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涉及到对自我及他者的认同,麦茨认为,当观众在观看电影时,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观众往往将自身认同为电影中的人物,而又意识到自己在电影中的缺席:“这是一面奇特的镜子,它酷似儿时的镜子,而又迥然不同。”“在影片放映时,我们像儿童一样处在低运动强感知状态,因为我们还是像孩子一样被想象界和幽灵俘获,而且是逆乎常理地通过一种真实的知觉。迥然不同,是因为这面镜子为我们映现一切,唯独没有我们自身,因为我们完全置身其外,反之,婴儿既在它里面,又在它前面。”[8]
麦茨的电影理论由以往经典电影理论对电影本体的探讨,转到对其他学科的借鉴,是迄今为止最科学、最系统的电影理论。
二、“镜象论”对“画框论”和“窗户论”的继承与突破
电影理论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的传统电影理论阶段和五六十年代以后的现代电影理论阶段。[9]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和巴赞的长镜头理论是传统电影理论的两个高峰,而麦茨的电影精神分析学则是现代电影理论的里程碑。
(一)“形式——内容——主体”的螺旋式上升
“画框论”提倡蒙太奇在影片中多种形式的呈现,主要探究的是电影形式方面的特点;“窗户论”认为银幕是人们观察世界的一个窗口,而这个窗口之外,是无限延伸的现实世界,强调的是电影的内容的重要性。这两种电影理论都主要致力于研究电影作为一种新兴艺术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的本体特性,可以说,经典电影理论确立了电影的独立性,同时确立了电影的基本拍摄手法和美学特征。它们相对而存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相互否定的,恰恰相反,蒙太奇理论对并不乏对现实的关注,爱森斯坦曾提出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观点“蒙太奇是镜镜头的一个阶段”[10]“镜头,如我们说过的,是蒙太奇的一个阶段”[11],这一观点和巴赞后来提出的景深镜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它们强调的都是单个镜头内部的场面调度;而巴赞并不反对蒙太奇,他反对的是蒙太奇的滥用,在《电影语言的演进》一文中更是肯定了蒙太奇在电影史上的重要意义,并给予《战舰波将金号》影片很高的评价。因而,把“画框论”和“窗户论”对立起来的观点是脱离实际的。
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日趋成熟,电影理论开始进入高校,跻身知识的殿堂,而20世纪各学科之间联系日益紧密,一些其他领域的学者开始对电影产生了兴趣,电影理论家也不再局限于对电影自身的探讨,纷纷寻找它与其他学科的契合点。精神分析学说被认为是20世纪最具开创性和影响力的人文科学,麦茨的“镜象论”就是在这一契机下提出的,它由电影本体论抽身而出,研究的是电影与观影主体的内在联系,主要凸显的是接受主体观景过程中复杂的心理过程。不难看出,由电影的外部形式,到它的本体内容,再到它的创作与接受,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电影理论发展线索。
与传统电影理论注重自身特性的探讨相比,现代电影理论更多地是把电影放在整个人类文化背景中去考察,使电影理论具有了人文科学的性质;与传统电影理论封闭式的研究方法相比,现代电影理论显示出一种开放的特点,运用其他人文科学学科的方法论多角度、多层次地展开电影研究;与传统电影理论通过传统的艺术学和美学概念来探讨电影的一般规律相比,现代电影理论通过一系列逐步形成的特有概念来探讨电影的一般规律。这些都使现代电影理论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12]
(二)对电影真实性的探讨
早在电影产生的最初时期,就产生了卢米埃尔兄弟和梅里爱之争,关于电影的纪实性和表现性以及电影自身的真实性的探讨从来没有终止过。爱森斯坦期望用蒙太奇作用于现实,通过对现实的主观干预来达到影响观众的目的,实现从导演到观众的思想和理念的传达,可以认为,他渴望通过电影实现真理的揭示;巴赞在他的影评《杰作:<温别尔托•D>》是提出:“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这名话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巴赞对于电影真实性的观点,他认为电影可以无限地接近现实,但永远都不可能等同于现实或者完全复制现实,所谓的“完整电影”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虽然爱森斯坦和巴赞的理论在表现形态上是迥异的,但是他们都是把揭示真实和表现真理当成了电影最重要的任务……在以真实为最高目标的问题上,蒙太奇学派和纪实美学理论是一致的。”[13]针对克拉考尔关于电影是“物质是现实的复原”这一理论表述,麦茨提出了“想象的能指”的理论表述,他认为“电影的特性,并不在于它可能再现想象界,而是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是想象界,把它作为一个能指来构成的想象界。”[14]他把电影的真实性分为两个层次来研究,分别是:电影这一艺术形式的真实性;电影表现内容的真实性。电影既是想象也是表现想象的手段。在第二个层次上,他深入分析了电影与梦的同构。
从爱森斯坦之真理,到巴赞之真实,再到麦茨之想象,这三位学者的观点并无高下之分,,他们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所处时代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他们都是正确的。他们对于电影真实性的探求为我们多维度地认识电影提供了可能,也给后来的研究者以启示。
(三)一以贯之的对人的关注
爱森斯坦在《蒙太奇》前言中多次强调人在电影创作中的重要性,“离开了人,不是出自人和人性,那就任何一点真正生动的现实主义的形式、任何一点真正生动的作品形象都不可能产生、出现和发展”[15]。巴赞的电影理论更是处处充满了对于人的关注、人道主义关怀,对人物处境的关怀。“巴赞的电影批评开拓了电影研究的广阔领域,涉及战后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等所产生的深远意义和对灵魂的考证,并运用存在主义现象学哲学和想象心理学考察了从空间真实衍生到物质界和精神界的本质真实。”[16]巴赞提出的“作者论”也表现出了他对于创作主体的关照。克里斯蒂安•麦茨的镜像论把精神分析引入电影,对人的关照深入到心理层次,没有对观影主体的关照,就不可能存在电影精神分析学。
“画框论”、“窗户论”和“镜像论”深刻地影响了电影的发展历程和人们对于电影的认知,每一种理论的出现都建立在前一种理论的基础之上,是对前者的批判和发展。但是,新的理论的出现并不是对前一理论的否定,相反,正是这三种理论的共同存在奠定了电影理论的不可动摇的根基。
注释
[1]李恒基,扬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1页。
[2][3][10][11][15](俄)C.M.爱森斯坦著,富澜译,《蒙太奇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第17页,第486—487页,第13页,第18页,第2页。
[4][5](法)巴赞著,崔君衍译,电影是什么?[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第54页,第248页。
[6][8][14](法)麦茨著,王志敏译,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第5页,第45页,第41页。
[7]王茜,拉康:镜像、语符与自我身份认同,河北学刊[J],2003年第6期,第130页—131页。
[9][12]许南明、富澜、崔群衍主编,电影艺术词典[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第27页,第28页。
[13]王志敏,陈捷,关于艺术真实、电影真实和现实主义的漫谈,社会科学[J],2007年第11 期,第177页。
[16]鸿钧,巴赞是什么?——巴赞电影真实美学与文化人格精神读解,当代电影[J],2008年第4期,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