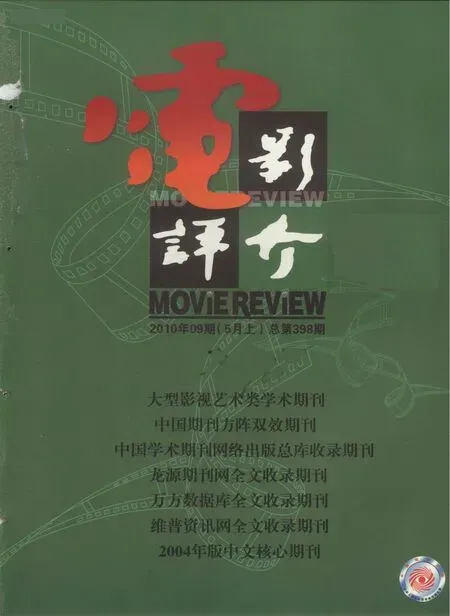视觉奇观演绎民俗叙事——浅析张艺谋电影的民俗运用
在张艺谋的影片中,几乎每部影片都展现出相当多的民俗,黄土地,大宅院,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的造型,京剧,皮影,婚殇嫁娶的场面等等,这些“民俗”往往集中典型地表现了中国的民间文化及地域文化,“但它们并不是民俗的记录.而是一种经过浪漫改造的民俗奇观。这种类型为中国的电影导演提供了一个填平电影的艺术性与商业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鸿沟的有效手段,同时也为他们寻求到了获得国际舆论,跨国资本支撑并承受意识形态压力的可能性……”
一、色彩是贯穿全篇的纽带
红色的审美愉悦效果。色彩对人的感官与心理的巨大影响,决定了它在影视作品中成为提供视觉愉悦的重要因素。电影《红高粱》通过一个男人和女人的故事,在高粱地发生种种奇奇怪怪的事,简单的思想表达出一种对生活热烈的态度,用红色就是最适合不过的了:“热炙的红色长长染布在菊豆与天青偷情时哗然而下,血红色的染池成了金山和天青两个鲜活生命的葬身之地。红色的大火烧掉了菊豆不堪忍受的染布坊——封建社会。”[1]
运用民俗营造视觉化奇观。张艺谋的影片画面有十分强烈的视觉冲击,《红高粱》中一片片密密麻麻的高粱地激情的摇曳,剥人皮的具有强烈刺激性的画面,荒野狂欢式的颠轿,大肆夸张的祭酒的场面都给人以强烈的欣赏欲望和可观赏性。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感官刺激几乎取代了理性思考,影片渲染了大红灯笼的点灯仪式,鲜红的喜庆的颜色更加重了影片的悲凉。
色彩的形象象征。《英雄》中“充满整个银幕的黑青色的秦王的军队,冷色的盾牌,血一样燃烧的红缨,以及震撼人心的呐喊”,使人禁不住慨叹秦王统一天下势如破竹的阵容之强大。[2]长空桀骜不驯,冷酷安详,他面队秦宫大内高手视若草芥的神情,使人不禁想到战争的残酷与皇权势力压迫下人的匍匐生存。
二、建筑民俗烘托背景
建筑场景象征思想主旨。除了色彩之外,建筑民俗在电影中同样也为一个背景的烘托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比如拍摄《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乔家大院,它是由南北走向的六个大院组合而成,而大院里面又套着小院,形成一种院中有院,院中套院的格局。体现的是一种“内外有别,尊卑有序”的伦理观。
《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四合院所象征的封建牢笼已经被描绘到了恐怖的地步:陈家大院秘不可测的深灰色建筑,高高的围墙,恐怖的角楼,阴森的甬道,整座大院与世隔绝。一种恐惧感始终悬在观众的心头,压抑的喘不过气来。表现了这个“黑森森的封闭院落所代表的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礼教双重挤压下人性的畸变”。[3]
建筑民俗有特俗的语义场。《菊豆》里面的主要场景是一个染坊,而这个“染坊的实景拍摄地点并不是一个染坊,而是徽州一个叫做南屏的古村落里的一座祠堂,而且是一座宗祠”[4]。祠堂建筑和民居建筑在风格上最大的不同点有两个,一个是它的体量比较大,规模比较宏阔,第二个就是在装饰上,民居的装饰比祠堂要富丽得多,比如说民居有一些雕成暗八仙、冰梅图等等图案的窗格,这在祠堂里是见不到的。因此说在客观上南屏的祠堂的确是被改造成染坊的最佳场所。
三、民俗成为影片描写的主题
对民俗进行特写。张艺谋影片中民俗的痕迹非常明显,在影片中给了民俗很多的特写和叙述。张艺谋的第一部导演作品《红高粱》中,一开场便是“我奶奶”要出嫁了,穿着红衣裳,一个老女人在给她“开脸”——应该说,这已是一个民俗的展示。但紧接下来的一个“颠轿”的场面,整整持续了十几分钟。给人以视觉,听觉上的强烈刺激。
《黄土地》中迎亲仪式、婚礼场面、黄土地、黄河、锣鼓、祈雨等民俗的浓彩重笔的描写占了影片三分之一,《黄土地》叙述的重心不是顾青、翠巧、翠巧爹等人物形象,而是土地、花轿、锣鼓、祈雨等民俗事象。
民俗展示社会生活状态。在《菊豆》中,整个影片中描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性的地点就是“秩序堂”,分上、中、下三厅,楼上放置本族的祖宗牌位,参加祭祀的各种严明规定,祭祀场面礼节繁多的仪式的描写,宗族、家长制的民俗观念被明确的传达出来。片中最典型的民俗场面莫过于杨天青、菊豆七七四十九次的挡棺仪式,以示对他们的惩罚和精神折磨。
影片《秋菊打官司》中,秋菊的每一次出门告状,都响起秦腔,高亢苍凉,极具感染力,与片中陕西方言和生活实景的交融,展示的是当代中国农村的原貌和农民真实的生存状态。
四、改造与虚构民俗
用虚构的民俗意象承载影片主旨。张艺谋“民俗”电影是远离现实却又源于现实,可以说不是中国民俗却又最像中国民俗,张艺谋电影对中国的民俗事像进行了非常精彩的艺术加工。《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点灯、灭灯、封灯”等一整套仪式,各房傍晚听召的仪式都是民间风俗中所没有的,这是张艺谋寻找民俗艺术精神的影像化表达的结果。
改造传统的民俗形式为表达主题服务。《红高粱》里的颠轿,《菊豆》中的印染操作等是可以找到验证的民间习俗,影片中表现的是对具体的细节作了艺术化的夸张。而《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捶脚、点灯等等则表现为一种没有时间地点特性的无法验证的民俗代码。
同样,《菊豆》中杨金山在中秋节点上红灯笼亲自对月跪拜求子,强调了他求子的急切心理。《红高粱》中我爷爷对酒坛撒尿居然造就了“十八里红”这个浓郁酒香的新品种,只是夸张地表现了主人公桀骜不驯的阳刚之气;再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点灯笼的情景,更是将此举作为一种信号,并不能从民俗仪式真伪的角度去考证。
结语
总之,张艺谋在影片中民俗的运用还是带给我们很多新的东西,民俗在影视中获得了新的审美意义,使画面更具有美感和视觉冲击力,民俗的创造性的事业,使影片的意义增殖,实现了寓言化的叙事效果。影视艺术从其发生形态和发展走向来看,是以民俗为依托和前提的,它是美的,也是民俗的。
[1]钟大丰,舒晓鸣.中国电影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P14.
[2]赵Ji..《英雄》vs《卧虎藏龙》4:1 [J].新闻周刊,2002,P35.
[3]葛颖.带果仁的巧克力—论“大众电影”的形态[z」//陈犀禾.当代电影理论新走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P102.
[4]张明.与张艺谋对话[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 P56.
[5]韩养民,韩小晶.中国风俗文化导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P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