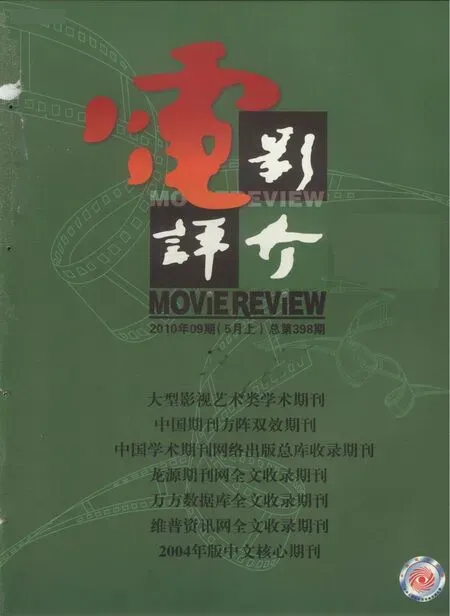试析《十月围城》人物塑造的价值取向
晚清以降,普及革命[1]的思潮,使革命在追求现代民主中成为必不可少的因素。梁启超以保皇立场肯定革命为“仁”、“群”、“公”;[2]革命派领军章太炎论述了“同处革命之世,偕为革命之人”应有之道德、信仰、热诚等。[3]民国成立后,梁启超认为“从甲午戊戌到辛亥,多少仁人志士,实在是闹得筋疲力倦,中间自然会发生一时的惰力。尤为可惜的,是许多为主义而奋斗的人物,都作了时代的牺牲死去了”。[4]因为“牺牲”希望通过“革命”实现“民权”和“民主”之“国”:“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亡则国权亡。”[5]在谈及革命过程中为民族国家、民权、民主等做出牺牲的志士猛士们时,鲁迅对革命与“牺牲”之间的关系的态度是矛盾的:“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结果)”,“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6]
以上思想家围绕如何认识“牺牲”从事的革命与其追求的目的——民主的互动关系的思考,至今还有使我们重新正视为追求“真正的民主之国”的“革命”成为“牺牲”的人物的必要性。[7]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的今天,《十月围城》通过人物塑造显示的价值取向,呈现着新世纪人们的聚焦点的设置和转移:探求卷入革命的各类人物的情感世界的丰富性,展示人物人性中积极执著方面,提供处于革命对立面的人物思想状态等等,都吸引着观众参与到电影思想内涵的建构之中。
与几代观众熟悉的人们加入革命阵营的模式诸如苦大仇深、党的教育等不同,《十月围城》没有把“垂死挣扎”的满清政府使人民“水深火热”的状态作为关注点,却探求了“没有人逼”却与革命发生了“关系”的各类人物的情感世界的丰富性,在这种“关系”的多样性中愿意使观众相信和感受到其中蕴藏的无限潜在的可能性。职业革命者拥有“革命”能救中国的亿万大众的信仰,相信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痛恨“主——奴”区分的不平等现实,要改变之并建立民主的中国,而且最终也在万般无奈之下改掉了“见血就晕”的“老毛病”;但面对无数的牺牲和凶险无比的风雨时,又都有“过不了自己”的痛心。当革命距离自己遥远时,商人把“革命”二字与“钱”等同;当知道革命将面临清廷的剿杀,明确意识到儿子与之相连时,想到了它与“造反”等同,“疯了”一样指责自己出资资助之革命者“疯了”;但对朋友委托使命的仁义,使他最终由“商人”变成“中国人”;但“非常时期”的“统一的规划”,却使“我们都是一份子”的激情无法落实在儿子身上,“良心”使其痛苦谴责自己是个“大骗子”。少林出身的小商贩因为有着痛恨“欺软怕硬”的“爱憎分明”,走向了“打洋人”“打坏人”的行列;忠诚于老板、憧憬着美好婚姻生活的车夫,为“能让老板高兴就好”,毅然负起“保护好少爷”的重任,执著地走向“找死”的道路;“什么都做”的赌徒,为了做 “一个有责任的父亲”,落魄公子抱着报恩、解脱人生最苦的惩罚、不问值与不值的“尊严”,走向了“明天”。用职业革命者的语词总结各类人物的牺牲与革命的关系,就是“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做革命。”
但探求卷入革命的各类人物的情感世界的丰富性,并没有成为影片展示人物人性中积极执著方面的障碍:看着自己最爱的人因自己而死的人生痛苦和自我惩罚。换句话说,影片选择展示“革命者,革之以命”的“牺牲”“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的价值取向时,没有刻意回避蕴含其中的悲壮意味,但又没有隐含其建设性地引导当今观众对人性美好道德情感建设的明确价值取向。影片符合主旋律对在集体事业中充分尊重个体生命价值的取向,同时也抓住观众的审美焦点,符合了当今时代人们历史地理解和尊重革命,以及对回归美好人性的希求。面对革命的血腥,商人坚决指出“我儿子绝对不能是”革命党,在“集合社会各界力量”时,嘱咐儿子听话“不要出门”,儿子牺牲后不禁老泪纵横;商人之妾、车夫、赌徒、小商贩、败落的富家公子对自己钟爱的人的纯朴、执著、无私的关爱之情,甚至高呼“这是大英帝国的香港”的人物,也为卷入革命的人们送来信息、枪支并护送这群队伍等等场面,都使观众感受到人性中美好一面对人的心灵的撞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革命的血腥和残酷对人们心灵和视觉的冲击力,也显示和刻画出人物性格的丰满性。
影片吸引观众参与影片思想内涵建构的方式还在于,它提供了处于革命对立面的人物对革命的无比仇恨,甚至也展示了其与前者构成对话过程时呈现出的思想状态,为追求民主的革命的艰巨性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作为洋学堂培养的军人,作为职业革命者的学生,人物有着自己不顾一切的执著,影片甚至以人物无比坚决的态度、言词和行动来突显了这一切。这个被革命者的老师称为“头脑愚钝”的“莽夫”,以自己受过西式教育、睁大的眼睛看清楚了世界,反驳了先生对学生的“错怪”,一定范围内颠覆了人们眼中这类人物所属本性——鹰犬的命名:自己毕恭毕敬、惟命是从于朝廷的原因在于,他认为皇权天赐,人生而不平等;而洋鬼子对国家的欺凌,造成了中国连年战乱和百姓的民不聊生,他也看清楚了洋人的狼子野心;指责“见血就晕”的教书匠与“救中国”的“大事”无关;剿杀“捣乱”的革命党,在他看来,就是学生遵照恩师授业要求,“已报国恩”。在什么是理想之国、造成民众灾难的原因和救国图存方式等几个方面,影片突显处于革命对立面的人物的这些声音,其目的当然是引导观众认识到“十月围城”时卷入革命的“牺牲”的悲剧结局的必然性,但又何尝不是愿意让观众必须理性地理解其中代表的价值取向的历史性。
影片突显出的人物塑造的以上三方面价值取向,应该能使观众不仅仅在其中获得情感的宣泄,更能把观众引向思考如何历史地理解和尊重历史中的人这一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影片制造的众声喧哗中,被其人物塑造的价值取向所吸引,保持着与它的积极交流和互动。
[1]民.普及革命[J].新世纪,1907(15).
[2]梁启超.释革[J].新民丛报,1902(22).
[3]章太炎.革命之道德[J].民报,8.
[4]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A].最近之五十年[C].抱一编.申报馆1923.
[5]梁启超.爱国论三[J].清议报全编(卷一第一集上之上本馆论说一通论上).横滨新民社1900.
[6]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63.
[7]任慧群.三重视角中的“粉末”与“革命”[J].电影评介,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