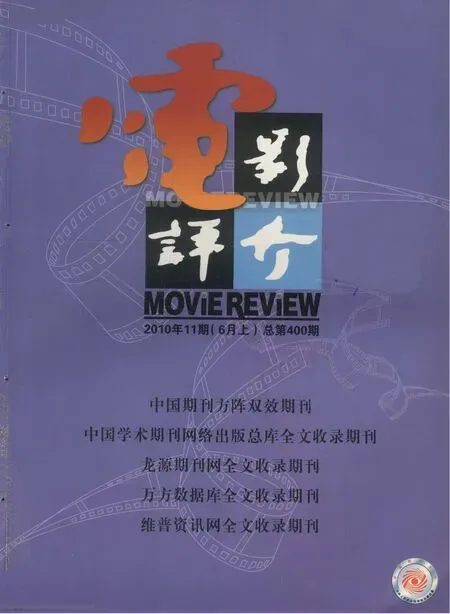都是“忠实原著”惹的祸——给新版电视剧《红楼梦》把把脉
在对于李少红导演的电视剧《红楼梦》的批评与赞扬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忠实原著”。批评者认为《红》剧从演员的选定到表演、从服装道具到场景设置、从旁白到配乐等等都距离原著太远,因而是不“忠实原著”。而赞扬者却针锋相对,认为上述各方面不仅非常忠实于原著,甚至比87版《红》剧更忠实于原著。就连导演李少红也在各种媒体上大谈自己“最”忠实原著。
看来,是否忠实原著,已经成为人们评价《红》剧改编成功与否的一把标尺,甚至成了改编的“死穴”:忠实原著则生,否则便死!
果真如此么?我看未必。
曹公的《红楼梦》是使用汉语言文字写成的文学名著,属于语言艺术。后人将其改编为影视剧,是把语言转换成了图像,即语言艺术变成了视觉艺术。二者在艺术性质和审美效果上有霄壤之别,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谈“忠实原著”就要做具体分析了。
纯从字面意思上看,“忠实原著”就是从形式到内容、从细节到整体、从艺术到思想……都和原著“不离不弃”,保持高度一致。这能够做到吗?能!那就是找一书生,把原著从头到尾一字不差地念一遍(类似于“广播小说”)。新版《红》剧的“旁白”在一定意义上就承担了这一任务,且李导也把这叫做“忠实原著”的表现,可惜她无法在电视剧中贯彻得彻底。
上升一个层面看,就是把原著当做影视剧作的脚本,编导要做的就是对故事稍加删改,写出分镜头剧本,制作成活动影像。其中的人物、故事、场景、结构都以原著为摹本,将文字描写的平面形象立体化、视觉化。这样的“忠实原著”充其量是摄像机的苍白拷贝,说得好听是照猫画虎,不客气地说是艺术创作无能的表现。
再上升一个层面看,“忠实原著”应该是改编者在尊重原著故事框架、人物形象塑造、场景设置和基本精神内涵的前提下,大胆增删与取舍,理出一条既属于原著又能表现自己独具艺术匠心的故事线索,由此而谋篇布局、铺排成章。
这样做首先需要改编者对原著有较深的理解,对其精髓有深入的把握,对其魂灵有极深的体悟,然后才谈得上哪儿该增、哪儿该减;何处可详,何处可略;谁主谁次,哪隐哪显,而不至于眉毛胡子一把抓,把拘泥刻板当成艺术创作,把亦步亦趋说成“忠实原著”。
如此说来,所谓“忠实原著”应该是影视剧改编的艺术准则,是一种既基本又宏观的审美要求,它不应拘泥于细枝末节,不应拘执于原著文本,它要求编、导、演具有高深的艺术修养,大胆的艺术创新精神,丰富宏阔的想象能力,出色的艺术表现才情——这一切不是一句“忠实原著”所能涵括得了的。
对于《红楼梦》这样的以写实为主而又融合了其他艺术描写手法的文学作品而言,现实主义精神是其贯穿始终的基调,改编者应该在这方面充分尊重原著,不能随意发挥,不然就会面目全非。而对于某些具有象征意味甚至虚幻意味的情节、人物、场景(比如太虚幻境、空空道人、金陵十二钗判词等)则发挥想象的余地就大一些。然而新版《红》剧在这两方面处理的都不够好,究其原因,还是“忠实原著”的创作初衷和改编观框住了编导的想象力和艺术表现才能。
先说写实方面。由于过于拘泥于原著的年龄,把个小宝玉、小黛玉、凤姐搞得奶气十足,道白象背书,行动象人偶,“打情骂俏”象过家家,何来“云雨初试”,又何谈“金玉良缘”?小毛丫头似的凤辣子又怎能辣得起来?宁荣二府上下几百人等又如何听从她调遣?原著中对于三人的描写是全面的、充分的,前有铺垫,后有照应,加以出色的行为、心理刻画,诗词歌赋点染,这一切诉诸读者的想象,顺理成章地在头脑中再造出一个个活生的宝、黛、凤、钗。而在电视剧中,这些人物未经渲染,不经点化,突然凭空而降到观众眼前,这如何才能让人相信他、她就是书中的“这一个”?所以相较而言,87版电视剧的演员在年龄上比原著偏大,这是非常明智的,是懂得影视剧与文学区别的表现。
在人物道白方面,李导为了“忠实原著”,把小说中人物语言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到荧屏上,让剧中人说着半白半文的句子(虽然这也是当年的“白话”),让观众听得云遮雾罩。除了“忠实原著”这一堂皇的理由外,恐怕更重要的原因是这样处理比重写台词来得省事儿。然而编导在这里忘了一个基本道理: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并非一回事!作为供阅读的文学作品,作家笔下的人物语言可以不必追求口语化,人物说话可以咬文嚼字,可以使用长句和复杂的句式,甚至可以使用富有文学色彩的修饰语,排比句等等。并且作家为了保持语言风格的统一,人物语言的基调基本上是一致的,虽有个性差异,但总体上不会破坏这一基调。然而把这样的句子都原封不动地搬进剧里,让人物满口书面语言,给人的感觉自然是很别扭的。
在服装道具方面,有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细节值得玩味。据有关媒体介绍,李导为了“忠实原著”,对小说中至关重要的道具通灵宝玉和黛、钗、凤的服装投入了不小的本钱。据称,为了追求真实,李导自己花了几万元钱买了一块玉,两面镌刻了文字,佩戴在于小彤(宝玉饰演者)项上。三位美女演员所穿华服则是著名苏绣大师的封山之作,每件价值四五十万。但问题是,这样做的效果如何?其实有时候真材实料的视觉效果并不最理想。观众难道会无聊到专门考究玉的真假与否,衣着是否华丽,并以此去评价电视剧审美价值和艺术品位?你可以买真玉,你可以让演员穿华服,你也尽可以让人物真哭真笑真搂真抱,但你能让黛玉真死、宝玉真疯吗?艺术本来就是虚构的,所谓“真实”也是假定情境中的真实,是让读者、观众“信以为真”。若连导演在观念上都混淆了艺术之真与生活、历史之真的区别,非得弄块真玉戴在宝玉脖子上,那么你的真实原则要贯彻到底,就得让宝玉真摔那块“劳什子”(真玉)。你舍得吗?
再说非写实方面。小说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叙说故事源起并人物身世,借空空道人、疯跛老道之口,外加“贾语村言”、“好了歌”,为全书定下了“空灵”与“虚幻”的精神基调,在全书故事结构上也无非起了个穿针引线和“起兴”的作用。然而新《红》剧却非得从这里也体现出“忠实原著”的精神不可,一边让旁白者在背后大念其书,一边用了小人书式的画面来诠释这所念之书,完全忘记了影视是用视觉形象来说话的基本道理,结果成了不伦不类的“小说挂图”,岂不大煞风景!
“忠实原著”?谁能完全做到?敢问少红导演,“红楼梦中人”的一颦一笑、一行一动都与原著无异么?他们的饮食起居、行坐起卧、偷情扒灰、明争暗斗能与原著一样吗?他们穿的衣服什么料子?他们住的房子什么砖石?他们说的话什么腔调?他们睡觉各自都做什么梦?他们吃饭各自都是什么滋味?“还泪说”怎么表现?绛珠仙子(黛玉)跟神瑛侍者(宝玉)的“木石前盟”如何还原?原著有名有姓的人物700多个,你才演了360多个吧?更不用说,弥漫全书的虚幻感、色空观、意淫意识、人生大悲叹等等深沉意味,难道是你手中一群偶人能够表演得出来的么?原著曾长期被视为“诲淫”之书,原著中多处情色描写、荤语脏话难道你也要一丝不苟地“忠实”表演?所以说,影视剧对于文学作品的改编属于艺术的“再创造”,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完全“忠实”,因为既然是改编,就必然有所增删,有所选择,有所创造,这才能见出改编者的艺术创造才能。若一味摹仿,一味还原,一味“忠实”,亦步亦趋,照抄照搬,即使是拍得画面再“唯美”,衣着再华丽,场景再奢华,也无非是一些表面文章,烧钱摆阔而已,与真正艺术创造的差距何止以道里计!
如果照猫能画出虎,那也是只假虎。很可惜的是,往往照猫画出的仍是猫,甚至是“非猫”,死猫。
反正说到底,都是该死的“忠实原著”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