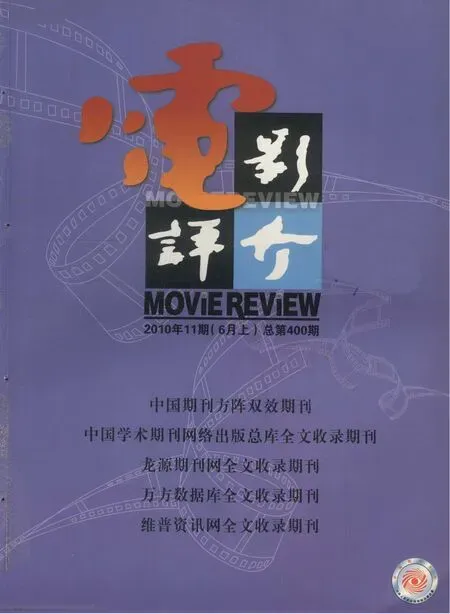为什么要与众不同?
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生命的短暂和倏忽即逝使她异常恐慌,对平庸的恐惧更使她渴望克服生命的虚无。对她而言,面对恐慌和虚无的最好态度是让自己成名以享受此世生命的与众不同。她没有走到否定此世生命、否定平淡的日常生活的极端道路。因此在她笔下,白流苏选择珍惜可能得到的并不完美的尘世生活,而曹七巧,当她连此世生活都被毁掉的时候,她也开始毁灭别人的生活。在这唯一能够看得见、经验得到的此间世界,我们该怎样面对我们时时刻刻置身其中的日常生活和那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平淡无奇的一生呢?这个熟识的此间世界是否必然意味着与梦想、与超越之间的紧张冲突呢?
令人不安的是,在近几年关于这一问题的几部电影中,主人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自己置于和平凡的此间世界的对立面,这个须臾不曾离开的分分秒秒的生命和琐碎的日常生活是她们逃离虚无和平庸的最大敌人。是的,她们需要的不仅是克服有限生命的虚无,她们还有更大的野心,就是超越那平凡的生活,成为卓越的、独一无二的那一个。如果生命本身就意味着平庸的话,她们不惜杀死自己的生命——那平庸的载体。是的,是她们,是那些女人们,是《时时刻刻》中被一个叫达洛维夫人的作家神秘地关联着的三个女人,是《巴黎野玫瑰》中疯狂的贝蒂,是《革命之路》中神经质的、杀死自己的爱珀尔,是《孔雀》中因梦想而自私到极致的姐姐,还有《立春》中自视甚高、目无下尘的王彩玲。在这些女性看来,平淡琐碎的日常生活代表的就是虚无和平庸本身,她们所看到的只是自己和梦想的关系以及由此衍生的自己和自己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生存的她们,忽略的是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而这恰恰是人的存在的特别之处:即在和他人的关系中与他人共在。她们把日常生活看作是平庸的,因此日常生活和这种生活中的整个关系都是她们的敌人,是这一切摧毁了她们的梦想和与众不同的可能性。在此,我选择其中的《革命之路》和《立春》作为自己分析的电影文本,来探讨两个问题:一,现代性追求永恒的道路的转折,这种转折抛弃了对彼岸世界的幻想,把永恒纳入到现实世界,当日常生活被视为对这个可能实现的现实世界的永恒的一种消耗时,二者之间的紧张冲突就出现了;二,沿着第一个观念的逻辑,对日常生活的痛恨呈现为对他人的爱的缺失,人与人之间是一种互为追寻梦想的障碍制造者的关系,这种爱的缺失最终导致的是对此间世界的全面否定和日常生活的彻底毁灭,这样的话,人的生命存在的基础和一切追求的依托在哪里?
《革命之路》中,爱珀尔和丈夫搬到革命之路居住。这条路的名字很诡异,它暗示了爱珀尔以激烈的方式反抗她认为平庸的日常生活的毁灭性命运。作为一个曾经的专业演员,爱珀尔不满足于那种和其他人一样的平淡生活,尽管她和丈夫被那条路上的邻居认为是最美满、最与众不同的一对夫妻。她最初嫁给现在的丈夫,也是因为她在他身上看到了与众不同之处。然而,她觉得自己正在沉沦,过着和别人一样平庸的日子。有人说,《革命之路》中爱珀尔和丈夫的生活就是《泰坦尼克号》中假如杰克依然活着并和罗丝结婚后所面临的困境。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爱珀尔和丈夫的爱情并不是被日常生活所消耗,而是爱情和日常生活的平庸被爱珀尔置于一种残酷的博弈中,如果爱情要赢,那么丈夫必须和她一起抛弃日常生活的平庸,否则,爱情将和日常生活一起被她抛弃和毁掉。在追求与众不同的过程中,爱情对于爱珀尔早已退居次席,如果不能与众不同,爱情也是平庸的。她希望丈夫和自己一起去的巴黎,也不是一种具体的活生生的日常生活,而是抽象的、被梦想装饰的符号。“到巴黎去”是她的“生活在别处”的梦想的诠释。她的丈夫,甚至她的邻居、朋友,以及在影片中出现的所有的人都被导演赋予同样的人生痛苦,那就是面对平庸的、与他人无异的日常生活,该何去何从呢?这种人生痛苦在电影中以一种在现代艺术中常见的经典影像显现出来,那就是爱珀尔的丈夫上班途中那些同样的衣服、同样的帽子、同样的表情或者说没有表情,所有的个体都被淹没在同质化的大众之中、淹没在抹平差异的格式化办公室中。当那些邻居和同事听说爱珀尔和丈夫要搬去巴黎之后,他们流露出的是羡慕、忌妒以及自己不能改变现状的悲伤。当爱珀尔的丈夫从被淹没的生活中看到了自己漂浮上来的希望之后,他不需要再去巴黎寻找摆脱平庸的可能了。于是,对于爱珀尔而言,死亡,毁灭这个平庸生活的载体——她的生命本身,就是她摆脱平庸的唯一可能,甚至,她也要毁灭腹中的孩子,平庸的生命和平庸的生活一样不应该延续。面对她的激进的反抗导致的悲剧,那些同事和邻居五味杂陈,大众在日常生活中的邪恶在面对爱珀尔的死时以淡淡的庆幸与不屑的态度难以掩饰地表露出来。人就这样被分成了两类:爱珀尔和非爱珀尔。然而无论是哪一类,人生都是痛苦的,要么忍受平庸,要么毁灭平庸的载体——生命自身。
可是,在人类的社会秩序中自我与他人的共在必然因为日常生活的趋同而陷入自我泯灭的循环吗?如果我们回头看一看古典思想的阐述,那么爱珀尔式的反抗显然是对既定的正义秩序的破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于社会的设计是从城邦整体开始的,如果一个城邦是按照正义公正地设计的,每个人都能按照其才能和天赋在城邦中有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那么这个社会秩序就是合理和正义的。而一个合理和正义的城邦必然保证生活于其中的公民处在正确的位置上,也就是与他的才能和天赋相称的地位与生活。但是对于爱珀尔来说,问题在于,她认为她应该过一种与她已有的生活不一样的生活,她并不认同自己现有的生活秩序是本来应该如此的。在《革命之路》中我们看不到宗教在其精神生活中发生什么样的影响,显然,爱珀尔要的只是在此间世界她的生命有与众不同之处。从这个角度看,她和奥古斯丁走向了一条同样的道路,那就是对此间世界的彻底否定,尽管在二者那里都未必是有意识地进行这种否定,并且其否定的出发点也完全不同。正如汉娜•阿伦特在《爱和圣奥古斯丁》中所分析指出的,奥古斯丁因为对于爱的对象的选择,贬低了终点也就是死亡的价值和意义,生命过程本身被抹平了。重要的不是爱的对象是什么,而是如何进行选择。爱这个世界并不是选择,因为世界就在这里,爱这个世界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他所选择的是这个世界本身不能提供的东西,是爱上帝。[1]这种爱的秩序,且不管在真实的人类世界中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就其内在逻辑上来说,它把此世的存在看作是无。奥古斯丁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其背后有复杂的宗教信仰的考虑,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我在此不作分析。他的选择的目的是为了使生活在尘世的苦难和罪之中的人通过救赎获得不朽。这样的不朽在奥古斯丁那里只能在彼岸获得,此间世界的生活是个过渡和桥梁,如果没有彼岸的希望,这个此间世界的生活就是完全的虚无。
但是,对于爱珀尔来说,她想得到的与众不同只是在这个此间世界,不是在这个此间世界的“这里”,就是在“那里”,是一个“别处”,是永恒在人的精神生活中抹杀后被时间死死限制着的不同空间形式,在她那里,对立不是此岸和彼岸的,而是须臾不离的日常生活的平庸和个体生命渴望的与众不同。这种与众不同就是生命价值的体现。如果个体生命不是与众不同的,那么这个生命就没有价值,就没有“过下去”的必要,没有价值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于是,当她认为自己没有任何希望可以过“与众不同”的生活的时候,她只能选择杀死自己。对于奥古斯丁的生活世界来说,无论这个世界怎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要在爱之中好好地过完此生以期得到上帝的拯救,进入永生。但是爱珀尔的希望只存在于此世,没有此世之外的选择。如果说在基督教的世代中,人的生活的意义最终通过爱完成自己的救赎,那么在爱珀尔的生活世界中,爱是缺失的,她的最终的也是最高的选择是自己的与众不同,说到底,就是她之所以作为她存在的理由。本来,这样的追求无可厚非,只是她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她一个人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并不能只从自身寻找,人的价值和意义一定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从自身和世界的关联中发现的。如果说奥古斯丁的伦理秩序中因为爱上帝而最终导致把自己、邻人和世界都置于否定的、虚无的状态,在把爱作为获得幸福的手段的时候造成了爱和幸福的根本性悖谬的话,那么,爱珀尔的爱的缺失同样造成了对他人和此间世界的恨。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恨和自我毁灭?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当基督教从人的精神生活中渐渐隐退,人摒弃了对彼岸世界的幻想,人们只能从“过渡、短暂、偶然”中抓住永恒。[2]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对波德莱尔敏感地捕捉和深沉地赞美的现代性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他说:“存在某种永恒的东西,它既不是在现在时刻之外,也不是在现在之后,而是在现在之中。”福柯在分析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这种认识时,非常肯定地指出这种现代性的态度并不是面对不断逝去的时刻的眩晕感,而是一种将现在英雄化的意志,这种态度中蕴含的是对于现在的肯定,正如波德莱尔说的:“这种过渡的、短暂的、其变化如此频繁的成分,你们没有权利蔑视和忽略。”[3]在这样的现代性态度中,“现在”,也就是当下的生活是追求永恒的场所,福柯说,在此人面临的问题首先并不是解放自己,而是塑造自己。显然,现代性的发展没有实现自己的初衷,它正在并且已经切实地演变为“在不断逝去的时刻前的眩晕”。爱珀尔脱离基督教传统的生活世界既不能在奥古斯丁的生活秩序中得到安排,也不能回到柏拉图的城邦社会秩序。奥古斯丁是在爱上帝的前提下安排尘世生活,把人的救赎的实现放在上帝之城中。柏拉图则在确定了每一个人的才能和天赋之后,让每一个人在一个井然有序的城邦中各安其位。在现代社会中,或者说对于爱珀尔以及她的世界中的人来说,认为每一个人的禀性是确定的这样的观念是难以理解和不可接受的。而且,影片中一个人是否能过上与众不同的生活并不和个人的禀性联系起来。爱珀尔的困境只是一个现代性的焦虑:如果我和别人是一样的,我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意义和价值呢?但是她没有想明白一个问题,即她应该从什么方面、到哪里寻找她自己的价值或者说存在的理由。于是,死亡成了她很自然的一个选择。这种冷酷的自我寻找道路和反抗平庸的方式,如果做更深一步的解读的话,我们也许还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广泛的政治隐喻:在这个社会中,如果生活是不公正和非正义的,人们是否应该走上“革命之路”,象爱珀尔一样进行一场血腥的社会革命呢?还是象其余的人那样在忍受中等待改变的可能性和希望?
无论如何,就个人而言,爱珀尔们都需要重新反思其整个价值选择和安排其生活的秩序与伦理,至于如何反思和安排,这是对整个现代性和尚未完成的启蒙理性的批判性思考,任务艰巨,非本文所能完成。我接下来要着手的是对另一个电影文本进行分析,试图呈现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和中国式的困境,那就是与爱珀尔生活的时代并不遥远却隔了万水千山的中国北方一个小城里怀揣梦想的丑陋女子——热爱唱歌剧的王彩玲。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王彩玲生活在一个和爱珀尔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这个文化背景有着很强大的连续的传统,而中间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换和断裂,对于这个转换和断裂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评价是个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很复杂,但又是准确和有效地讨论王彩玲的命运的根本前提,不能避而不谈。
基本上,在新文化运动之前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连续的、融贯的,其主流是儒家的正统思想,中间不断有外来文化的融入,但是都在儒家文化强大的整合力面前被自信地吸纳。此外,无论整体文化中的异质元素有多少,儒家和道家、佛教思想在整合之后都有相对明确的影响和功能范围。在三者之中,儒家无论是在道德伦理领域对人的精神生活的约束和熏陶还是在政治范围内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塑造上,都对个人的生活进行着整体性的规约。道家和佛教在世俗的人伦日常生活中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影响仍然只是具有弥补性质的功能,当然,这并不是说,弥补性的作用就意味着它是不重要的,而是说,正因为这种弥补作用,才使中国人尤其是古代有追求、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在进退之间能或多或少地找到一点精神平衡。这种状态在持续了一千多年后,随着十九世纪后期国运日衰、传统文化被不断质疑和挞伐,新文化运动以一种激烈的姿态开始了对自己的传统的革命。无论这个革命是否成功,也无论其后果是什么,其中隐含的逻辑都完全是文化上的“成者为王败者寇”的思维模式,既没有考虑整个历史发展进程的多重因素影响,也缺少对东西方交锋的背后文化之外的力量的探究,更没有面对西方文化强势进入时的冷静反思和批判。这种以成败论英雄的对待文化的态度不仅是中国历史发展到危机时刻的慌不择路,也是人类生活演进中幸福观的功利色彩的不断强化。但是这种慌不择路只在最肤浅的层面上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那种深入骨髓的观念和文化习惯并没有因为这一次粗暴的革命而被抛弃,在此成问题的只是什么是被改变的,什么仍旧遗留了下来。我只稍微说一下那没有改变的,或者至少直到王彩玲生活的时代仍然根深蒂固的。
儒家三不朽中,依次为立德、立功、立言。能立德者为最高境界,几可称圣,这样的人少之又少。求其次者,能立功、立言的则较多,也是大多数人谋求功名、建立个人乃至家族价值的途径。这种价值都是在人类的世俗生活中实现的,并不涉及彼岸世界。如果说基督教在爱上帝的前提下返回到对人类世界的关怀,儒家的价值观则是在对天和神的存而不论或者说悬搁态度下直接面对人类当下的世俗生活。以孔子来说,他并非不关心天道和命,子不语怪力乱神,是因为他对天道和命充满了神秘感和敬畏感,以人之渺小无可窥测天意。所以在孔子的三畏中,第一敬畏的就是天命。在人生价值落实到当下的世俗生活的前提下,我们就可以谈谈对传统中国人来说重要的忠孝和家国了。在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和个人生活秩序的建构中,有一个从自我到家庭到社会和国家的渐进上升的修养和实施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从诚心正意、格物致知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自我完善和社会完善的良性循环。忠孝家国在这种循环中并不处于对立面,所谓忠孝不能两全,是在具体情境中进行家、国两者之间的选择和平衡。把家国这一对概念进行转换,对应的人生价值领域就是家庭的日常生活和更能体现个人价值的事业前途。这两者之间一般都能进行较好的协调,即使为了一方而放弃另一方,也都能在当时的环境中寻找到有力的价值支持。在面临两难的时候,选择的出发点更多地是责任的权衡,往往是责任更重大的那一方成为选择时的优先考虑,其背后是传统伦理的诉求和约束。在这一点上,传统中国可以说是在一种封闭的不变的时间观中保持着始终如一的态度。但是,新文化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人个人价值的实现受到了挑战,个人的价值实现途径虽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是背后却没有与之相应的传统伦理和道德来保障其实现和维持其平衡。所以,《立春》中的王彩玲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和自己的梦想放到了非此即彼的极端对立的困境。
影片中王彩玲被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她是一个难能可贵地追寻梦想的小人物。为了自己的梦想,她放弃了享受任何日常生活的快乐。日常生活与梦想之间的极端对立是谁造成的?这却是一个需要深究的问题。王彩玲的眼中,那个她生活其中的小城市就是平庸的代名词,她鄙视那里的一切。唯一让她的生活出现过一丝亮色的,只是一个长相英俊的和她一样梦想着有朝一日跑到北京、摆脱平庸的绘画爱好者。很难想象爱情的定义在王彩玲那里是对于梦想的共同追求,如果那个借找她学习声乐之机追求她的工厂男工也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王爱玲和他之间又会发生什么样不同的故事呢?在王彩玲实现梦想的过程中,我们并不能明确地看出真正的障碍到底是什么,因为,在电影中并没有考量王彩玲的实际才能如何,其次,影片一个重要的线索是在强调王彩玲想方设法买一个北京户口。影片似乎在暗示,王彩玲梦想破灭的最重要原因是她没有北京户口。如果这样,这部电影就是一个政治批判。在这样的批判中揭露的是,社会的非正义和不公平毁灭了个体寻求梦想的所有可能,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生没有希望,生命是彻底的、无法改变的悲剧。如果政治批判是影片的意图,那么,他们是否意识到,王彩玲在某种程度上合作演出了这个悲剧,并且隐秘地渲染了她所生活的社会的悲剧氛围?这并不是信口雌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梦想都是值得称许的,关键在于追求的是什么样的梦想,以及对梦想的追求是否一定意味着和日常生活的冲突、和他人的对立。
影片中以一种惯性的思维方式把王彩玲和他人放在对立的位置上,她鄙视所有的人,并且自视比别人高贵,因为她有梦想,有与众不同的想法和追求。对王彩玲需要质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她有什么权利鄙视别人的生活和存在,她有什么权利认定别人是平庸的?当她对别人怀有这样的认识和态度时,她和那阻碍并毁灭她的梦想的力量没有本质的区别。第二,如果她追求的只是纯粹的唱歌剧,为什么非得到北京、巴黎唱?难道对于她而言所谓的梦想只是离开一个保守落后的小城到北京出人头地?这样的话,她不比她生活的那个小城的任何人高贵和优越。如果这个质疑让一些人不能接受的话,影片最后她没有买到北京户口放弃唱歌剧进而放弃教书即教音乐,改以杀羊卖肉为生,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影片的目的是政治批判,对王彩玲这个人物的塑造只能说削弱了其政治批判的力量,因为当梦想的追求者把梦想作为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手段时,她自己就在实施一种暴力和压迫,她以自己对别人的鄙视和傲慢增加了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阴暗。在这个过程中,爱和悲悯始终都是缺失的。而爱和悲悯的最直接的源头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悲剧处境的切身体认,并因这种体认达成对别人的谅解和爱。推己及人,忠恕之道,在王彩玲那里成为稀缺的品质,她助长了她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冷酷和残忍。传统伦理崩溃之后,追求功名之心未改,什么才是进行自我完善和道德涵养进而协调自己与他人共在的有效生活秩序呢?
爱珀尔的悲剧是现代性带给人的寻找自我的生存焦虑,王彩玲则是在传统的废墟上和他人厮杀的狼。前者是每一个在现代性的碾压下无可奈何呻吟着的不断退化的个人,后者是和自己也和他人战斗的铁血斗士。无论是爱珀尔还是王彩玲,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选择,建立新的生活秩序,在这个新的秩序中,人不是为了抽象、干瘪的与众不同而生活,而是为了那被遗忘的原初梦想——幸福而不断地思索和寻找。
注释
[1]Hannah Arendt, Love and Saint Augustine,edited and with an interpretive essay by Joanna Vecchiarelli Scott and Judith Chelius Stark,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76-77.
[2][3]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见《现代生活的画家•现代性》一文).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23页、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