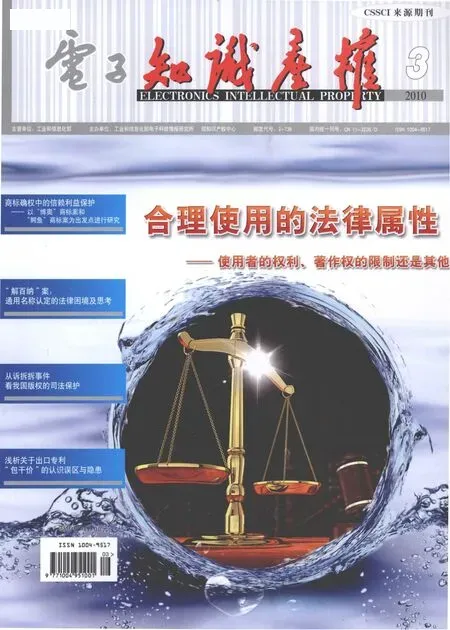合理使用的法律属性
——使用者的权利、著作权的限制还是其他
朱 理/文
合理使用的法律属性
——使用者的权利、著作权的限制还是其他
朱 理/文
合理使用的法律属性问题有着重大的实践意涵,我国法学界对此一直存在理解偏差。运用大陆法系主观权利和客观权利两分法以及霍菲尔德的权利理论,论证了合理使用是使用者的特权,是一种客观权利。法律规范的属性和正当化根据的不同都不会影响合理使用的特权或客观权利属性。如果著作权人利用合同或者技术措施妨碍使用者实现合理使用,使用者也无法获得法律的强制救济。
合理使用 著作权 特权 客观权利
探讨合理使用在法律属性上的定位,不仅是著作权法理论的需要,更是实践的要求。随着我国著作权法对作品的技术措施开始提供保护,明确合理使用的法律属性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使用者权利说和著作权限制说的缺陷
我国学者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所注意,并且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索[1-2]。对于合理使用的法律属性,他们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使用者权利说和著作权限制说。前者认为合理使用是使用者的一项独立权利。与之相对,后者则认为,合理使用是 “对著作权人主张著作权的一种限制”[2]40,“不是授予使用者任何具体的民事权利”[2]43。
他们的分析存在诸多问题。在分析工具上,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所使用的权利概念的多重含义,造成了分析的混乱。例如吴汉东教授认为,合理使用“乃是使用者依法享有利用他人著作权作品的一项权益”[1]130。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权益?到底是主观权利保护的直接利益还是客观法保护的反射利益?我们不得而知,只是从作者的其他只言片语中,我们才得到了一些信息。譬如吴教授指出,著作权人负有相应的义务——“服从使用者的意思而进行的作为或不作为 (主要表现为不加禁止与干涉他人合理使用不作为)”[1]139,至此我们才知道他所称的权利是一种主观权利保护的直接利益。要成为一种主观权利,它必须有相应的义务人承担义务并得到法律强制力的保障。可是,从笔者的阅读范围来看,尚未见有立法规定著作权人负有不禁止或干涉他人合理使用的义务,也没有看到有立法规定使用者无法实现合理使用时可以获得法律救济。仅此一点,使用者权利说就难以成立。董炳和先生则认为,合理使用“不是授予使用者任何具体的民事权利”[2]37。他的核心论证过程是:如果合理使用是一种具体民事权利,则使用者可以向著作权人主张合理使用权,“著作权人负有不妨碍使用者权利实现的义务,他不得采取任何妨碍使用者合理使用作品的措施,否则使用者可以要求排除妨碍”[2]43,既然使用者在著作权人采取措施妨碍其实现合理使用时,不能主张排除妨碍,那么使用者所享有的就不是一种具体民事权利。这个推理过程本身无法成立。我们知道,一种民事权利并不总是具有排除妨碍的效力,通常只有绝对权才有这种效力,相对权则通常不具备这种效力。从使用者不能主张排除妨碍这一理由出发,只能证明使用者不享有绝对权,不能同时证明他不享有相对权,更无法得出使用者不享有任何具体民事权利的结论。
就著作权限制说而言,它实际上并没有揭示出合理使用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对著作权构成限制的因素有很多,例如保护期限、思想/表达两分法、善意侵权在特定条件下不承担赔偿责任等等,都对著作权强加了某种程度的限制,这些限制与合理使用是否具有相同的性质?如果性质不同,合理使用的特质又是什么?对此,限制说的宽泛用语无法给我们更多信息。从这个角度看,限制说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
或许由于分析工具的缺陷,再加上视野的限制,两位作者都没有认识到,或者仅仅是粗浅地触及到,合理使用的法律属性对于著作权人能否通过技术措施影响合理使用的效力这一问题具有重大价值。他们没有注意到有些国家或地区立法上已经出现的新现象——禁止通过合同排除合理使用的效力。因而,他们对这些规定能否给合理使用的法律属性造成影响也没有进行分析。
“权利”是一个含义丰富、外延广泛、定位模糊的词语。“权利”是指主观权利还是客观权利?是狭义的权利还是广义的权利?两位先生的论述对这个问题都缺乏清晰限定。为了能够比较清晰地定位合理使用的法律属性,我们将从两个不同的维度来考查,这两个维度分别是:大陆法系法学理论上的主观权利/客观权利两分法和霍菲尔德的权利理论。在此基础上,再分析规定合理使用的法律规范的不同以及合理使用的正当化根据的不同是否会影响它的法律属性。
二、主观权利与客观权利两分法下合理使用的法律属性
从某种角度来看,私法是调整社会生活资源的法律。私法根据资源对人类的重要程度,给予不同水平的保护。有的生活资源受法律完整保护,当对它们的享有受到干扰时,可以借助法律的力量排除干扰而得以享有;有的受法律保护相对较弱,当对它们的享有受到干扰时,视情形或可救济;有些则不受法律保护而放任存在。它们分别是权利资源、法益资源和自由资源[3]10,51。可见,“当生活资源之享有受到干扰时,未必均以法律力量贯彻之,只有以法律为后盾担保其实现者,方为权利”[3]51。因此,生活资源所代表之利益在法律处遇上有层次之区别,有的利益受法律的严格保护,以权利的面貌出现;有的仅以法益的形式出现,保护较弱;有的则被法律放任之。在大陆法系的私法上,向来有主观权利和客观权利的划分,1.主观权利和客观权利的区分来源于德语中“Recht”一词的多义性,客观权利也可以称为客观法,实际上是指实体规范的总和。因为客观法规定了社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个人可以享有的利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称为客观权利。本文也正是在这个角度上使用“客观权利”一词。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第21-22页。它们分别用来保护权利资源和法益资源。合理使用显然是著作权法授予使用者的一种利益,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利益在法律上的层次如何?立法者希望将之保护到何种水平?换句话说,合理使用是使用者的主观权利还是客观权利?
让我们从主观权利的定义出发。法国学者让·达班从主体和他人两个角度来定义主观权利。他认为,从主体角度来讲,主观权利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归属-控制”关系,即客体归属于某个主体,主体能对客体施加控制,形成一个“专属于权利人的领域”[4];从他人的角度看,主观权利意味着对第三人的对抗力、不可侵犯性和可请求性——“任何人都不得侵犯主体的权利,权利主体则得要求他人尊重自己的权利”[4]。其实,这两个角度是相反相成的,如果主体对客体没有某种控制或归属关系,也就无法对第三人产生对抗力。所以另一位学者只从他人这个角度给出了定义:“主观权利是指法律规范赋予主体的权能,即为了实现个人利益,要求他人为或者不为一定的行为、容忍或者不作为的权能”[5]152。
根据这些定义,我们可以认为,主观权利至少应该具备四个基本特征。这四个基本特征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一是权利主体和客体之间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归属关系。二是权利主体对客体具有某种排他性的控制。在控制关系中,要形成一个专属于权利人的领域,必须存在客体所归属的确定主体。这个主体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多个人,但不能是不确定的人,否则排他性就不存在了。三是主观权利与义务的相依性。“任何主观权利的法律逻辑条件是他人的相应法律义务,该义务以某个客观的法律规范为根据。”[5]154在立法上则表现为,如果要设立某种主观权利,就必须规定相应的义务;两者应当同时设定,否则主观权利形同虚设[5]154。没有相应义务的主观权利是不存在的。四是救济的可请求性。主观权利应该是可以请求直接救济的。主观权利受到侵害,权利人可以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请求,要求该机关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或者给予赔偿。这一点是由主观权利和义务的相依性决定的。主观权利自身就蕴涵着他人的义务,当义务被违反时,法律必须给予权利人获得救济的机会。
客观权利是指由于法律规定的反射效果给主体带来的某种利益。客观权利所带来的利益不是法律直接授予主体的,而是法律规定产生的反射效果,这被称为“反射效应理论”。2.该理论由Jellinek(耶里内克)在20世纪初提出。
在如下两种情况下都会有反射利益的存在:一是为公共利益而规范特定行为的法律会造就反射利益。例如,北京市政府规定禁止任何人在春节期间于二环路以内燃放鞭炮。这个规定对二环路内的所有人都产生了一种宁静的利益,它是禁止规定的反射效果,尽管它的主要目标并不在于保护这种利益,而是规范特定行为。假如公民A违反这个规定燃放爆竹,公民B没有要求A不得燃放的主观权利,A也不对B负有不得燃放的义务,A的义务是针对政府的。是否禁止A的行为应该由政府有关部门依职权决定。二是某些法律的规定使得某种利益的实现得以可能时,也会产生反射利益。例如,人们并没有参观柏林或巴黎博物馆的“主观权利”;但是那些收藏品必须向公众开放。在公共利益方面,在开放日和开放时间内,政府不能禁止某人进入该建筑内部。3.这是耶里内克自己给出的例子。参见Lucie M.C.R.Guibault,Copyright Limitations And Contracts:An Analysis of the Contractual Overridability of Limitations on Copyright,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2),p96.当然,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例如为了接待外国元首,博物馆在开放日被关闭了,公众中的任何成员也不能要求博物馆开放或者给予赔偿。
从上述两种客观权利的发生情形,我们可以归纳出客观权利的主要特征:一是客观权利受益人的不确定性。二是客观权利受益人所获得的利益是法律规定所带来的反射利益。三是客观权利关系中,负担承受者不对受益人承担义务。负担承受者不负有保证受益人获得该反射利益的义务,如果说他负有义务的话,也是对政府或者国家负有义务。四是在没有得到该反射利益的情况下,受益人没有个人请求权。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客观权利与主观权利的主要区别:
(1)利益归属的主体不同。对于主观权利而言,利益归属的主体肯定是可以确定的人,主体存在封闭性;而客观权利的受益人则往往是不确定的人,是符合条件的任何人,具有开放性。
(2)负担承受者是否对利益享有者负有义务不同。在主观权利的关系中,必然存在向权利主体负有义务的义务方;在客观权利关系中,虽有负担承受者,例如上例中的公民A或博物馆,但是它们两者都不对利益享有者——开放性主体之一——负有义务。
(3)是否赋予个人以救济请求权。主观权利所保护的利益如果无法实现,权利主体可以诉诸于有关机关,有关机关通过强制力迫使义务人履行义务或者给付赔偿。对于客观权利而言,它所保护的利益只有通过法律的反射效应才存在,并且不能归属于任何特定个人。这种权利的拥有者对于保护其“合法利益”受到更多限制,个人并不享有救济请求权。
(4)利益的直接与否。主观权利所保护的利益是法律直接以主观权利的形式分配给权利人的,法律的目的就是保护该主体个人。客观权利所带来的利益是法律规定的负担承受者承受法律负担产生的反射效果,不是法律直接保护的目标。
现在让我们检验一下合理使用的法律性质。
以“为私人目的使用”为例,这是合理使用的典型方式之一。首先,使用者与客体——被使用的作品——之间没有所谓的归属关系。作品基于作者的创作产生,在归属上应该属于作者而不是使用者。或许有人会主张,使用者与被使用的作品载体之间存在物权上的归属关系——使用者对其持有的作品载体享有所有权。但是这种对物的所有权并不能产生复制的效力。否则,我们就可以把自己买到的书籍随意复制。而且,如果对物的所有权可以直接具有复制的效力,那么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图书馆等公益组织为保存版本而进行复制的例外也就没有任何必要了,因为图书馆对书籍本身的物权就有制作备份的效力。所以使用者与作品载体之间在物权上的归属关系与我们此处的分析无关。
其次,使用者无法完成排他性的控制。因为根据法律的规定,只要为私人目的之个人都可以进行相关的使用,例如复制,A使用者不能排除B使用者对作品做相同的使用。这一特点在形式上表现为使用者一方是不特定的个人。
再次,如果把“为私人目的使用”看作是使用者权利,那么在逻辑上必然要存在相应的义务方和需要遵守的义务。可是在传统的著作权法上,我们没有发现法律规定有要求保证使用者的私人目的复制得以实现的义务,也没有找到承担义务的相对人。在规定合理使用时,各国著作权法往往采用“……不构成侵权”、使用者“可以……”或“得……”的句式,它们实际上仅仅规定了使用者可以如何,而没有规定相应的义务人及其义务。相反,它们经常还规定使用者在实施合理使用时需要遵守的条件和限制。
最后,如果使用者无法实现法律通过限制和例外赋予他的利益,他也无法请求救济。传统立法上的合理使用通常都没有规定使用者无法实现合理使用时的法律保障措施。可见,虽然著作权的合理使用例外使得使用者可以由此而获得利益,但是这种利益仅仅是一种可能,没有相应法律措施的保障,所以不是一种主观权利。
在大陆法系对法律保护的利益做主观权利和客观权利二分的框架下,既然著作权的限制或例外给使用者带来的利益并没有达到主观权利的层次,就只能归属到客观权利的范畴之中。这是一个逻辑的推论。从合理使用的内容分析,我们也可以印证这个结论。
“……不构成侵权”或者使用者“可以……”、“得……”这些表达方式实际上可以转换为“著作权人无权禁止使用者……”。经过这一转换,我们立即发现,它实际上就是上文所述的客观权利的第一种形式——规范特定行为的法律产生的反射利益。同样以“为私人目的使用”为例。根据法律的规定,“为私人目的复制作品不构成侵权”,意即“著作权人无权禁止使用者为私人目的复制作品”。这就使得为私人目的复制的行为被排除在版权保护范围之外,著作权人承受了这一负担,间接有益于作品的使用者。使用者因此获得了实施著作权法规定的具体行为的客观权利。可见,虽然著作权的合理使用例外对使用者有利,但是尚不足以确立一种主观权利,它们实际上仅仅是著作权人承受法律负担的一个反射效果。在这里,合理使用的规定并非直接针对使用者的利益,而是限制著作权人的权利,从而给使用者造就了一种客观权利。
三、霍菲尔德权利分析框架下合理使用的法律属性
美国法上不存在主观权利和客观权利的区分。但是美国法学理论中的权利分析哲学可以为我们具体分析合理使用的法律属性提供一种精致的分析工具。在霍菲尔德之前,美国司法判决中对权利(right)和义务(duty)等的用法极为混乱,充满了变色龙似的词语,霍菲尔德的目的在于明晰这些概念的含义,使其得以“正确地简单化”。为此,在他那篇经典论文里[6]16,霍菲尔德区分了四类法律关系、八个法律概念,然后按照它们之间的相应(correlative)和相反(opposite)两种关系构造成如下图表:

权rig利htpr特ivi权legep权ow力erim豁mu免nity法律上的相应关系 义务 无权利 责任 无权力dutyno rightliabilitydisablity法律上的 权利 特权 权力 豁免相反关系 无权利 义务 无权利 责任
这八个概念分别有自己的相应方和相反方。其中权利(狭义)、特权、权力和豁免构成我们通常所说的权利(广义),而义务、无权利、责任和无权利构成法律负担。这四组法律关系是分析法律现象的“最小公分母”[6]16。霍菲尔德对这四类法律关系做了详细的分析,我们无意重复他的论证,但是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分析合理使用的法律性质时需要用到的两类法律关系:
(1)(狭义)权利-义务。(狭义)的权利本质上是一种“要求权”(claim),即权利人要求义务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时所处的法律地位。义务是指应权利人的要求必须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时义务人所处的法律地位。(狭义)权利的相应方是义务,即权利则必然要求相对方负有义务,有权利必有义务,无义务则必无权利。如果义务人没有履行权利人所要求的作为或不作为,那么权利人可以请求有关国家机构使用强制力迫使义务人履行,或者赔偿权利人所受的损失。例如,假定甲有权利做A行为,那么其他人就有让甲做A行为的义务。甲就有权利请求义务人让他实施A行为,请求权的内容可以包括要求义务人不得妨碍他从事A行为,或者要求义务人做使其能够实施A行为的积极行为。如果义务人违反了义务,使得甲无法实施A行为,甲可以要求国家机构利用强制力迫使义务人履行义务或者赔偿损失。因此,(狭义)权利是允许性的,权利人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但是与权利相应的义务则是强制性的,当权利人提出请求时,义务人必须履行。
(2)特权-无权利。特权的概念是最容易导致误解的词语,霍菲尔德没有对特权做出定义,而是通过特权的相应方和相反方这两种关系来阐述特权的内涵。特权的相反方是义务,其相应方是无权利。如果甲有做A行为的特权,根据特权的相反方是义务,可知甲没有不做A的义务;根据特权的相应方是无权利,则可知他人没有权利要求甲不做A。正是在相应和相反两种关系中,我们得以明确特权的内容。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知道,如果甲有做行为A的特权,这仅仅意味着法律没有设定甲不得做A的义务,他人没有要求甲不做A的权利,法律对甲做A的行为或者对此保持沉默,或者设定了许可,仅此而已。因此,如果说(狭义)权利必须从对应的义务人的义务(作为或不作为)来体现的话,特权则只能从特权主体自身行为得以反映。法律并没有对其他人设定保证甲行使和实现该特权的义务。如果法律设定了他人协助甲实现该特权的义务,即他人或者负有不得妨碍甲做A行为的消极义务,或者负有积极协助甲实现该行为的积极义务,那么甲所拥有的就不再是特权,而是权利。因此,对于特权而言,其实现无法得到法律的直接保障。4.这里的直接保障是指法律通过设定义务的方式使得特权得以实现,因为义务必然伴随着责任,所以直接保障还意味着权利人在无法实现权利时可以诉诸国家强制力。特权无法得到法律的直接保障,不等于法律对特权没有保护作用。在特权的实现机制中,一是依靠特权人自己的力量,二是法律通过对特权人其他权利的保护来间接达到特权实现的目的。霍菲尔德用格雷教授小虾沙拉的例子幽默而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A、B、C、D如果都是沙拉的主人,他们可以对X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吃沙拉;我们许可你吃,但我们并没有同意不干预你。”这一例子中存在特权,因此,如果X成功地吃到沙拉,他没有侵犯任何一方的权利;同样清楚的是,如果A死死拿着碟子致使X吃不到沙拉,A也没有侵犯X的任何权利[6]35。
以霍菲尔德的权利理论为工具,我们对合理使用的法律属性可以获得更清晰的认识。仍然以“为私人目的复制例外”为例。无论是“使用者为私人目的复制不构成侵权”,还是“使用者可以为私人目的使用复制作品”,转换成霍菲尔德的分析模式可以表述为“使用者没有为私人目的不得复制作品的义务”,它丝毫不涉及使用者是否有使用作品的(狭义)权利;此外,上述表述还可以转换为“著作权人没有要求使用者不得为私人目的复制作品的权利”,但无法得出著作权人负有协助使用者实现为私人目的复制的义务。当然,如果法律在上述规定之外,附加规定了著作权人不得妨碍使用者的消极义务,或者协助使用者实现私人目的复制的积极义务,使用者的“为私人目的复制”就能够成为一种真正的权利。如果没有这种义务的存在,“为私人目的复制例外”就只能是使用者的特权——一种法律没有给予直接保障的特权[7]。它仅仅是著作权人允许使用者吃的那盘“小虾沙拉”而已。在美国,合理使用被普遍地认为是一种特权,5.“‘合理使用’是一种由版权人以外的人不经版权人许可以合理方式使用版权材料的特权,不管授予版权人的专有权如何。”Horace Ball,Copyright and Literary Property,260(1944),cited in Rosemont Enters.,Inc.v.Random House,Inc.,366 F.2d 303,306(2d Cir.1966),cert.denied,385 U.S.1009(1967).这也为我们的结论提供了辅助说明。
四、强行法和任意法分析框架下的合理使用性质定位
法律规范依效力强度可区分为强行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前者不能依约定而变更,后者惟有在当事人无相反之约定时才适用[8]。
我们通常用两种判断方法来区分强行法和任意法。(1)形式判断。由于任意法和强行法以当事人能否通过协议变更该法律规定的效力为区分标准,如果法律条文明确规定“当事人另有约定或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或者“当事人声明可以除外”,那么该规范即属任意性规范。但是,没有规定“另有约定或声明除外”的法律规范却不一定是强行性规范。只有法律明文规定当事人不得以协议排除该规定的效力,才属强行性规范。(2)实质判断。任意性规范通常仅仅涉及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强行性规范与第三人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在判断过程中,我们需要分析法律条文对应的法律规范所协调的利益冲突。如果当事人协议变更或者排除的某个法律规范只是涉及到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不会直接影响到第三人利益、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则该规范通常是任意性规范;反之,如果当事人以协议方式排除某个法律条文的效力会对第三人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产生损害,那么该法律规范应该具有强行性。
传统上规定合理使用的法律规范属于任意法还是强行法?我们以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的规定为例。如果从形式上来识别,至少该条第4项和第5项显然属于任意性规范,因为它们都规定当事人声明的可以除外。6.我国《著作权法》第 22 条第(4)、(5)项。从实质上来判断,如果著作权人与某个使用者经过平等的充分协商,通过合同约定排除或变更该条第1至12项中的任何一项规定,原则上都不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因此这些限制和例外都属于任意性规范。譬如,假定著作权人与某个学校约定,为课堂教学使用不得少量复制其作品,7.该约定排除了《著作权法》第22条第(6)项的适用。这并不会对学生教育造成多大影响,学生和学校只要购买该作品即可。况且该合同只是在该著作权人和该学校之间有效,其他学校仍可以为课堂教学合理使用其作品。即使有时会涉及到第三人的利益,但通常也不会对第三人的利益造成实质影响。例如作者与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约定该出版社将其作品改成盲文出版时,需要向其支付报酬。8.该约定改变了《著作权法》第22条第(12)项的效力。尽管有这个约定,盲人群体并不会因此受到多大损害,因为通过支付报酬,该出版社就可以将该作品改为盲文出版,而其他出版社不受合同约束当然可以出版。相反,该约定给予作者更大的利益,可以激励其创作更多的作品。法院完全没有必要否定这些合同约定的效力。所以,我们认为,著作权法传统上的合理使用规范属于任意法的范畴。
随着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著作法中出现了一些强行性的合理使用规定。以《欧共体计算机程序指令》为例,指令规定,“与第6条、第5条(2)和(3)规定的例外情形相违背的合同约定无效。”9.《欧共体计算机程序指令》第9条(1)。其中第6条规定的是反向编译例外,第5条(2)和(3)则分别规定了使用者制作计算机程序备份的例外和为研究、学习或功能测试目的之例外。10.《欧共体计算机程序指令》:第5条(2):在使用所必需的限度内,合同不得禁止有权使用计算机程序的用户制作备份。第5条(3):有权使用计算机程序复本的用户在被授权进行下载、显示、运行、传输或存储的各种活动中,有权对该程序进行研究、学习或者对其进行功能测试,以确定构成其要素的思想和原则,无需取得著作权人的专门授权。这些规定明确排除了当事人之间相反约定的效力,此时,这些规定合理使用的法律规范就已经由任意法规范转变为强行性规范。法律规范性质的这种变更是否会改变限制或例外的特权或客观权利属性?它是否意味着反向编译、制作备份已经成为使用者的权利?
在具体情况下,限制或例外由任意法转变为强行法,意味着相应利益保护的强度有了提高。但是这种提高是否足以把特权或客观权利提升到权利的层次尚需具体分析。
《欧共体计算机程序指令》把限制或例外由任意性转变为强行性的方法是否定与合理使用规定相反的合同约定的效力。这种方法排除相反合同约定的效力,赋予了著作权人以合同方式尊重具体的合理使用行为的义务。但是,除了相反的合同约定无效之外,这种方法没有规定著作权人需要以其他方式尊重合理使用行为,更没有规定积极的直接救济手段。因此,对于著作权人而言,这种规定方式仍然没有产生要求著作权人不得妨碍,或者应该协助使用者实现合理使用的一般性义务。由于这种义务以及相应直接救济手段的缺乏,我们认为,尽管该限制或例外具有了强行性,但它仍然只是一种特权。所以,仅仅排除相反合同约定的效力不足以使得该限制和例外上升为一种法律权利。11.相反的观点,可以参见Pierre Sirinelli,Exceptions And Limits To Copyright And Neighboring Right,WCTWPPT/IMP/1,Geneva,December 6 and 7,1999,p40.
如果从大陆法系客观权利角度来看,结论也是如此。我们在上文曾经阐述过客观权利的两种情形,其中之一就是规范特定行为的禁止性法律产生反射利益的情形。排除相反合同约定的效力实际上是法律禁止合同做出相反约定,间接使得使用者可以从该规定中获益,恰好属于该种客观权利类型。
可见,仅仅规定与之相反的合同约定无效并不足以把该种合理使用提升到权利高度。对于“软件持有人制作软件备份复制件”这一合理使用行为而言,即使与之相反的合同约定无效,它也仅仅是一种客观权利,是一种特权,是软件持有人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法律并没有为它提供直接救济手段。如果立法者企图通过合理使用规范赋予使用者以权利,还需要对著作权人设定不得妨碍或积极协助的义务,并且提供直接的法律救济手段。不论哪一种分析框架,都取决于实在法的规定如何。当法律对限制和例外规定了直接救济手段时,谁又能否认它构成一种权利?
五、合理使用的正当化根据不同是否会影响其特权属性
在著作权法上,合理使用的正当化根据可以分为三种:基本权利和自由、公共政策、经济学根据。它们反映了立法者对使用者的合法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目标的承认。不过,由于不同的合理使用行为背后蕴涵的使用者合法利益或公共利益各有差别,立法者给予的重视程度可能不同。这会影响合理使用作为特权或客观权利的法律属性吗?
我们知道,一种合理使用行为可能有多种根据,一种根据也可能支持多种合理使用行为。以“为私人目的之合理使用”为例,它的正当性是通过多种根据得以证明的,例如使用者的隐私权、促进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以及交易成本理论等,都对“为私人目的之合理使用”提供了正当性。前者根据属于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范畴,中者属于公共政策的内容,后者则是经济分析理论的结论。对于通常利用表达自由而得以正当化的“为批评和评论目的引用”,经济分析理论也同样提供了有力的证明[9]。因此,各种合理使用的正当化根据并非是固定不变的。难以想象它们的法律属性会随着正当化根据的不同而变化。
上文的分析已经指出,作为使用者特权或客观权利的合理使用如果要被提升为权利,法律必须设定著作权人不得妨碍或者积极协助使用者实现合理使用的义务。在义务人不履行义务时,法律还需设定直接的救济手段,通常是赋予权利人以诉权。合理使用的正当性根据本身无法直接为当事人个人设定义务,当然也不能为使用者直接设定权利。
不过,对于以基本权利和自由为根据的合理使用行为而言,由于它们在宪法上的重要地位,国家可能根据宪法负有保护每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义务。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国家的这种义务不仅包含不得侵犯个人的基本权利或自由,有时还包含要求国家积极作为,为基本权利或自由的实现提供设施和条件。这种状况是否对相应的合理使用的法律属性产生影响?
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因为在这种宪法关系中,同样没有赋予个人以请求权,而仅仅对国家课以单纯的保护义务。“由这个义务所衍生出的行为要求及命令,却并不能赋予人民可以直接要求立法者应该有所作为之请求权。”[10]以引用为例,它的正当性根据是公民的表达自由和信息自由。几乎所有现代国家的宪法都会规定国家有保护公民表达自由的义务,有的还要求国家为公民表达自由的实现提供相应设施。但是国家所负的这种义务是针对全体公民的,对于使用者个人而言,国家并不负有具体的义务。即使由于某些原因使用者无法对作品进行引用,使用者个人也不得要求国家给予强制性的救济——迫使著作权人提供引用得以实现的手段。所以,合理使用的正当化根据的强弱不会改变其特权或客观权利属性。
六、结论
在大陆法系理论中,使用者根据合理使用规定所获得利益是法律规定的反射效果,属于客观权利的范畴。它的范围受到著作权法律规定的严格限制。使用者既不可转让该客观权利,又没有实施该权利的独立诉权。在霍菲尔德的权利分析理论中,使用者根据合理使用所拥有的是一种特权,它仅仅表示使用者没有不得利用该限制或例外的义务,没有赋予其他个人以不得妨碍或者协助实现合理使用的义务,也没有赋予使用者以直接的救济请求权。规定合理使用的法律规范的属性不会改变合理使用的特权或客观权利属性。合理使用正当化根据的不同虽然会对国家所负的义务有影响,但是对个人的权利义务状态没有影响,同样不会改变限制和例外的法律属性。EIP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
[1]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128-142.
[2]董炳和.合理使用——著作权的例外还是使用者的权利[J].法商研究,1998(3):36-43.
[3]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4]雅克·盖斯旦,吉勒·古博.法国民法总论[M].陈鹏,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37.
[5]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M].高家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6]Wesley N.Hohfeld.Some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J].Yale L J,1913(23):16.
[7]Jeremy Waldron.From Authors To Copiers:Individual Rights And Social Value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J].Chi.-Kent.L.Rev.,1993(68):859.
[8] 考夫曼.法律哲学[M].刘幸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55.
[9]William M.Landers,Richard A.Posner.The Economical Structur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117-118.
[10]陈新民.宪法基本权利之基本理论(上)[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19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