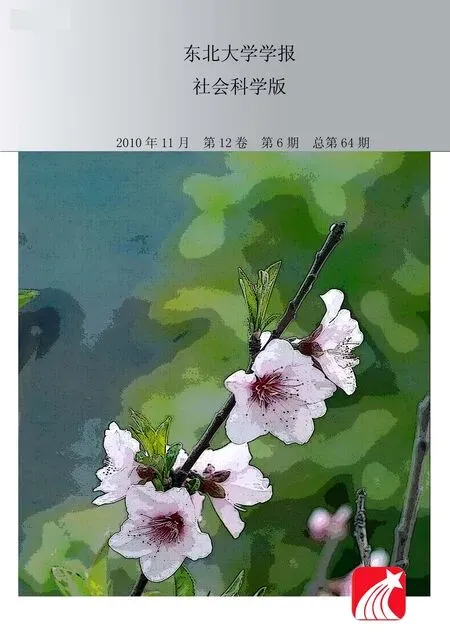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和文化反思的交错与简化
----晚清至五四文学启蒙话语的考察
鲁 毅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就各自内涵而言,有其明确的界线和旨归。“启蒙”的概念来自于西方18世纪的文艺复兴,在晚清接受西方新思潮的过程中,“启蒙”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虽然在传输过程中,其内涵必然发生位移,但大致的主张却为最初几代启蒙者所认同,即主张个体的独立、自由、平等,以人的解放和人权保障为旨归,倡导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人权意识,这些成为“启蒙主义”最基本的内容。然而传统民族心理和特殊的时代诉求,使得民族认同的社会思潮也如影随形,与启蒙思潮相交错,其中也涉及到对传统文化的反思,都对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包括文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几股思潮的复杂关系却显得扑朔迷离,因此,我们须要再次审视它们,理清其中的关系。本文试选取晚清梁启超倡导“新小说”的启蒙话语、民初以徐枕亚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创作,以及五四陈独秀、鲁迅等人的启蒙话语为切入点,考察不同时代的思想者对这几股思潮理解的差异及其相应的认识逻辑思路,以揭示它们从晚清到五四的流变及其对文学史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 晚清:梁启超的“新小说”启蒙话语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3]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梁启超启蒙思想的逻辑思路,即“新小说”是为了“新民”。但梁启超的启蒙思想并没有止于这一步,在《新民说》中,他认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至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4]593,又如“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4]589,很明显,“新民”和国民的独立,最终指向国家的独立,即“新民”是为了“新国家”。由此可以总结梁启超的逻辑思路:新小说→新民→新国家。
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出现了大量以这种观念创作的“新小说”,包括梁启超自己也写了《新中国未来记》这样的作品,表现出浓厚的政治功利性,因此,袁进、刘纳等学者认为晚清小说“过分迎合当时社会/政治动力,却忽略了更宽广的‘人文’经验脉络;毕竟社会/政治的变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5]21。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却“责难晚清小说家虽然逐渐看出写作与国家命运间的关联,却缺少足够的眼光及勇气强调社会/政治的动力,终必导向解放与革命”[5]21。前者批评“新小说”过分注重文学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关联,后者则批评“新小说”不够革命,嫌这种政治性的因素太少,两种截然相反的批评意见,却都同样看到了晚清“新小说”与民族、国家救亡图存之间的联系。
回顾一下晚清的时代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逻辑思路的形成。梁启超等人是在甲午战败、国家危亡的时候,借来了启蒙思想,并认识到小说的启蒙功用可以直接导向救亡图存的民族、国家认同。同样,严复所表达的启蒙思想也直指这样的民族、国家认同,在《原强》中,他反思了甲午战败的原因不在于技术的落后,而在于“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6]13,因此,进行“开民智”、“厚民力”、“明民德”[6]15的思想启蒙,才是当务之急,于是,启蒙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振兴和民族的富强。这种将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紧密相连的逻辑思路,在晚清形成了共识,同时从后来五四启蒙思想家的话语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相似的认识逻辑。
二、 民初:以徐枕亚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创作
鸳鸯蝴蝶派文学诞生于辛亥革命前后,这一派的启蒙性向来被认为是缺失的,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以启蒙为己任的文学流派,但正如王德威所言:“作家在概述其意向时所说的,可能与他们实际在作品中所写的,根本是两码子事”[5]26,因此通过细读文本,即他们的“话语”,可以考察出鸳蝴派所具有的“隐性启蒙”,这有助于我们梳理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和文化反思对整个时代文学产生的规整和影响。
鸳蝴派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对“情”的极度张扬,这种对个体生命体验的抒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之理解为是对个体权利、自由的一种张扬,尤其表现在婚恋题材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鸳蝴派文学自然具有启蒙的色彩,只不过不如五四文学那样具有理论深度,更没有明确地提出某些主张,而是用文学作品去呈现这种微弱的启蒙之光,因此,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隐蔽的启蒙”。周作人曾对鸳蝴派大作《玉梨魂》中“寡妇恋爱”的内容作出过评价:“近时流行的《玉梨魂》,虽文章很是肉麻,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祖师,所记的事,却可算是一个问题”[7]。周作人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派小说的价值,他们提出的婚恋问题,为五四作家的思考与抒写做好了准备,从这个角度讲,这派小说又具有了一种“前启蒙”的价值。
以徐枕亚的作品《玉梨魂》和《雪鸿泪史》为例,两部作品为同一个故事,对何梦霞与白梨影之间的爱情进行了至情至性的描写,两个人为爱情付出了一切甚至是生命,这让读者为之动容,虽然作品中有“发乎情,止乎礼”的部分说教,但作品更精彩或者说更难以掩饰的是对“情”的真挚抒写,这些也足够压倒其他一切,而具有了人类的普世价值。它与启蒙思潮相契合,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读者对那个时代传统文化的认同,也为下个时代即五四的来临,做好了以文学言说代替思想宣言进行诠释的准备。李泽厚认为:“这些似乎远离现实斗争的浪漫小诗和爱情故事,却正是那个新旧时代在开始纠缠交替的心态先声。感伤、忧郁、消沉、哀痛的故事却使人更钟情更怀春,更以个人的体验去咀嚼人生、生活和爱情。它成了指向下一代五四知识群特征的前兆。四顾苍凉侵冷,现实仍在极不清晰的黑暗氛围中,但已透出了黎明的气息。”[8]
由此可见,在这个过渡时代中,由思想启蒙始发的逻辑认知出现了两条路数,一条如梁启超等人,由思想启蒙直指救亡图存的民族认同;一条如鸳蝴派小说,虽未明确提出启蒙,却以描写人类普世性情感的作品进行“隐性启蒙”,间接提出了个人婚恋不自由的问题,而这些却都指向了传统文化(文化层面的民族想象共同体),即文化层面上的民族认同,而且对于鸳鸯蝴蝶派而言,他们的民族政治认同与民族文化认同是截然分开的,各自保持着独立性[注]如《玉梨魂》中,作者设计男主人公何梦霞最后战死于武昌城下的情节,体现了徐枕亚在政治层面上的民族认同意识,但《玉梨魂》的主题显然不是在宣扬这种民族、国家意识,因此,在徐枕亚的创作中,这种民族政治认同与民族文化认同是截然分开的。,这使得将启蒙引向政治层面民族、国家认同的可能性减小,所以鸳鸯蝴蝶派的真正价值在于,他们并没有将思想启蒙导向政治层面的民族认同,而是引向了对文化层面民族认同的反思[注]在文化层面隐含的反思,除了前面提到的爱情方面,还包括对封建礼教产生的离心力。徐枕亚、李定夷等鸳蝴派作家的哀情、艳情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对封建名教的信仰危机,使读者对传统的礼仪廉耻产生了疑惑。,虽然他们无力完成反思这个任务,却为五四学人开启了一扇大门,使他们的思考能够触及到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有了重新构建文化层面上民族、国家认同的可能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一阶段在文化层面进行反思的缺失。
三、 五四:陈独秀、鲁迅等人的启蒙话语
晚清梁启超、严复等人强调国民的启蒙、觉醒,但这一切却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与民族的振兴,所以便由思想启蒙直接导向了一种民族、国家的认同。而民族、国家认同是一个复合性的概念,其中既有政治层面的认同,也有文化层面的认同。国家富强、民族进步,对外抵御外侮,本就是民族、国家认同的题中之义,但这种认同还应包括对整个民族、国家文化整合性象征的集体认同,而忽视了文化层面的认同,就很容易流入对传统儒教专制主义文化潜意识的默认,从而缺失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性,所以,即使名义上主张启蒙,也容易导致所谓的几个人的专制统治。
到了五四,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对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专制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君臣、父子、家族观念等,显然成为了传统文化的整合性象征。五四这代思想者们以启蒙去对抗这种专制,主张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在文学上对“非人”的文学进行猛烈的抨击,主张“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由此来看,他们由启蒙始,指向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想了他们所谓的新文学和新文化的集体认同(“人的文学”),这都可以看做是前一阶段文化层面民族认同链条上的延伸和拓进,但是这种重构的思考还未来得及深入,他们又匆匆地或者说本能地导向了政治层面的民族认同,即所谓的救亡[注]由于近现代中国沉重的民族灾难,使得生长在这一时空下的作家本能地具有了一种关心时弊的民族、国家意识,从梁启超这代“新小说”家开始的用文学表达民族、国家意识,也在五四作家身上形成了一种本能和惯性,虽然他们触及到了文化的反思与重构,甚至带有全盘否定式的偏激,但这种本能与惯性,加之外部政治风云的变幻,很快将他们的视线转到了政治层面的民族认同上,即由“文学革命”步入“革命文学”。。
鲁迅曾在《摩罗诗力说》中言:“文事式微,则种人之运命亦尽,群生辍响,荣华收光。”[9]在这里,鲁迅是将文学的启蒙与“种人之运命”、民族联系在一起的。鲁迅开始所持的科学救国思想,所写的《北极探险记》、《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科幻小说,还有《人的历史》、《科学史教篇》等论文,其旨归亦是指向革新政治与救亡图存的。再比如幻灯片事件,他说:“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0]。依然是抱着改变“愚弱”国民的心态,实践文学救国的梦想。尽管他言:“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11]47,主张个体的启蒙:“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11]58。“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11]52,但又言:“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11]57,最终仍是指向一种“人国”的民族与国家观念。鲁迅提出“任个人而排众数”的命题,其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在君主专制、君主立宪、代议政治之外为中国寻找别样的救亡途径,其实效如何姑且不论,但很明显,鲁迅是带着“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11]58这样强烈的现实感、危机感、责任感而思索的。
陈独秀的启蒙思想显而易见,1915年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的《敬告青年》中,对中国文化提出了六项主张:“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12]159-162,鼓吹“科学与人权并重”[12]162。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一九一六年》中言:“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13]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吾人最后之觉悟》中又言:“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14]这些都表明陈独秀主张个人的民主、平等、自由等基本权利,但是应该注意到,这些主张往往是与政治、国家、民族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的。通过上面的言论,可以这样来理解,即实现多数国民的自觉、自动、觉悟、自由、独立、平等,这一切都是为了所谓的共和、立宪,所谓的“政象”,依然是指向救亡图存的民族认同。“新文学运动是作为一个运动骤然展开,并很自然构成‘五四’新潮的中坚力量,投入其中的新派文人都自觉怀有救国救民的大愿,由文坛而社会‘全面进化逐新’的观念使他们激动振奋”[15],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整个中国近代的民主论者当中,很少有人是纯粹出于自由而要求民主的,绝大多数人乃出于救亡和富强的目的而涌向民主”[16]。
1904年,陈独秀曾经在《安徽俗话报》第5号上发表《说国家》,认为“国家要有一定的主权。……这主权原来是全国国民所共有,但是行这主权的,仍归代表全国国民的政府。一国之中,只有主权居于至高极尊的地位,再没有别的什么能加乎其上了。上自君主,下至走卒,有一个侵犯这主权的,都算是大逆不道”[17]。在这里,陈独秀所表现出的这种国家意识是相当明确的,因此启蒙的任务被理所当然地归到了民族与国家认同上。陈独秀一方面认为:“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18]386;另一方面又认为“社会支配个人力量十分伟大”[19],“个人之在社会,好像细胞之在人身”[18]386,“人生在世,个人是生灭无常的,社会是真实存在的”[18]386。再如胡适,他曾经在《易卜生主义》中倡导个性主义,并创作了如《终身大事》这样张扬五四个性精神的剧本,但在《不朽》中,他又强调社会不朽,主张个人依赖于社会、个人认同于社会整体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由此可见,以集体主义为表征的民族、国家认同,与以个人的自由权利为特征的思想启蒙,始终是纠合在一起的,没有形成实质性的对抗,因此,五四学人在继承第一代启蒙者思维的路数上,又趋向了统一。
但是周作人的启蒙话语却明晰了这种交错与置换,一方面他认为:“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20],强调个体的独立、自由;另一方面却又警醒着:一切蔑视个人权利的社会都是“白痴的”,只有形体而没有精神生活的社会,如果要是牺牲了人的个性来侍奉这种社会,“那简直与借了伦常之名强人忠君,借了国家之名强人战争一样的不合理”[21]。但像周作人这样洞悉到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言说中发生置换危险的毕竟是少数,不足以扭转五四思想潮流的整体面貌,因此,这种含混不清的观念,也将对以后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 结 语
从晚清的启蒙主义思潮开始,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思想家,将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联系起来,认为个人的觉醒必将带来民族与国家的复兴,这导致了对民族认同理解的简单化,而忽视了文化层面的民族认同,于是带来了两种后果:一方面是对文化层面民族认同的反思不够。很明显,梁启超这代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虽然没有达到五四学人对儒家传统专制文化的批判力度,尽管如此,之后的鸳蝴派虽未有启蒙的理论和宣言,但对于个人情感的真挚抒写以及对当时婚恋问题的揭示,却表明触及到了对文化层面民族认同的思考。而“五四”新文学虽有指向民族文化认同的一环,但又很快地导向了政治层面的民族认同,所以导致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重建存在着诸多缺憾。另一方面,这种简化略去了对文化个体生存权利的肯定,即对多元文化形态的一种否定,表现在文学上,只认同于政治层面,往往救亡的文学,如左翼文学容易成为一元的声音,使得其他文学形态被排挤到边缘,甚至以隐性的形态存在。总而言之,从晚清到五四,作家们对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和文化反思思潮理解的简化思路,对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梁启超. 译印政治小说序[M]∥陈平原,夏晓红.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38.
[3]梁启超.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M]∥陈平原,夏晓红.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50.
[4]梁启超. 新民说[M]∥易鑫鼎. 梁启超选集:下.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
[5]王德威. 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7]周作人. 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N]. 每周评论, 1919-02-02(3).
[8]李泽厚.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213.
[9]鲁迅. 摩罗诗力说[M]∥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65.
[10]鲁迅. 呐喊·自序[M]∥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438-439.
[11]鲁迅. 文化偏至论[M]∥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12]陈独秀. 敬告青年[M]∥任建树.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13]陈独秀. 一九一六年[M]∥任建树.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199.
[14]陈独秀. 吾人最后之觉悟[M]∥任建树.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202.
[15]温儒敏,李宪瑜,贺桂梅,等.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6.
[16]毛丹. 陈独秀的民主神话及其思想资源[J]. 二十一世纪, 1994(24):39.
[17]陈独秀. 说国家[M]∥任建树.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45.
[18]陈独秀. 人生真义[M]∥任建树.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19]陈独秀. 新教育是什么?[M]∥任建树.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327.
[20]周作人. 新文学的要求[M]∥艺术与生活.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22.
[21]周作人. 自己的园地[M]∥自己的园地.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