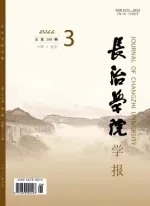赵树理作品中民俗书写的结构功能
林秀明,赵 坤
(福建儿童发展职业学院 人事处,福建 福州 350013)
赵树理作品中民俗书写的结构功能
林秀明1,赵 坤2
(福建儿童发展职业学院 人事处,福建 福州 350013)
赵树理在作品中始终能够把“民俗书写”置放在农村民俗文化背景下来加以阐述,并将其“整合”到他的艺术审美理念之中,这就使得他作品中的“民俗书写”呈现出独特的结构功能:作品中的人物在民俗规约下形成了诸如“算账”等行为习惯;民俗影响并参与到对作品情节的建构之中;在“民俗氛围”背景下形成的作品主题趋向,系统而又连贯,“民俗化”的叙事结构功能在这里得到更大程度的“彰显”。
赵树理;民俗;结构功能
民俗代表着一种积久成习的生活实践与文化认同的模式,对于民众来说,它规约并构建了“合情合理”的生活框架。由于赵树理对于“地道”的乡村风俗的“熟稔”,所以他深知民俗在农村生活中所具有的黏合力。他在作品中通过具体的民俗书写表现出了民俗的结构功能。本文拟从民俗规约下的人物行为习惯、民俗建构下的故事情节、民俗“审视”下的主题趋向等三方面加以探讨。
一、民俗规约下的人物行为习惯——以“算账”为例
民俗作为“流行于民众的民族固有的深层的本质文化”[1],它以不成文的规矩、“生活相”为表征,风行于民众之中,这种传承过程本身也可以看做是民俗在民众中间的“俗化”过程。民俗在民众中间的“俗化”并不是俗气,本质上,它是指个体对所属群体千百年沉积凝聚而成的群体意识、共同心理气质的认知归一,它通常是通过群众在民俗规约下形成的一些“行为习惯”来具体加以体现的。
三晋大地独特的民风民俗概括为三个方面:“敦厚质实、重利轻名”、“俗尚俭啬”、“其俗刚悍、其性倔赖”。[2]我们在阅读赵树理的叙事类作品中深切感到,诸如“重利”、“俭啬”、“倔赖”等民风民性,大都与“算账”这一“民俗”行为有着天然的内在契合性。
笔者认为,“算账”作为赵树理笔下人物的“典型”行为习惯,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民俗“规约”的区域性集体行为。这是因为,民俗首先是作为“生活文化”而存在的,这种“文化”含纳着民众的生活智慧、生产经验,贫瘠、艰辛的农村生存处境、直接取资于土地的限定性的生活条件,促使农民们只能对自己有限的生产生活资料精打细算,这是乡土社会一代又一代的持家传统与经验,惟有如此,才能“活”下去。其次,正是由于乡村社会艰辛的现实生活境遇,才迫使人们思考任何问题时都难以离开基本的生命生存范畴。“算账”作为民俗行为习惯,被“传承”、“沿习”,本身就说明了人们执着于实际利益、眼前利益的“务实”观念。再次,当我们把“算账”所指涉的“精打细算”、“务实”等观念置放在民俗视野下加以“审视”时,就会发现它并不隶属于“私”。无论是它的内在诉求,还是它的功能彰显,都是围绕着对各种生活事务的经营来加以展开的,在这种“经营”中他们更多地是在“自保”而不是损害外人利益。
“算账”作为人物的民俗行为习惯,在赵树理笔下不仅仅只是“纯粹”的“民俗”“事象”的展示,而是借助于“民俗化”的叙事结构功能生成了凸显“农民”与“政治”之间复杂关系的暖味性空间。如果说《有个人》中宋秉颖在年关时节对自家一年以来收支情况的“算账”,还基本属于没有“政治意义”及“政治力量”介入的“纯粹”的民俗化个人行为的话,那么,赵树理自此之后的作品中凡是涉及到“算账”的部分都不再“单纯”——“算账”的民俗行为习惯与对应的政治意义联袂而出,构成了赵树理作品的独特表现力与审美景观。
在建国前的小说作品中,赵树理大都将“算账”与农民的“翻身”联系在一起。赵树理认为,农民只有明白了“算账”的重要性,才能够实现真正的翻身。在这里,“算账”不仅仅只是人物的一种民俗行为习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被当作群众拥有“翻身”意识与行为的政治性象征符号。具体而言,“算账”作为群众的民俗行为习惯,在群众中间有着强大而牢固的凝聚力与影响力,当群众通过“算账”这一行为对自我现实境遇有了明确体认之后,往往会重新“审视”政治思潮变迁下农村的诸种关系,政治理念在这时作为“嵌入部分”顺接到群众这种民俗思维中,促使群众主动“吸收”,并学会运用新政治理念来提升自我的“政治觉悟”、完善多重利益范畴中的现实抉择。只有在这样的精神基础之上,农民的真正翻身——即“翻心”才会得以实现。《孟祥英翻身》中,孟祥英当上西峧口妇救会主任后,在灾荒年组织妇女上山采野菜,一直采到秋风扫落叶,“算了一下总账,二十多个妇女,一共采了六万多斤。”群众通过这次“算账”,“都佩服孟祥英能干”,意识到“家家野菜堆积如山,谁也不再准备饿死”的现实利益,因而孟祥英的工作迅速地获得了群众的主动支持,“孟祥英一说领导割白草,这些妇女们的家里人都说:‘快跟人家去割吧!这小女是很有些办法的!’”“翻身”的意义在《李家庄变迁》中公审大会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与其说农民们公审大会上清算出李汝珍杀了42人、小毛打了79人的“罪迹”,掀起了大会的“公审”序幕,倒不如说这样的“算账”体现出了群众在新形势下愈加自觉的“翻身”诉求。在《福贵》的结尾处,福贵在表诉会上向地主王老万算着一笔笔的帐:“每年给你住上半个长工,再种上我的四亩地,到年头算账,把我的工钱和地里打的粮食都给你顶了利,叫我的老婆孩子饿肚。”,“我饿肚是为什么啦?因为我娘使了你一口棺材,十来块钱杂货,怕还不了你,给你住了五年长工,没有抵得了这笔账,结果把四亩地缴给你,我才饿起肚来!”,福贵的“算账”不只是为了寻找自己曾经“挨的打”、“受的气”、“流的泪”、“饿的肚”的原因所在,最终目的是让王老万为自己当众“正名”——福贵“我究竟是好人呀是坏人?!”在《小经理》中,赵树理直接将群众的能“算账”与“翻身”联系在一起,鲜明地指出了“算账”对于群众“翻身”的重要性。作为合作社经理的三喜,当他通过自学掌握了“记账”的方法之后,实现了他在合作社工作上的“翻身”,并以此获得了对落后分子王忠真正的领导权。
在建国前,由于“算账”这种“个人行为”所包含的执着于个体现实利益的本质内容,有着与“翻身”相契合的部分,再兼之当时的各种运动都是要在算账的基础上展开,因而“算账”是“合情合理”的。它的意识形态的利益诉求与现实政治的同构性,为赵树理赢取了政治与艺术的双重声誉。建国之后,时代的“转型”以及时代思潮的激进化“转向”,内在地要求农民在面对国家、集体、个人三者间的关系时,必须予以重新审视与抉择。随着“集体”逐渐取代了“个人”,“个人的行为”大都被“集体”所“包办”,“个人”只有依托于“集体”才能获取到本身的存在价值,对于农民而言,如果还执着于个人,这显然是不适时宜的,“他们只要大公无私地为公社劳动,自然有人为他们计算工分,‘算账’不再是农民需要的了。”[3]赵树理在这个时期努力地想“跟上形势”并且试图“在实际工作中争取主动”,甚至是热切地祈望能够尽快地抵达“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和一定的思想水平”[4],因而他在“政治热情”及“思想水平”上尽力地“认同”主流意识形态对农民“算账”行为性质的重新“界定”,即在集体为农民个体包办“算账”的所有的事宜的大环境下,不再允许农民个人“算账”。如果存在,那也只是落后农民所关注的问题。《老定额》中曾经十分积极的林忠之所以在后面被称为“落窝鸡”,主要是因为他总是在关于定额的“算账”上斤斤计较而被视作不再有“革命精神”;《“锻炼锻炼”》中“小腿疼”、“吃不饱”之所以被杨小四贴大字报、被群众批判,主要是因为她们总是计算着做工分多的活。然而尽管如此,旧有的“算账”之于农民在利益衡定中的惯性作用,在赵树理实际创作中并没有本质的改变。“检查我自己这几年的世界观,就是小天小地钻在农村找一些问题唧唧喳喳以为是什么塌天大事。”,“我自参加革命以来,无论思想、创作、工作、生活各方面有何发展变化,有什么缺点、错误,也就是说是个什么成色,始终是自成一个体系的。入京以后,除在戏改方面受了些感染(也因自己本身就有爱好封建戏曲的弱点)外,其他方面未改变过我的原形……”[5]对于赵树理而言,农民习惯于“算账”,是他们在现实生活环境条件下秉承的民俗生活行为经验,它积淀于群众的共同心理认同之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而他对建国后农民的这一个体行为习惯,虽时时放在“落后思想”的层面进行批判,但在“批判”中更多地是“宽容”式的“理解”。《三里湾》中,马多寿决定入社,一方面来自于“刀把子地”的“失守”,另一方面直接来自于他“算账”后对入社比不入社“收入的粮食就更多了”的现实形势的功利认识及“趋利”选择——对于农民来说,主要是通过“算账”来充分了解各项政策。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当“浮夸”等“左倾”思想盛行于农村之时,赵树理发表了一些“顶风之作”,大谈实干精神,“算账”作为人物“实干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一种全新的状态在文本中加以展现。在《实干家潘永福》中,赵树理特别写到了潘永福的“经营之才”,并指出“他这种才能仍然是从他的实干精神发展而来的。”在“开辟农场”部分,潘永福通过“算账”意识到了与农民换土地、种粮食的不划算之处,从而促使他决定在农场种苜蓿,最终获得了成功;在“小梁山工地”部分,潘永福并未过于相信技术员关于两个库址投工、投资等方面的“算账”,而是结合实际情况具体看待;在“移矿近炉”的部分,潘永福通过“算账”觉得土铁路的工程是个“傻事”,不划算,就建议上级把它停了下来,重新调整开矿路线。
建国之后,赵树理除了在文学文本中借用人物来“算账”,还通过大量的论述、杂感、书信等非文学文本来亲自为农村“算账”,在具体的“算账”中体现出了他这一时期创作思想的复杂性。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算账”作为研究赵树理创作思想的“切入口”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二、民俗建构下的故事情节——以民俗生死观念对于情节的影响为例
在赵树理很多作品中,民俗描写本身就是作为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显现”的。无论是《盘龙峪》中以春生为首的十二个干弟兄的“结拜”、群众的演戏、唱戏、“邀神”,《小二黑结婚》中“二诸葛”的“占卜”、“三仙姑”的“跳大神”,《福贵》中福贵的“赌博”、“偷窃”、“当鼓吹手”,还是《邪不压正》中刘家给软英下聘礼,《登记》中的“罗汉钱”,《求雨》中的“求雨”等,“民俗”都成为作品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情节的进一步发展。然而,除此之外,在赵树理的一些其他作品中,民俗并未直接作为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发挥审美效用,而往往转变为某种“民俗事象”、“民俗观念”,参与到对作品情节的“潜在”的审美建构之中。我们以民俗生死观念对于赵树理作品情节的相关影响为例,来分析这个问题。
民间对生、死的看法,通常能够体现出群众特定的民俗审美心理与文化精神。在民间,人们往往将“生育”看成是“喜”,把结婚看成“喜”,甚至还会把“死亡”也看成是“喜事”,有“红白喜事”之说。“生死”既然“无常”、“无法预料”,尤其是对于“死”更是无法抵抗,那么人们只能转向对“生”的“注重”,从“生殖崇拜”到对生育信仰的虔诚,从“观音送子”、“麒麟送子”到“长寿锁”、“虎头鞋”,均体现出这种共同的民俗信念。[6]同时,民间还视死亡为“转生”,把死亡看成是生命的延伸和重新开始,因而人们把“葬礼”看成像“婚礼”一样的隆重,正所谓“事死如事生”。
在赵树理的一些作品中,这种民俗观念不仅体现为诸如“婚俗”、“葬礼”等具体、直接的情节构成部分,而且还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对人对事物的认识方式与把握方式,与人物的命运起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同时,这种民俗观念还为作品情节的发展营造了浓厚的民俗文化氛围。赵树理解放前后的大量作品中,都有意将“反封建”、“政治动员”的“现代”主旨予以“民俗化”,将之植入民俗范畴对“生”与“死”的“审视”之中。“生”是对“死”的补偿,这不仅代表着一种伦理准则,也有利于激发民众的政治自觉性与现实斗争性。
《有个人》中,正是由于在传统民俗观念下将“死”看成一大人生礼仪,对葬礼极为重视,宋秉颖才在他父亲死后,不惜卖地(几经周折才卖出去)、借钱(借的是高利贷,欠下的利息就有四十五元)办殡葬,这本身就构成了故事的情节,同时也加剧了秉颖生活的穷窘,孕育并生发着情节的跌宕起伏。《福贵》中,福贵娘病危之时挂念着的只有自己孩子的婚事,“我自己的病自己明白。死我倒不怕!活了五六十岁了还死不得啦?我就只有一件心事不了,给福贵童养了个媳妇在半坡上滚,不成一家人。这闺女也十五了,我想趁我还睁着眼给她上上头,不论好坏也就算把我这点心尽到了。”福贵娘对“死”的坦然,也是来自于“死”的“不可抵抗”性,她将之转化为对“生”的“注重”,尽心地办好了福贵与银花的婚事(虽然限于生活所迫,婚事办得比较简单,但依然是“有模有样”)。福贵娘死后,无论是“央人抬棺木”、“请阴阳”,还是“缝缝孝帽”、“挂挂白鞋”、“坐坐锅”、“赶赶面”,都办得可谓隆重。赵树理在这里,不仅揭示了这种民俗观念,而且还指出了它与人物命运变迁的关联性,福贵因为办丧事借了“老家长”王老万三十块钱,还债无力,只好去给王老万当长工,“福贵从此好象两腿插进沙窝里,越圪弹越深。”在《李家庄的变迁》里,赵树理让“政治力量”参与其中,使得这种对待“生死”的民俗观念有了新的内容以及新的“审视”维度。作品结尾处,特意把“公祭死难人员”与“欢送参战人员”的活动安排在同一天进行。结尾处,李家庄全村人为了庆祝抗战胜利,决定在旧历八月十五召开庆祝大会,“十六日公祭抗战以来全村死难人员”,到了十六日那天,“公祭死难人员的大会,还照原来的计划举行,可是又增加了个欢送参战人员大会。”,“开祭的时候,奏过了哀乐,巧巧领着两个妇女献上花圈,然后是死者家属致祭,区干部致祭,村干部领导全村民众致祭,最后是参战人员致祭。”这样的“公祭”,被安排为庆祝战争胜利的活动之一,与民间的“葬俗”有着相通之处(都是为了抚慰、平衡失去亲人的悲伤),但也有所区别,如果说纯民间的“葬俗”往往建立在民众将“死”看成“转生”、“再生”的共同民俗信念及心理寄托之上,那么这里的“公祭”在顺应民俗观念的基础上更注重对“过去”、“往昔”的“缅怀”,通过“慎终追远”来更好地对待“生”、卫护这得来不易的“生”,联系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要参军、保家卫国。因而在欢送参战人员大会上,大家都发出这样的感慨,“现在的李家庄是拿血肉换来的,不能再被别人糟蹋了”,“我们纵不为死人报仇,也要替活人保命。”
三、在“民俗氛围”背景下形成的主题趋向
前文我们已经谈到,“民俗”的呈现方式是多维度的,它往往以“观念”或“行为习惯”作为表征方式。“多维”的“民俗”,较早就被赵树理有意或无意地植入到他的创作题材之中,并随着他艺术理念的不断成熟,成为其文化观念的主要构成部分——在“民俗氛围”背景下形成的作品主题趋向,系统而又连贯,“民俗化”的叙事结构功能在这里得到更大程度的“彰显”。
(一)以“家庭”、“家族”的相关“民俗”来“聚合”农村诸种社会关系
乡村社会因系乎土地而具备了较大的稳定性,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往往通过某种约定俗成的方式固定下来。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家庭”、“家族”之于农民生活成规、认知思维的“场域性”,围绕它们的一系列的相关民俗通常以“内部氛围”的存在方式影响着农村社会诸种关系的生成与展开。
“由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组成的最小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共同体,谓之家庭;几个或更多的同姓家庭,由于血缘关系构成了家族。”[7]有关“家庭”、“家族”的风俗,都是通过“血缘关系”来“聚合”的——无论是以家长制统治为代表的“家规”,还是在乡村社会独有黏合力的血亲宗族观念,都体现出了这点。
之所以将“家长制”归入民俗的范畴,是因为在传统社会中有关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角色定位,对家庭内部生产、消费等日常生活的相关“经营”,都要通过“家长制”这种约定俗成的方式固定下来,而人们对于它已经产生了“惯性”的“接受”与“传袭”的状态。赵树理在很多作品中揭示了传统农村家庭中的“家长制”。《三里湾》中马多寿表面“糊涂”,实则以“家长制”管理着这个家:“铁算盘”尽管精明,但对“糊涂涂”的话都是言听计从的;为防止老四(马有翼)再被“鼓闹跑了”,以“家长制”强行让有翼辍学(还差半年就中学毕业),牢牢地“看管”住有翼;他对老婆“能不够”并非真怕,“实际上每逢对外的事,老婆仍然听的是他的主意。”此外,“糊涂涂”在“刀把子地”上的“家长制”作风,着实曾让公社开渠一度举步维艰。《杨老太爷》中铁蛋的革命也是经过杨老太爷的同意的,而当铁蛋当上边区政府干部回家后,杨大用立即向铁蛋“索钱”,理由是“我不管你是谁的干部,你先是我的儿子!”《十里店》中尽管王家骏是进步青年,但婚事还是要听从王瑞的安排。《邪不压正》中软英的婚事要听从王聚财的家长制管理。赵树理在以上作品中揭示了作为民俗范畴的“家长制”在农村社会中的主要表现内容、呈现方式:其一,它对“内”按照自身的意愿,强行地“介入”到儿女的个人生活、思想情感之中,阻碍了儿女们的“进步”与“幸福”;其二,它对“外”与新的生产组织的内在要求形成了抵牾之处,损害了集体利益。而这些,都是此类题材主题趋向的重要构成部分。
乡村社会中独具黏合力的血亲宗族观念,当它们被“整合”到民俗范畴加以言说时,它们自身的“伦理性”在民众中间就有了覆盖面较广的凝聚力与影响力。在赵树理的作品中,这种“伦理性”在农村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点:其一,农村政治统治与家族统治的合一。传统的乡土社会,行政村长都是由地主担任。由于乡村社会因系乎土地而具备的稳定性,除非农民因天灾人祸的逼迫再也无法在村庄中生存下来,鲜有人口的迁徙,因而就使得一个村庄的人多了一层宗亲关系。而地主由于在经济上、政治上处于优越地位,也就在宗族之中处于统治的地位。于是,地主的统治往往同时与宗族的统治相结合。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既有经济的压榨,也有“以族权代替政权”的“惩罚”。比如《福贵》中,福贵和银花结婚时要请作为“老家长”(族长)的王老万来陪客,而这个地主王老万不仅雇佣福贵当了五年长工,压榨得福贵又欠债又缴了地(生活苦不堪言),而且还以“族规”试图将当“忘八”的福贵“打死”、“活埋”,从而逼得福贵远走他乡。其二,“展现了血亲宗族观念与乡土观念在农村社会中所具有的黏合力。”[8]比如《锻炼锻炼》中,“吃不饱”认为“小腿疼”比他有“硬牌子”,为什么呢?“小腿疼比她年纪大,闹荡得早,又是正主任王聚海、支书王镇海、第一队队长王盈海的本家嫂子,有理没理常常敢到社房去闹。”在“小腿疼”看来,血亲宗族观念(支书、队长均是本宗族的人,她是他们的本家嫂子)让她敢于去“说理”(虽然“理”更多属于其自私自利的现实利益考虑),因而每当她的“落后”思想、行为在以杨小四为代表的青年干部(他们不是她所在宗族成员,是“异己者”,是“外人”)面前“碰壁”时,她最先想到到王聚海面前“伸冤”,这固然有王聚海“和事佬”作风的原因,但更多地应归于其内在的伦理诉求——血亲观念在农村社会中的“黏合力”促使“吃不饱”寻找“自家人”来为自己说话。再如小说结尾处,当“小腿疼”向杨小四求情时,却遭遇了周围的一致“沉默”,“小腿疼看了看群众,群众不说话;看了看副支书和两个副主任,这三个人也不说话。群众看了看主任,主任不说话;看了看支书,支书也不说话。全场冷了一下以后,小腿疼的孩子站起来说:‘主席!我替我娘求个情!还是准她交代好不好?’……有个老汉说:‘看在孩子的面上还是让她交代吧!’……”作者选取了“小腿疼”的孩子、“老汉”作为叙述视角的特定人物,说出了叙述者的声音,伦理观照来自于血亲观念。
(二)在“民俗氛围”背景下形成的明确批判性话语指向
“乡村的诗意的平静、稳定、安全等等,是以生活的停滞、缺乏机遇、排摈陌生、拒绝异质文化、狭小空间、有限交际等等为条件的,是以一切都已知、命定、相沿成习、是以群体(宗族、村社)对于个人的支配为代价的。”[9]这里既谈到了乡土社会的传统面貌,又涉及到了乡村世界的本质属性。在这样一个“排摒陌生”、“拒绝异质文化”的乡村社会,相沿成习的民俗就有了较为“稳定”的“存在空间”,民众的思维定势、认知逻辑都要受到民俗的规范。具体到赵树理的作品中,民俗在强化特定群体成员对其的主观心理认同的过程中,往往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民俗氛围趋向:一方面因沿袭传统民俗成规而形成了相应的封建意识与落后思想;另一方面农民们在艰辛生活中形成的包裹着自保意识与自卑意识的相关民俗观念(如安命意识、民俗地域偏见等)使得他们面对乡村“霸权”时,常常“默认”了“不公道”的“权力”的“推行”。在这种“民俗氛围”背景下,赵树理作品主题呈现出明确的批判性话语指向。
西方学者曾意识到《催粮差》与《刘二和与王继圣》的共同主题是“有权者滥用职权的行为和社会对这种滥用职权的默许”,“这两个故事的主要人物、人事的表现的场合同时没有受到战争、革命和反传统观念的影响,这两个场面是报道过去人生插曲的自身完整的场面。因而这两个作品只牵涉到时间上极有限度的场面,对将来的演变毫无推测。”[10]这两篇“非主流”的创作,不具有更多艺术本体之外的目的,因而从这个层面来说,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赵树理本人对旧农村社会的透彻看法。《刘二和与王继圣》中刘二和的改变是“他通过发现社会中并无正义,而失掉了他的天真单纯的观念。”[10]刘二和作为“外来户”的孩子,被村长王光祖的儿子王继圣蔑称为“草灰羔子”,体现出了民俗的地域偏见性。在这种民俗地域偏见性的氛围背景下,作为“外来户”的老刘、老黄、老张,惹不起本地人,还受到本地人的欺压,这些都促使刘二和“天真观念”(想“独立”)的“夭折”。而《催粮差》中红沙岭的农民之所以对崔九孩的霸权行为采取默许的态度,是因为农民们在艰辛生活中形成了包裹着自保意识与自卑意识的相关民俗观念氛围。由此可见,赵树理一方面在文本中试图对抗各种各样的乡村霸权,为农民争取利益;另一方面也“忧虑”于旧乡村的“安命”、“自保”、“自卑”的民俗氛围,“忧虑”于这种民俗氛围对于农民“觉醒”、“翻身”的“桎梏性”。而这些,都构成了赵树理作品中明确的批判性话语指向。
总之,由于赵树理对于地道的乡村风俗的“稔熟”,所以他在作品中始终能把“民俗书写”置放在农村民俗文化背景下来加以阐述,并借此来承载、传播、伸张农民立场;同时,由于他兼具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所以又能将这种“民俗书写”顺畅地“整合”到他的审美理念之中,这就使得他作品中的相关的“民俗书写”呈现出独特的结构功能。
[1]陈勤建.文艺民俗学导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10):65.
[2]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3]邱雪松.赵树理与“算账”[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4.
[4]赵树理.和青年作者谈创作——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的发言[A].赵树理全集第4卷[C].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10):306.
[5]回忆历史 认识自己[A].赵树理文集第4卷[C].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352,360-361.
[6]高天星.葛操民俗审美心理意识与文化精神[J].民俗研究,1995,4.
[7]陶立璠.民俗学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149-153.
[8]黄修己.赵树理研究[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71.
[9]赵园.地之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73.
[10]中国赵树理研究会编.赵树理研究文集(下卷):外国学者论赵树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8.5.
I206.7
A
1673-2014(2010)06-0023-06
2010—11—03
林秀明(1965— ),女,福建福州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研究。
赵 坤(1982— ),男,福建福州人,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 史素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