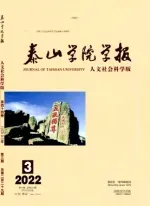文化产业视域下我国当代文学期刊生存研究
赵 强
(泰山学院汉语言文学院,山东泰安 271021)
20世纪 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文化产业也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和推崇的新兴产业。但这个概念及它所代表的内涵变化是不折不扣的舶来品,是西方大众文化思潮和中国市场经济相结合所形成的新的经济范畴。文化产业最初的翻译和文化工业是一个英语词汇“Culture Industry”,但是这个概念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最初提出的目的是为了完成法兰克福学派对此的批判,以至于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对“文化工业”的态度都是批判的和否定的。相应的对这个词的中文翻译,也是在批判的立场上加以使用的。但是随着文化经济的发展,对文化的经济属性的认识更加科学和理性,时代的语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文化工业”更多地被“文化产业”这样一个中性的词语所代替。1980年初,欧洲会议所属的文化合作委员会首次组织专门会议,召集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共同探讨“文化产业”的涵义、政治和经济背景等问题。“文化产业”作为专有名词从此正式与其大众文化母体脱离,成为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文化 -经济”类型。这一概念虽是借自西方,但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又有着具体的内涵。正如扬州大学李春媚博士所指出的:“在当今中国语境中,文化产业通常是指从事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活动的特殊性产业门类的总称。其特征是以产业作为手段、以文化作为资源来进行生产,向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从最高决策层面对文化产业的发展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支持。报告在‘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中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产业。此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1]从以上内涵的界定中,不难看出文化产业的特殊性就在于是把传统上认为纯粹精神产品的文化商品化和产业化了。这种转变不仅仅是观念上的调整,其对现实中的大量文化生产部门的实际影响更是巨大的甚至是致命的。其中承载着重要使命,以传播精神食粮,陶冶读者情操,提高审美情趣的当代文学期刊则成为文化产业化转变中的首当其冲者。
当代文学期刊作为当代文化建设中的主要阵地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刘增人先生在其《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中指出:“文学期刊是现代文学诞生的母体,又是现代文学发展的温床……文学期刊,执行着现代文学开展文化批判与社会批判乃至政治批判的功能,已经成为一种现代社会的准‘公共空间’。在文学期刊里事实上存在一块文人们月旦时政、臧否人物、控制舆论、制导话语的具有相当独立性的领域。”[2]这里虽然谈的是现代文学期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对当代文学期刊同样适用,从对公共空间的认识高度进而可以从理论上阐发文学期刊所承担的重要文化功能。著名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他的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了“文学公共领域的概念”,他首先对“公共领域”进行了规范:“所谓公共领域,首先是指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共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3]而文学公共领域则是市民社会在公共领域的形成中,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领域,他们借助报纸杂志、沙龙、咖啡馆等媒介和场所传递信息、发表意见从而相互沟通达成一种共同的有关文学领域的整体看法和共同想象。而这一切均有赖于文学期刊这种重要的载体,它是文学公共领域形成的前提,也是社会公共领域形成的重要平台和依据。正如杜春梅所总结的:“哈贝马斯的理论中界定了文学期刊的两个功能,第一,文学期刊传达着人物私人化的内心世界。哈贝马斯认为,文学公共领域是从完备的公众主体的内心领域发展起来的,文学应该表达市民社会家庭内部的私人生活。第二,文学期刊担负着文化批判的的功能。哈贝马斯认为,文化批判是传达公共舆论的重要形式。艺术评论员是公众的代言人、教育者,他们可以教育启发公众也可监督声讨作者……但随着文学公共领域的转型,特别是以大众传媒为先导的文化消费主义渗入,当代文学期刊逐渐消弱了它本身固有的两大社会功能,文学批判意识逐渐被消费意识所代替,形成了哈贝马斯所认为的‘文学消费的伪公共领域’。”[4]可见哈贝马斯不但对文学期刊的文化功能有高度的重视,同时对文学期刊随着消费文化的流行而带来的转变,表示出一定程度的担忧和否定性情感判断。这其实也正是把文学期刊作为文化产品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因为文化产业中的产品,毕竟不同于其他物质产业的如汽车、电子产业的生产流通及纯粹商品属性。文化产业还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特性在于其中所包含的非经济性的属性,如意识形态属性或者是文学的审美属性等非物质因素。彭继红在其专项研究中对此有详尽的分析:“文化产业与意识形态的内在联系源于文化产业本身具有文化和产业的双重特点。这种特点表现为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文化属性从很大程度上说就是意识形态属性,这种属性最主要地是体现在精神文化产品对于意识形态资源的依赖。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精神生产的社会本质,指出精神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和阶级的精神生产,因为支配着物质资料生产资料的阶级,必定同时支配着精神资料的生产,所以精神文化产品中就必然蕴涵着一定阶级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担负了宣传教育、审美娱乐和协调精神一致的功能,这就是文化产业的社会效应。同时文化产业也具有经济属性。文化是人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成果,人的劳动能够创造价值,特别是人的脑力劳动能创造出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作为人类劳动创造的文化由于有一定的价值性,就能够按照产业模式进行运作。从文化的功能上看,具有创造性的,适应社会需要的文化知识、科技、思想、艺术等在实践中能产生巨大经济效益。文化的的经济属性决定了文化产品的生产与经营必然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目标的。”[5]作为产品要以追求经济利润的最大化为目的,而作为文化则要以传承文明,传播特定的意识形态要求及审美意识,遗憾的是这种双重目的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却并不能有机地统一在一起。这种矛盾和困惑最典型地体现在当代文学期刊的生存现状上。有的刊物编辑直接发出他的疑问,在《面向市场还是面向文学?——关于文学期刊生存的思考》中作者表达了他的困惑,并且认为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商品化潮流汹汹涌涌,人文精神大面积陷落,粗劣庸俗的文化产品充斥市场的时候,纯文学期刊成为捍卫民族心灵、批判现实丑恶、指引民族前行的灯塔,因此应该坚持文学期刊的纯文学立场,进而要求加大政府投入。这种认识恰恰表明我们的当代文学期刊从业者,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文学期刊作为文化产业的特殊性和双重性——那就是文学需要面对和坚守,而市场同样必须面对和适应,那种只指望靠政府输血的做法,还是过去那种计划经济观念下的保守立场。因此当代文学期刊从业者的观念必须要转变,不要再把自己看作是国家工作人员,是从事高尚的文化事业的社会精英,对于商品经济和市场化表现出自命清高的漠视和鄙夷,从而对文化市场的开拓表现出有意的忽略。这显然是一种故步自封式的一厢情愿,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谁都无法抗拒的时代潮流。通用公司总裁杰克·韦尔奇的口头禅是:“文化产业是属于这个时代最有挑战力商人的最大蛋糕”,这句话道出了世界范围内对文化产业的认识。事实上在许多发达国家,文化产业都成为增长最快的产业。“据统计资料表明,美国400家最富有的公司有 72家是文化企业,美国的音像业仅次于航天工业居于出口贸易的第二位,占据了 40%的国际市场份额;英国文化产业年产值近 60亿英镑,平均发展速度是经济增长的 2倍……2003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 1274万人,实现增加值 3577亿元等”[6]。因此说,这既是一种世界潮流,也是我们国家不得不面对的一种冲击。事实上,在 2005年原先属于国有集团的出版机构——中国出版集团正式挂牌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从事业单位整体转制为企业,而在当年度,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成为国内出版领域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了真正以资产为纽带的资源整合和跨地区、跨媒体的整合。以上虽是出版集团的产业化,尚未涉及到文学期刊的生产体制的变化,但这充分表明中国文化产业化的大势所趋。当代文学期刊的生存和发展策略,必须在这样一个文化产业的视域下具有前瞻性和全局性的考虑,才有可能彻底地长远地摆脱困境,在市场整合和优胜劣汰中获得长足的发展和坚韧的生命力。
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大多举步维艰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998年是文学期刊运行最为艰难的一年,许多著名的文学期刊在这一年宣布停刊:《昆仑》、《漓江》、《小说》等杂志相继宣布停刊,被称为“天鹅之死”。而其他尚未停刊的期刊也通过改版、改名在苦苦支撑,但其生存依然步步荆棘、四处碰壁。这与当代文学期刊生存方式的改变有关。众所周知,从“十七年”一直到 80年代初期,文学期刊尤其是由各级作家协会和文联主办的纯文学刊物,依靠政府拨款维持运转。即其生存和发展经费都是由政府投入,与其发行量及市场营销没有任何关系。而其在体制上属于事业型单位,特别是一些省级文学期刊,他们的人员配置是服从于上级主管部门,期刊编辑部本身在人员配置上没有多大权力,因此期刊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也无法得到有力保障,更无法接受市场的检验。而当代文学期刊生存艰难的出现主要就出现在经费来源的改变上,进入 9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文化产业的兴盛,政府对于传统的自己供养的文学期刊不可能继续维系,因为政府的职能也在发生变化,将期刊及文化出版业推向市场就是一种必然选择。当政府的经费供给结束之后,一个文学期刊要想生存就必须靠自己的实力在市场上养活自己。但是,一方面是传统的供养体制所形成的只考虑上级及作者而从不考虑读者的思维惯性,所导致的对文学消费市场的忽略,另一方面则是从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层面看,文学的边缘化已经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70年代末 80年代初文学和文学期刊的辉煌让很多从业者的回忆充满了甜蜜和陶醉。当时,普通文学期刊发行量有四五十万份,知名刊物的读者更是数以百万计。作家能够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这样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可谓“一举成名天下闻”。不但作品广为传颂,而且也成为作家名气和地位的象征。但是现在还有多少人关注文学和文学期刊呢?当代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多媒体共生的传媒社会。广播、电视、网络等便捷的视听方式、丰富多彩的形式、不断变幻的视觉效果对纸面阅读的冲击是强大的。相当数量的人每天看电视的时间超过 4个小时,阅读时间大为减少,阅读节奏的加快必然要求阅读内容和阅读习惯有所改变,因此文化快餐式的文摘、选刊更为畅销就是这样一个事实,相反的以关注心灵为特长的文学成为时代的弃儿,相应的文学期刊的读者群就逐渐萎缩,一些知名文学期刊定数的下降,也说明了这一点。《花城》的定数好几年都没能超过 3万,《收获》每期也就 10万份左右,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遍布全国的省级文学期刊就更不用多说了。当然读者远离文学的问题,单靠文学期刊的魅力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把读者重新拉回来的,这是整个社会文化环境包括读者文化层次提升的一个整体工程,但这也与文学期刊质量的下降有一定关系,比如有读者说:“我疏远文学期刊,并不是我不喜欢文学了,也不是更多的娱乐媒体在我心中超过了文学期刊,而是因为我对当时刊登的文学作品看不上眼了,觉得那里大部分作品都是无病呻吟。”[7]真正远离文学的人,文学期刊拉不回来,但仅有的读者群如果由于文学期刊自身质量的低下而再次流失,那文学期刊还能靠什么来生存呢?
很多文学期刊现在寻求的改革之路大多数并不成功。比如通过有意识地策划和包装集中推出一批作家作品以引起市场的关注。如 1994年 4月,《钟山》与理论刊物《文艺争鸣》合作,为“新状态文学”鼓吹;《北京文学》在 1994年第 1期推出“新体验小说”;《作家》在 1998年第 8期推出了“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1999年,《时代文学》、《作家》、《青年文学》联合举办“后先锋小说联展”,并且配发了脱离文本的理论主张,目的自然是想从理论到创作都能引领时代潮流和热点,还有其他刊物的各色各样的口号与策划等等。但是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也就能热闹一阵,甚至在文学史上都只能“事如春梦了无痕”不会留下什么印记。因为它为策划而策划没有坚实的文学创作做支撑,只是提出新的术语口号来哗众取宠,跟普通的商业炒作没什么区别,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学期刊的生存现状。另外如黄发有先生在《九十年代文学期刊改制》中所提出的五种模式:“一是向‘杂’过渡。在坚持文学性或保留一定比例的纯文学版面的前提下,拓展话语空间,走泛文学路线,增加期刊的信息含量。二是办成特色鲜明的专刊或曰‘特’刊。期刊对目标读者进行细分,从漫天撒网的大众传媒转向快速精准的定位传播,专门面向某一特定的读者群,采取定点、高效的‘聚播’(focusmission)策略;三是走一刊多版的路子,拓展刊物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在保留纯文学基地的前提下,开辟新的试验田。四是打破地域限制。一些地处边缘的地方性文学期刊在坚守纯文学路线的前提下,突破封闭的办刊视野,与中心地区的文学刊物接轨,形成互动与对话的呼应。五是另觅出路,改版为远离文学的文化类、娱乐类、综合类期刊。”[8]通过进一步的分类论述,也发现了一些相对成功的文学期刊。比如《天涯》、《萌芽》、《佛山文艺》、《山花》、《南方文坛》等,当然这中间也有大量改制不成功的期刊,甚至很多夭折的如《长江》、《湖南文学》等。因此这五种方式并不是所有文学期刊都可借鉴的,而且其基本思路就是以压缩纯文学的发表空间,通过拓展迎合市场的资讯评论热点的发表空间来吸引读者,而赢得市场的生存。这样,有些期刊是可以生存了,但还能称文学期刊吗?文学和它还有什么关系吗?不管怎么样求发展和求生存,作为文学期刊的文学特点决不能改变,否则就等于对文学期刊的谋杀。
那么,如何在保持文学作品地位即坚持文学审美精神特性的前提下赢得市场的认可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要想实现文学和市场的双赢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市场的需求此前已经分析过,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充斥着大众传媒的时代,一个陷入追逐利益的急功近利的时代,你登载什么样的文学作品能吸引读者的消费阅读呢?对于一个远离文学的读者群你就是再怎么策划与经营,也不可能把他们唤回到文学期刊面前。偶尔的一小部分对文学保持热情的读者,他可以阅读但他不需要购买,他可以有很多途径获得这种文学的阅读,就如很多人爱看电影,但你让他花钱去影院他肯定不愿去,他不是花不起,而是认为花得不值。现在的时代,如果有人自费订阅文学期刊那他得首先把自己说服。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实,人们对文学期刊不急切、不必要也不惟一,这恐怕是你无论如何改变也很难调整的,这与整个社会的大的文化环境有关。山东文学期刊也是如此,当年山东的《山东文学》、《时代文学》也曾产生过巨大的轰动效应。《山东文学》自 1988年以来,曾连续两次在全省优秀期刊评选中获奖, 1993年在华东地区优秀报刊评审中荣获优秀期刊二等奖。既坚持文学追求又保有地方特色,仅1993年就有 17篇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著名期刊选载。《山东文学》还培养和推出了年轻作家,较好地完成地方期刊推出新人的任务。但是近几年生存的压力也同样摆在《山东文学》这类省级期刊的面前。《山东文学》的副主编许晨说:“文学期刊的发行量大幅萎缩是个不争的事实,发行量小想拉广告太难了,从我们社长到副主编及普通编辑都有创收任务。”[9]创收就是找钱,就是要生存,这是一种必然的困境,那么如何改变这种处境呢?那种只想在刊物内容上下功夫,调来改去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但是为了纯文学期刊的纯净,而再让政府继续输血和供养也是不现实的。难道让所有的文学期刊都去迎合市场而降低文学的水准吗?显然也是不现实的。真正的出路就应该是改变管理体制,走集团化之路,强化功能分区,实现经费互补,做大做强文学自身,让喜爱什么的看什么,对文学期刊而言就是把文学期刊从作协或文联的事业单位中分离出来,因为作协和文联本就不擅长市场的竞争,他们所属的从业人员也都是远离世俗的清高之士,让他们出去求神拜佛拉赞助跑发行,无疑是对他们人格的侮辱和折磨。因此让文学期刊的编辑们不要再为钱的事去不务正业,也就是说要有经费作为支撑,而经费来源就在于形成集团化后的经费互补,通过在文化市场上获取的利润来弥补纯文学期刊的出版发行经费。中国作协当年就曾试图走文化产业集团的道路。其实国外文学期刊的运作大多是由其依附的出版、报业集团提供经济支持。而新组成的出版集团就可以重新整合编辑、发行和出版人员,在对文学期刊从业人员的优化组合和减负的同时,用出版集团的利润补贴文学期刊的运转费用。因为不管是业内还是业外人士,大家都知道在这样一个文化语境下,文学期刊靠卖自身的文学是养不活自己的,不管你期刊上登载的文学作品多么优秀,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我国当代文学期刊的出路就应该是在突围之后,对文学的坚守。既不要追逐市场的喧嚣与享乐,也不为五斗米折下自己的腰,当文学作品风光不再,当文学回到文学之后,它就注定了自身寂寞和沉静,既要面对文化产业的时代大潮,又能在突围和坚守中找到出路,这就是文学期刊的大幸,更是文学的大幸。
[1]李春媚.文化产业·文化工业·大众文化——涵义与功能的廓清[J].湖湘论坛,2009,(1).
[2]刘增人.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4]杜春梅.对中国当代文学期刊转型的思考[J].消费导刊,2009,(5).
[5]彭继红.改革开放 30年文化产业发展与意识形态变迁的相关研究 [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9,(1).
[6]天海翔.中国文化产业[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7]祝孝成.文学期刊的反思 [J].文化观察,2004, (3).
[8]黄发有.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期刊改制[J].南方文坛,2007,(5).
[9]许晨.文学期刊举步维艰[N].齐鲁晚报,2005-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