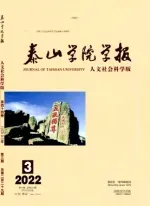白居易的生命意识及其与佛教的关系
邹 婷
(苏州职业大学教育与人文科学系,江苏苏州 215011)
白居易是一位具有强烈生命意识的诗人。体弱多病、生性敏感使他对人的生死、衰病等问题表现得异常关心。公元 789年,年仅 18岁的诗人便在《病中作》里表达了自己对老病等生命问题的重重疑虑:“久为劳生事,不学摄生道。年少已多病,此身岂堪老?”诗中对“摄生道”的向往凸显出白居易对自我生命的强烈关注。羸弱的身体不仅促发了诗人对时光推移中万物凋零的感伤,而且增强了诗人对自身变化及其生命流程的关注。草木的盛衰、花朵的凋落、时令的交替等自然现象的变化都极易引起诗人的迁逝之感:“凉风从西至,草木日夜衰。桐柳减绿阴,蕙兰销碧滋。感物思自念,我心亦入之。安得长少壮,盛衰迫天时。”(《秋怀》)“今夕未竟明夕催,秋风才往春风回。人无根蒂时不驻,朱颜白日相隳颓。”(《短歌行》)“节物行摇落,年颜坐变衰。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途中感秋》)“引手攀红樱,红樱落似霰。仰首看白日,白日走如箭。年芳与时景,顷刻犹衰变。况是血肉身,安能长强健?”(《花下对酒》二首之二)诗人对自然界变化的感叹又时时与其对自身生命的敏感联系在一起。这份特有的敏感,诗人也有所自觉,正如他在《新秋喜凉》中所总结的:“光阴与时节,先感是诗人。”对白居易来说,白发、年龄、疾病等与自身有关的状况都是其诗歌表现的重要内容。这正是其强烈生命意识的外在表现。据粗略统计,在其诗作中,仅“白发”一词就出现了大约 74次。在诗中提及到“病”字的也有 400多处,这其中也包括了一些直接以“病”字为题的诗歌。更引人注目的是白居易“好纪年岁”的特点。据洪迈的《容斋随笔五笔·卷八》中的记录,从“此生知负少年心,不展愁眉欲三十”到“寿及七十五,俸霑五十千”的 40多年间,白居易约在 78首诗中记下了自己的年纪。这种对生命的过度关注常常牵动着诗人易感的情思,凸显出诗人对生命流逝的焦虑意识。早在贞元十六(801)年左右,白居易就已经注意到自己的变化了:“忧极心劳血气衰,未年三十生白发。”(《生离别》)此后,这种因白发、落发等生理变化而作的感伤诗也就更多了。在《叹发落》、《初见白发》、《感发落》等诗中,白居易以诗人特有的敏锐观察着自己生命的流程:“多病多愁心自知,行年未老发先衰。随梳落去何须惜,不落终须变作丝。”(《叹发落》)“我有一握发,梳理何稠直。昔似玄云光,今如素丝色。”(《叹老》三首之二)“今朝复明日,不觉年齿暮。白发逐梳落,朱颜辞镜去。”(《渐老》)“白头老人照镜时,掩镜沉吟吟旧诗。二十年前一茎白,如今变作满头丝。”(《对镜吟》)从“未老发先衰”到“白发生一茎”,从“一沐知一少”到满头白发丝,诗人仔细观察着自身容貌的变化并将这些琐细之事记入诗中,但他的“观”与通常意义上的“观”有所不同。诗人的敏感及其自身的生命意识使白居易的“观”带有了某种自身对生命主体的自觉。正是这种自觉使他较早地意识到自我的执着所带来的苦恼。为了摆脱自我的痛苦,诗人开始自觉地寻求“摄生道”。虽然老庄、道教、佛教等都包含了所谓“摄生”的道理和方法,但在诗中白居易对佛教之理表现得更为重视和倾心:“已感岁倏忽,复伤物凋零。孰能不惨凄,天时牵人情。借问空门子,何法易修行?使我忘得心,不教烦恼生。”(《客路感秋寄明准上人》)“不学空门法,老病何由了。未得无生心,白头亦为夭。”(《早梳头》)“由来生老死,三病常相随。除却念无生,人间无药治。”(《白发》)诗人反复在诗中表达了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所引发的觉悟向佛的思想。其“感不甚则悔不熟,感不至则悟不深”(《和梦游春诗一百韵》)的心得表明对花开叶落等自然现象和生老病死等生命现象的观感成为白居易证悟佛理的推动性因素。
作为文人士大夫,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和强烈的生命意识使身处仕途的白居易深刻体会到佛教“苦谛”中的诸种苦恼和忧虑。特别是在痛失爱女后,诗人清醒地自觉到自己的变化:“悲来四肢缓,泣尽双眸昏。所以年四十,心如七十人。”(《自觉二首》之二)面对“灰死如我心,雪白如我发”(《送兄弟回雪夜》)的自己,白居易在《夜雨》、《自觉二首》等诗中不厌其烦地表达了自己学佛销苦的想法。这种辞繁言尽的表达正反映出中唐时代才出现的“这一新的、更具主观性的诠释的自觉意识”[1](P4)。美国学者宇文所安从西方文化的立场出发注意到了白居易主体意识的自觉及这种自觉与其诗作间的微妙联系,并以白诗中的《念金銮子二首》为例进行了解析。白居易在两首诗中表达了自己失女的伤苦及其所作的反应以及自己对反应所做出的反省式的认识。面对失女的打击,诗人虽然知道“理”所带来的安慰不能战胜自己的情感,但为了摆脱痛苦他只好选择了“聊以理自夺”。这种暂时的“以理自夺”的状态还是轻易地就被一次与女儿乳母偶然的相逢所打破。相逢是偶然的,结果却是必然的,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忘情人”。通过建构创作这两首诗,白居易对自己所洞察到的情胜理的事实作出了自己的诠释。这种诠释则“标志着人们对主体意识的自觉”,“在白居易的诗中,我们看到主体为感情所打动,对这些感情来说,仅仅识‘理’(理性原则或自然法则)是不够的”[1](P66)。表面上看,诗人似乎只是表达了无法抑制的失女的苦痛。但笔者认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诗人在第一首诗中所进行的处理则显示出主体性背后所隐藏的自觉性意识。正如宇文所安所分析的,第一首诗中白居易并没有按照“感 -应”的普遍模式来表达失女之痛,而是从叙说失女开始,然后述说了自己三年来因以“理”排遣痛苦而获得了暂时的安慰的事情。但在诗的结尾处他却直接表达了苦痛并直露地用了“因”字将此时的伤心与相逢联系起来:“唯思未有前,以理遣伤苦。忘怀日已久,三度移寒暑。今日一伤心,因逢旧乳母。”(其一)诗中对比了情与“理”,这种对比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反省式的诠释行为”[1](P65)。接着在第二首诗中,诗人试图重新以“理”自遣但这种慰藉却转瞬即逝了。诗末的“惭将理自夺,不是忘情人”。则道出了借“理”也无法抑制的痛苦之情。这种通过表达痛苦来反思痛苦并揭示出“理”对有情众生的有限作用本身就是诗人对自己无法克制的失女之痛所作出的个人化的诠释。其实,在这种“有感而发”的诠释的背后是诗人对自己的主体意识的自觉,即诗人在主观上意识到单靠“理”来销苦是有限的。
白诗中所表现出的“主体意识的自觉”以及他对情胜“理”的个性化诠释与佛学思想密切相关。“佛教是一种人文思想,是一种主体性的哲学”[2](P614)。因为“佛教往往不是在主体和客体的分离和对立中,而是在两者的统一和合一中,并以人为主导来论述外部世界的问题”[2](P614),所以佛教哲学思想又是“重视人的主体性思维的宗教哲学”[2](P602)。白居易很早就对佛教的博大精深思想和助人解脱的特点有所了解,因此他与中唐时期影响较大的几个宗派都有密切接触,尤其是禅宗。“白居易与禅宗当时最著名的四支——北宗、牛头宗以及南宗的菏泽宗、洪州宗——都已有了接触,在他们的接触过程中并通学了各宗禅法”[3](P287)。而禅宗对心性尤其重视,特别是慧能及其顿悟说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人的生命主体的地位”并进而为“发挥主观能动性开辟了广阔道路”[2](P417)。在与禅宗的密切接触中,白居易的生命主体意识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这种生命主体意识的加强又促使他更加自觉地深入探索自我的主体意识,并在诗中表现出来。正如《念金銮子》的两首诗一样,诗人无法承受女儿早夭所带来的痛苦,所以有感而发创作了诗歌。但实际上,诗人在承认以“理”遣怀失败并发觉自己“不是忘情人”的同时,也意味着他又向佛教迈进了一步。因为佛教的“妄”、“缘”等佛理虽然没能抑制他的悲伤之情,但在佛禅重视自心的熏陶下,诗人已经意识到了“理”的局限和情的难以克制,而这种认识为诗人深入体悟和实践佛理提供了基础。此后,白居易更加重视看空外物和自我,以销尽心中烦恼。在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主观意识的自觉”的共同作用下,白诗也一直在自心之“感”与超脱心之“感”的心境中游移。
一方面,强烈的生命意识使白居易常常感时、感物,关注自我;另一方面,“主体意识的自觉”又促使他观照自心,超脱物我。在《题赠定光上人》一诗中,白居易曾借着对定光上人的描绘表达了自己所理解的佛禅对生命超脱而达到的境界:“二十身出家,四十心离尘。得径入大道,乘此不退轮。一坐十五年,林下秋复春。春花与秋气,不感无情人。我来如有悟,潜以心照身。误落闻见中,忧喜伤形神。安得遗耳目,冥然反天真。”萧驰指出:“‘春花与秋气,不感无情人’是禅家漠视世事变幻、哀乐不入的生命情调之写照,‘感物’和‘感时’的题旨在此作为‘误落闻见’、‘伤形神’而被否定。”[4](P186)这首早年的诗作表明诗人一直希望自己能够通过佛理有所超脱,自然他对自我之形神、心境等也就更加重视。因此其诗作中庄禅并用的现象也更明显:“本是无有乡,亦名不用处。行禅与坐忘,同归无异路。”(《睡起晏坐》)“欲学空门平等法,先齐老少死生心。”(《岁暮道情》)“七篇真诰论仙事,一卷壇经说佛心。”(《味道》)这种庄禅合论的出现,一方面是基于白居易对禅宗特别是对将老庄的自然无为与般若智慧巧妙结合的洪州禅的体悟和实践;另一方面则是源于他对自身主体性的发掘。在游移不定的心境中白居易进行着个人化的表达:“曾陪鹤驭两三仙,亲侍龙舆四五年。天上欢华春有限,世间漂泊海无边。荣枯事过都成梦,忧喜心忘便是禅。官满更归何处去,香炉峰在宅门前。”(《寄李相公崔侍郎钱舍人》)“功名宿昔人多许,宠辱斯须自不知。……前事是身俱若此,空门不去欲何之?”(《自题》)“丹霄携手三君子,白发垂头一病翁。……终身胶漆心应在,半路云泥迹不同。唯有无生三昧观,荣枯一照两成空。”(《庐山草堂夜雨独宿寄牛二李七庾三十二员外》)“行立与坐卧,中怀澹无营。不觉流年过,亦任白发生。不为世所薄,安得遂闲情。”(《咏怀》)“有起皆因灭,无睽不暂同。从欢终作戚,转苦又成空。次第花生眼,须臾烛过风。更无寻觅处,鸟迹印空中。”(《观幻》)由这些诗句可以看出,“荣枯”、“功名”之事和“身体”、白发的变化总能引发诗人叹逝伤老、昨是今非的无限感伤,但同时诗人也在努力运用“外物尽虚空”、“无生”等佛理达到禅宗所谓的“无念”、“无住”之境界。生死、聚散、穷通等都是牵动白居易有“所感”的因素,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人生有情感,遇物牵所思。”(《庭槐》)“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与元九书》),只有佛教能够解脱这些“情”与“感”所引发的一切火宅焚烧之苦,也只有通过佛禅之法才能识得本心,从而达致“置心为止水”、“度脱生死轮”(《自觉二首》之二)的目的。
愈至晚年,已浸深于佛教的白居易在诗中所表达的叹老悲秋之情反而愈少,看空外物和自我的佛理则愈多了:“步月怜清景,眠松爱绿阴。早年诗思苦,晚岁道情深。夜学禅多坐,秋牵兴暂吟。悠然两事外,无处更留心。”(《闲咏》)“道场斋戒今初毕,酒伴欢娱久不同。不把一杯来劝我,无情亦得似春风。”(《叹春风兼赠李二十侍郎二绝》之二)“衣食支吾婚嫁毕,从今家事不相仍。夜眠身是投林鸟,朝饭心同乞食僧。清唳数声松下鹤,寒光一点竹间灯。中宵入定跏趺坐,女唤妻呼多不应。”(《在家出家》)跏趺坐禅、斋戒修行、无生无念之观已经逐渐成为诗人晚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垂暮之年真正到来之时,诗人不仅能够以平静的心态对待生命的流逝,还以超然之态回应了他人的叹老之情:“今朝览明镜,须鬓尽成丝。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亲属惜我老,相顾兴叹咨。而我独微笑……生若不足恋,老亦何足悲。生若苟可恋,老即生多时。不老即须夭,不夭即须衰。……当喜不当叹,更倾酒一卮。”(《览镜喜老》)此类为老而作的诗中已经不见了从前的自惜自叹,也没有了所谓“理”胜情的自省式的诠释,取而代之的是深谙佛理的白老所体悟到的“生死终无别”,“无生即无灭”(《赠王山人》)的旷达之心。面对春意与秋风,诗人不再被“前心”、世事所困扰,而是在平和的心境中真正享受当下的闲适与美感:“老夫纳秋候,心体殊安便。睡足一屈伸,搔首摩挲面。褰帘对池竹,幽寂如僧院。俯观游鱼群,仰数浮云片。闲忙各有趣,彼此宁相见。”(《新秋喜凉因寄兵部杨侍郎》)“花边春水水边楼,一坐经今四十秋。望月桥倾三遍换,采莲船破五回修。园林一半成乔木,邻里三分作白头。苏李冥蒙随烛灭,陈樊漂泊逐萍流。虽贫眼下无妨乐,纵病心中不与愁。自笑灵光岿然在,春来游得且须游。”(《会昌二年春题池西小楼》)“鸟栖鱼不动,月照夜江深。身外都无事,舟中只有琴。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心静即声淡,其间无古今。”(《船夜援琴》)无论贫病,在由诗人自己所创造的“‘私人空间’里,白居易拥有并诠释了这个‘私属’的空间,而这个空间也成为自由的所在”[1](P71)。这也是深悟佛理的人才能获得的心的“自由”。
对生死等问题的极度关注使白居易自觉地接触佛教等“摄生”之道,而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激发了他对自身生命“主体意识的自觉”并深化了诗人对佛理的体悟。晚年浸深于佛教的诗人充分领会了佛禅的心性之理,获得了属于自己的“闲适之境”。白居易生命意识的变化与自觉反映出他与佛教尤其是禅宗间复杂而又密切的关系。
[1][美 ]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2]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萧驰.佛法与诗境[M].北京:中华书局,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