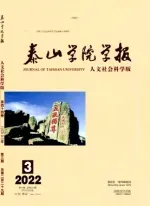大道无名 大师无界——在顾随诗词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周汝昌
(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9)
[一]
大师去已远,天际散遗芬。
爱马支公俊,雕龙慧地文。
一生三化备,八法六书均。
风雨高楼在,凭谁仰及群。
[二]
大道无名久,先型有象尊。
倦驼千里路,苦水一杯醇。
作剧红氍上,登堂绛帐门。
思量杜陵叟,芳意与谁论?
授业周汝昌拜书
己丑闰五月十八 2009.7.10
今天这次顾随诗词研讨会的召开,是我多年来期待实现的一个重要愿望,也为我们中华诗词这条大命脉的不断繁荣发展增加了一份讨论学习、交流共进的良好范式。
讲起先师顾随先生,我要说二句话八个字,就是:“大道无名,大师无界。”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民、先圣、先贤常说的那个“道”,本来没有名称,因为不知道怎样称呼它才好,无可奈何中这才挑选了一个“道”字姑且作为代表,所以,我们说大道的本质在大自然中存在,不可捉摸,无形之中却实有此道、此理存在。换言之,“道”本无名,称之为“道”,不过是个假名而已。那么,“大师无界”,又为何义呢?在我看来,顾羡季先生这样的大师是很难用一个界别或者科目来称呼,说他是什么“界”的大师,比如文学界、史学界、哲学界等等。在我看来,不应该用这样的分界法把顾先生框定了——框定也就是把他狭隘化了。因此,我们的大会主题尽管是顾先生诗词作品的研讨,而实质上应该说是他的人格、道德、文章的学习研讨。比如:我和先生请教一首诗或讨论一首词的时候,涉及的问题范围甚广,绝不限于文章、典故的事情,而我所得到的印象是先生在回应这些问题时,真是无所不通,而且,他只用上几句话就能说到“透亮”之处,有时入木三分,有时一针见血,令你恍然、憬然、心折、口服,真好像他对你提出的任何一方面的话题都深入研究过的一般。所以,我才说,像他老这样的真大师是不能用一个什么“界”字而划定而紧紧缚住的。当然,我这样说又不是完全雷同于宋人的“功夫在诗外”的那种见解、论调,相反,我是想这样来说明先生的无所不通、无所不透,却正是他为了诗而下的真实功夫——我的“翻案文章”就是先师顾羡季大师的一切功夫,都是为了“在诗内”而绝非“在其外”。
此意既明,方可专就诗词的这一方面来粗加讨论。我和先生 20年的书札来往诗词唱和,所获得的印象至少包括以下几大特点:一,先生对诗词的鉴赏、评论、要求,实际上包括了汉字、汉文的形、音、意、神、韵、情、致……;二,不论理、意、境、事、人……要传达起来,都必须是要活生生的。作品和人一样是一个宝贵、可喜、可爱、可敬、可佩的生命,而不止是一堆文字符号。“活”是作品的第一义,切忌落于一个“死”字上,“死”,就是机械化,就是八股化,就是堆砌、粉饰、忸捏、做作、搭架子、装派头,一切似乎变化多端而总不脱离一个“索然寡味”、“没有生命”。三,既然作品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它就要表现出一种活气、朝气、英气、爽气、灵气、逸气,总之,是骨肉俱全、脉络贯通、品格高尚;四,要向上,要自创,切忌人云亦云、鹦鹉学舌、陈言套语,所谓“向上一路”,似禅家的用语,禅家的精气神讲究走自己的路,不要缀人脚跟。而所谓自创者,又不是无源无本张口乱道,而是从旧的传统脉络中脱化出崭新的风格、境界、智慧、见解。所以,先生常常鼓励我们要发扬蹈厉,有向上进取的精神志向,不怕向老师提出质疑的问题。所以,禅家甚至明言“呵佛骂祖”,要“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先生对于汉字的一切特色、优点,考虑得最为深透,他是一位诗、词、曲贯通的大作家,而这种文体是最要讲求音调格律的,他对此要求得很严格,绝不认为这是琐末之事的可有可无的细节。例如:他老人家批评我的那一点拙作时,不止一次指出,说我的七言律开头主体两部分尚时见可取之处,惟独结句其音偏“哑”,不知何故?老师的意思是不愿多说,要我自家留意,或可改进……。对此所涉原由很是复杂,又因偏重于我个人的问题,不宜占据大会的太多时间,我只能把它提出来,举例说明先生对于音律的要求之严、讲究之精,实非一般作家所能望其项背。
关于音律格调问题,先生特别注重,他只要听你口中读上几句,就知道你懂不懂音义的重要关系。他说:会念的人一出口,便把字句原意全都“念”了出来,不用注解;其次,他的另一个讲授重点是教给人们汉字文学讲求文采,文采不等于字面上的华丽、美观,堆砌各式各样的形容词,那好比涂脂抹粉都是表皮上的事情。他喜欢引陆机《文赋》的名言,“石蕴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正是这个大道理。说到这儿,不妨顺带讲一讲他特别尊崇《文赋》和《文心雕龙》,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文艺理论的两座宝库。先生不仅仅是一位文论专家大师,而且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实践家,对此,我们此刻难以尽叙,有待大家今后不断研求领会才行。最末一点,先生讲授常常喜欢以禅喻诗,老师的意思是,把禅与诗放在一起来讲,并非是表明讲禅就等于讲诗,禅与诗二者并不雷同,先生只是借用禅家传授的方式来讲授诗的道理。我理解为:禅在寻求真理和讲授真理时,都特别注重把世间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比方、标记、表达、表演等都要破除尽净,因为那都是一种“障”。“障”是什么?就是它把你和真理之间设上了隔离障碍,而你真正需要理解和表现的主题实际却被它淹没和替代了。诗人想题咏一个主题,他必然首先直接了当地去接触那主题本身的一切,否则,你便是被许多的“障”隔离欺骗了。例如:你要咏月,却不去直接观察感受天空中的一轮明月的境界,而你提起笔来,首先想的就只是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再不然就是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那么,这种诗作出来之后,必然就是一堆掌故,老套陈言的堆砌,最多不过是从新组联一次罢了,这儿没有你对月亮的崭新、鲜活的感受领略,你的作品就成了“障”的堆砌物。假使古往今来我们中华的诗 (词曲)都是这样的东西,这可怕不可怕?好了,时间有限,我想说的自然是并不止此,但是我想,我们对顾先生的诗词曲的丰富遗产,进行认真的探索、学习的话,不妨从上面所列的几个要点来作指南,或许能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我个人从幼遭逢乱世,失学、废学很多次了,平生所经历的学校老师很多,回想一下,我最为佩服而崇敬的首推苦水词人羡季大师,对他的研究异常重要,这次大会只是一个开始,真诚希望由此为一个重要标志,把研讨会适当分期继续下去,我相信这对我们中华的诗歌文学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也是对先师羡季先生的最好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