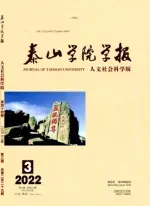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第三条道路”——从列宁论农地制度的“美国式道路”、“普鲁士式道路”谈起
李聪
(泰山学院政法系,山东泰安 271021)
邓小平曾言,“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有功的”[1],坊间则有谚语“要吃米,找万里”。从 1977年 6月万里担任安徽省第一书记起,在邓小平改革思想的指引下,由万里领衔并在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中国农村影响最大的原创经济理论和实践,是中国农地制度变迁史中最重大的制度创设。而这种农地制度变迁与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 1905年~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所提出的西方国家农地制度变迁的“普鲁士式道路”和“美国式道路”绝然不同,我们姑且称之为“第三条道路”。本文在对比阐释此两种道路基础之上,梳理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第三条道路”的艰难历程、中国特色和精神实质。
一、自由放任的“美国式道路”
列宁提出农地发展的道路的时代背景是在19世纪末 20世纪初,无论德国还是俄国关于农业的争论的中心都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发展的道路问题:是维护农民小私有制,还是承认并顺应资本主义大地产、大农业发展的趋势?因此,列宁“美国式道路”理论是取决于当时俄国革命的“情景理性”,是针对俄国当时革命的实践要求,在彰显“革命”这个主题的前提下而提出的。列宁“美国式道路”的解释学意蕴就是取其暴风骤雨的反封建的革命行为之意。
然而,难道“美国式道路”真的是通过暴力革命割断农奴制大地产这一长在社会肌体上的“赘瘤”之后按资本主义农场经济的道路自由发展的小农经济,进而形成美国资本主义现代规模化经营模式的吗?从表象上看是这样。其实“美国式道路”的真正过程是严格保护私有产权,在工业带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求中缓慢地完成的。其实质是近乎放任自流的“个人至上主义”的价值理念在起作用。
从“五月花号”航船上的清教徒到美国的立国先贤,从《独立宣言》到《美国宪法》,无不在倡导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以及对个人权力的尊重进而对保护个人福祉的私有产权的保护。这种立国理念表现在农业发展上就是美国通过立法的形式不断地满足公民对土地的私有产权的需求。
在美国宣布独立以前,以托马斯·杰斐逊为首的《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在制定土地法律时尊重广大美国民众的要求,按照“国有土地成人皆有,小块占有,免费使用”的平分土地原则,进而把美国建成以农民经济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美国宣布独立以后,响应群众的土地要求,1785年颁布的第一个土地法令规定: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国有土地一次性购买不得少于 640英亩,每英亩的拍卖底价仅为 1美元。据统计,从1796年到 1860年,美国联邦政府把占本土面积75%的土地资源投向了资本市场,共出售国有土地 2.75亿英亩。1800年将出售国有土地的最小地段降为 320英亩,1804年降为 160英亩,1820年降为 80英亩,1832年降为 40英亩,同时将每英亩土地售价由 2美元降低至 1.25美元。1841年颁布的“先买权土地法案”规定:“占地人”有权按最低价优先购买自己开垦的不超过 160英亩土地。1862年颁布的《宅地法》又规定:“凡年满 21岁的男女公民,只需交付 10美元的申请费,在所申请的 160英亩的宅地上定居和垦殖 5年后,就拥有对该土地的最终所有权。”据统计,从1860年到 1950年,美国将 2.5亿英亩国有土地授予了西部移民。由此可见,“美国式道路”的过程就是根据美国民众的要求,将国有土地逐步私有化的过程,是个人至上主义价值观在农业领域的具体体现。
同时,“美国式道路”又是按照“自由权利”的原则在工业优先发展而后带动农地规模化经营的,这使美国农业由小块土地私有化经营逐步过渡到资本主义大农场生产。首先,美国工业的发展为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提供了契机。以人口数量为例,1800年~1900年的 100年间,美国总人口由 530万人猛增至 7600万人,农业劳动力的比例由 74.4%下降为 37.5%,从 1870年到 1910年的 40年间,美国城市人口由 621.7万人增加到4199.9万人,增长了 7倍,乡村人口所占的比例由 74﹒ 4%下降为 54﹒ 3%。同时,工业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先进的生产工具,这为农业的规模化经营进一步提供了工具上的可能,“如果没有从海岸导向内地的铁路、没有连接河道的运河、没有横跨大陆的铁路和电报、没有往返于大河和沿海航道上的汽船、没有能割大草原草皮的农业机械、没有征服诸土著民族的连发枪,荒野原是不可征服的。”[2]所以,“美国南北战争以后,农业革命把农业从原始的、拓荒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产业变成了一个在科学的、资本主义的和商业化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现代产业。”[3]在这一时期,“美国人生活中的中心事件就是国家从一个巨大的、农业的、乡村的、孤立的、地方的和传统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工业的、城市的、一体的、全国的和现代的社会。这个进程开始于 19世纪 70年代延续至 1900年以后。”[4]由此可见,美国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其工业的现代化,而这个过程的完成都是在市场自由交易原则下历史地完成的。
同时需要指出,广义上的“美国式道路”其实是“渐进”的而非“革命”的,从 1870年到 1910年的 40年间,美国农业中资本主义所处的阶段比较接近于工场手工业阶段,而不是大机器工业阶段。在农业中,手工劳动还占优势,机器的使用相对来说还很不广泛。据统计,直到 1900年,美国土地面积在 20~174英亩之间的农场主占到了全国农户总数的69.7%。
综上所述,“美国式道路”是在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指导下尊重民众的创造精神而缓慢形成的,其最显著特点是自由放任、自下而上。
二、专制暴力的“普鲁士式道路”
所谓“普鲁士式道路”就是以普鲁士最为典型,通过自上而下改良的方式实现资本主义农地规模化经营。政治上的分崩离析和经济上的互相独立是德意志民族的主要特征。马克思曾经指出: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5]而对于一个身处在列强环伺的欧洲和诸侯林立的德意志民族中间的普鲁士王国来说,摆在它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借助国家的强力,倡导“国家至上主义”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19世纪初,实行所谓“施泰因—哈尔登堡改革”,极力主张把“领主制农场”改变为容克地主式的资本主义农场经营。1807年 10月,在国王的支持下以国家的名义颁布了《关于放宽土地占有的条件限制和自由使用地产以及农村居民的人身关系的敕令》和《关于废除国有土地上农民世袭人身隶属关系的法令》(简称《十月敕令》),逐步解除了农村居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放宽对农民人身自由权利的限制,同时还保留了一些农民应负的封建义务。1821年通过的《公有地分割敕令》规定:对以前领主和农民共同使用的土地,可根据当时的使用情况在领主和农民之间加以分割,进而把它变成私有土地。虽然如此,但在德国农村却还是保留了中世纪封建庄园式的统治方式。在这种制度下,一方面由于容克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不断激起农民的反抗斗争;另一方面,由于广大农民被固着在土地上并陷于赤贫,影响了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所急需的劳动力的供应和国内市场的扩大。这与普鲁士政府制定的通过王朝战争以武力统一德国的国策不相适应。普鲁士经济要发展,实力要壮大,统一要完成,必须改变农业中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1850年 3月 2日,普鲁士政府颁布了《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法》,该法无偿废除了农民应满足地主行猎权等方面的次要的封建义务,但对诸如年贡赋,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等主要的封建义务必须赎买。赎买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缴纳相当于年贡赋 20倍的赎金;一种是将相当于赎金的份地割让给地主。除少数富裕农民通过赎买成为自由的自耕农外,其余的多数农民破产沦为雇农。这样,得到大量赎金和土地的容克地主,有的用赎金做资本,开始经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有的把庄园扩大改造成资本主义的农场或牧场;而那些政治上获得了自由,经济上却破了产的大批农民被迫流向城市或进入农场,成为自由廉价的雇佣劳动者,接受资本家的剥削,这就为普鲁士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普鲁士式道路”的这种“国家主义”特色可以通过“铁血宰相”俾斯麦在 1862年9月30日的就职演说得到证明。他说“当代重大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解决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德意志所瞩望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普鲁士的武力。”但这条道路对普鲁士的广大农民来说,却是艰辛、漫长、充满血泪的,普鲁士政府于1854年通过的《关于雇农权利规范的法律》规定:“容克地主可以专横地对待农奴、甚至包括肉刑。”所以,列宁认为普鲁士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同时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成、以警察来保护的军事专制国家。在这种暴力机器的统治下,个人权力空间逐步萎缩,虽然德国曾经过短暂的魏玛民主时期,而国家主义却始终是德国的思想地图上的主体价值。
比较而言,“普鲁士式道路”与通过自下而上的个人本位变迁路径的“美国式道路”相反,德国农地制度的变迁处处彰显着“国家”的威力。因此,德国农地制度变迁的显著特点是“国家至上主义”。
三、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第三条道路”
通过对“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式道路”的分析可知,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文化传统和与欧美各国的迥异土地资源禀赋,中国农地制度变迁却有着极具特色的中国元素。而这种元素的最好体现就是不同于“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式道路”的,由万里在安徽率先进行的农地制度改革的“第三条道路”。它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其显著特点是农民对土地只有经营权,没有所有权。这种农地制度改革是在反“极左”斗争中逐渐形成,“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同时进行的,国家主导和个人利益相得益彰,市场取向和计划调节并行不悖。以下结合中国农地改革历程具体阐释万里农地改革的“第三条道路”不同于前两种道路的内涵及其特色。
1997年 10月 10日万里接受有关单位、学者、记者的联合访问,在采访中万里认为农村第一步改革过程中同“左”的错误做斗争,大体有三个回合:第一个回合是突破学大寨的框框,坚持以生产为中心;第二个回合就突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第三个回合是突破“不许包产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民充分的自主权。而这种对“左”倾思潮作斗争源于中国不同于“普鲁士式道路”和“美国式道路”的原初农地制度安排: 1950年 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和阐述了土地改革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导全国开展土地改革。这是本阶段的标志性法规,主要内容是废除封建剥削的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1953年初,全国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直接结合,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大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家靠强大的专政力量采用强制性激进式的土地制度变迁方式,有力地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转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这种暴风骤雨式的变迁迅速地将新制度安排好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降低了寻租机会,节约了制度变迁成本。这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土地变迁方式。在这个阶段上由于特殊的国际背景和时代主题,政府权力得到空前强化,农地制度改革无从谈起;1953~1978年,集体经营阶段,尤其是 1958年以后,为扩大规模经营,中央实行“小社并大社”,进而又推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这种制度一直存在到 1978年的改革开放。
从理论上讲,在万里主政安徽进而形成中国特色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中国用来指导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与土地政策调整的理论积累,来自于马克思制度变迁和所有制理论以及前苏联农村土地制度模式的实践经验,而未能充分考虑中国的历史国情、地理国情、生产力水平等因素。在这个阶段上,虽然政府付出了巨大的制度成本却没能非常有效率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论述了人有利他和同情的秉性,而在《国富论》中更旗帜鲜明地指出人的自利性会导致社会财富的巨大积累。如果以 18世纪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者的观点来看,在此阶段上中国的土地政策缺乏必要的人性基础,而这种人性基础逐步体现在极具特色的中国农地制度改革之中。
1977年 6月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在邓小平改革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万里尊重安徽凤阳小岗村十八户农户的“大包干”的首创精神,把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础上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阶段逐步过渡。
在这种农地制度激励下,到 1978年时,全国粮食作物总产量是 30477万吨。到 1984年时,全国粮食作物总产量一跃达到 40731万吨,人均占有 800斤,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使困扰中央决策层几十年的最大难题——吃饭问题,得到了解决。在国家得到巨大的物质保障的同时农民个人的生活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国家和个人获得双赢,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向好的帕累托改进状态。
从学理上分析,1978年以来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其中,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上体现了激进性质,而制度体系的其他配套制度则采取诱导性制度来逐步完善。小岗村村民的自下而上的变革,使制度实施的阻力小,实施成本低;制度安排的可逆性大,便于制度修正和调整,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制度变迁组合模式。该制度完全确立后转变为渐进式方式,通过农民内生的制度需求,来渐进地、缓慢地推动制度改革。
为了使“第三条道路”惠及更多的农民,万里在主管全国农村工作中,还主持了从 1982年起连续五个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这五个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绘制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整幅蓝图。当然,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需要法制的巩固,1993年 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并公布实施。从这时起,包产、包干到户,也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法律地位。
在农地制度的变迁过程中,万里敏锐地觉察到,包产、包干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上是使农民变成了相对独立的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将使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因此,1980年 7月,万里在总结过去 30年农业的经验教训时,讲到“我们中国没有经过商品经济阶段,缺乏现代化经济的管理经验和科学知识”;指出“在过渡阶段,商品经济得不到发展,就必然影响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万里在强调市场取向的同时也没有完全否定计划的作用,尤其是在市场的基础上强调宏观调控的重要性。
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第三条道路”的总体的特征表现为在政府权力和民间权力的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很有机地做到“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循序推进,没有陷入要么本本引领实践,要么实践缺乏制度的怪圈。即制度建设和实践推进相得益彰,相互促进,既不拔苗助长也非枝蔓丛生,在解放草根、释放动能的同时加强制度的供给和政策的适当刺激。
因此,“第三条道路”显示出的精神气质是有机的而非机械的,渐进的而非断裂的,流动的而非凝滞的,协商的而非专断的。“第三条道路”既不主张“美国式道路”的近乎放任自流做法,更不效法“普鲁士式道路”的专制统摄的做法。而是使国家、集体和个人处于利益协调过程中,通过彼此相互协商甚至是谈判,可以达到没有一方受损而有一方得利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在照顾彼此利益的前提下有机渐进地实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
“第三条道路”的实质是国家正义基础上的个人权益保护。其最终在减少社会体制变迁成本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这不同反响的农村改革之路又印证着万里不屈不挠的改革创新精神和求真务实精神,作为一名改革者,万里注定是一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界碑式人物。
[1]《万里文选》编写组.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为《万里文选》出版而作[N].人民日报,1995-10-05.
[2][美 ]LoSo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3]韩启明.建设美国:美国工业革命时期经济社会转型及启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4][美 ]CALHOM,CHARLES W.The Gilded Age [M].Sholarly Resources Inc,1996.
[5]马克思.资本论 (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