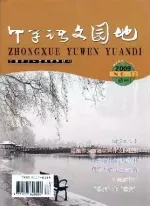文化解读张爱玲小说中的怀旧意识
王晓娟
汪曾祺有句名言:“小说是回忆。”这话用在张爱玲身上,非常贴切。细读张爱玲的小说,可以看到许多没落贵族家庭的故事。蕴蓄于她的作品内在情绪上的,则是对历史与人世沧桑的喟叹,这种喟叹中又饱含了浓浓的怀旧情绪。
一、旧家族的回忆与怀念
怀旧,是张爱玲小说中重要的文化特征。而怀旧又主要体现在小说的文化氛围及小说中的人物身上。
从背景上看,出身于封建旧式贵族家庭的张爱玲对她所描写的过去时代非常熟悉。张爱玲小说中的一切,从雕梁画栋到陈设器具,从深宅大院到衣着服饰,作者的描摹细腻独到,无不与其受旧家庭中的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有关。张爱玲的小说体现了衰败的旧中国封建文化的灰暗、糜烂和死寂。来看张爱玲的小说。此时已是民国,社会在变化、在发展、在振荡,她却为我们描绘着一个又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小的“清朝”。它们既是《金锁记》中的姜公馆、《琉璃瓦》中姚先生的家,也是《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等没落的旧式贵族家庭。留学归来的童世舫对于曾经怀念的古代中国文化,最终也是“感到难堪的落寞”,张爱玲也深有同感。旧式生活的腐朽与没落,她真切地体验过,在作品中也予以充分表现。通过对旧式家庭日常生活的细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的描写,张爱玲将过时的旧文化、旧的生活方式立体化,使之成为环绕着主人公挥之不去的阴影。旧式文化的衰落也在这种颓废的背景中得到真切的表现。
除了文化背景的不同,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也存在差异。一方面,文化背景对生活其中的人有着深远影响,张爱玲小说中旧的文化背景使生活其中的人不自觉地沾上了那种陈腐的气息。另一方面,虽然小说里的人物都十分怀旧,但在张爱玲的笔下,描绘的都是些平常人,讲的都是细琐的生活小事,没有崇高悲壮的英雄,没有波澜壮阔的场景。我们看到,张爱玲小说的主角有相当一部分是最能代表旧封建文化背景的人——旧贵族、清王朝的遗老遗少,在家族的衰败中,他们除了怀旧还是怀旧。因为对他们来说,眼前的日子缺少光明、缺少希望,而今后的日子也是一片灰暗,他们只能不自觉地从过去的生活里寻找记忆来宽慰自己,抚慰失望的心灵。他们缺少追求,拥有的只是一些可笑的陈旧信念和人性上的弱点,张爱玲以看透一切的调侃对他们精神上的病态进行了无情的嘲讽。
二、身世经历、传统文化对张爱玲怀旧意识的影响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怀旧是一种自欺欺人,是人类心理自我平衡、自我调适的一种手段。在生活逆境中,怀旧又常常是人们取之与压迫自己的现实相抗衡的手段。一旦人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没有快乐、没有幸福时,便会从过去旧有的生活中找寻曾经有过或自以为有过的幸福和快乐,并以在怀旧中的自我肯定来安慰或逃避现实生活中的生存尴尬。张爱玲小说中的遗老遗少是如此,而张爱玲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张爱玲出生于显赫的旧贵族家庭,从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从古老记忆走出来的她,自然会在进行小说创作时时时刻刻回望古老记忆。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她所出身的贵族家庭又以无法挽救的趋势没落衰败了下去,怀旧与没落的情调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从张爱玲的家庭生活来看,她也十分不幸,父母关爱缺乏,这种创伤使她过早地积累了对世界的敌意、恐惧以及对人与事的否定情绪。而张爱玲成长的社会背景,正是新旧交替、战乱频繁的二三十年代,浓重的战争阴影笼罩着全社会每个人心头,也使得她产生一种强烈的生存危机感。这些使她染上一种深沉的孤独感和被遗弃感,更导致了她对人性、对历史文明发展的悲观失望。于是,她就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刻意营造一种荒凉的文化氛围,并用一种尖锐的眼光来看待小说中的人物。
有人说:“张爱玲是晚清的中国士大夫文化走向式微与没落之后的最后一个传人,……同时又生存于贵族文化的没落时期而携上了浓重的末世情调……”确实,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张爱玲所持的是一种文化末世感的心态。作为一个宽广的概念,文化包括了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日常习俗、道德规范等等。张爱玲所在的旧家族,不可避免地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及封建意识,长时间的耳濡目染,使其深谙旧的生活方式,熟悉旧式人物的习性,这本身就说明了她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传统的道德意识又以一种文化积淀的形式渗透到她的潜意识中,并最终产生了一种无意识的复归指向——传统性。传统中国小说对张爱玲的影响也很大,尤其是《红楼梦》等古典小说。除此而外,中国古典戏曲中所独有的典型的东方忧患意识和中国传统哲学中老庄哲学的虚无弃世、悲观绝望等情绪都溶入她的思想,对她的个人气质、情感判断、审美趣味等影响深远。她的悠闲的人生态度、对于琐细日常生活的兴趣、幻想的气质以及常常袭上心头的落寞都有与此息息相关,她也因此而常常沉浸在飘渺虚无的回忆中。
三、人性的透视与历史的哀矜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张爱玲作品中显示出了极为深刻的悲剧生命意识和悲剧历史意识。她面对东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冲击,在文学领域中对历史和人性都做出了极为深刻的阐释,完成了上世纪中后叶对于人性与历史的深刻反思和探求。
张爱玲有着极为深沉的悲剧历史意识。在张爱玲的故事里,她不仅描写了遗老遗少们的实际生存空间,也描绘了他们所拥有的文化空间——集摩登与封建于一体的畸形文化,从而充分展示了特定历史时代的文化困境。旧文化的衰落反映了旧的生活方式的崩溃,而衰落的旧文化对人性的压抑和渗透使人与文化的关系变得牢固而久远。张爱玲就这样把旧文化下的人性问题,作为自己小说中最具深层意义的内核和凝聚点。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人性是自私、冷漠的,人性的力量是软弱的,人性是功利的、庸俗的,人们逃脱不了情欲的控制……她用自己的笔几乎触及到了人性深处所有的隐秘的角落,抒写着她对脆弱人性的深刻洞察,对人性恶的敏感透视,而这种洞察和透视又处处折射着那个特定时代的畸形文化形态。由于张爱玲怀旧者的心态,以及从怀旧的角度观察人生的视角,她对笔下的人物,充满了哀矜,她说:“因为是写小说的人,我想这是我的本分,把人生的来龙去脉看得很清楚,如果原先有憎恶的心,看明白之后,也只有哀矜。”对于贵族阶层和封建没落时代的眷恋与缅怀,使得张爱玲的人性批判始终笼罩着悲伤与无奈,也缺少了一定的解剖力度。
四、苍凉的目光与悲悯的情怀
细读张爱玲的小说,最让人无法忘怀的还是张爱玲在透视人生世界时所表现的冷峻苍凉和回顾历史时所流露出的悲悯情怀。
张爱玲曾阅读过西方文学中如毛姆、威尔斯、奥尼尔等作家的作品,这些西方现代作家对人类文明的幻灭感深刻影响了张爱玲,使她在精神内核上认同了现代西方非理性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认为:人生是无望的,世界是荒诞的,人是与他人、社会、世界分离的。这一哲学观念决定了她最基本的情感基调:否定与不信任一切,从根本上对历史文明的创造与延续给予否定。
从根本上否定人类文明,这一现代看法和张爱玲悲观的情感基调一起,注定了她必然的悲剧文学心态。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做好人还是做坏人,她都不给他们留任何出路。无论婚姻还是恋爱,最终都要归结到悲观绝望与苍凉孤寂上,无法逃脱。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张爱玲从自己独特的目光出发,还赋予了笔下的人物,特别是女性人物一种超越传统的气质和精神。这些女主人公往往在柔顺的传统形象下面有着现代意识,流苏、七巧甚至霓喜这样带有较多原始性的女性也意识到“男人靠不住,钱也靠不住,还是自己可靠”。她们要在艰难的环境下生存,她们在行动和思想上必须抱着世俗的实用态度,这种世俗的实用态度,从本质上是等同于西方的现代精神的。所以尽管旧小说与张爱玲的创作息息相关,但从文化精神上说,我们可以用张爱玲评价《海上花》的观点来说明她自己:“作者尽管世俗,这种地方他的观点在时代与民族之外,完全是现代的、世界性的。”
总之,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张爱玲的怀旧是对中国现当代历史的一种反思,对中国家族制度的一种批判,对人性的一种剖析。因此对张爱玲小说的怀旧意识进行文化解读,是一个理解她作品的思想、内容、特点和美学特色的关键性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