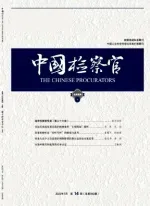当刑事法律遇上中国式改革实践
——王某案引发的思考
文◎赵开年
当刑事法律遇上中国式改革实践
——王某案引发的思考
文◎赵开年*
霍姆斯法官曾经说:“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一直是经验。”而当我们中国还不是非常健全的法律体系与中国前无古人的改革相遇的时候,我们不仅缺乏慎密的法律逻辑,甚至于更缺乏完美的经验。
首先,任何刑事犯罪本身都是对于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本身的侵害。在犯罪的本质特征上,无论是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处罚性的三特征说,还是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罪过性以及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性的四特征说,甚至于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等等两特征说,社会危害性都是刑事犯罪的本质特征。而社会危害性就是应受刑罚处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根据最基本的“谁投资、谁受益”以及“无义务,就没有权利”的原则,在兽医站收益状况不能满足日常开支的情况下,兽医站实际上已经不具备任何投资的能力,王某、邹某、陈某、张某、魏某等人出资兴办的经济实体,其资产理所应当归结于其投资人所有。而且,在该站其他职工由于考虑经营风险而未参与集资的情况下,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其他职工当然地不享有相应的经营权与利润分配权。由于经济实体本身的资产并非国有财产,所以作为贪污犯罪客观方面的公共财物在本案中并不存在。客观主义刑法理论又认为,刑法上的结果是指对法益的侵害与侵害的危险。因此,违法性的根据在于行为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的结果,即结果恶才是违法性的根据。这便是后来被称为结果无价值论的基本观点。由于王某并没有超越自己的投资范围以及投资的权力非法取得任何国有资产,所以其对于国有资产的权益没有发生任何侵害,也就不具备刑法规定的贪污犯罪的法益侵害性或者是符合定罪的结果无价值论。
当然,王某等在经济实体经营过程中以及经济实体的处置过程中,其赢利以及处置资产所得都曾经用于兽医站这一国有事业单位,从资产的处分权上似乎可以得出经济实体资产属于国有资产的结论。2000年,王某请乡党委处理资产未果;2002年,王某出卖经济实体资产所得款项18万元用于兽医站偿还债务、购买办公用品及职工家属治病等开支。从兽医站实际享有利润分配权以及乡党委的资产处置权上,我们可能认为经济实体应当是属于国有资产,但是认定资产最重要的原则是经济实体本身的投资主体。由于集资人签订协议约定分红和风险承担办法,那么兽医站与王某等之间并非借贷关系,也就是兽医站对于经济实体的资产没有任何义务,也不承担任何资产损失的风险,经济实体的资产当然地不属于国有资产。虽然盈利曾经用于兽医站开支以及王某请求实质代表公权的乡党委处理资产,其本身并不影响资产性质的认定。
其次,王某自身的行为不具备主观违法性,或者是不具备贪污犯罪这一目的犯的主要特征。作为非法占有的犯罪都是属于目的犯,而目的犯都必然具备主观的违法性。“主观的违法性在考察行为之违法性时,纳入主观视角,可以说是一种更为全面的违法性理论。构成要件是一种违法类型,因此在构成要件的内容上,也不仅仅包含客观要素,同样也存在主观要素。最初所指的主观要素就是指目的犯之目的等特定的主观要素,后来才扩及故意与过失等一般的主观要素。”[1]贪污犯罪的主观方面就是追求对于国有财物的非法占有。王某为了自己投资资产的安全,在乡党委2006年严重怠于行使自己职权的情况下(实际上,乡党委也不应当行使资产的处置权),2009年王某卖掉经济实体资产所得24万元,分得11万。既然王某当初投资进去,其收回自己投资的行为完全属于对于自己资产的一种处分行为,而且从数额上讲也没有超越自己当初的投资范围。其从客观方面没有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所以主观违法性与客观违法性结合认识分析,其行为不具备刑事违法性。
最后,王某的行为不具备职务行为的基本特征。根据《刑法》第93条,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王某2006年6月办理了退休手续,其本人也就不再具备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虽然其本身实际上对于经济实体本身存在一定的管理权限,但是由于经济实体属于其为主体投资兴办的,其管理权限属于投资者的民事权利;而且即使是经济实体本身的资产属于完全的国有资产,在并没有得到乡党委授权的情况下,其对于经济实体的管理最多属于民法意义上的无因管理,而无因管理并不是职务行为。认定王某涉嫌贪污犯罪,完全忽视王某已经退休三年以及没有任何委托授权的事实,所以是对于贪污犯罪的职务行为扩大化解释。
中国社会三十年来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的法律也在接受巨大的变化。如果其有过错的话,那就是由于国家的改革导致当初兴办经济实体的时候,对于经济实体的相关法律规定不是非常清晰,以至于在经济实体的盈利处理等方面造成一定意义上认定经济实体自身资产性质的困惑。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法律能够完全规范改革实践,那样的话实际上也就不是改革了,特别是当初鼓励兴办经济实体的改革。所以给予实践以一定的空间,或者说是刑事法律在改革地带留下一定的空白,那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也正因为如此,当刑事法律遇上中国式改革实践时,我们既要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也要坚持刑罚的谦抑性原则,促使刑罚权行使主体以及行使过程的内敛。我们不应当因为王某等没有正确地行使自己的民事法律权利,将盈利用于国有事业单位而动摇罪刑法定的根基,毕竟贪污犯罪的对象是国有资产,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
王某职务犯罪案件对于如何强化公权和私权的划分,以及动用不同的法律手段处理不同的法律关系也同样有着重要意义。按照民法专家梁慧星教授的观点:“权利首先区分为公权和私权,以与公法与私法相对应。其区分标准分歧,通说为‘法律根据说’。即以权利所根据的法律为标准,根据公法所规定者为公权,根据私法规定者为私权。民法为私法,民法上的权利属于私权。”[2]当然,对于财产权等私权的保护,在刑法有明确规定时也会上升到动用刑法的方式进行保护。具体到本案,王某本身是投资主体,其因为投资而产生的权利义务显然属于我国民法所规定的,所以其产生的权利属于私权,而私权的纠纷首先是民法这一私法调整的范畴。如乡政府与王某等因为财产关系的处理纠纷,应当由民事纠纷的当事人之间协商处理,或者是以民事诉讼的方式请求人民法院以民事审判的方式进行裁决。
也许有一天我们中国的法治也需要法律逻辑,更需要法律经验。但是在这个社会改革和转型的时代,作为刑事司法,更需要严格的法律逻辑和可靠的法律经验。离开法律逻辑和法律经验,进入法律误区就不远了。
注释:
[1]陈兴良、周光权:《刑法学的现代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98页。
[2]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70页。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法学博士[62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