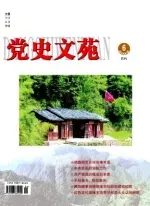金融危机导致美国话语失势或霸权终结?
赵 斌
(湖北交通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冷战结束以来,关于美国单极时代的思考从未停止。2008年美国华尔街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大海啸对美国这一极超带来了全面的冲击,亦再次让美国霸权终结的话题摆置台前。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霸权是否真正走向历史的终结,我们试图从国际关系学界主流理论的反思中找到答案。
一、美国霸权论及其影响力控制力面临的挑战
谈及国际政治中的霸权国,我们可以联想到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描绘的雅典和斯巴达,也可以认为是17-18世纪号称“日不落帝国”的不列颠英国,乃至我们更热衷于讨论的冷战时期的美苏,以及后冷战时代的单极美国霸权。在国际关系研究上,一般人们讲霸权时经常想到两个例子,那就是19世纪的大英帝国及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美国。讲到这两个霸权时,西方人爱用 “英国治下的和平”“美国治下的和平”两个词来形容。在这种霸权形势下,那个惟一的超级大国经常觉得自己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解决别国的问题,不与别国商量,起码是不管别国愿不愿意。霸权国还为体系内的其他国家提供公共物品,这种公共物品即体系的稳定秩序。由于霸权国的存在,其他行为体(包括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都能享受到 “追随”(或称搭便车)的好处。因此,“霸权稳定论”一度甚嚣尘上。“慈善的霸主”“仁慈的帝国”成了美国单极稳定论者的招牌口号。[1]
然而,在全球化时代,美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面临着全方位的挑战。不论是盟国日本,还是被视作伙伴的欧盟,乃至一度被看成对手的俄罗斯与中国,都不同程度地被当成影响美国全球霸权之“非我”,从而逐渐社会化为美国政治精英和大众的认知。库普乾认为,美国时代行将终结,缘于统合中的欧洲作为历史巨人的兴起。[2]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著名地缘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在其20世纪90年代末的力作《大棋局》中论述了关于在欧亚大陆防止一个反美同盟的出现。从其笔墨着力渲染的论断来看,美国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唯一的全球性霸权国。为了延续霸权地位,美国的目标自然是要在欧亚大棋局上防止一个反美联盟的出现。冷战后帝国式的俄罗斯和大中华的联盟将可能是美国未来的主要敌手。[3]另外,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其《大国的兴衰》中预测美国霸权即将终结,其原因在于美国的过度扩张。[4]因此,美国霸权的终结论一度成为学界、政界、商界的热议话题。
二、从话语霸权的主流理论中论证美国霸权终结与否
由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长期垄断话语霸权的正是美国学派构建的主流理论,因之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主流话语的缺失中找寻到关于霸权终结与否的有力论据。
首先,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即是我们考察的主流话语之一,它与美国霸权的兴衰可以说是同生共存的,我们可以把现实主义理论与论断当作美国霸权的一面镜子,从中清晰地看到美国霸权的历史轨迹与理论烙印。该理论兴起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20年危机中,以E.H.卡尔的《二十年危机》为代表,尔后汉斯·摩根索的权力政治论更是将现实主义推向主流理论的宝座,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则将其发展到顶峰,而新现实主义的体系结构理论更是堪称国际关系学中的牛顿定律。然而,我们回溯历史,现实主义的兴盛与美国霸权的历史轨迹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现实主义理论从来都是毫不掩饰美国霸权,并与霸权的兴衰同呼吸、共命运。二战的爆发一度宣告自由主义理想的破灭,美国政治精英们在现实主义理论对阵理想主义的反击号角中加入了反法西斯战争;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格局,也一度因乔治·凯南为主要代表的“遏制”思潮找到了强有力的精神皈依;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海湾战争、阿富汗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似乎现实主义理论的强势总是与美国对外战争的胜利所表现出来的霸权行为形影不离。然而,现实主义这一主流话语,其理论的缺失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沃尔兹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即以理论的解释力著称,却由于其静态性未能预见冷战的结束;9.11事件以后,将现实主义理论发挥到极致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在面对21世纪的崭新国际政治面貌时,其科学性和理论性亦难掩苍白,不仅较之于传统理论缺乏创新性,在阐述新时期美国霸权时也不免有些自嘲,称美国只是西半球的一个地区霸权,而非全球霸主,也无所谓真正的全球霸权。现实主义理论的各个分支流派,在与其他学派交锋的学理论争中,时而耀眼,时而黯淡失色,尤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及至九十年代末遭到来自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等全方位的挑战。同样,比照这一时期的史实,美国霸权若显强势张力,现实主义理论则更趋于垄断话语霸权,而美国霸权逐渐式微,则批评理论争鸣不断。尽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活跃了思想,有助于学术进步和理论繁荣,然而,在笔者看来,这恰恰也可以从现实主义这一主流话语的失势中,如同照镜子一般明晰地反应出美国霸权的衰落,而现实主义理论这件美国霸权强势时期必备的冷酷外衣也逐渐地被装点成怪诞的礼服。我们仍然记得70年代初欧佩克石油战带给了西方自由世界长达十年的滞胀,美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自由世界欧洲一体化对美国单极时代的新挑战,这些都不是现实主义理论单枪匹马可以应对的。如同金融危机这样的历来被现实主义视作“低级政治”的经济议题,更是难以在其中找到只言片语。
其次,由于美国霸权的维持需要新的理论为其辩护,金融危机时期,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更有复苏的理由。比如其核心理论如相互依存论,金融危机时世界经济政治的相互依存表现得淋漓尽致,相互依存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在美国霸权的自我修复行为中得以印证,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宣称,正是美国在金融危机中表现出来的脆弱性及此产生的非对称相互依存导致美国处于“危机四伏”中,让学界乃至政界急于惊呼美国霸权的终结,让人遁入美国霸权历史终结的幻境。因此,但凡我们耳边响彻的“美国时代终结”“霸权终结”的论断,无一不是受到现实主义理论哑火这一现状的误导,而事实上,终结的既不是现实主义理论,更不是美国的霸权,仅仅是脆弱性与敏感性相互依存不足以确证提供公共物品的霸权终结,因为尚无迹象出现体系内外的挑战国。同时,软权力因素的影响,由于仍然在全球化信息时代掌握着软权力的优势,美国霸权的影响力仍将持续,但由于受困于诸如金融危机等“低级政治”进程的束缚,其控制力在可见的将来会打折扣。
这一切都恰恰反应出了当前美国霸权的病态,其实不仅金融危机时期,应该确切地说是在冷战的结束、苏联这一美国最强大的“非我”遭遇历史终结后,美国却陷入了帝国的迷思。体现在对外政策上,就是较多自由主义式的理性思考,而非现实主义的持续扩张,硬权力的声势还在,却倾向于对软权力的把持。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限于金融危机时期的窘迫环境,在面对传统国际政治问题时表现得更加温和,也更加注重软权力的控制和影响。如能源战略的调整和对伊斯兰世界的政策,在金融危机时期这一大背景下,注定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对永葆美国霸权更具诱惑力和可实践性,在主张多边主义合作的当代世界,也更容易觅得国际合作,以形成维护美国霸权秩序的国际机制。
另外,建构主义之于文化、角色认知的理论似乎理应承担起使该学派更具解释力的话语使命,并突出人文关怀。文化霸权在美国霸权中的色彩较为黯淡,布热津斯基认为文化优势被美国所忽略。塞缪尔·亨廷顿也曾认为美国文化面临着危机,并表现出了文化民族主义的焦虑。[5]金融危机条件下,美国的文化认同危机更为严重,而在这一情势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却更有助于分析体系内其他大国的反应,即并没有出现一呼百应的反美联盟或霸权的挑战者。危机中角色的认知,各国既不表现得像霍布斯文化中的“敌人”,也不再单纯地再现洛克文化中“对手”角色的认知,而是部分地实现了类似康德文化的“朋友”特征,在体系中互助、共度难关,并且突出了国际关系中对于人文的关怀,如我国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债券,帮助美国人民度过危机,为走出金融危机重塑信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贡献,则体现了这种建构主义式的人文关怀。
如上所述,金融危机时期的美国霸权面临着的是其主流话语的失势,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的是霸权的病态,而非病危,更不是霸权的终结,任何一种国际关系理论都只能解释国际社会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能穷尽所有。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当中,美国主流国际关系话语霸权的失势及其理论的硬伤表现得更为明显,需要对理论进行整合,方能全面理解之。现实主义这一主流话语的失势也不能完全掩盖其学理上的持久生命力。同样,随着美国在金融危机中逐步走出困境,其霸权国的姿态将改头换面,理论上更偏向于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为其辩护,而对外政策中仍可映射出现实主义的大国政治魅影。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这时就断定美国霸权终结了,那么,很可能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又重新燃起世界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关注(比如朝核危机、伊斯兰世界与反恐),我们是否又该重新认同“美国霸权死灰复燃”呢?
三、金融危机下美国霸权时代不会终结
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霸权仍然表现出单极做大的倾向,体现在其控制力下降但影响力仍然强大,以及软权力与硬实力的优势。无政府状态的体系结构下,由于代价过于高昂,且容易引起新的安全困境,增加多极化走势下的不确定性,所以,各大国既不会也不愿轻易承担制衡重任或扮演挑战国身份。可以肯定的是,无政府体系部分呈现康德文化的属性。话语霸权失势是真,体系文化的霸权受到挑战,极超霸权终结则言过其实。
任何提出体系外挑战美国霸权,让我国做反美先锋的想法都过于激进。因为体系外的代价过于高昂,且容易反为掣肘,“中国威胁论”可能因之真的成了大国政治的悲剧。因此,审慎、隐忍的、体系内负责任参与,积极推进和谐多极新均势的理念与外交出路方为上策。中国既做负责任的大国,又不可忽视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灵活外交;捍卫民族国家主权利益,避免“反成掣肘”“盲目当头称反美先锋”的羁绊。邓小平的“冷静观察、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仍然可以指导我们在金融危机时期应对“病态”的美国霸权时保持清醒和冷静,从而努力实现我国的和平崛起,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1]参见Robert Gilpin.Warand Change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2]库普乾在其《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与21世纪的地缘政治》中揭示了冷战丧钟宣告的并非美国的最终胜利,而是其全球主导地位走向衰亡的开始。
[3]参见 Zbigniew Brzezinski.The Grand Chessboard: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1997.
[4]参见 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VintageClassics,1989.
[5]参见 Samuel Huntington.Who Are We:the Challenges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Simon?&Schuster,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