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里的城市故事
文/杨平
电影与城市,一个是想象生存,一个是真实生存,或许很多时候重要的不是意义,是感觉。
侯孝贤在对他的影片《最好的时光》作阐述时曾说:“生命中有许多吉光片羽,无从名之,难以归类,也不能构成什么重要意义,但它们就是在我心中萦绕不去。譬如桌球房里放的老歌“Smoke Getsin Your Eyes”。
城市和电影,都会老去,变成老城、老电影,但属于这座城的电影被留下来,变成了最好的时光。最好,不是因为最好所以我们眷恋不已,而是倒过来,是因为永远失落了,我们只能用怀念召唤。
现在,不妨让我们认真回想记忆中那些因为电影而让人记住的城——
第一站:巴黎,为爱存在

有人说电影是眼睛的冰激凌,那么电影中的巴黎,就是冰激凌上顶着的那颗红樱桃。
外乡人很容易把巴黎想成天堂一样的地方。《上海滩》中的许文强,临死前的遗言就是:“你知道我要去哪里……我要去……巴黎。”那还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呢。吴宇森《纵横四海》中的巴黎,更是如梦中情人一般完美。塞纳河畔,白色游船上黑衣美艳的钟楚红回眸笑问周润发,对岸的建筑是哪里?周的回答颇不解风情:“大众妈妈院呗。”谈笑间,刻骨铭心的爱情已经滋长在异乡如洗的碧空下。
其实东方人不用为自己的“巴黎情结”找借口,好莱坞有部得了很多奖的歌舞片,片名就说明一切了:《一个美国人在巴黎》,讲的就是某美国画家来到巴黎,在一个富婆和一个漂亮女孩之间周旋。他在巴黎人雪白蓬松的床上做了个甜梦,醒来后在鲜花盛开的街道上高歌,夜晚又在波光粼粼的塞纳河边起舞,而这一切最终是为了爱情。是的,在梦中,巴黎的大街小巷都因爱而存在。《红磨坊》中,年轻的诗人克里斯蒂安在巴黎的红磨坊买醉,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这里最漂亮的妓女萨汀,不管结果是圆满还是破碎。《花街神女》中,在巴黎红灯区巡逻的警员爱上了这里的一个妓女。为了成为她惟一的客人,警员不惜伪装为英国贵族,惹下一身麻烦。《日落之前》中,已婚的美国作家与一个法国女人在巴黎再续前缘,全然无视世俗的规则。
但是,只有真正的巴黎人才能看懂城市浮华背后的精神源泉。《巴黎圣母院》中古老的玫瑰形花窗和永不停息的钟声见证了人性的极美与极丑,《悲惨世界》中穿行于下水道中的冉阿让见证了从拿破仑帝国到七月王朝的腥风血雨。直到《巴黎最后一班地铁》,二战期间剧院内狭小盘曲的地道木板上居然铭刻着“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的箴言。
二战后,意大利大导演贝尔托鲁奇在巴黎撕开了工业文明的面具,在《巴黎最后的探戈》中,来自美国的中年男人和法国少女在空屋里干柴烈火般燃烧了3天,男人爱上了少女,却被她开枪打死。倒是法国影史上投资最高的文艺片《新桥恋人》让我们重新感受到爱的温暖。比诺什饰演的千金小姐被男友抛弃后露宿于新桥,与流浪汉产生爱情,但富家女后来提出分手,重新回到原来的生活,伤心的流浪汉用枪打碎无名指……最终富家女在飘雪的圣诞夜来到烟花灿烂的塞纳河畔与流浪汉重逢。影片用巴洛克风格铺陈出一个梦一样的巴黎,而我们除了感受爱情的伟大外,也窥见法国人崇尚的自由、平等与博爱。
第二站:纽约,欲望永不幻灭

纽约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摄影棚。”美国电影工业诞生于纽约,先有纽约电影的繁荣,后有今天的好莱坞。成百上千部电影在纽约拍摄,这座城市因此在胶片上呈现出千变万化的景象。
1945年以前,电影中的纽约基本上是摄影棚中搭成的街道。《死胡同》、《猫人》等影片中,纽约阴暗而恐怖,这种惊魂不定的氛围直到二战后才结束。
二战以后,纽约本土的艺术家们有机会回归城市生活本身。纽约在难以计数的影像中彼此拼接、映照、交织:《西雅图夜未眠》中帝国大厦上铺陈已久的浪漫;《纽约的秋天》中长岛的碧海长天和中央公园的绚烂黄叶;《蒂梵内早餐》中奥黛莉·赫本漫步的第五大道……
托马斯·沃尔夫曾这样描述纽约:“不论它多么可恶,想到它就像想到一个自豪热情的美人;在那里欲望永不幻灭,人人觉得自己的一生会称心如意,自己的饥渴会得到满足。”的确,纽约是一座让人既爱又恨、令人欲去还休的城市。
真正在支离破碎的影像中整合纽约的是马丁·斯科塞斯和伍迪·艾伦。
这座城市渗入了他们的骨髓,赋予他们一种完成电影梦幻之旅的冲动。
马丁·斯科塞斯的影片中,人们找不到与纽约的健康沟通方式,他把冷漠的长镜头对准了纽约社会的最底层,其正式亮相影坛的作品《穷街陋巷》就逼真地再现了纽约小意大利区的闭关自守和无法无天。在获戛纳金棕榈奖的《出租车司机》中,斯科塞斯更加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纽约对人的异化:一个出租车司机常年生活在孤独和黑暗中,为了解救一个12岁的雏妓,他拔刀相助。面对城市的冷漠,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极端暴力,斯科塞斯显然对纽约感到绝望。
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伍迪·艾伦的电影大多以纽约为背景,如《安妮·霍尔》、《曼哈顿》、《百老汇的丹尼·罗斯》、《大都会传奇》、《子弹横穿百老汇》等。艾伦心中的纽约是诗意、幽默而浪漫的。第50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安妮·霍尔》讲述了一个既神经质又缺乏安全感的纽约男人的爱情,有很大的自传成分。《汉娜姐妹》围绕纽约娱乐业大家族三姐妹的故事,讨论的仍是大都市人的爱情和欲望,展现了曼哈顿上层中产阶级的生活。1979年的《曼哈顿》堪称纽约“小资”生活集大成者:纽约的喜剧作家戴维斯在写一部小说时,他的第二任妻子也开始以他的性生活为主题撰写小说,严肃的主题融入了喜剧元素,而且采用了黑白摄影,非常有情调。
伍迪·艾伦出生于一个贫苦的纽约犹太家庭,但他并不仇视这座城市。恰恰相反,在《曼哈顿》的旁白里,伍迪·艾伦传达的是对纽约的热爱和理解——事业上的失意、生活中的孤独、城市角落里的颓唐都可以忍受而且必须被接受。
凭着对纽约情调的玩弄,伍迪·艾伦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欢心,美国的“小资”们已经习惯了那一本正经而又不造作的讲述方式。伍迪·艾伦这么说:“这是美妙的城市,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们也权且这么相信吧。
第三站:东京,与童话有关

东京有过一个爱情故事,是关于赤名莉香和永尾完治的。
东京夜晚的路灯下纪录着他们紧紧的拥抱,东京寒冷的大街上留下了他们所有的爱恨情愁,东京的机场在开始的时候曾荡漾过莉香清脆调皮的喊声“完治,完治”,当这一切都悄然远逝,东京在我心里成了一座丰富伤感的城市。
东京太过繁华,以至于每一个初来此地的年轻人都不能免去双眼的迷离和慌张。不晓得该看哪里,不晓得该把心朝什么方向张开。完治在这里犹豫和选择的时候,《四月物语》里有一个名叫阿彩的北海道女孩默默地走在了东京的街头。她来寻找一份没有回答的承诺,她其实听不见任何的声音。
可是这样大的城市有多少悲伤和错失与她相遇,幸好还有那个潇洒不羁的拓已大夫。他把受伤的她从医院偷出,在朋友的阁楼上小心翼翼的呵护她,照料她。夜晚的东京工地上有拓已没命干活的身影,白天的东京超市中有他为她买内衣时羞涩的表情。于是东京在那一刻装满了温柔和感动,尽管最后的相聚仍然是在北海道苍茫的星空下。
东京还是充满了友爱和亲情的城市,在《爱的名义下》贵子享受着友情的丰厚和终于坦然的心境。而在《同一屋檐下》生活着的是亲密关爱的五兄妹。东京还有渡边博子的幸福和怀疑,还有《三月的狮子》中疯狂相爱的兄妹,还有《东京之眼》里叛逆报复的单纯少年,还有《东京日和》的摄影师对妻子解不开放不下的爱。东京是时尚,流行,拥挤的现代都市。东京交错的城市街道,每一寸土地上都留下了或悲伤或喜悦的离合纠缠。梦想散落一地,真诚和伪装同时在城市的每一间屋子里肆意荡漾。走在东京,我真的不能保证自己的清醒和理智。东京是这样一个容易让人陷落的地方,迷失的时候连身体带灵魂一起放逐。
这就是东京永恒的魅力。
第四站:香港,相信梦想
香港电影是香港最鲜活的组织细胞,无论你是在香港的街头走走停停,还是在反复翻看香港电影,永远都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如果有一天你和香港也擦身而过的时候,你是否会记起曾经在电影里面的多少次邂逅。
20多年来,香港这个约600万人居住的城市,一直拥有着规模在全球数一数二的电影王国。香港电影的发展就像这样一只平凡的麦兜,胶片和齿轮不会停滞,光影的传奇还在续写,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努力,为梦想努力!
麦兜的梦想很多,他虽然有点弱智,但却有一个比春田花花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去日本,去加拿大,去美国更酷的梦想: 他想去马尔代夫。
马尔代夫,那里椰林树影,水清沙幼,是位于印度洋上的世外桃源……
麦太把出生纸小心翼翼放在行李箱里,母子俩高高兴兴地出门,麦太却带着麦兜登上了香港缆车总站——海洋公园。“妈妈说,要早机去,晚机返,这样才合算。”麦兜回忆道:“那是我生命里最美好的一天。”
李小龙、黄飞鸿、吴镇宇、周润发……和香港底层市民以及所有的童年一样,相信梦想,相信在充满挫折感和刻板呆滞的生活中,只要有梦想,只要努力实现,人人机会平等,人人都可以成为英雄。麦兜为了练习抢包山,在麻将桌旁的书柜上艰难地爬上爬下,麦太则为了此项运动能够成为奥运项目,儿子能够成为奥运冠军,对着英文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写了一封给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英文信:
亲爱的主席……你有孩子吗?我有一个孩子,我希望他能够抢劫包山,成为冠军……你忠实的麦太。多谢合作。
长大以后的麦兜说:“其实,我始终对抢包山没有多大的兴趣,但是我爱我的妈妈……”
海洋公园永远不是马尔代夫,抢包山也永远不会成为奥运项目。
但是香港电影在变,周星弛的无厘头小市民童话逐渐变成幻影英雄《长江七号》,曾经是好莱坞般的香港影业也在另谋出路。曾经为一只圣诞夜火鸡欣喜若狂半年的麦兜,在影片结束后说道:“其实,一只火鸡最让人心动的时刻,就是从橱窗里面看见到吃第一口为止。剩下的就是吃下去和吃完的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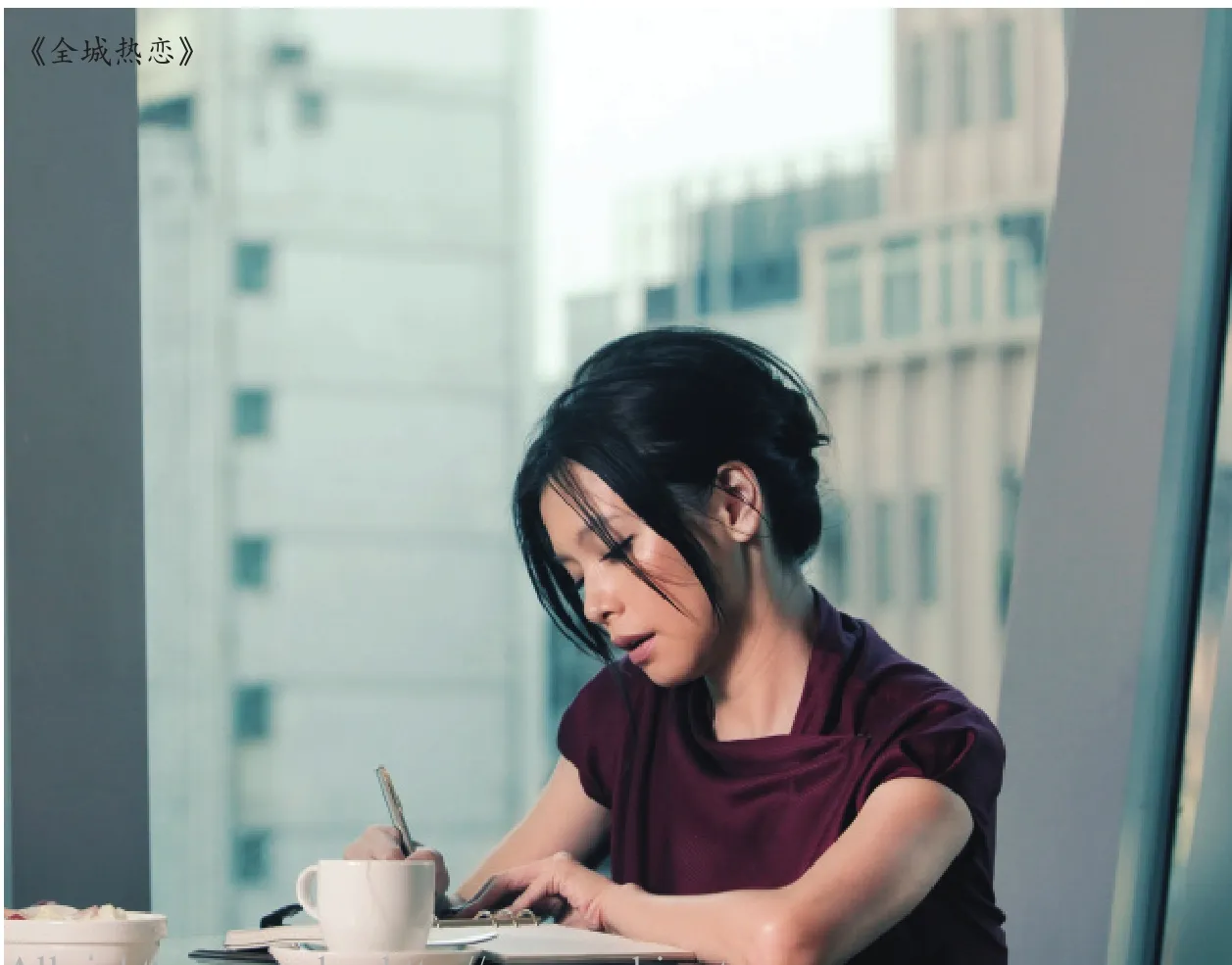

而在我单纯的眼中,香港电影和那只火鸡一样,电影成全了我们妄图看到世界另一面的梦想,并且多数观众都会从中找到自身的心灵默契,就像钻石配晚装,珍珠配婚纱,当你想怎么搭配时,那都是你的梦想!
第五站:台北,在东西间迷失
在中国的城市中,台北非常特殊。在游子心中,它是异乡;在原乡人心中,它是故土,这是历史给它的复杂角色。电影记录了台北城市化的过程,也造出关于这里的种种想像。
说起真实的台北,不能不提杨德昌,他的作品一直都用冷静的思考来透视台北人的生存状况。在著名的《牯岭街少年杀人案》中,观众可以看到上世纪60年代真实的台北社区。出身于外省公务员家庭的中学生小四喜欢流行音乐却因此卷入少年帮派斗争,在学校无辜受罚,而父亲又遭特务审查,在无助而逆反的心情下,他杀死了背叛自己的女友小明。各地口音的外省人的挫败奔忙,平民社区封闭而贫寒,“眷村”(随军逃去的家眷形成的小村落)的孩子无人照管地成长……城市中弥漫着混浊灰暗的空气。
20世纪90年代的台北已经是一个文化多元的大都市,而杨德昌却对其表达了一个“儒者的困惑”。《独立时代》中,台北十多位白领、艺术家、大款轮番出场,他们彼此之间关系复杂:同学、同事、同党,官场、情场、商场、婚姻、爱情、同居,一群外表时髦的台北人在每个中国人都懂的“人情”迷局中陷入了困惑。如何看待台北这个西风正劲的儒教社会,杨德昌给出的答案似乎是,“做自己认为对自己最有益的决定。不论是选择吃一个汉堡还是一碗牛肉面;是用针灸或是服用抗生素。”
同样是讲述台北普通人生活的《一一》为杨德昌赢得了第53届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中年男人简南俊面临着家庭和事业的转变,在小舅子的婚礼上,岳母突然中风,而简南俊则重新爱上年轻时的女友。杨德昌借台北一家人的感情起落讽喻了台湾人在传统与现代等价值观方面的对抗。
这种对抗在戴立忍的《台北朝九晚五》中表现得更直接。坚持爱情信念的现代处女Eva,相信爱就要用身体证明的Ben,白天在幼儿园当老师晚上变成夜总会女王的Vivi……他们展示的是台北年轻人的迷茫困顿。
台北的很多场所和风景都被定格在了胶片上,悠长的街巷与滴水的沟渠,建国中学和北一女中,西门汀的电影院和世贸中心的咖啡连锁店,带卡拉OK的路边摊和阳明山寂静的公路,东区百货公司的精致橱窗和西区的小阁楼。《麻将》中久居台北的英国男人对他的法国女友说,“看啊,这儿多么好!”
终点站:北京,瞬息京华

1905年,电影传到中国,照相馆老板任景丰用胶片纪录了谭鑫培表演的京剧《定军山》,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谭先生。片子随后被拿到了前门大观楼嘈杂人群中放映。一时万人空巷。在风雨飘摇的晚清,这个面容模糊的人,一路向我们走来!如今已走过百年。古老的北京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电影让北京有了一种独特的坚定从容和疲倦的沧桑。在大时代的悲欢离合中,北京永远是最活跃的一块,风头是其他任何城市抢也抢不走的。
为了实现拍电影的梦想,众多北漂们放弃了美好大众生活,到北京当导演当编剧。住胡同民宅,看深奥片子,整严重失眠。
天桥、东单小市儿,还有等在北京电影学院门口做梦的孩子们,所有的一切都在适应着新的法则,在电影《末代皇帝》中有一场戏,年轻的溥仪梦想着冲出皇宫,他已经看得见门外的行人,听得见街市的嘈杂,可就在他的脚将要迈出去的刹那,太监关上了宫门,将他阻挡在了紫禁城内。那些做着千秋大梦的帝王将相谁会想到,有一天,静寂的故宫会响起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的声音,到现在竟已成绝唱。
1982年在凌子风拍摄《骆驼祥子》的时候,为了能重现老舍先生笔下的北京,楞是花了16万在北影搭了“西四一条街”。影片的主要角色全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物,为了能达到原汁原味的效果,连影片中抬轿子和抬棺材的杠夫,拉洋片的艺人都是请的老行家。
让我等人楞是在电影中,看到了对北京的一种深情,放任不羁背后的深情。凌子风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终其一生都在用光影,刻画定格他生命冥想的东西,在刘晓庆和姜文主演的电影《春桃》里:神武门的宫墙、北海的白塔、故宫的角楼、什刹海的水,用影象和声音还原了自己儿时的北京。
在《城南旧事》的结尾,大片大片的红叶叠化镜头里,英子向童年的北京作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也是我童年的记忆,那是向往的首都。
“海面倒影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是电影对北京的描述。担当着政治和文化中心之职能的北京,在电影里无法不体现浓烈的政治色彩。
接下来,我们拥有了《阳光灿烂的日子》,在那里我们看到70年代北京小孩的生活中,马小军和一大帮同学举着花环在跳集体舞。这个时候的北京,有很多的伟人雕塑,除了大杂院和胡同,部队大院也成为另一个阶层生活的场景。
这就是宏大叙事的北京,真实的在迷茫和期盼中悄悄变化着,在北京出了太多有名的导演,而我想说的却是一个非著名导演:杨天乙。
1996年,杨天乙搬进北京清塔小区,有一天她看见一群人,觉得他们好看,就用摄像机记录了他们。一部讲述退了休的老头的纪录片。一群地道的北京老人,操着纯正的京腔,从清晨到夕阳西下,在墙根下晒着太阳,天南海北地聊天。中午回家吃饭,午后接着出来,再到五点钟左右回家吃饭、睡觉。年复一年,镜头中,老头们渐渐在减少。忽然有一天,有个老头的孙子死了,老头坐在冬日的墙角边哭泣,老泪纵横。别的老头来安慰他,不说话,只是紧紧握着他的手。平凡的老头们,在北京的胡同和街头平凡地老去,甚至是死去。
这是属于北京的电影气质,平实的让人感动,如同那辆王小帅的单车,每天准时交换。在最后,那个城市孩子伸出手去,而农村孩子背起那辆本该属于他的、被砸烂的自行车,缓慢地走在大街上。他是不是就是我们自己?在渐渐成熟之中,再次坚定而悲壮地走进这座不是自己的、但注定要融入它的城市。
无论是因为它而爱上一座城,还是原本就迷恋发生在这座城市的点点滴滴,电影和城市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身未动,心已远”,我们在电影的时光里旅行,跟着它走遍万水千山!


